但风吹来了你的舞步
◎莫泊桑的祝福
母亲给我烧完麦片粥后,拖着瘸了的右腿,走到凉席边,对我说,阿叶,喝完麦片粥后,你拿镰刀去河边砍点青草,喂牛,就到靠近我们家镰刀田的那一段。
我点了点头。夏日凉爽的风拂过我的面颊,我迅速喝完麦片粥。
我走到破旧不堪的厨房墙角拿起那把使用了三年的镰刀。镰刀,闪闪发光,应是母亲最近磨了一次。
很快汗水便从我的额头涔涔往下掉,那是一片荒芜的红高粱,没有张艺谋《红高粱》里的红高粱那么繁盛。每逢无聊时,我便扯着好伙伴衣袖,说,我们去圣地吧。每一次,好伙伴都不会拒绝。我们在红高粱里穿梭来穿梭去,时而锋利的叶片,划伤我们稚嫩的脸颊,留出鲜红的血,但,我和伙伴们还是一如既往从家迈着我们轻快的步伐,向这里进发。
这是靠近我家镰刀田大约一千米的地方。红高粱挂着穗的叶片随风摇来晃去,我看着它们,不由得弯起嘴角。
我缓慢走向红高粱,我想躲在那儿睡一会儿。这是个难得的星期天,难得母亲煮麦片粥给我喝。
当我走进红高粱地时,奇怪的事发生了,我听到一阵持续猛烈的咳嗽声。我吓坏了,猛地捂住眼睛,我感觉到毛发悚然,额头渗出了硕大的冷汗。
我透过指缝向里面望。什么也没有。也许是我的错觉。红高粱依旧欢快的摇摆着,稍头掠过一只海蓝色的大鸟。大鸟嘶鸣着飞向远方。我壮着胆子,继续向前走,我找到了一片阴凉的地块,把草用脚踩了踩,用手压了压、捋了捋。我躺下,把镰刀放在身边,用手倚着头,靠右边,深深呼吸,草香夹杂着红高粱的芳香,沁人心脾。
当我快要入睡的时候,咳嗽声再度响起,咳——咳——咳——
我立刻抄起身边的镰刀,立起身,向咳嗽的声源方向走去。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在吓唬我。
我走了很久,也未发现那个发出怪咳的人。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再度躺在我方才睡觉的地方。我想,这也许只是我的幻觉。
但是,我睡不着了,睁着眼睛,开始回味昨天和张小霞在桥上,站在一起望着夕阳的快乐场景。
当我因为回忆微微弯起嘴角,咳咳笑起来时。一个戴着草帽鼻梁上架着一幅银丝边椭圆形眼镜的老人拨开芦苇出现在我面前。我诧异站起来。
他干咳了一下。我想他就是方才吓唬我的人。
你有想过把天空中漂浮的风筝烧掉吗?老人捋了捋白花花的胡须。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问。我不想。我说。
哦。老人似乎失望的摇了摇头。
燃烧风筝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老人蹲下身来,把草帽取下来,放在身边,露出花白的头发。
是吗?
是。
你燃烧了多少只风筝?
数不清了。老人伸手捋着额头沁出的汗珠,他的出汗速度比我快,不时就有豆粒大晶莹剔透的汗珠划过他的脸颊。
我曾经一次燃烧了二十三个风筝,那二十三个风筝挂在光秃秃的洋槐树上,我爬到树上,让我的女朋友把汽油拴在麻绳上,汽油吊上来,均匀的挥洒。之后,一根火柴,便结束了这一切。说完,老人疲惫的干咳了两下。不过,眉头却舒展开来。
你为了你的女友,做这一切?我好奇的问。
你真聪明。老人很满意我的发问,伸出手抚摸我温热的脸颊,他的手,有一丝冰冷。
我女朋友已经死了二十一年。她叫丁叮。我有时会叫错她的名字。叫叮当。老人说完,抽出抚摸我下巴的手。
你的女朋友是怎么死的?
其实她没有死。
你说什么?
其实她没有死?
那是怎么一回事?我紧紧握了握镰刀的木质把柄。我觉得老人开始糊弄我。
老人似乎极不情愿回答我的反问,伸出食指捣了捣暗黄的草帽。
她在和我燃烧完那二十一只风筝之后,说,她要走。那一次的火光就像海市蜃楼。风筝的木头支架和树枝发出霹雳啪啦的响声。她说,美极了。但是,之后,她却提出,她要走,而且,要尽快。
我踹了她一脚。老人淡淡的音调,让我想起张小霞昨天晚上和我的约定——星期天傍晚,我们做一只风筝,形状要像公鸡头。
她骑着我唯一的毛驴沿着我们常常漫步的那条野花繁盛的小径徐徐向西消失在五彩斑斓的霞光中。在她走之前,我们做了一个鱼形的风筝,她把它涂上五颜六色,亲自爬上自己选的一棵光秃秃的洋槐树,她把风筝挂在树梢上,然后用我递给她的油,洒满树干。
从此你就没有见过她?我抓耳挠腮,看了看在叶片的罅隙下闪闪发光的镰刀。
老人陷入了沉思。
她其实只消失了二十一天,这二十一天,我燃烧了二十一只风筝。自己做,自己燃烧。老人停下来,摸了摸雪白的胡须。哎,对不起那二十一棵杜鹃树。我选择的是杜鹃树。
太阳已升到头顶,我眯着眼睛看了看,对老人说,对不起,我得走了,我还要割草,我家的牛,还没吃饭。
老人把破旧的草帽重新戴上,把别在麻绳造就的裤腰带上的细长烟斗取下来,从肮脏的右口袋掏出烟袋,捏了一把,塞在烟槽里,擦亮火柴,火柴照亮他嘴角倾斜的细长皱纹,那看起来,就像被人细心的划了几刀。
小伙子,我会送你一只风筝。老人毫不费力的抽了一口,淡淡的说。
是吗?我想起,我的张小霞。
那会是一只不寻常的风筝。老人隐晦的撇起嘴角。
我和老人分别了。镰刀田下边的草果郁郁葱葱。我砍了很久,大汗淋漓,心跳加速,但是,青草,还是不够。不够,我就拼命砍。累了,坐下来,看篮子里,还是不够。继续砍。直到天空投射下那种美丽的霞光。霞光把不远处高粱地晕染上一层绯红。
我很饿,而且开始疲倦。我挎着为数不多的青草,往家踽踽独行。
走到家门口,一阵扑鼻的肉香沁入鼻孔。我深深的吸着,我从未闻过肉香,自从我的爸爸去山上拉石头,下坡翻车以来。我走到厨房,看见一个系着绿色围巾的背影。她正炒着菜。香味就是从那锅里传出来的。我欣喜若狂。
妈妈。我喊。
女人转过了头,她不是我的妈妈,脸上的皱纹比我的妈妈更深更多。她和妈妈一样,慈祥的看了我一眼。我说,我妈妈呢。
女人不慌不忙的把菜盛出来,那是蒜薹炒肉,昏暗的白炽灯下,红通通的。
我没有见过你妈妈。女人平静的声音,让我觉着这里并非宁静的村寨,而是更平静的深湖边。
这是我的家?我焦急起来。我已失去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命根子,就像我是她的命根子。
她叫什么名字?
晴花。我回答。
哦。她可能是去找风筝去了。
饭桌上放着热气腾腾的白饭。我狼吞虎咽吃完蒜薹炒肉和两碗白饭。我从未,如此这般,饱过了。我摸着微微鼓起的肚皮,用手抹了抹嘴边的菜油。
你遇见过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吗?女人捋着黑亮的头发。
我妈妈呢?我没回答她。
她不会再回来了。女人加重了语气,不满的跺了跺脚。
为什么?我慌张起来。
她去寻找风筝了。
为什么啊。谁指使她去的?
不知道。
我失望的趴在饭桌上。泪水夺眶而出。
别哭。孩子。女人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抚摸我的脸颊。
你是老爷爷的女朋友?我无奈的说。没有一丝好奇。我满脑子都是偶尔做麦片粥给我喝的妈妈。她是那样漂亮。
女人点了点头。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女人紧张得胡乱抓了下脑门的头发。
你爱他?
我爱他做的风筝。
他说,你喜欢燃烧风筝。
女人迅速点了点头。
我们去找妈妈,好吗?我说。
等天黑的时候。
天黑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路。
月明星稀,今晚。
可是,我从田里回来的时候,天空可是乌云密布。
你相信我。
好吧。我疲倦的更深的趴在桌子上。微微闭上眼睛。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坐在一辆亮堂的板车上。我张开眼睛,抬头看了看天,月光很亮。
我们去找妈妈吧。我对坐在前边的人讲。
她二话没说,抽起健壮的驴。
驴在泥泞的小路上,飞奔起来。道路两旁是茂盛的璎栗。它们迅速在倒退。
我转头看我家还亮着的灯,隐隐觉得难受。
你梦见过死亡吗?孩子。女人头也不回的问。
自从我的爸爸死后,我梦见过一次。是一个追赶风筝的人。
男人还是女人?
记不清了。
我们抵达一家灯光明亮的客栈,客栈前,放着一匹正在吃草的马。
妈妈。我喊着走进客栈。
客栈里挤满了人。
你是来找那只风筝的吗?坐在门边一个端着酒杯的人问我。
我来找我妈。
你妈叫什么?
晴花。
她走了。
去哪儿了。
走之前,她说她去找她丈夫。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没记错的话,应是西边。
方才的皓月当空,成了黑云遮天。女人抽响驴背。
女人的头发突然就散乱起来,远处黑云开始亮堂,那是枝杈纵生的闪电。驴车愈来愈快,我的身体跟着左摇右晃。
你遇见过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吗?女人第二次开口问同样的问题。
你是他女朋友?我说。努力控制不让自己从驴车上掉下来。
女人放慢车速,扭过头,张大嘴巴,露出腼腆的笑容,点了点头。
可是现在他已不爱我。他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
另外一个女人是谁?
会缝制绣花鞋的女人。
绣花鞋,就能取悦他?
他从未穿过绣花鞋。女人重重抽了驴一鞭子。驴立刻飞奔起来。道路两旁疯长的麦田反射出刀光剑影的亮光。我开始想念我的红高粱地。
他为什么不穿?
她从不给他穿。
那他怎么还喜欢她?
他想让我撕心裂肺。
他为什么喜欢她?
因为她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既然一模一样,为何移情别恋?
也许等你找到你娘的时候,你会得到答案。
马车在一条荒草凄凄的河边停下来。女人在我小便的时候,消失了。我隐约听见哭泣声,循着这声音,我跨过河,走到了我的红高粱地。
红高粱地,暗暗沉沉,我疲倦了,随意弄了块地,抚平草后,躺下入睡。
梦里,我的父亲变成一个变戏法的魔术师。他立刻变出一把手枪。枪法精准,天空数只白鸽扑腾着身子,掉落地。父亲走到我面前,说,我会送你一只风筝。然后,把枪放到嘴边,吹了吹冒着枪气的枪头。
我要风筝做什么?我说。
父亲再次射杀一只鸟,不过,这一次是一只雄壮的秃鹰,秃鹰落在我的脚边,血染红我的草鞋,我的脚湿润起来。
燃烧它。父亲严肃起来。
我要我娘。我也同样严肃起来。我觉得,我从未有过如此的底气,在和他说话的时候。
你娘只是一个靠绣花鞋诓骗男人的女人。父亲把枪别在裤腰带上,向前方湿润的草地,缓慢的走。
我娘从不做绣花鞋。我反驳。
她只在黑夜操作,她的手,称得上巧夺天工,她是那种有力道的人。父亲说完,再次掏出枪,射杀了一只乌鸦,乌鸦掉在地上,他捡起来,拎在手里,鲜血染红草地。
他的脚步愈发的快,很快把我甩在后边,他像个陌生人,把我重重甩在身后,就像我是一只无关紧要的野鼠。
我从未如此慌张。月光惨淡,乌鸦遮云蔽日。他们发出惨淡的嘶鸣。
当我近乎绝望的时候,我的耳边响起响亮的咳嗽声。他的手上拿着我的镰刀,他砍下自己的大拇指,右手拿着一只怪模怪样的风筝,他把大拇指上的血均匀涂抹在风筝上。他没有戴草帽,他的头发不再是花白,一片乌黑。我要送你我的风筝。他抽起烟斗,把血流干净的大拇指仍在湍急的河水里。他开始抽烟斗。
女人也许在等你。我说。
他说,但风吹来了你的舞步。
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你说,但风吹来了你的舞步。
我说了吗?
你说了。
我抚摸着花花绿绿的风筝,笑容溢出嘴角。
醒来时,浑身疼痛。风筝在我手里,我想到张小霞浅浅的微笑,我深深撇起嘴角。
月光皎洁得就像一轮圆盘。耳边传来老人的歌声。他一边咳嗽一边唱歌。他的头发花白,不是乌黑发亮。我搓了搓手,亲吻了下风筝。谢谢你。我说。
老人摆了摆手,他的花白胡须,不知何时消失,他脸的皱纹却加深,沟壑丛生。他抽起烟斗,烟雾缭绕,模糊了他的脸,他看起来像我的父亲。
我打了个喷嚏,耳畔传来一阵可怖的鬼哭狼嚎。月光照亮老人的脚,他的脚上不是上次和我一样编制精良的草鞋,是一双隐约看得见什么花的绣花鞋。大概是杜鹃花。
老人注视着远方,顺着他的目光,惨白一片。我站起来。
能告诉我,谁给你缝制的绣花鞋吗?我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一个扎着马尾的女人。老人毫不思索的回答。那口气,就像上街买一条任人宰割的鳗鱼。
我娘也扎着马尾。晚风令我发抖,我嘴唇不由得打颤。
老人低头俯视着绣花鞋,绣花鞋的杜鹃花冉冉发亮。
也许绣花鞋可以代替燃烧的风筝。老人淡淡的音调,像窑洞中掠过的细风。
我娘也扎着马尾。我重复了一遍。
扎着马尾的不一定都是你娘。
但是,有人讲她缝得一手绣花鞋。
别人的话,不可信。
她不是别人。
谁?
女人。
什么样的女人。
把驴抽得噼里啪啦的女人。
老人不打算刨根究底,抽了口烟斗,喷出大团烟雾。
女人骑着通体纯白的高头大马停在我家茅屋粗壮的杜鹃树前。老人和我已经把他送给我的风筝挂在距离杜鹃树不远的一棵白杨树上,老人说服我把风筝挂在白杨树上。我迷迷糊糊的答应。我忘记我的张小霞,我的张小霞在霞光里,支离破碎。老人说,你只有一线希望。烧掉它。烧掉它,你或许还可以见到你母亲。
女人从高头大马跳下来,一脚踹在老人的屁股上。
女人说,这种场景,怎能少了我?
老人憨笑起来。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
于是,我擦亮火柴,白杨树顿时噼里啪啦。我眼角开始酸涩,泪水划过脸颊,沾湿我的右手大拇指。火光照亮站在一旁皱纹收缩了一些的老人和穿着发白军服的女人,女人旁若无人的哈哈大笑。老人脱下绣花鞋,扔向熊熊大火,说,但风吹来你的舞步。
白杨树和风筝以及老人的绣花鞋沦为一片黑炭后,天空下起瓢泼大雨,雨点使得黑炭冒起皑皑白烟。
这是女人和老人分手后,第一次碰面。
女人答应再给老人绣一双绣花鞋,上面绣上老人指定的烟斗。老人答应用最好的麻布,为女人做一只风筝,上面画上女人年轻时的瓜子脸。
女人和老人,分别哈哈大笑。女人扯着老人的脖子,狂热的亲吻。
大雨在我跨上女人的高头大马的时候,静止。天空飘来父亲送给母亲的蓝色丝带,落在我的手上。丝带写着,但风吹来了你的舞步。魔窟。
我拿起皮鞭,抽响马屁股,骏马奔驰起来。
风沙砾石擦过我的脸,鲜血从中火辣辣的溢出。我顾不得疼痛,响亮的抽着鞭子,马随之飞奔。抵达魔窟村的时候,穹月滔天,远处,传来猫头鹰的咕咕声。
最近的地方,是最有希望的地方。
我走到村口亮着灯的第一个土培房。虚掩的门内,昏黄烛光下,带斗篷背对我的女人随着我脚步临近愈发大声朗诵圣经。墙的四周到处挂着绣花鞋,房梁上巨型风筝缓慢摇晃,咯吱咯吱的响。绣花鞋纹丝不动。
女人停止朗诵圣经。步履蹒跚的走向我。缓缓抬起头,虚脱的笑了笑。
绣花鞋开始晃荡,巨型风筝更剧烈的摇晃。
母亲,跟我回家。女人是我的母亲。
绣花鞋要给老人。
老人燃烧了绣花鞋。我加重语气。
你这个骗子!
我不是骗子,我是你儿子。
我儿子可不骗人。
我焦急的来回踱步,舔了舔嘴角凝固的血。咸味,在胃里兴风作浪。
门砰地关上。母亲放声大笑。笑声带着哭声。
母亲随着狂笑转变成把驴背打得噼里啪啦的女人。
女人,没有撒谎。
你是谁?
你母亲。
我母亲不是这个样。
母亲撅起嘴,说,你这孽障。
我捡起桌子上唯一的苹果,狠狠啃了一口。
我把苹果扔向悬空的风筝。风筝开始燃烧,红彤彤一片。母亲,捡了几双鞋,走出门。
母亲恢复原有的模样。转过身,对我说,我怀孕了,怀着一个男孩。
我瞠目结舌,我把口袋里僵硬的麦燕饼扔到躺着的马边。马伸出舌头,吃进嘴里。
男孩说,我的风筝在哪儿?
母亲说,已经沦为灰烬。
男孩嚎啕大哭。
我说,母亲,我们回家吧。
母亲吃吃笑起来,垂头认真抚摸隆起的肚皮,她的肚皮就像熟透的瓜壳。
孩子的名字,就叫阿叶。等我燃烧完老人送给我的第一个风筝,我就生下孩子。
阿叶是我的名字。我说。
阿叶在我肚子里。
阿叶是我。我大声咆哮。
你可以生很多孩子,但,不能叫阿叶。
母亲吃吃笑声诡谲的转变成哈哈大笑。
请别再笑了。
哈哈。
请别笑了。
哈哈哈哈。
请别笑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会和阿叶找到他的父亲。
好,我们这就走。
可是,他还在我肚子里。
我摇摇头。
女人从拖拉机上跳下来,老人熄了火。女人举起腰间日本武士刀,脱下军服,使其碎尸万段。女人平和看着满月,对老人说,这是你追我时,送给我的。老人无奈点点头。老人表情,错综复杂,就像中了邪。母亲不敢看女人,女人向母亲逼近,眼睛布满杀气。
天空电闪雷鸣。雨点淅淅沥沥砸在脸颊。
女人扇了母亲一巴掌。
母亲手中的绣花鞋,跌落在地。老人走过去,慌忙捡起。
你为什么迷惑他?女人对母亲说。
他说,但风吹来了你的舞步,当我问他要不要亲吻我脸颊的那一刻。母亲平静的挪动左腿。
老人沉默不语。泪水从眼眶滑落,滴在绣花鞋上。
茅草屋熊熊火光照亮女人光洁的胳臂,她拿出武士刀,用刀尖扯住破烂不堪的军服,扔向大火。老人摘下破草帽,趴在地上,痛哭失声。老人擦着泪水,走到拖拉机旁,拿起陈旧古老录音机,播放英文歌。
英文歌,偏哀伤。我哆嗦着身子,如鲠在喉。我走到母亲身旁,拍了拍她肩膀。母亲面无表情扭头看我。
红如血的棺材,我和女人、母亲、老人,一人一支点抬起。棺材里装着死去的父亲。风沙迷蒙我们的眼。老人剧烈咳嗽。
老人的破草帽被风掀起,飘逝。老人已是白发苍苍。他赤裸的上身,骨瘦如柴。
我们沉默不语,庄严肃穆向西边进发,我们不曾感觉到肩头的重负。牛毛细雨打湿我们的衣襟。
据说,坟场的每一个墓碑前都屹立着一个风筝。我们要给父亲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于是,我们暂且放下棺材。母亲和女人在硕大的麻布上用五颜六色的颜料涂抹,老人拼凑着我用斧头砍成的木条。
当我们再次进发的时候,电闪雷鸣,风雨大作。风筝绑在棺材上方,纹丝不动。
坟场聚集了数以万计的麻雀,它们蹲在电线杆上静静注视着我们。
父亲将得以安息。我们抛开土,挖了大坑。
棺材入土的那一刻,麻雀飞离电线杆,激烈的叽叽喳喳着。它们开始攻击每一个坟前的风筝,风筝瞬间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我们的风筝被叼到电线杆上,麻雀们纷纷流出泪水,浸润着它。麻雀带走了风筝。老人开始撕心裂肺的咳嗽、女人从棕榈树间找到一件少了三颗纽扣的军服套在身上、母亲的容颜逐渐改变接近女人、我的手指和心冰凉。我们沉默的埋了父亲。父亲将得以安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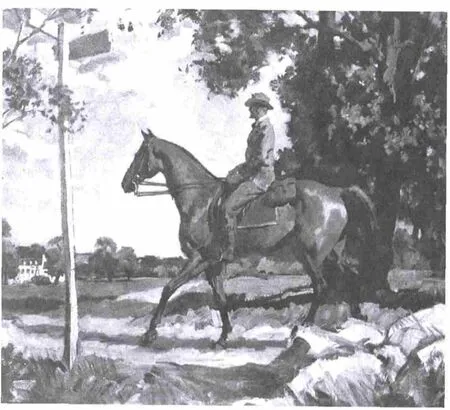
世界经典插图选登哈东·辛德布罗姆为《女士之家》杂志创作的插图。
方才所有支离破碎的风筝开始燃烧。
女人开始欢快跳舞。老人蹒跚着跟着她的步伐。母亲蹲在坟前,望着惨淡的月光,亲吻从口袋掏出灰暗色绣着唐代胖女人的绣花鞋。
麻雀们狂烈的啁啾声,依稀可辨。
我走到母亲面前,从她宽大的口袋掏出一双绣花鞋。穿上绣花鞋,老人和女人停止跳舞,默默注视着它。
我得做一个风筝。
我对自己说。
月光明亮起来。
我向红高粱地走。母亲躺在地上。女人和老人坐上马车,向南飞奔。
张小霞向我招手,她脸上挂着阴沉的笑容。她脖子上系着我送给她褪了色的红领巾。
我说,但风吹来了你的舞步。
她说,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我说。
你说了。
我没说什么。
烧风筝的祭祀或者说祈祷行为,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据说,第一个做这事的人是村里一个患癫痫的女人。她站在自家楼顶把自己做的纸风筝浇上汽油,风筝燃烧了很久,之后,她的癫痫便减轻许多,能正常和正常人交谈,只是反应稍慢。然后,烧风筝的传说,便在这一带流传。但是,并不是每一次燃烧,都可以带来福音。一些人因此丧命,譬如隔壁王妈村的王妈做了一只十米宽十米长的龙头风筝,风筝迅速烧完,而她原本希望家庭可以更和睦一点的愿望,却演变成丈夫迅速来了外遇,而她则不久于家中狭小储物室饮弹,血溅在墙上,形状像海鸥。但是,这慢慢成为习俗,很多人会在特殊的日子或想要的时候燃烧风筝。愿望圆不圆满,已不重要。
张小霞说完这些,便爬到我家猪圈后边的白杨树上,把我们涂得五颜六色的风筝挂上去。白杨树涂满汽油。
白杨树噼里啪啦起来。风筝迅速被火舌淹没。火光照亮张小霞绯红的脸。
老人曾拿着母亲缝制的精致绣花鞋,问,为什么,你放不下丈夫?
母亲扔下手中的伙计,说,他让我感觉,我是这个世界他唯一的女人。
他说过什么话?
但风吹来了你的舞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