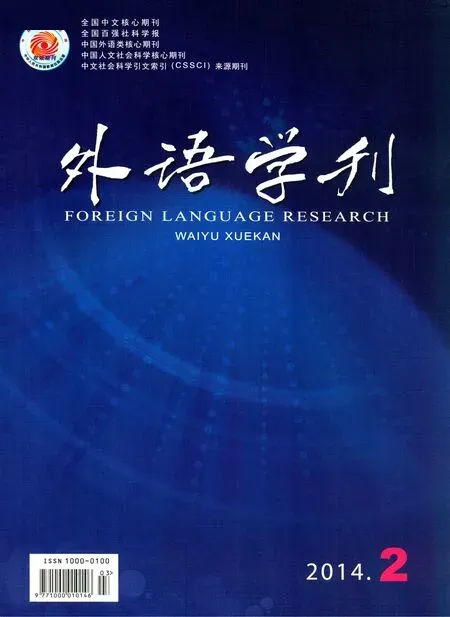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达洛维夫人》中的女性形象
赵冬梅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 200433)
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达洛维夫人》中的女性形象
赵冬梅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 200433)
女权主义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生奋斗的重要目标。作为一名有着女性自觉意识的现代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创作无疑会渗透其女权主义主张。她借助文学创作来思考女性问题和女性面临的困境;书写男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束缚;呼唤女性冲破羁绊,争取物质与精神的独立与解放。本文通过分析伍尔夫小说《达洛维夫人》中的女性形象,阐释维多利亚时代男权制社会中女性的尴尬处境以及作者期望靠女性的抚慰力量拯救人类、实现双性和谐境界的女性主义观点。
男权制社会;伍尔夫;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的抚慰力量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出生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伍尔夫的早年生活在新旧递嬗的时代度过,她经历了西方新旧妇女运动的转型期。那时,尽管有些女性已有女权主义意识,并且希望从传统父权制社会塑造的贤妻良母形象中摆脱出来,却很少有女性能把自己的身心感受真正表达出来。对此,伍尔夫深表痛惜。在她之前, 英国女作家对女性权利和命运的关注也多停留在情感层面,很少能上升到一个理性层次,同时思考女性的生存方式、社会地位也相对零散、不系统(刘爱琳 2007:135)。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的现代小说《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1925)则是“促进新女权运动实现的第一步,并在战争期间开始唤醒人们的女性意识”(Naik 1989:109) 。 伍尔夫主张女性在男权至上的社会里保留“自己的房间”。她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几个女性形象,探讨当时女性左右为难的处境,从中可以察觉到她们对自主意识的渴求,同时也体会到她们在男性世界束缚下的种种无奈。
1 女性意识的觉醒
女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夫人)、萨利·赛顿、伊丽莎白、基尔曼小姐、布鲁顿夫人等都表现出强烈的女性自主意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克拉丽莎,强烈渴求享有独处空间和求知权力。她仅有一个女儿而不是一群孩子,这说明虽然她是一个母亲,但与其他传统女性比较,她是一个自主性较强的女人。而且在成为妻子和母亲后,她总是感觉自己“依然保持童贞,这一想法就好像裹在身上的床单,无法消除”,她“就像修女退隐”一样走上自己的阁楼 (伍尔夫1989:21) 。这里,“童贞”指女性的自由和完美。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自己全身完全放松,才能揭下女性要时刻保持规矩的面纱,自由展示真正的自我,一个真实的克拉丽莎才会出现;也只有这时,才允许她拥有自己的精神空间,产生顿悟的瞬间,“就在那一刻,她看见了光明:一根火柴在一朵藏红花中燃烧,一种内在的含义几乎被表述了出来”(伍尔夫 2001:29) 。虽然那一瞬间很快就会消失,达洛维夫人却维护了自己的个性和独立。
达洛维夫人难以让人了解,在一定限度内不愿被人接近,不愿与人沟通,而且自我克制,禁止自己激情突发。就夫妻之间来说,她与达罗卫之间似乎相敬如宾,却是精神上的陌路人。“她的床会越来越窄”,这暗示她婚后性生活的冷淡。这不仅仅由于惧怕,还因为她不愿做浪漫主义爱情的牺牲品,最重要的是因为她具有强烈的反抗被控制的意识。她渴求隐私和独立,即使夫妻之间也不例外:“人都有一份尊严,一份孤独, 即使夫妻之间也有一道鸿沟,这是你必须尊重的。克拉丽莎看着他开门时想到,因为你自己不愿放弃它,也不愿违背丈夫的意志去夺取它,否则就会失去你的独立,你的自尊——毕竟这是无价之宝”(伍尔夫 2001:107) 。 她内心具有随时会被世俗破坏的独创性、敏锐易感的天性和诗意,希望通过隐私和独立保护它们,由此反映出她具有护卫自由的心灵和人的本色不受侵犯的强烈意识。
达洛维夫人本质上是位有雄心的女性:她一心想成功,而且能够自己断然做决定,寻求和保证自己的稳定生活。“她会认为人没有权利两只手放在口袋里懒懒散散地虚度时光;人应该干出点什么,成为某种人物。”( 伍尔夫 2001:68)她心中一直念念不忘她的旧情人彼得以及他们之间失败的关系。她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与彼得结婚,以后的日子会很清贫,虽然生活会更浪漫,关系会更亲密,放弃彼得是很痛苦的抉择:“虽然多年来她一直忍受着利箭钻心般的悲伤和痛苦”(伍尔夫 2001:7),然而她与彼得的过分亲密令她长时间窒息,因为彼得常常评论她一番,这些评论性言辞会限制其做事的自由。她憎恨彼得窥视她秘密的自我——作为女性的脆弱,不是社交名流,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家庭主妇。而且,彼得不能忍受她有独立性,必须彼此把每件事都摊开。彼得有很强的嫉妒心和控制欲,与他在一起克拉丽莎无法拥有“自己的房间”。相反,她选择达罗卫(理查得)作为自己的丈夫反映出她对知识和感情空间的需求:“因为在婚姻中,对于一天又一天同住在一所房子里的两个人来说,必须有一点自由, 有一点独立,这点理查德给了她,她也给予了理查德”(伍尔夫 2001:7) 。从达洛维夫人反思自己的恋情及婚姻不难看出,她本人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性,具有反对控制、追求自由的向往和诉求。
此外,她组织的宴会也可视为标榜女性创造力和肯定女性价值的场合,因为她能把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聚在一起,在那个小圈子里又重新燃起生活的生机,并使自己成为其他人生活的一部分。达洛维夫人认为,“设宴是一种奉献:联合、创造”(伍尔夫 2001:109 ), 是一种很难用语言表达,并且无论如何也不能指望男人会理解的活动。
小说另一女性人物萨利·赛顿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想破除私有制。年少时,她常做一些违反常规的事情,泼辣、任性、浪漫、爱冲动、鲁莽、不拘小节,与别人无话不谈,甚至毫不忌讳地谈论性。她的行为常常惹怒大人们,被视为不规矩。她因自己拥有女性的身体、气质而惬意,尽力维护自己作为女性的权利,并大胆为妇女争取权利,尤其是选举权。可见,萨利是世俗的反叛者,她不甘成为维多利亚时代那种羞答答、沉默寡言的典型年轻女孩。正因为她这种桀骜不逊的性格是克拉丽莎所缺乏的,她才受到克拉丽莎的崇尚,并使克拉丽莎对青年时代与她的友情十分怀念。而且,伍尔夫也称道萨利的行为:大伙儿都对她膜拜(也许除了父亲),那是由于她的热情、活力——她既绘画又写作。直到今天,村子里有些老大娘还记得她,并向克拉丽莎问候“她那穿红大氅的朋友,那个聪明透顶的姑娘”。
达洛维夫人的女儿伊丽莎白则象征充满激情的新一代女性形象。她曾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冲出与世隔绝的压抑环境,踏上一辆城市公交车,像海盗船行驶在海洋中,任凭其想象力自由驰骋,完全忘记自己淑女这一形象。伊丽莎白具有冒险精神的环城漫游反映出她对为她规定好的家中天使这一角色的强烈不满,想挣脱周围的种种控制和束缚。她只想在乡间独处,自由自在地过日子;或者单独跟父亲一起在乡下逗狗玩,这样就可以逃脱不得不去参加的宴会。她认为,女性同样可以从事男性从事的事业,想寻找富有挑战性的职业,想自由选择做医生、农民或像其父亲那样成为一名政治家,而不愿像她母亲那样做“完美的主妇”。在30年前,女性从不敢想自由选择职业,想的只是安守本分,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伍尔夫塑造的伊丽莎白这一形象体现出作者对新女性的期许以及对年轻一代女性的希望。
战争期间,由于形势所迫,一些妇女除做家务外,还可以做其他各种工作。有些妇女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之后成为职业人员。尽管在当时人数与男性比起来少得可怜,就业机会也远远达不到与男性平等,但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小说中,基尔曼小姐就是一位职业教师——伊丽莎白的历史老师。她是个充满智慧、受过教育的女性,能在社会问题、历史、妇女社会地位等方面启迪伊丽莎白。从基尔曼小姐身上可以看到下层妇女愤世嫉俗的情绪和更为高涨的争取平等权利的呼声。基尔曼小姐看不惯克拉丽莎上流社会的做派:“你这个既未经历过悲伤又未享受过快乐的人,你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 在她的身上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欲望:要征服她,要揭露她。如果她能打倒她,就会感到轻松些”(伍尔夫 2001:112)。
另一位女性布鲁顿夫人则具有很高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胸怀大志,热衷于与英国青年男女一起把加拿大开发为殖民地,渴望占据政治要位,控制家长制的世界,实现自己的抱负。
以上伍尔夫塑造的几位女性人物都渴求自由、独立、自我价值实现。这一方面表明维多利亚男权制社会中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伍尔夫要“杀死房中的天使”的女性主义主张,贤妻良母式的“房中天使”形象是当时男权中心的集中反映,借由塑造和描写“房中天使”的反叛,实际上是在呼唤人们从女性本体出发重新认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强化女性的支配意识,解构男权中心。
2 无奈的顺从
由于身处父权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女性解放只是一个神话。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尽管极力实现自我,但也意识到桎梏中的自我存在和残缺不全的女性生活最后还是难以逃脱无奈顺从的命运。
克拉丽莎对婚姻的选择、她举行的宴会反映出其对女性权利的要求和对女性自身创造力的标榜,同时也体现出她具有独立精神人格的自我与她作为上层阶级家庭主妇的社会角色、家庭角色之间的冲突;揭示出她不由自主的外在行为与内在真实体验之间的矛盾。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始至终还不能摆脱那个时代陋俗的束缚,还不能随心所欲追求本该属于女性的真正自由,只能采取折衷方式,躲入自己的斗室,以消极方式卫护纯净而孤独的性灵。
首先,克拉丽莎对婚姻的选择反映出其对女性权利的要求受到男性限制,因为其丈夫理查得是她“自己的房间”的基础, 她的稳定生活来源于丈夫。一方面,她没有职业,经济上不能独立,完全依靠丈夫;另一方面,她“自己的房间”事实上是在理查得的许可下才拥有的。此外,她是直觉敏锐、脆弱易感的人,而理查得是个非常理智的人,理智是直觉的支撑,从这方面看,理查得又是她精神上的慰籍。可悲的是,克拉丽莎在追求自己的空间、力求保持自我人格的独立完整时,内心却又冲突重重,她并不完全醉心于已得的自由。她是一位上层阶级社会的妇女,还不能完全摆脱世俗的影响,为追求稳定的生活而拒绝了彼得, 嫁给达罗卫,并获得了从世俗观念看来十分成功的婚姻生活。但她反复回顾青年时代的生活,当年的恋人彼得一直萦绕在她意识里,她的心理活动微妙地透露出她内心深处潜藏着某种不满,因为她不敢断定自己是否不再爱着彼得,她渐渐怀疑她的婚姻、丈夫和令她满意的生活。有时,她真想离开她那狭小的生活圈子,与彼得一起踏上全新的征程,想重温他们过去的浪漫时刻,可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又时时刻刻提醒着她、束缚着她。而她自己为了掩饰其不愿直面的这种感觉,不断对自己肯定当年的决定,丈夫是令她满意的。她有意让自己在世俗生活中感到陶醉,潜意识里却是为了回避内心尖锐的质问。最后,克拉丽莎不可能与习惯势力彻底决裂,相反,却有极强的虚荣心和本能迎合上流社会。宴会,这种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符合克拉丽莎作为上层阶级主妇的社会角色、家庭角色所喜欢追求生活乐趣的天性,她关心官衔职务,尽力使自己适应上层社会,与周围人和谐相处,想借以排解心中那份孤独、空虚。然而,她引以为豪和别人看来非常荣耀的宴会并没有掩饰住她内心的无聊和空虚,因为“尽管她热爱这一切,感受到它的激动和刺激,然而这些表面的东西,这些成就是很空虚的;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这些是成就,但是在她内心深处却不是”(伍尔夫 2001:155)。在宴会达到高潮,但却听到赛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时,她心有灵犀,不免一颤,引起息息相通的共鸣,因为她很清楚,赛普蒂默斯是以死来抗议压制与迫害,维护自由的心灵和独立的个性。而自己则穿着晚礼服在宴会上周旋,“她把时间都浪费掉了,午宴、晚宴、自己无休止地举办宴会、说些毫无意义的废话、说些言不由衷的话、使头脑迟钝、丧失分辨力”(伍尔夫 2001:70)。 一瞬间的负罪感淹没了她,这种感觉源于她对自身生存方式的某种愧疚与自责。
归根结蒂,通过描写克拉丽莎这一女性人物的独立精神、人格与她作为上层阶级主妇的社会角色、家庭角色之间的冲突,伍尔夫旨在反映女权主义意识的日益增强以及女性处境在维多利亚时代男权主义压制下的艰难。
由于特定时代萨利也和克拉丽莎一样对女性权利的要求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她的精神反抗被男权至上的力量扼杀,在这种力量的长期压制下消磨殆尽。比如,男权制社会的代表休·惠布雷德在吸烟室吻她,说是作为对她异常行为的惩罚,因为她是个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的女人。然而, 她不久便进入当时典型的家庭妇女行列,与一家纺织厂的老板结婚,成为罗塞特太太、5个孩子的母亲,变成一个自我满足和习俗尊奉者,再也没有年少时的激情:“她的声音中已没有了昔日令人陶醉的圆润甜美,眼睛也不像当年她吸雪茄烟、身上一丝不挂地跑过过道去取自己的海绵包时那样闪闪发亮了”(伍尔夫 2001:161)。
不可否认,一回到家里,伊丽莎白就恢复了父母的乖巧女儿这一角色——端庄娴静、妩媚可爱:“人们开始把她比作白杨树、比作黎明、风信子花、幼鹿、流水和园中的百合花,这使她的生活成了一个负担,因为她只愿不受干扰地在乡间做她想做的一切”(伍尔夫 2001:121)。可见,伊丽莎白不得不在男性和女性世界中选择——或者进入男性力量角逐的圈子而被认为不规矩,傲慢无理;或者屈服于世俗,做一个娇柔女性而成为男性爱慕的对象。她内心那种开拓冒险的精神总与古老的世俗观念冲撞,总也不能彻底挣脱那牢固的枷锁。
基尔曼小姐也是男权制社会的牺牲品,她男性装扮,行为粗鲁,故意压制自己的女性气质。她社会地位低下,与克拉丽莎这位上层阶级妇女相比更是自惭形秽,因此痛恨克拉丽莎的优雅,极力敌视这位上流社会妇女的代表。为了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生存,她故意像男人那样富有攻击性,想控制伊丽莎白,占据其灵魂,但这种目标终因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而告终。
布鲁顿夫人尽管具有很高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胸怀大志,但由于身为女性,只能通过男人争取职位,最后不得不委身于次要位置。如果她身为男性,早就可以率领部队,用其铮铮铁骨击退反叛力量,成为大英帝国的真正爱国者。可现在,她只能“手握在了一根想象中的,如她的祖先可能握过的那种官仗上,她昏昏欲睡地握着这官仗,仿佛统帅着部队向加拿大挺近”(伍尔夫 2001:100)。
3 女性的抚慰力量
当时,女性既渴望自由平等又摆脱不开传统体制和习俗的束缚,基于这种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伍尔夫试图结合女性自身的特质提出独具女性主义特色的救世良方:用女性的抚慰力量拯救世界。在她看来,首先妇女具有合作、平和、温婉、抚慰的柔性特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舒缓男人的攻击欲、控制欲、野心、狂妄和凶残,解构两性的二元对立,建构两性的和谐图景,这有利于有序社会的建立;同时女性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避免人类自我毁灭的命运。这一救世良方在《达洛维夫人》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因为恐惧、孤独、虚无始终折磨着饱受战争摧残的人们。伍尔夫认为,减轻或消除战后人们遭受的精神痛苦,需要博爱和精神抚慰。克拉丽莎举行晚宴的目的也是为了给战后的人们提供一个心灵沟通、融合的场所和渠道,使人们能在晚会中打开心门,彼此沟通交流,消除因战争和男权专制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从某种意义上讲,达洛维夫人组织的晚会非常重要,同时她自身也产生一种“去联合,去创造”的欲望,她要把分散在各处的人们聚集起来,因为“这就是一种贡献”(胡新梅 2005)。这是克拉丽莎智慧的选择:让一个个孤独的灵魂相互交流、致意。因此,克拉丽莎晚会上向宾客们提议,庆祝“人类交际的愉悦和观赏美景的欢乐”。
伍尔夫在小说中特意安排一位在地铁站对面唱着古老情歌的老妇人,这位原始女性显然是女性创造力、大地繁衍和力量的象征。从其声音可以感受到尽管在男权制社会压制下,女性不可磨灭的伟大力量依然存在。其歌声淹没男性势力,回响在男权至上的城市里——整个伦敦的上空:“当这首古老的歌在摄政公园地铁站的对面流淌出来时,大地鲜花盛开、郁郁葱葱;虽然歌声来自这样野荒的出口,只不过是地上的一个洞,而且还泥泞非常,缠结着树枝和杂乱的草茎,然而这首古老的汩汩流淌的歌,渗透过岁月交缠的根茎,渗透过枯骨和宝藏,形成涓涓细流,淌过人行道,沿着马里勒波恩街流向尤斯顿街,在肥沃大地上留下一片湿痕”(伍尔夫 2001:73)。刻画这位老妇人是伍尔夫对女性高唱的一曲赞歌,给长期受压制的女性以心灵扶慰,给她们自信。
伍尔夫认为,相比男性,女性更具有一种凝聚和沟通的力量,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更具有平和、温婉、抚慰的特质,同时渴望和平,抵制暴力。正是具有这些特质,才能消解男权制社会的失衡局面,使人类真正走上解放之路。伍尔夫对女性力量的赞扬为解构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达到双性和谐境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伍尔夫在小说《达洛维夫人》中阐明了维多利亚男权制社会中女性既渴望自由平等又摆脱不开传统体制习俗的束缚时左右为难的处境,表明伍尔夫希望女性消除茫然神色,摆脱所有羁绊,大胆争取自己权利并期望靠女性抚慰力量拯救人类的女性主义观点。
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房间[M].北京:三联书店, 1989.
胡新梅. 战争:创伤与女人——从女性视角析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6).
刘爱琳. 论伍尔夫女性主义的历史意义[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7(4).
弗吉尼亚·伍尔夫. 达洛维夫人[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Mepham, J.VirginiaWoolf,ALiteraryLife[M]. Kingst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1.
Naik, S. The Woman’s Question: A Study of Virginia Woolf’sMrs.Dalloway[A]. In C. Gilbert(ed.).TrendsintheTwentiethCenturyLiteraryCriticism[C]. New York: Schoken, 1989.
【责任编辑王松鹤】
OntheFemaleCharactersinVirginiaWoolf’sNovelMrs.Dalloway— A Feminism Approach
Zhao Dong-me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Feminism is Virginia Woolf’s ever lasting target. As a modern writer concerned about women’s status, her feminist propositions are reflected through her literary creations. She thinks about women issues, their unfair treatment in society so as to call for women’s liberation and independe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emale figures in Virginia Woolf’s novelMrs.Dallowa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laborate on the women’s peculiar dilemmas in the traditional Victorian society and the author’s point of view that women’s soothing power can save mankind and realize bisexual harmony.
patriarchy; Virginia Woolf; awakening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women’s soothing power
I106
A
1000-0100(2014)02-0130-4
2013-12-23
——解析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的艺术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