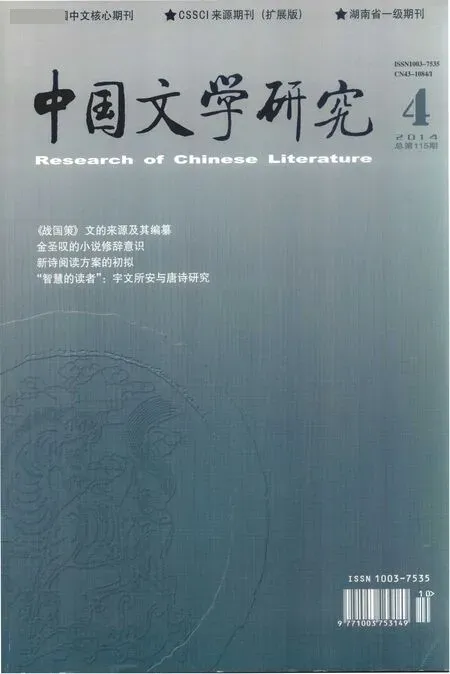金圣叹的小说修辞意识
毛宣国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一
中国小说发展到明清之际,其文体形态与叙述方式已日趋成熟,一些小说批评家,开始从理论上重视小说的文体与修辞特征。比如,瞿佑将“其事皆可喜可悲,可惊可怪”(《剪灯新话序》)作为传奇写作的标准;凌云翰用“述奇记异,其事之有无不必论,而其制作之体,则亦工矣”(《剪灯新话序》)来概括传奇作品的艺术特色;袁于令提出正史以纪事贵在传信和真实,小说是传奇贵在幻妙(《隋史遗文序》);天都外臣提出小说是“太平乐事”的消遣,在艺术创作上须“虚实”参错,“不必深辨,要自可喜”(《水浒传叙》)等观点,都意识到小说以虚写实表现现实的修辞特征。李贽、叶昼、冯梦龙是明代小说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李贽将“真”、“传神”、“妙”、“奇”作为小说评价的重要标准(《忠义水浒传全书发凡》),叶昼认为小说妙在“逼真”,妙在人情物理的处理上(《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回评》),冯梦龙提出“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警世通言叙》)的观点,肯定小说离不开虚构,都注意到小说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文体与修辞特征。
不过,上述理论家对小说特征的认识,从总体上来说还受制于传统的“史贵于文”文学观念的影响,将小说与经史相比附,重视小说的道德教化功用,还没有真正将小说看成是独立于经史之外的文体而充分重视小说的修辞功用。而这一切,在金圣叹的小说批评中,则有了很大的改变。
不少研究中国小说源流与发展的学者都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小说文体发展与史传文学的关系。“六经皆史”,史在中国文化中的绝对权威,也决定了它在中国叙事文类中的绝对权威地位。与欧洲小说起源于神话不一样,中国小说与神话虽然有着一定关系,在文体上却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中国神话并不是直接演化成为叙事文体的小说,而是被历史化,演变成为史传一类的历史文体。史传文学如《左传》和《史记》在叙事语言、结构方式、题材处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后世小说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是由于史传文体的叙事是以“史”而非以“文”为中心展开,是史的价值远重于文的价值,所以中国小说在史传文学母体内的孕育并没有形成对小说自身价值的重视,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小说修辞意识的发展。传统目录学对小说的认识信守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小说的价值在于“实录”。小说得之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真伪混杂,与正史的价值无法相比,但决非虚妄之言。即使像魏晋志怪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那样记录鬼神怪异的作品,对于作者来说也是信以为实的。这种观念在明代中叶有了转变,标志性的见解是胡应麟所提出的“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的观点。即使如此,胡应麟并不把“虚构”看成是小说文体的本质规定,他在进行小说分类时,仍把小说归属于子部或史部,认为近实者为小说,近虚者非小说。胡应麟的小说分类主要针对的是文言小说。明代批评家对白话小说的认识也是如此。比如,冯梦龙提出了“事赝而理亦真”的观点,意识到“虚构”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性,但他仍然认为小说的地位远低于“史”,认为小说因为其通俗性可以看成是“六经国史之辅”,其价值不过是“佐经书史传之穷”。在明代中叶,以《三国演义》讨论为肇始,引发了一场关于历史小说的争论,在这一争论中,绝大多数人是站在传统的“慕史拟史批评”立场上,肯定小说作为历史,特别是“正史”的附庸与补充而存在。如蒋大器强调历史小说应“事纪其事,亦庶几乎史”(《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张尚德提出的“羽翼信史而不违”(《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等观点,亦是如此。
与慕史拟史的批评观相联系的是对小说道德教化功能高度重视与肯定,这种观念也制约了小说修辞意识的发展。本来,小说作为一种修辞艺术离不开道德价值的选择与评判。就像《小说修辞学》作者布斯所说的那样,“小说修辞的最终问题是,决定作者应该为谁写作”,“小说只有作为某种可以交流的东西才得以存在”,所以“不能把道德问题看成是与技巧无关的东西而束之高阁”。不过,中国传统的小说观体现出来的道德问题,常常不是是否容纳道德内容与价值评判的问题,而是过于夸大小说道德说教的功能而忽视小说自身的价值。金圣叹之前的几位著名的小说批评家——李贽、叶昼、冯梦龙,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夸大了小说的道德教化功能:或把《水浒》看成“忠义”之书,认为上自“有国者”、下自“贤宰相”都应该看《水浒》,看了就会转变忠义只在水浒不在朝廷的反常现象,找到治国救民的良方(李贽,叶昼);或认为小说作为“六经国史之辅”,具有“导愚适俗”以“振恒心”的教化作用,小说应该“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冯梦龙)。这种认识对于提高小说地位有着积极意义,同时也造成一些理论误区,使小说受制于经史和道德教化观念而忽视其自身的价值与修辞特征。
金圣叹的小说批评则与之不同。表面上看,金圣叹的小说观念与前面提到的小说家的观念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他言小说,也喜欢与《史记》、《左传》一类史书相比附,试图通过攀附“史”来抬高小说的地位;也重视小说的道德功用,反复申言自己评点《水浒传》的目的就是要“诛前人既死之心”,“防后人未然之心”,也就是说警示后人,不要把宋江等人的造反行为误解为忠义行为,以乱了封建社会的人伦纲常。其实不然,因为他是从“才子书”的角度来认识小说的价值。所谓“才子书”,如他自己所选定的六种——《离骚》、《庄子》、《史记》、《杜诗》、《西厢记》和《水浒传》,是明显不同于“作书以德”的圣人之书的,它的目的不再是立德载道,而是“著书自娱,以消永日”(第十四回夹批),将“文”而不是“道”放在首要的地位。在《〈水浒传〉序三》中,金圣叹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立场:“夫文章小道,必有可观,吾党斐然,尚须裁夺。古来至圣大贤,无不以其笔墨为身光耀。只如《论语》一书,岂非仲尼之微言,洁净之篇节?然而善论道者论道,善论文者论文,吾尝观其制作,又何其甚妙也!”
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金圣叹反对将《水浒传》看成是“忠义”之书,认为它只是施耐庵的“饱暖无事,又值心闲”,“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秀口”之作(《读第五才子书法》)。也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金圣叹超越传统的道德教化和“史贵于文”的立场,确立了一种新的小说修辞观念,那就是将小说当成小说看,不再将其看成是经史的附庸与羽翼,充分注意到小说不同于经史之书的文体与修辞特征。他提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的区分,明确了小说不同于历史著作的修辞特征。“以文运事”,是叙述历史上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历史事实作者是不能任意改变与虚构的,而“因文生事”则不同,它的着眼点是“文”而不是“事”,“文”是作家叙述描写的东西,从“文”出发,就不会拘泥历史事实的真与假,就可以充分发挥作家的想象与虚构,写出现实生活中没有,在艺术家眼中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事”来。基于这种“文”与“事”的区分,金圣叹又提出“文料说”,认为“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第二十八回总评)。“文料说”并不否定“事”,因为没有“事”的空“文”,会成为虚假、无意义的东西,但是若只有现实中存在的“事”,缺乏艺术加工,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则无法流传。所以,不是“事”而是“文”,是“为文计不为事计”才应该成为小说创作的根本。从这里,可以看出金圣叹的小说观念与现代小说修辞观念是相通的。浦安迪认为,小说中的修辞有两个层次:“广义地说,指的是作者如何运用一整套技巧,来调整和限定他与读者、与小说内容之间的三角关系。狭义地说,则是特指艺术语言的节制性的运用。”基于这种区分,他指出:“现代文学批评家一般认为,一个故事用什么语言,如何被叙述出来,往往比故事本身的内容更为重要。”这即是金圣叹所说的“因文生事”,“为文计不为事计”。金圣叹提出这一观点,实际上表明他已意识到小说的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意识到小说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修辞艺术,是作者如何运用语言技巧讲述故事以影响读者,从而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积极交流关系的艺术。
二
具体说,金圣叹所说“文”,也就是贯穿在他小说批评中强烈的修辞意识,首先是通过他的“文法”理论充分体现出来的。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他严厉地批评了“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的倾向,反复强调《水浒传》阅读的意义就在于使人们懂得文法:“夫固以为《水浒》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也”(《水浒传》序三),“《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识字,便当教令反复细看,看得《水浒传》出时,他书便如破竹”(《读第五才子书法》)。
对于金圣叹的“文法”理论,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受到“选家评文”的方法甚至是八股文法的很深影响,所以不是一种小说理论与批评。其实,金圣叹的“文法”理论虽然受到“选家评文”方法甚至是“八股文法”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从评点小说实际出发的,是对小说艺术经验的总结。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例举了十五种“文法”: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敷粉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不省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横云断山法、鸾胶续弦法,大多都是针对小说叙事的方法与技巧而言的。在《水浒传》、《西厢记》的具体评点中,还涉及到众多的“文法”,如那碾法、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移堂就树法、狮子滚球法、对章作锁法、擒放法等等,也多是与小说与戏曲的叙事技巧与结构相关。金圣叹的“文法”理论虽然重在技巧与方法方面,却不是与内容无关的。比如,金圣叹论及“烘云托月”法的妙用,认为写人物如同“烘云托月”,画云是为了画月,云画不好,月也就画不好,如果云画好了,观众也就会被月所吸引,不再去注意云彩的美。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金圣叹“文法”理论的用心。表面上关注的是技法与形式,实际上则是形式后面所隐含的内容。只是内容在这里不再是与形式无关的,已转化为具有美学意义的形式,由形式来承载与体现。小说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如何写,所以不是“事”而是“文”才是小说得以成功的关键。金圣叹将小说叙事的重点从人物事件转向隐藏在其后的种种“文法”,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读者应该善于从形式方面,即从小说的结构章法、情节安排、细节与语言描述等修辞手段方面来看待小说的叙事与思想意义表达。为说明这点,我们不妨看几个具体的事例。
比如,《水浒传》所写的几乎都是绿林英雄好汉,所叙述的故事也差不多,无非是行侠仗义、官逼民反。如何写出其中的差异,金圣叹提出重要的美学修辞原则——“犯中求避”。他说:“亦以文章家之有避之一诀,非以教人避也,正以教人犯也。犯之而后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则避何所避乎哉?”(第十一回总评)《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提出“正犯法”和“略犯法”,亦是强调《水浒传》的创作敢于“犯”。比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和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之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林冲买刀后又写杨志卖刀,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后又写武松醉打蒋门神,都是“犯”。唯能“犯”才能有所“避”,在相似性中寻找到差异,写出不同的人物性格,使故事情节安排不至于雷同与重复。金圣叹说:“此书笔力大过人处,每每在两篇相接连时,偏要写一样事,而又断断不使其间一笔相犯。”(第十九回总评)比如,几番写梁山好汉与官兵的水战,事件完全相同,但具体的叙事与描写则完全不同。“犯中求避”,既避免了人物与故事的简单重复与雷同,又写出了人物与故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又如,《水浒传》第三回,浓笔重彩地写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两番使酒,打坏山门,搅乱禅堂,可在两番使酒之间又插入一段看似不经意写来的劝诫酒徒的文字。金圣叹对此大加赞赏,批了很长一段文字,认为这种写法好似“千岩万壑、崔嵬突兀之后,必有平莽连延数十里”一样,以舒其磅礴之气;又好似“水出三峡,倒冲滟滪”之后,必有“数十里迤逦东去,以杀其奔腾之势”。它不仅写出了生活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而且还“令读者一番方了,一番又起,其目光心力亦接济不及”(第三回总评),心中充满了新奇与愉悦。这里,金圣叹涉及到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故事讲述中,注意节奏技巧的变化。这实际上也是事关小说修辞的重要问题。金圣叹所说的“横云断山法”和“欲合故纵法”,主要讲的就是小说叙事要注意节奏技巧的变化,做到错落有致。“獭尾法”,按金圣叹的解释是:“谓有一大段文字后,不好寂然便住,更作余波演漾之”,讲的也是小说叙事要注意节奏技巧的变化,要做到高低起伏,留有余味。他还提出“闲笔”论(“偏是白忙时,偏有本事作此闲笔”第五十二回夹批),“急事缓写”(“每写急事,其事愈宽”第六回夹批),“间架”(第三回总评),“极省法”和“极不省法”(《读第五才子书法》)等等,主要也是针对叙述节奏技巧变化而言。金圣叹对小说叙事节奏技巧的重视,目的是为了加强小说的叙事力量和修辞效果,避免叙事的平直单调,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使读者产生更强烈的阅读兴趣。
再如,《水浒传》写景阳冈武松打虎,反复出现了“哨棒”这一物件;写紫石街的潘金莲见武松、西门庆等人,反复出现了具有象征意味的“帘子”。金圣叹用“草蛇灰线法”这一术语来形容这些物件描写的特点,认为它“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读第五才子书法》)。“草色灰线”这一文法曾遭到胡适的贬斥,认为它是八股选家流毒的典型体现,用这一方法分析作品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其实,“草蛇灰线法”是金圣叹总结出来的写人物的重要修辞手段与方法,它的特点是抓住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细节表现人物心理与性格。比如,像紫石街“帘子”描写:从最初的“帘子开处”和“妇人出到帘子下”的叔嫂相见,到潘金莲冷冷清清独自一人立在帘子下等“叔叔”,见到武松“踏着那乱琼碎玉归来”急切“揭起帘子”,再到武松出远门前叮嘱武大迟出早归到家里放下“帘子”,最后则是潘金莲自觉与武大吵闹无趣便每日“先自去收了帘子”以致不小心失手打了西门庆,这些描写非常传神地表达了潘金莲——一个内心充满欲念,面对现实又寂寞无奈的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所以它在小说中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像一根红线串联起小说的故事情节,使小说叙述的人物故事更加充实和具有艺术的神韵。
谈到金圣叹的“文法”理论时,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那就是“文法”与人物性格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都把“性格”论作为金圣叹小说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金圣叹的小说批评,更关心的是故事情节的展开而不是人物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所以他的“文法”理论的重心也在情节结构而非人物性格方面。《水浒传》写一百单八好汉,不是从一百八人写起,而是从一百八人的对立面高俅写起。在这之前,又安排了一段洪太尉误走妖魔和一个不在《水浒》英雄之列的王进被高太尉逼走的故事情节,之后又有并非梁山主要英雄人物的史进出场。这样的出场顺序与安排,在金圣叹看来,显然不是为了表现人物性格,而是为了体现了作者结构上的用心,服从于《水浒传》思想意义的表达。所以他在小说第一回评点中极力称赞《水浒传》这种结构安排,认为它凸显了《水浒传》“乱自上作也”的思想主题,是《水浒传》这部书宏大叙事的开始。《水浒传》的主线索是梁山英雄为官府所逼反上梁山,但中间的故事叙述和结构安排则采取分人物传纪的写法,从单个人的命运写起,每一个重要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身世与交代,彼此之间又存在着某种关联,最后形成人物的大聚合,在水泊梁山大聚义。这样的写法,对人物性格的描绘当然是有益的,但是也不能忽视人物在小说整体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晁盖和宋江是《水浒传》中最重要的人物,却直到小说第十三回和第十七回才出场。为什么这样安排?在金圣叹看来,是从《水浒》一书整体结构考虑的。他说:“如以晁盖为一部提纲挈领之人,而欲第一回便先叙起,此所谓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书者也。”(第十三回总评)又说:“《水浒传》不是轻易下笔,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过百十来遍。若使轻易下笔,必要第一回就写宋江,文字便一直帐,无擒放。”(《读第五才子书法》)将晁盖、宋江等人放在较晚的时候出场,运用的是一种“擒放”技法,它是《水浒传》作者成竹在胸的表现,使《水浒传》所叙述的故事显得跌宕起伏,没有违背《水浒传》人物传纪相续,从小的聚合走向大的聚义的基本章法,很好地体现了《水浒传》结构的整一性。《水浒传》中还有许多次要人物如张青、曹正等的出场,金圣叹用“贯索奴”一词来概括(第十六回总评)。所谓“贯索”,就是说这些人物像一根绳子将主要人物系结在一起,他们的出场主要起在情节结构上穿针引线的作用。类似的人物还很多,比如,王进、史太公、牛二、林冲火烧草料中的店小二夫妇等,他们在小说中的出现,是为主要人物的出场和故事情节发展服务的,当某个主要人物的故事情节终结了,他们在小说中的作用也就消失了,不再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存在。
三
在金圣叹的“文法”理论中,有两种技法值得特别重视,一是“绵针泥刺法”,一是“背面铺粉法”。它们的提出,不仅涉及到《水浒传》写人物的重要方法,而且涉及到小说叙事本体特征认识的重要修辞形态与原则——“反讽”。
这两种技法,在金圣叹看来,特别适合《水浒传》最重要的人物宋江的形象塑造。在明清的小说批评中,宋江多被看成是肯定性的人物,看成是“忠义”的化身,比如李贽就称赞宋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忠义水浒传叙》)。其中也有不同看法,如托名为李贽的容与堂刊本的评点中就有一些关于宋江的负面看法和揶揄挖苦之词。金圣叹对宋江这个人物是彻底否定的,认为《水浒传》所写梁山好汉一百零七人,“都有一百七人行径心地,然曾未有如宋江之权诈不定者”(第三十六回总评)。同时,对塑造这个人物的方法则大加赞赏。金圣叹称这种方法为“曲笔”,认为它与《史记》写汉武帝很相似:“初未尝有一字累汉武也,然而后之读者,莫不洞然明汉武之非是,则是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第三十五回总评)这种方法,在金圣叹看来,又突出体现在“绵针泥刺”和“背面铺粉”之类的反讽笔法运用上。比如,第三十五回,宋江被官军围捕,宋江哄他父亲,说是“孩儿挺身出官也不妨”,也不愿意落草为寇。而在这之前,作者浓墨重笔地叙写宋江为江湖朋友指路投奔梁山,显然与此相矛盾,反讽之意甚明。紧接作者又围绕宋江开枷和戴枷一事大肆描写:宋江被押去江州,被梁山好汉中途救下,花荣要为宋江开枷,宋江不肯,道是“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而后来,到了穆家庄等地,宋江又同意开枷。对此,金圣叹批了一个字——“假”,并评点到:“于知己兄弟面前,偏说此话,于李家店、穆家庄,偏又不然,写尽宋江丑态。”(第三十五回夹批)
类似的批语和评点还很多,比如,晁盖每次要领兵下山,都被宋江劝住,金圣叹认为这是用“深文曲笔,遂与阳秋无异”的春秋笔法,表面上写宋江尊重晁盖,实际上却是一心想取代之。又如,小说第三十七回李逵结识宋江,宋江给了李逵十两银子,李逵天真的认为宋江“仗义疏财”,非常感动,并以自己赌输了银子不能回请宋江为憾。这里实际上是运用了反讽的笔法,以李逵的真来反衬宋江的假,十两银子便买了李逵的心。金圣叹还指出,以银子收买人心并不是只针对李逵,而是宋江收买人心的通关利器:“然宋江以区区猾吏,而徒以银子一物买遍天下。”(第三十六回总评)“银子”在小说中的反复出现,只是作者用以嘲笑宋江的一个物件,它所讽刺的是宋江的假仁假义和老谋深算。
金圣叹为什么要将宋江看成是一个最具有反讽意味的人物?表面上看是与他“削忠义而仍《水浒》”,反对将宋江等人的造反行为说成忠义行为的政治思想动机是吻合的。深层次看,却与明清小说长篇小说的兴盛和文人们以小说叙事的生活立场与态度相关。
“反讽”(irony)这个术语来自西方文学理论。对于“反讽”的语义界定,学术界有很多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弗莱所说的“反讽这个词就意味着一种揭示人表里不一的技巧”。笔者认为,反讽可以看成是一种利用表面的言词矛盾来透视事物本质的方法,所追求的不是表层而是深层的艺术表达效果。中国古代没有明确提出“反讽”概念,不过从其内在的文化和文学精神看,应该是更接近“反讽”的。中国哲学的“反常合道”原则,中国史传文学的“春秋笔法”传统,中国诗学的美刺讽喻观念,应该说都与“反讽”修辞有着某种精神联系。这种反讽修辞,到明清时期,随着长篇小说的兴盛与繁荣,有了更突出的表现。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长篇小说的兴起都意味着小说叙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意味着“反讽”叙事意识走向成熟。卢卡奇认为(长篇)小说与史诗叙事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反讽成为叙事的典型形式。在他看来,小说已失去了古代史诗所展示的那种整体感与和谐感的社会基础,它面临的只是一个破碎化的现实,精神与物质、现实与理想、外在世界与内在心灵之间面临着巨大反差,所以只能以反讽的眼光看待世界。“小说的反讽是世界脆弱性的自我修正”,它意味着小说家面对复杂纷繁的现实一种自我调整与反思。明清长篇小说对反讽叙事的重视也具有这样的意味。浦安迪认为,对明代奇书文体最出色的文学成就把握,只能从反讽的眼光出发。明清小说叙事,无论描写绿林好汉的气概和统一天下的伟业,还是描写取经救世的圣迹,均介入一层曲笔的“反面”翻案意味。“这种手法,看来好像不过只是信手拈来的玩世戏笔,其实暗蕴着严肃文人的思想抱负”。
金圣叹对“反讽”修辞的重视,其意义也在于此。金圣叹对《水浒传》有一个重大修改,即腰斩《水浒》,去掉了梁山好汉被招安的内容,并在小说结尾中补上了卢俊义做梦,水浒英雄被朝廷尽数斩杀的情节。这一修改颇遭人非议,认为它反映了金圣叹顽固的封建正统的观念,而在笔者看来,它其实是金圣叹对待社会现实的复杂矛盾心态和思想抱负的体现。在《水浒传序二》中,金圣叹说,他之所以“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是因为“存耐庵之书其事小”,“存耐庵之志其事大”,是“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这种忧患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忧将宋江等人的造反行为说成忠义,后人则会纷纷效法;二是忧奸佞当道、贪官误国,因为这样也会造成天下纷乱,动摇封建皇权的统治。正是出于这种忧患,金圣叹提出“怨毒著书”说,云“为此书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设言一百八人,而又远托之于水涯”(楔子总评)。“怨毒著书”之说亦可以解释金圣叹为什么要否定忠义说,删除招安的情节却对梁山好汉啸聚山林的行为抱有深厚的同情。因为在金圣叹看来,梁山好汉的行为虽不合忠义之道却是事出有因,它是天下无道,乱自上作的结果。金圣叹还用佛学的“因缘生法”说来解释《水浒传》的创作,认为《水浒传》所发生的一切都与作者的主观设定相关,是因缘而生,一切皆有定数。这种叙事策略的采用,从表面上看与其受到佛学思想的影响有关,深层次看,正反映出他政治和道德评判的两难:既不愿意放弃官方意识形态立场,将梁山好汉的造反行为说成是忠义,又对梁山好汉啸聚山林的行为抱有深厚的同情,所以只有将梁山好汉的故事看成是因缘早定,空幻与虚无的。因为只有在一个空幻虚无的小说世界中,小说批评家所面临的道德价值和政治立场的选择才会被淡化。也正因为此,“反讽”成为他评点小说中人物与事件的重要方法。因为唯有“反讽”,将宋江为代表的“造反受招安”行为看成是一种“褒贬固在笔墨之外”的艺术描写,才能化解金圣叹既要否定梁山好汉的“忠义”行为又对其命运深表同情时所面临的种种矛盾,才会超越单一的政治和道德标准评判人物,才会在种种矛盾与差异中寻求到一种平衡,才能做到不是将关注点放在作品所描写的表层的人物与事件上,而是投向作品的深层意味和潜在意义,以更加冷峻和超然的眼光来看待小说所表现的事件与人物。
四
金圣叹的小说修辞意识还包含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它重视读者的接受,重视小说批评对读者的引导作用。本来,随着小说评点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形式的兴起,读者因素和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就被凸显出来。因为小说评点所面对的对象不像传统诗文那样,主要针对遣怀述志、娱兴怡情的士大夫文人,而是走向民间与书坊,与大众消费群体的审美需求紧密联系起来。而大众由于其知识和文化修养方面的局限,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小说家的艺术用心。再加上上层社会的文人大多轻视小说,把小说看成是消遣排闷的工具,所以需要小说评论家的精心评点和引导,以更好地理解小说的思想与艺术价值。明代小说理论家蒋大器论述历史小说创作的意义时曾指出,虽然这一类小说“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但是由于不像历史著作那样“理微义奥”,“不通乎众人”,而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所以极易为读者喜爱和接受。反过来,批评家也应该充分考虑读者接受特点对读者进行引导,以使读者充分理解作者的艺术匠心和作品的内涵。明代小说批评家袁无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提出“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忠义水浒全书发凡》)的重要观点。不过,金圣叹之前的小说批评家对读者因素的重视,主要还是围绕小说的通俗化思潮进行的,强调的是小说“谐于里耳”、“导愚适俗”、感人快捷的艺术功用,而很少进入到小说文本分析的层面。金圣叹对读者因素的重视则进入到这一层面。所以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读者接受原因和评论导向的考察,而是一种与小说文本、技巧分析密切相关、充分重视作家创作与读者阅读心理的修辞性批评。
按照伊格尔顿对现代修辞学的界定,所谓修辞学就是研究话语“是如何结构和组织起来,并且考察这些形式和手段对于种种实际境况中的种种特定读者产生的效果”。这也就是说,修辞学不仅仅要研究作家如何运用特定的修辞形式与技巧,更重要的是要考察这些形式与技巧的运用如何传递给读者,对读者的心理产生积极的影响与感染作用。金圣叹的小说修辞批评正具有这样的意义,它非常重视文本形式与技巧的分析,但这种分析又是指向小说的修辞效果,通向作者与读者的心理,对读者的心理有着积极引导作用的。
在小说阅读中,有两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一是将小说作为闲书和消遣排闷的作品,浮光掠影地对作品进行阅读,对作品的理解停留在表层意味上而缺乏深层意味的把握;二是对作者缺乏充分的信赖,过分强调读者的主动性而忽视作家的修辞意图与思想意义表达。金圣叹对这种两种倾向都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作家提供的文本的好坏,所选择和运用的小说技巧是否成功,艺术境界表现是否完美,都会直接影响到小说修辞效果的产生,影响到读者对小说的阅读。所以他提出艺术表现的“圣境”、“神境”与“化境”说,强调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关键在于剪裁,有“全锦在手”和“全衣在心”而不是“全锦在目”和“全衣在目”,应该有所写,有所不写,留有余味,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水浒传》序一)。同时,他还意识到在文学接受活动中存在一种现象,即读者只浮光掠影地阅读作品而忽视作者的惨淡经营和良苦用心,只关注外在的故事情节而忽视内在的思想意蕴和新颖的艺术表现,他将这种现象称为“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于是提出“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读第五才子书法》),要“见文当观心”(第五回夹批),强调读者读书,要善于把握作者的意图和作者赋予文本的意义,得作者之心,成为作者的知音,切忌那种“随文发放”,“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读第五才子书法》)的阅读方式。同时,他倡导对文学作品的细读,特别是对作品的“文法”,包括“字法”、“句法”、“章法”、“部法”的细读。他认为只有通过“细读”,方知“是其一篇一节一句一字,实杳非儒生心之所构,目之所遇,手之所抡,笔之所触矣。是真所谓云质龙章,日姿月彩,分外之绝笔矣”。(第二十五回总评)
不过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金圣叹忽视读者在文学阅读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他提出“读者精神”,“不为作者所满”(《读第五才子书法》),“读者之胸中有针有线,始信作者之腕下有经有纬”(第九回总评)等观点,均是要求读者积极参与文本和体验文本,充分发挥读者在文学鉴赏活动中的能动性与主体性。他对作品的具体评点便很好地体现了这种主动性与参与性。比如,他对梁山好汉劫法场救宋江等人的情节的评点:“使读者乃自陡然见有第六日三字,便吃惊起,此后读一句吓一句,读一字吓一字,直至两三叶后只是一个惊吓。吾尝言读书之乐,第一莫乐于替人担忧,然若此篇者,亦殊恐得乐太过也。”(三十九回总评)这段评点表明,在金圣叹看来,当读者置身其境,深入体验文本所制造的故事情节悬念后,就会获得极大的快乐。又如,第二十七回写武松发配到孟州城,管营有意要免他一百杀威棒,武松偏不领情,金圣叹对此评点到:“妙,然而何也?我又欲疾读下去,得知其故;又欲且止,试一思之。愿天下后世之读是书者,至此等处,皆且止试思也。”文本的细读完全是以读者积极主动的心理体验为基础的。他还提出“想见其为人”(二十五回总评)的观点,所谓“想见其为人”,就是要充分发挥读者的想象力和情感能力,设身处地体察人物。比如,《水浒传》第三十六回有一段描写:宋江在船上受了惊吓,忽然听得有人要救他,待宋江“钻出船上来看时,星光明亮”。金圣叹对此批点道:“此十一字,妙不可说。非云星光明亮,照见来船那汉,乃是极写宋江半日心惊胆碎,不复知天地何色,直至此,忽然得救,夫而后依然又见星光也。盖吃吓一回,始知之矣。”这段批语正是“想见其为人”,即评点者化身为作品中的宋江这一人物,所以他才能深入体验到宋江此时此刻的复杂微妙的心情。不仅如此,即使对作品中文字描写极其简略和文本信息并不丰富的地方,金圣叹也充分调动自己的艺术想象力,深入揣摩和体察,有所发现,给读者以积极的心理引导。比如,第十九回刘唐给宋江送书信和黄金,作者并没有详细描写,只是一笔带过,金圣叹却从中悟出作者的用心,予以细致的解读,从小说简单的文字描写中想象出刘唐交信交金、宋江接书信看书信每一细节。这种解读未必是作者心中无,却一定是读者心中有的体验,而这正是小说修辞效果赖以产生的重要前提。
有论者将金圣叹的“文法”欣赏和批评与西方的新批评理论等同起来。新批评理论重视文本语言结构分析和文本细读,其实也是一种重视修辞形式分析的批评理论,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联系与相似。但是,新批评将“文本”置于绝对优先地位,强调应排除文本之外的因素将文本孤立起来“细读”,重在通过文本的语义分析来寻求文本结构自身的统一与和谐,而金圣叹的“文法”论和“文本”细读论则是以沟通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使作家所创造的作品为读者所充分欣赏理解为前提的,所以二者又不能简单等同。在金圣叹的文本与技巧分析的背后,始终有读者与作者的身影的存在。所以他不像新批评那样走向文本中心,而是在以文本分析为基础时,张扬“读者精神”,将读者的阅读心理放在重要地位,以形成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默契与互动。而这些,正是金圣叹小说修辞批评的价值所在,值得我们充分的重视。
〔1〕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以下关于金圣叹著作的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标注。
〔3〕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胡适.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
〔5〕弗莱.批评的剖析〔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6〕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 小说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