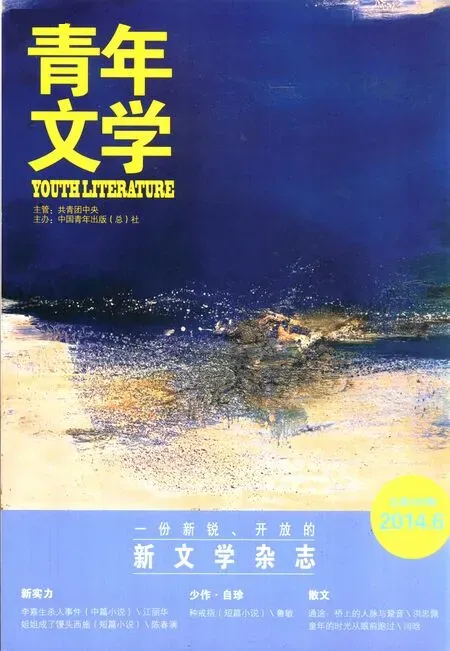林宗龙的诗(组诗)
林宗龙
父亲的摩托
绵延的电线连着远方,天空中
一只落单的鸟,像公交亭下等车的女孩,
父亲骑着摩托,载着生病的我,
穿过茫茫的暮色,和越来越沉的荒凉。
立秋刚至,草木还未在经验中枯黄,
石头和石头一样的事物,
继续以流动的方式柔软下去。
那是他的儿子,透过后车镜,
看到父亲不再年轻的脸,像骨头一样,
在生活的碎片里,反射出坚硬的光,
这车前的那束灯,是父亲撑开的手,
照着隐约的童年,以及前方
逐渐暗下去的路。我坐在车子后座,
就像小时候,骑在父亲肩上,
在那个杧果成熟的季节,
父亲抱住我的双腿,我抓着父亲的头发,
穿梭在溢满稻香的羊肠小道。
可现在,这个一脸皱纹的中年男人老了,
他的儿子也已经当上了父亲。
在这条无始无终的公路上,
他们正以另一种形式,穿梭在另一个
即将变成记忆的日常里。仿佛时间
又一次停止了,我一直没有告诉他的妻子,
那个平静的时刻,
是我的第二次出生。
给你买生日礼物
我记得那天乌云越来越厚,
像一个人在做重要决定前的思索;
他沿着树一样的路要去哪里?
亲爱的,只有你明白他的心思,
那接下来的事可能是树叶长出刺,
大卡车停靠在绿色的邮筒旁,
废墟的芦苇如喷泉突然冒出,
一些神秘的惯性改变着秩序,
在陆地与陆地之间,在一根圆木
漂浮的钟面——我爱着你,
但始终没有发出声,就像那天
我记得他徒步走了几条街,
乌云越来越厚,雨却迟迟未至。
寂静岭
刚下过雨的草地,露气逐渐散去
从林间传来的布谷鸟叫声,混着清晨通透的寂静
像积蓄了一股明媚的力量
我坐在床沿,看着熟睡中的小宝贝
有时候,他翕动着小嘴
嘴角轻轻咧开,像梦见阳光中跳跃的小鹿
有时候,他会像小羊羔一样
把手举过头顶,贴在柔软的耳朵旁
像是听见母亲从森林深处,微笑着慢慢地走了过来
有时候,我想着他快快长大的样子
在那无限的流逝中,和他的父亲一起赶着火车
想起酗酒的卡佛
他在怀念俄勒冈州的新月市
等于我在怀念那扇没有火车头的门
我到过那里,只有我到过那里
金灿灿的稻穗,在月光中泛起微澜
我到过那里时,风停住了
成群的犀牛在空荡中四散开来
我看见他酗酒后平静的双眼
他凝视着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
等于一种悲悯覆盖一种悲悯
所有的人都在说,你无法再回去了
那生活的父亲,捕鹿人的脸
就是那片深蓝的海,涌起的赤潮
日常
谷雨将至,无雨;
风一吹,玉兰的花瓣
就落在了透明处;
清晨买完菜,妻子和我
会从荷塘路穿过。
树木掩映,地上的光
像从圣经上漏下来,
微润,细密;
这容易让人忆起
远方的朋友,以及火车上
发生的事。
那年立秋,多云,
我去了一趟北方,
天空高远,
白杨孤独,收割完的谷物
在平原上堆成小山;
我惊异于这流动的宁静,
像此刻,我无比欢喜于
这简单的日常;
谷雨已过,小满,芒种……
在回家的路上,我牵着妻子
小心翼翼地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