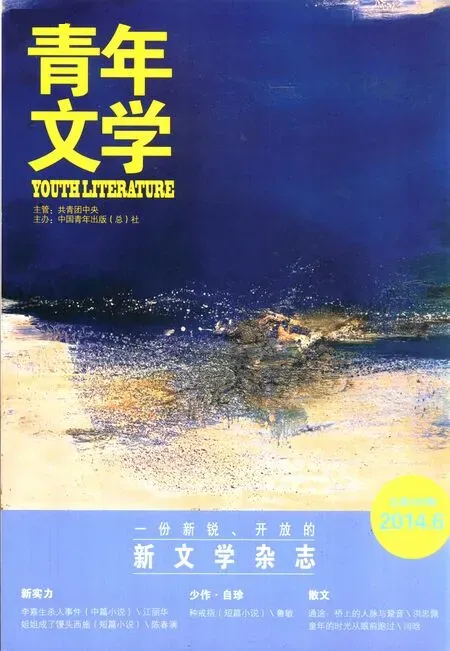姐姐成了馒头西施
文/陈春澜 [短篇小说]
付萍十七岁那年,是一九七八年,也就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这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家里突然来了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中等个、圆脸、微胖,模样和爸爸差不多,只是爸爸的脸白,这个人的脸黑。付萍想:爸爸和这个人,像自己蒸的馒头,爸爸是碱小时的馒头,这个人是碱大时的馒头。
付萍那时刚学着蒸馒头,凡事都能联想到馒头问题。在她眼里,世界上最难的事莫过于蒸馒头,只有把发好的白面揉进不多不少正好的碱面,出锅的馒头才能又大又白又耀眼。但那耀眼馒头的荣光,属于母亲,不属于她,她蒸的馒头不是碱大就是碱小。她觉得妈妈是世界上最精明的女人,没有一件事办不利落。
黑馒头的来人走后,母亲让白馒头的父亲上街去打酱油。然后把付萍从另一个屋子喊出来,母亲偷偷瞅了她一眼,看见她手里还拿着书,边走边看,母亲在心里轻轻地叹了口气,说:“萍萍,你去替人考一次试吧。”低着头说话的母亲不看付萍,看着手中正在织的毛衣。付萍也不看母亲,她盯着自己的书看,边看边问:“替谁?啥考试?”
“替一个乡下远房亲戚的孩子,就是今年的高考,别的,你就不用问了。”母亲终于说出了最难说的话,她长出了口气,仍然埋头织毛衣,好像织毛衣才是全天下最当紧的事。
付萍手中的书“啪”的一声落到地上。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摇着母亲的胳膊问:“妈,那我怎么办?”
“你学习那么好,晚考一年怕啥!”
在最近的一次家长会上,付萍的班主任老师朗声宣布:像付萍同学,现在就完全可以回家睡觉去了,不用担心,到考试那天醒来去考就行。深受鼓舞的母亲,把头抬得高高的,回家就教付萍蒸馒头。母亲用蒸馒头的悠闲盲目地展示了她和班主任老师同样的感受,他们对付萍高考这件事是一百个放心、二百个信心满满、三百个底气十足。母亲相信付萍今年能考上大学,明年照样能考一个更好的大学。
“替考可以,复读一年,我不愿意。”付萍对母亲说,“如果那样,我情愿待在家里蒸一年的馒头。”
母亲说:“不用你蒸,你不想复读,那就在家里自学一年,明年再考,反正这个替考的事,妈就给你做主了,不去也得去。人活在世上,有多少事是你想做的呢,妈还想当皇后,每天有人侍候着,什么也不用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可是,能行吗?别人不清楚,你还看不见。妈每天不仅赶死赶活地去上班,还得带你和你弟弟,供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尤其是你,小时候最能闹病,隔几天跑一趟医院,妈带你这么大容易吗?妈不懂大道理,但知道你学习好,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学习好,也是大人这么多年苦心培养的结果。妈就求你这么个事,你还不答应妈,现在翅膀还没硬了,就不听大人话了,将来考上大学有了本事,妈说话更是……”
付萍低着头,听着母亲的数落,看着地上掉的书也不去捡。她双手抓着上衣的一角机械地揉搓着,揉得手都疼了,母亲的主意还没变。母亲的决定不是衣服,是铁板钉钉儿,她揉不动。在母亲一浪高过一浪的哭诉中,付萍走到母亲身边,接过她手中织的毛衣,放在床上,抱住母亲的肩膀安慰道:“妈,你别生气了,我去替考。”
付萍不敢和母亲硬顶牛,大事小事,对与错都得听母亲的。母亲有心脏病,母亲说是生她时落下的病根。付萍想求父亲,她不想替别人高考,她要自己考自己的。可是,父亲在这个家里做不了主。再说,父亲重男轻女,对弟弟管教的多,对她的事干涉的少。不论大小事,都是一句话:问你妈去,你妈觉着好就好。
老师是付萍能想到的最后一棵救命稻草,尤其是班主任老师对她最好。第二天早上,付萍背起书包就要去学校,她想老师有办法让母亲改变主意。可是,母亲根本不给她翻牌的机会,更不会让她把替考的事捅给老师。她还没走到门口,母亲就从后面扯住了她的书包带说:“今天你就不用去上学了,一会儿我就去学校,和你老师说,你得了传染病。”
母亲在医院挂号室工作,开个假病假条对她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她拿着一张“急性传染性黄疸型肝炎”的诊断建议书,找到了付萍的班主任。班主任无奈地摇头:“真是太遗憾了。”母亲点头:“可不是,得病不由人啊!”
高考前一天,母亲领着“病中”的付萍,坐了八个多小时的火车,来到了远离省城的一个偏远小县城。一下车,付萍就看见那个黑馒头男人忧心忡忡地出现在站台上。他问母亲:“怎么就你,孩子不肯吗?”母亲把身后的付萍一把拉到了他面前。他伸手就去拽付萍背上的包,要替付萍背。付萍往旁边紧躲了两步,冷着脸说:“谢谢叔叔,我自己行。”他尴尬地缩回手,扭过头和母亲说:“那我带你们去住的地方。”
他在前,付萍母女在后,三个人沉默地走进了一家小旅馆。住的地方安排好后,他要带她们一起去外边饭店里吃饭。付萍说:“妈,我不饿,要去,你去。”母亲说:“那就算了,我们在火车上吃了,明天还要考试,你走吧。”黑馒头男人再没说什么,临出门时把一张准考证放在了桌上。
准考证上照片是付萍的,名字不是。母亲指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叮嘱道:“萍萍,记住,从明天起,你就是郑好,有同学和你说话,你就指指嗓子,什么话也不要说,赶紧躲开。”
母亲多虑了,进考场前,除了那个讨厌的黑馒头男人,没有一个人和她打招呼。进了考场,更没人搭理她。倒是付萍几次想站起来,和监考老师说,这个准考证上的人,不是我,我不是郑好,我是替考的付萍。可是,她不敢,她不能坏妈妈应承下的事。妈妈说了,要像给自己考一样好好地考。还放了更狠的话,今年若是故意考不取,明年你也别想考自己的。
三天的高考,很顺利地结束了。黑馒头男人把她们母女送到了返程的火车上,列车员最后一次催送客的人下车时,付萍看见,站在过道里的黑馒头男人动作麻利地从身上掏出一百元钱,俯下身来,用讨好的口气和坐着的她说:“给你的。”
黑馒头男人手里拿的是第四套人民币里面值最大的一张,去年才出的,也是付萍见过的最大的钱数。她想拿上,攒起来买个录音机,可是,她怎么能拿他的钱?她不是为钱替考的,是为了母亲。如果是为钱,多少钱她都不愿意。她故意把头扭过去,看着车窗外。
车窗外的小站台,在晚霞的映照下,呈现出一派没心没肺自得其乐的神情。在这种喜洋洋的神情里,有不多的几个送客男女,稀稀拉拉胡乱地向车上的人招手。他们这一招手,差点把付萍的眼泪招出来。想到不久之后,身边这个黑馒头男人也会这样兴冲冲地和远走高飞的郑好招手,付萍就觉得这个小站台真是岂有此理,叫什么名字不好,为什么偏偏叫“下马塔站”,好像专为嘲弄自己似的。没有她付萍的下马,能有郑好的上马?
黑馒头的男人下车不一会儿后,车开了,付萍又把目光转向车厢内。车厢里,陆续有人从包里往出掏吃的干粮,也有人端着杯子到车厢连接的地方去打水。母亲有点讨好地和付萍说:“他特意给咱们买了肉蓉方便面,两毛五一包呢,还有一只带包装的烧鸡,打开就能吃。”
“我不饿。”付萍声音很低。
母亲瞅了付萍一眼,想说什么强忍住没说,弯腰拿出另一个包,那里有她们来时从家里带的麻花和散装的泡面,她给付萍泡了一碗,把麻花掰开泡进面里说:“好好吃饱,咱们还有明年。”
考完最后一门那天,母亲把标准答案递到她手里:“萍萍,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家。你估个分告诉人家,人家也踏实,咱们走得也安心。”付萍保守地估了一下说:“按去年的标准,超重点大学的线应该是没问题。”母亲听了安心地笑了。母亲如释重负的神情让付萍感到说不出的伤心,伤心的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到来年的高考。
在等待明年高考的日子里,母亲没有让付萍在家蒸馒头。九月份开学前,付萍的班主任老师几次上门劝“康复”的付萍回原校插班再上一年高三,付萍不愿意。老师又把她介绍到了另一所学校,正好,小付萍一岁的弟弟付杰也在这个学校读高三,学校索性就把姐弟俩放在了一个班。校领导拿着付萍的进校测试卷,对推荐她的原班主任老师说:“谢老同学割爱,弟弟就很优秀,想不到,姐姐比弟弟更优秀。”
付萍和付杰上了同一所学校,最高兴的人是父亲。他把儿子叫到跟前说:“姐姐能和你一起学习,是你的福气,姐姐不是别人,有问题不要自己在心里闷着,要多问姐姐。”母亲也把付萍叫到跟前叮嘱道:“你是姐姐,你要多帮着点弟弟。”付萍笑了:“妈,你和爸怎么了,我也是去当学生,又不是去当老师。”
付萍嘴上这样讲,行动上对付杰可是一点没保留,姐弟俩每天白天一起上课,晚上就在一个桌上脸对脸共同学习到深夜。毕竟付萍是又上一次高三,更多的时候,是她带着付杰一起学。
都以为姐弟俩双双考入名牌大学是十拿九稳的事,谁料,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行。就在高考的前三个月,家里突然又来了陌生人,这次,不是一个,是一群,他们是父亲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母亲显然没有接待群体来访的能力,她手忙脚乱、语无伦次,完全没有了去年面对黑馒头男人的那份从容。她说,快,快去学校,把付萍和付杰都接回来。
付萍做梦都没想到,在那个万物蓬勃向上的四月天里,她的命运又一次急转直下。那天下午,正上化学课,教室的门被突然推开,教导处主任走了进来,他用极其温和的声音把付萍和付杰同时喊了出去。付萍和付杰领会错了主任的温和,俩人往出走时,脸上都挂着天真烂漫的微笑。付萍在前头走,付杰跟在后头,付萍回过头来笑着招呼付杰:“快点,要不,有好事全让姐抢了。”说这话时,付萍哪里能想到,等待他们姐弟俩的是父亲意外去世的消息。
父亲是煤矿的技术员,死于井下冒顶事故。“人死不能复生。不管老付是怎么走的,走了就走了,重要的是活着的人还得活。”父亲单位的领导这样劝母亲,母亲点头,她心里清楚,同样是活,先前想好的活法就得跟着变。到山砍柴,到河脱鞋,走到那步就得说那步的话。打理完父亲的后事,母亲把矿上给的二百六十元抚恤金,锁到箱子里。然后,把付萍和付杰叫到跟前说:“你们姐弟俩商量一下,谁去考大学,谁留下来顶替你爸去上班。反正,这个指标不能白白作废,它是你爸用命换的。再说,你爸走了,妈现在只能供一个,不说供不起,就算供得起,妈身边也不能没个人照应吧!”母亲把该说的话说完后,叹口气,倒在了床上。
付萍站在当地,咬着下嘴唇,半天不说一句话。她想自己要是能重生一回就好了,让付杰当哥,她当妹。可是不行,付杰一落地,头上就有她这么个姐姐,不说大一岁,就是大一分钟也是姐姐啊!姐姐是最疼弟弟的,姐姐怎么有脸和弟弟争。可付萍想起母亲去年对她说的话“你学习那么好,晚考一年怕啥”,她的心就放不到肚里,心不踏实,人就会乱说话,所以,她不说话。
付杰和姐姐挨着站着,也咬着嘴唇,也不说话。付杰不说话,付萍不怪他,小的时候,付杰贪玩,不爱学习,没少挨父亲的打,被父亲打怕了的弟弟从小就不爱说话。其实,付杰是在等着付萍先开口。小的时候,家里有了好吃的,母亲总是给他俩平均分配,一人一份。付杰总是狼吞虎咽,先把自己的一份消灭掉,然后,就直着眼睛看着姐姐吃,姐姐这时总会主动再匀一半给他。从小到大,付萍没有不让着付杰的时候,付杰想让姐姐再让自己一回。
姐弟俩的沉默惹恼了母亲,她坐起来,用手拍着床,声泪俱下:“都不说话,好,你们都去奔自己的前程吧,都不用留下来陪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妈。”说完,母亲用头撞着墙:“干脆我也死了算了,省得活着当你们的累赘。”知女莫如母,母亲是哭闹给付萍看的,她知道付萍一向心软,禁不住她这么折腾。
果然,和付杰并排站在当地的付萍,一步冲到床上,把母亲从墙边拉回到床上躺下。然后,身子靠墙面朝母亲坐在床上。在家靠娘,出门靠墙。现在,娘不让她出门,娘也出不了门,出不了门的娘撞墙是假,要靠她是真;父亲走了,她就是娘的墙。付萍探过身子,拉起母亲的手,扭头看着付杰,说:“小杰,我留下管妈,你去高考。”说完,付萍起身下床,走回自己的房间。再出来的时候,手里拎了一大堆书和作业本,当着妈和付杰的面,她把书和作业本一把火全烧了。
因为父亲是工伤,付萍的工作解决得很顺利,短平快,不到一个月,付萍就退学上了班,她被安排在矿上最大的职工食堂。大食堂分工明确,付萍选择了面案,负责做各种面点,山西人爱吃馒头,付萍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蒸馒头。揉馒头的活儿,她不讨厌,从小就喜欢,只是那时是自己觉着新鲜好玩,跟着母亲在家瞎起哄。现在是命运对她的安排,日复一日的生计,天天都得干。想到自己没准得蒸一辈子馒头,付萍常常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
看着落寞的付萍,母亲给她打气,行行出状元,淘粪工时传祥,还能和刘少奇握手,受毛主席接见。咱好好蒸馒头,肯定能蒸出大气候。其实,在母亲的心里,她并不想什么大气候,她只想付萍能安安分分地守在自己身边。她越来越老了,她的身边没了男人,不能再没有付萍。不在自己身边的孩子,再有出息也指不上,蒸馒头的付萍才是留给自己的依靠。
付杰的高考成绩出来后,付萍看着付杰的成绩单,骄傲地想,自己到底是姐姐,她去年给郑好考的分怎么也要比弟弟今年的分高,至少也能高出二十多分,可惜,分再高也没用,沾光的人是郑好。付萍问母亲:“妈,你说那个郑好去了大学,人家就发现不了照片和人不一样吗?”
母亲不吭声,母亲又在织毛衣。织了一会儿,母亲放下毛衣,认真地劝起了付萍:“萍萍,别想那么多,妈就从来不爱想过去的事,过去的事再想也没用。替考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不用老说。这就好比送到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人家的了,你不用老惦记的。一个人一个命,兴许,就该着人家上那个大学。再说,上大学也不见得有多好,毕了业天南地北的还不知分到哪里,妈想见你一面都不容易。你想,你爸爸单位怎么着也是个国营大单位,没准,上了大学还分到集体单位呢。”
付萍想不到自己随便问的一句话,引出了母亲这样一番扯不清的大道理。付萍说不过母亲,也怕母亲,这怕里其实有一半是付萍的孝顺,她不想伤母亲的心。母亲常说,孝顺孝顺,没有顺哪来的孝。从此以后,付萍再不敢在母亲面前提郑好两个字。
母亲的眼界没有那么宽,你就是让她望穿双眼,也望不到几年之后大学毕业的郑好,根本没把国营和集体放在眼里,她挥动着付萍给她装上的隐形翅膀,跟着八十年代的出国风潮,飞越了国门,在一家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供职。郑好的天空越来越辽阔,远远不是每天低头蒸馒头的付萍抬头就能望到的天空。
付杰上大学走的前一天晚上,付萍悄悄地对弟弟说:“小杰,姐想求你一件事。”付杰面有愧色,他对付萍说:“姐,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你能上个比我更好的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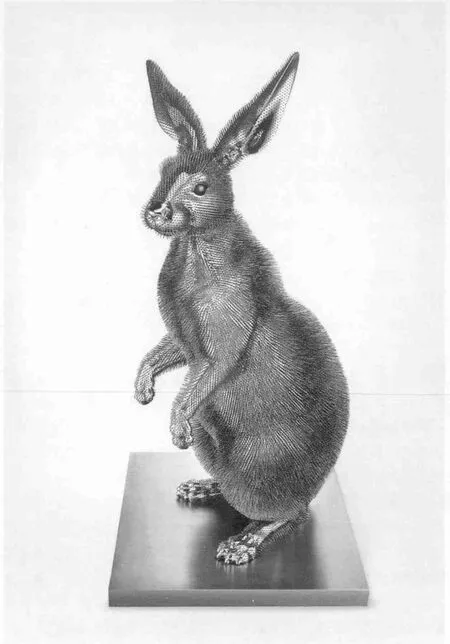
一向柔软、温暖的皮毛哪儿去了?面对近十五万根“缝衣针”重构的金属兔,碰触棘手,温存不在,坚硬、冰冷、刺痛、距离……艺术家以独具创新的语言表达了对自然生命的悲悯与敬畏、对人类恶行的反思与控诉。名称:千针万痛作者:解勇材料:不锈钢、缝纫针姐姐成了馒头西施
“小杰,你误会姐了,你是咱们家唯一的男孩,我当姐的,愿意让你好。姐是想求你到了大学后,帮姐找个人,这个人叫郑好,妈说是咱们家的远房亲戚,姐去年就是替她考来着,要不,姐现在都大二了。姐去年考的那个分肯定能上了北京的大学,你不知道姐多想去北京念书,可惜,再高的分,也是替人家考下的。不知道她到底上了哪所大学,有没有因为穿帮被学校退回去。”
想起母亲的千叮咛万嘱咐,只要你不说,这事永远不会被人发现。付萍也千叮咛万嘱咐弟弟:“小杰,你悄悄地帮姐打听,姐已经这样了,只是好奇,没有祸害人家的意思,你不要让人发现,找到也只是把她现在的情况告诉姐就行了。记住,千万不能让妈知道这件事。”
付杰不敢报北京的大学,报了云南大学,付杰指着地图告诉母亲:“离太原有两千多公里,得坐好几天火车,还得到西安中转。”
“那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哭也哭不回来。”
付萍安慰母亲:“妈,报的时候,你不是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再说,不是还有我在你身边吗?”
“得亏有你。”母亲说这话时,更觉得不让付萍考大学是对的。母亲劝付萍,知足常乐,蒸馒头也没什么不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不愁吃不愁喝。要是放在一九六〇年,能在食堂上班,还不把人羡慕死。
付萍不语,心说,都快八十年代了,还翻六十年代的老皇历?现在,谁羡慕的不是大学生,报上都把大学生称作“天之骄子”,她也想当“骄子”。可惜,人们眼里的她不过是个“馒头西施”。所以,母亲的话,付萍不爱听。她爱看付杰的来信。付杰每次给她的信,她都平平展展地收起来,看着信封底下大学的落款,就好像自己上了大学一样,颇为自豪。有次,她扬着手里的信和食堂的姐妹们说:“我弟弟从大学里寄来的。”一个菜案上的女孩,很不屑地当众讥笑她:“有什么可显摆的,再好的大学也是你弟弟的大学,又不是你的,你不是和我们一样,就一个食堂做饭的。”
付萍收起信,收不起的是自己对大学生活的那份由衷的向往。每天晚上回到家,付萍都要把付杰的信颠来倒去,看上一遍又一遍。从付杰的来信里,付萍看到了诸多可以点燃她的新名词,她记住了阶梯教室、大课、男生公寓、女生公寓、学生会和社团,还有老乡会等。看到了老乡会,付萍又在信里特意问起了郑好,可付杰的回答是:“姐,还是找不到,也许她就没敢上,也许她上了,已经被退回去了。”付杰的信里,从来没出现过郑好两个字,付杰总是写她怎么样,她怎么样。付萍突然觉得中文很有意思,如果交谈的双方谈到一个人,从不用名字称呼这个人,而是一直用代词他或她,这样,无形中,就把被指的这个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指远了,一下就指到了千里之外。她笑了,弟弟还是和她亲,也长大了,学会安慰姐姐了。
付杰是一九七九年上的大学,一入学就通过老乡会帮姐姐打听郑好,可是,问到的人都说不知道。那时电脑稀缺而金贵,像旧时王谢堂前燕,别说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就是在大学也不多见,更没有互联网,打听人的途径又窄又有限。就在付杰绝望地以为有负姐姐重托的时候,那个让他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郑好,得来全不费功夫地和他不期而遇。付杰大四那年寒假,送同屋的一个同学去飞机场,在机场的候机厅里,同学突然被一个看上去很体面的高个男人拍了一下肩膀,然后,同学一回头,四目相对的同时,俩人就拥抱到了一起。抱了一会儿,那个男人指着他问:“这是……”
“我的大学同学,一个寝室的哥们儿。”
那个男人伸出手,和付杰礼节性地握了一握,又转身笑着和同学说:“一会儿,我也介绍你认识个人。”说着,他朝刚从洗手间走出来的一个女孩频频招手:“快过来,郑好,遇上发小儿了。”
听到叫“郑好”,付杰的心“咚”地跳了一下,再一看,整个人也差点跳起来。付杰看着一步一步向自己逼近的郑好,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细长的身材,细长的脸,细长的眼睛,小巧的嘴,天,这不是付萍,我的亲姐吗?
这个和付萍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子,听完对付杰的介绍后,微微点头,轻轻一笑。这个微笑让付杰确定,眼前这个人绝对不是他的亲姐付萍。付萍不是这样的做派,在家乡蒸馒头的付萍,不会这么含蓄地微笑,这是见过世面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性女人才有的浅笑,淡定、自信,还有那么点不显山不显水的神秘。
在家里陪母亲的付萍,也不会出现在机场,付萍没有坐过飞机,就是火车也只坐过一次,那就是替郑好高考那次,那是付萍出门最远的一次。郑好老家那个小县城,也是付萍到过的最远的地方。
付杰忘记了自己怎么和那个男人,还有挽着那个男人的郑好道的别,他迷迷糊糊地目送着郑好挽着那个男人的胳膊幸福地通往安检口,他突然十分想念姐姐。此刻,付萍在干什么呢?是在弯腰和面,还是低着头揉馒头,或者是把揉好的馒头正一个一个耐心地摆往笼里……付杰突然觉得心里堵得慌,他问同学:“你那发小儿刚才是不是说,那个女孩子叫郑好?”
同学愣了一下,看着神情恍惚的付杰开起了玩笑:“付杰,你小子是不是看上那个郑好了,一见钟情啊!你可劝住点自己的痴心妄想,我那发小儿自己已不简单,老子更不简单,我们从小住一个大院,他爹是我爹的老上级。你没听他刚才说,郑好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下个月就要结婚嘛。”
付杰凄惨地一笑:“我知道我是谁,不过看见郑好,想起一个人。那个人可没她的命好,本来能考上大学,可阴错阳差总是考不成。”
他问同学:“你那发小儿是哪个大学的?”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
付杰心中甚是感慨,付萍果然把郑好送到了北京。付杰那年寒假回家的时候,特意绕道北京,专程去了一趟北京对外经贸学院。几经周折,付杰找到了郑好的一个同乡。没错,郑好的老家就是姐姐说的那个叫下马塔的小县城,也就是说,郑好肯定是付萍替考的那个人。真相终于在付杰的心里大白了。怪不得能替考,原来付萍和郑好她们是一对双胞胎。
付杰从北京回太原的路上,心情沉重,一点也没有完成任务后的释怀,看来,谜底原比他和付萍想的复杂。之所以他有一个亲姐,而不是两个,付杰能想到的思路是郑好出生不久后,就被父母送人了,后来父母为了弥补他们把郑好送人的愧疚,才让付萍去替她高考。付杰觉得在告诉付萍真相之前,必须先征得母亲的同意,因为对母亲来说,付萍和郑好,手心手背都是肉。
付杰提着行李,直接去了母亲工作的医院。他直截了当地问母亲:“我是不是有两个姐姐?付萍是不是双胞胎?”母亲吃惊地看着付杰。付杰任性地又喊了一声:“妈。”这一声“妈”让母亲放心了,看来付杰知道的并不多。母亲镇定地回答:“不要胡说,这话和我说说还行,千万不能和你姐瞎说。”就像父亲从来不打骂付萍一样,母亲也从来都是由着付杰。付杰习惯了在母亲面前的任性,他固执地追问母亲:“妈,你和我说,是,还是不是?”
“不是。你快回家休息,妈还要上班。”
付杰没心思休息,他拖着行李来到了付萍的食堂,母亲的态度让他生气,他偏要把这一切告诉付萍。当付杰突然出现在七八米宽的大面案前时,穿着白围裙的付萍举着两只面手,细长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她想拉付杰的手或者拍拍弟弟的肩膀,可因为手上沾着面粉,什么都做不了,付萍只是憨憨地笑着说:“付杰,你回来了,是不是没拿家门钥匙,你吃饭没,快坐到外面凳子上,姐给你打点饭。要不,先喝口热水。”
看着兴奋得满地打转却不知做什么才好的付萍,尤其是她那满脸没有修饰的憨笑,付杰突然决定忘掉那个机场里和眼前这张相同的面孔,他不能让郑好的浅笑伤害或打击到付萍的憨笑,母亲说得对,不能和姐姐瞎说。世界上长得一样的人多着呢,但能处处让着他,这么疼他的姐姐就付萍一个。付杰眼睛一湿,决定放弃考研。他和付萍说:“姐,我是专门来告诉你,你准备明年的高考吧,我一毕业就分回太原,你去考大学。”
付萍愣了一下,赶紧高声把话岔开,她怕同事听到付杰说的话。她已经把弟弟保送研究生的事说出去了,弟弟是她在同事中最大的骄傲。至于付杰让她考大学,那是不可能的,妈怎么舍得放她走。这没影的事,让同事听到不好,别人会说她好高骛远,不安心工作。付萍着急地摇着两只沾满面粉的双手,用胳膊肘把付杰推了出去:“付杰,有话咱回家再说。”
那天晚上,付萍和付杰又像在高中时一样,面对面地争论了一夜。付杰劝付萍:“姐,你能考,过了年你才二十二岁,补习几年的同学也有你这么大的。”
“不是我年龄大与小的问题,我说的是你的问题,你保送了研究生不上就是半途而废。这不是小时候分苹果吃,你有一个,我就得有一个。你知道姐,就算再好的东西,姐也愿意都给了你。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说好的读研,怎么能说变就变?你是不是怕妈不供你?姐供,只要你能上,你上到博士,姐都供。”
在另一个屋子织毛衣的母亲,听见付杰让付萍明年再考大学,心想:这个付杰,上了几年大学也没长大,想起一出是一出。我可不要儿子来管,我还怕受儿媳的气呢。就算你能孝顺我,可谁敢保进门的儿媳是个什么样的人。想到未来的儿媳,母亲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新的想法。
付杰说得对,郑好就是她的女儿,二十多年前,她生下付萍和郑好这对双胞胎一年后就和前夫离婚了,她带走了大郑好三分钟的付萍,不为什么,就因为付萍那时比郑好能闹病,付萍那时叫郑萍。她改嫁给付杰的爸爸后,付萍才又随了付杰他爸的姓。
让姐姐付萍替妹妹郑好考,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郑好在继母手里太受制,她这个亲妈听一次就哭一次。高考前,前夫找上门来,想让付萍替郑好考,郑好学习不如付萍,只有付萍替考才能保证把郑好送到外地的大学,远离继母。母亲当时没多想就同意了。谁也没长后眼,谁能想到第二年,付杰的父亲,好端端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付杰虽说不是她生的,但却是老付家留下的唯一的根。为付杰念书的事,老付活着时没少操心,现在,老付走了,她这个做后母的能让付萍去考、付杰不考吗?
为此,母亲一直觉得亏欠着付萍,可一直也想不出个补救的办法,现在见他们姐弟俩都能这样为对方想,就有了把他们一辈子拴在一起的心思,反正纸里包不住火。看来付杰已经知道了付萍和郑好的身世,不然,他不会家也不回就去问她。孩子们都大了,有些事瞒是瞒不住的,还不如她这个当妈的早为他们拿了主意。这样不但拴住了付萍,就是付杰飞得再远也会飞回自己的身边。她进老付家的门时,付萍一岁八个月,付杰才七个多月,起先,两个孩子一起吃她的奶,一边一个,后来付萍断了奶后,付杰吃到五岁上学才断的奶。如果付杰能做她的女婿,真的比付萍找了任何一个毛头小伙子都称她的心。
有一天,母亲趁付杰不在,把付萍又叫到跟前,这次,她没有打毛衣,她几乎是趴在付萍的耳边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听母亲要让自己和付杰亲上加亲,结为夫妻,还有前面说得一大堆乱七八糟,付萍呆住了。“妈,这怎么可能,根本就不可能,简直是天方夜谭。”她目光呆呆地看着母亲,完全被母亲过去的突然复杂化搞晕了,她觉得母亲不应该离过婚,那个黑馒头男人也不应该是她亲爸,付杰也不应该还有一个死了的亲妈,她不想让自己和付杰有这么乱麻一团的家庭背景。
付萍一直觉得她们家是单纯而美满的,一个亲妈,一个亲爸,还有一对亲生的姐弟,这就是她成长的家。就是父亲走了,这个家依然有三个最亲的亲人支撑着,温暖而坚固。现在,母亲用真相打碎了它的坚固,它像玻璃做的房子一样不堪一击,说倒就倒,变成一堆特别容易伤人的碎玻璃碴儿,付萍的思绪在这堆碎玻璃碴儿中小心地躲来躲去。
她想起了小的时候她牵着付杰的手和院里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藏猫猫,付杰胆小,总是要和姐姐藏到一处,而游戏规则是各藏各的,为这,小伙伴们几次不带他们姐弟俩玩。后来,付萍就自己不玩,让付杰跟他们玩,她把付杰藏好后,她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给付杰站岗放哨。想到付杰的胆小,付萍觉得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一地的碎玻璃碴儿扎到弟弟,如果不告诉他,这个家就是缺了父亲这个角,其他三个角在他心目中也会永远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
母亲老了,她得提醒母亲,能不说的就永远不要说。知道得多,痛苦就多。付萍问母亲:“妈,小杰知道这些吗?”
“妈怎么会傻到先和他讲,你毕竟是妈亲生的。”
“那就千万别和小杰讲。”付萍说,“就像你不让我问你郑好的事一样,我们永远也不要再提过去的事了。如果小杰知道,你不是他的亲妈,我也不是她的亲姐姐,那小杰会受不了的,他在这个世界上,岂不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付萍想起埋了父亲那天,小杰哭着和她说:“姐,从此我们就光有亲妈,没有亲爸了。”这句话让付萍多会儿想起来,多会儿就会像刀割一样的心痛。她和母亲表态:“付杰永远是我的亲弟弟。”
亲姐弟怎么能谈婚论嫁呢。母亲后悔不应该和付萍说这些,如果她不说,付萍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过去。付萍的亲爸虽说还在,但那个厉害的继母,郑好都不让多管,更不会让前夫认付萍。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是收不回来了,好在付萍大了,母亲相信付萍的本性,不会为此小看自己的。
先不说母亲怎么想,单说付萍听了母亲让她嫁付杰的提议后,见了付杰心里总有点别扭,倒是付杰姐长姐短的,以前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大年初五那天晚上,付杰从同学家玩回来后,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装苹果的大纸箱子,付萍边帮着往下解,边说:“小杰,大正月的,没见你给人家带东西去,回来时,倒要人家这么一大箱苹果,多贵啊!”
“姐,你还没打开看,里面不是苹果,是我给你带回来的书,她妹去年高考用过的,在他床底下摆的,我都给你借回来了,连参考书都有。”
听弟弟这么说,付萍一把拽住绑箱子的绳子说:“那就不要往开解了,你给人家送回去,我不考。说好的,你考研,怎么能说变就变呢?”
春节过后,正月十四那天,付杰要回学校了。付萍领着一个陌生的小伙子来家里帮付杰扛东西。去火车站的路上,付杰有意走得很慢,付萍以为他走不动,停下来等他,付杰指着走在前面帮自己扛包的人,小声问付萍:“姐,你不是处对象了吧,他可是个厨子啊。”付萍打断他的话:“付杰,别这样说,姐又是什么呢?他是个不错的厨子,别看他是我们食堂掌勺的二厨,但都说他炒的菜比大厨炒的好吃。”
为了让母亲彻底死心,也为了让付杰能安心读研究生,付萍执意要嫁给比自己大六岁的厨子。母亲见女儿找了个厨子,虽然心里有点失落,可看着这个小伙子憨厚老实,一米八的个头,不胖不瘦,人也长得挺好,虽说比付萍大了六岁,但母亲知道付萍的心,付萍就是不想等。母亲是个明白人,她转而又劝付萍:谈婚论嫁讲究个门当户对,虽说你心气高,但蒸馒头的找个炒菜的,也算般配。只有般配了,你日后才不会受他的制。付萍点头。
母亲还是亲自己的,母亲想让她嫁付杰,不全是为了母亲的养老,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好,女人谁不想找个比自己高的。可就是打死付萍,她也不能找付杰,不说从姐弟关系一下转变成夫妻关系,付萍先就拧不过来这个别扭劲,更主要的是,那样对付杰也太不公平了,倒像是她们母女合起伙来欺负他这个没亲爹亲娘的孩子。付杰一个正牌大学的大学生,凭什么要娶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做饭的她,就因为她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付杰吗?付萍当初让付杰去高考,自己顶班,一半是因为母亲愿意自己留下,另一半就是自己打心眼里愿意弟弟好。在她心里,自己永远是付杰的亲姐姐。
付萍和二厨的婚礼,定在了那年的八月十九日,专挑了付杰放暑假能回来的月份。婚礼就在付萍他们食堂办,主持人也就地取材,请了爱热闹的食堂管理员,因为两位新人都是自己食堂的人,管理员就存心要拿这两个孩子起起哄。面对众多来宾,管理员学着神父的口气,问胸前戴着大红花的新郎:“范厨师先生,你愿意娶我们美丽的馒头西施付小姐为妻吗?”
二厨一脸茫然,他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捅管理员的胳膊,着急地问:“领导,你没告过我要问这啊?”管理员不理他,故意对着话筒大声说:“请新郎范厨师先生当众回答我的问题。”
说完,就把话筒放在二厨面前,二厨脸红脖子粗,本来新穿一身蓝色的毛料中山装就够不自在了,现在更被管理员耍弄得急出一头汗来,这又不是在教堂,他又不是洋人,让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愿意”三个字,他可说不出口,最后,他对着话筒含糊地表态:“凑合吧。”
声音虽小,但有话筒扩音,台下的人还是听见了,大家先是一愣,后又捧腹大笑。管理员也在笑声中,换成了嘻嘻哈哈的腔调,转而又去逗身着大红套裙的付萍:“美丽的馒头西施付小姐,你愿意嫁给我们食堂最能干的范厨师、范先生吗?”
付萍想说,我愿意,本来就是她愿意的嘛。可是,她和身旁的新郎一样,面对这么多熟悉的亲戚、朋友、同事,她也不好意思说“我愿意”。付萍想了想,说:“将就吧。”
付萍的回答再一次把来参加婚礼的人都笑翻了,只有付杰没笑。想起郑好,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觉得他和郑好,都是有福气的人,这辈子,他们都摊上了一个好姐姐。虽然付杰不清楚郑好和付萍到底谁大,但他希望是付萍大,这样,他的心里好过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