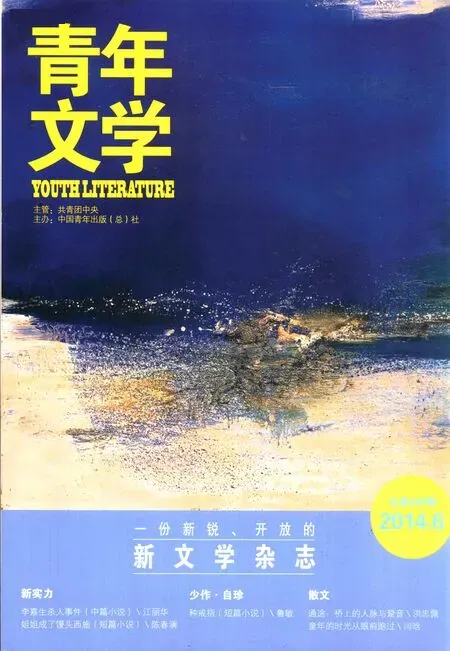种戒指
文/鲁 敏 [短篇小说]
【作品】
秋季,棉花收获,玉米收获,花生收获。而我们麦子、特立独行的麦子,还只是一粒粒野心勃勃的种子。老女人高高举起手播撒,从她光秃秃的指间,我们坠落进懒洋洋的大地。
播撒的老女人步调踉跄,因为她有一双小脚,她曾经以此为资本,骄傲地嫁进了家境殷实的男方。可是,正因为有家有产有吃有穿,现在她成了一个典型性的大富农,人人喊打。所有的贫下中农们,人家都可以在墙上贴忠字、刷红色标语,但她家的门楣与窗棂,屈辱地空空荡荡。不仅如此,就在昨天,两袋烟工夫,她家所有的绸缎衣裳、珠花簪子、绞银手镯、镂金耳环、洋大头,全都被抄走啦,哈哈,听说那是她从结婚后就开始攒的,打算留给孙子孙女们的……瞧,这老女人多会打如意算盘,多会过日子似的,可算来算去,全没啦。

鲁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江苏东台,现居南京。曾荣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奖、中国小说双年奖等。出版作品《纸醉》《取景器》《伴宴》《惹尘埃》《六人晚餐》《九种忧伤》《此情无法投递》等十二部。有作品被译为德、法、俄、日、英、西班牙、意大利等文。
我听到老女人突然瘫下来,烂面条似的,她滚到地上,捂着嘴巴翻着身子叫唤:我的簪子、我的手镯、我的耳环、我的洋大头哪……
她的眼泪鼻涕和成一团流畅地淌下来,一直淌到泥土里,淌到我们身上。哭吧滚吧,哦呀,多么舒服,一撮黑土,一把眼泪,秋风软软,这正是我们萌芽期最中意的养分。
——十月下地,三月抽穗,五月收割,六月燃秸。麦子的一生,连头带尾,九个多月,跟人类在子宫里黑乎乎的时光差不多,大地上仅有的时光,从绿油油到金灿灿,轻轻地随风摇摆,沉甸甸地相互亲吻。这一茬麦子的所见所闻,有着你意想不到的荒唐与精彩。
当第一阵冬风从我们头顶的电线杆边打着呼哨穿过,我们冒出的绿芽儿就从星星之火进入燎原之势了。
我知道,老女人有一床绿色缎子的被面,被抄掉了,可是现在,看看我们,真要比她的被面子漂亮多了!从浅绿到深绿,从毛茸茸到肉嘟嘟,我们这样的绿,是肥厚而结实的绿,替整个大地都盖上一层绿缎面被子啦!多么浪漫主义!
可老女人不满意,还是整天哭哭啼啼的,为她失去的宝贝们哭泣,每走到一个房间,想到这房里曾经有过什么,而现在,又失去什么,她便开始抽咽,还像打摆子似的浑身发颤,这真令人烦躁,连她男人都受不了啦。他从前不曾打过女人,可当他发现家中竟然连一床像样的棉被都找不到时,第一阵冬风里,他对老女人举起了巴掌,像贫农那样,粗暴地打起了女人。
“死女人,我叫你嚎丧!我叫你嚎丧!”打了一会儿,老男人举到半空的胳膊突然停住,接着拐了个弯,接二连三地给自己扇起了巴掌,“打死你这作孽的东西!”
这家的年轻女人,也就是小媳妇啦,可能不喜欢听到扇巴掌的动静,她悄悄捂着嘴巴跑出来,跑到田边,跑到我们身边,这才迫不及待张开她的樱桃小嘴,“哇”的一大口,吐出一团尚未消化的饭食,哇,哇,她接着又吐了两小口。
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吃惊,接连一个星期,几乎每顿饭之后,她都要跑到我们这里,朝我们的头面上吐出她刚刚吃过的饭菜。白白黄黄,拖着长长的黏液,我觉得有些恶心,兄弟们倒是习以为常,他们说:这就跟猫屎、鸟粪差不多,挺滋润的。
听到媳妇的吊呕声,老女人突然一抬手,挡住老男人仍在空中挥动的巴掌:“等一下再打,让我听听她的呕吐声。你知道吗,我一听就知道,是肚子坏了,还是肚子有了。我还能听出来,是男的,还是女的。”
老女人神秘地竖起耳朵,瞧瞧,真是封建流毒!还这么重男轻女。
“去,儿子,去看看。”
这家的年轻男人一向有些愚笨,在老女人的催促下,他慢吞吞地追出来,没轻没重地拍着小媳妇的背:你,是有了吧。
都是你干的好事。小媳妇脸红起来,把男人的手拉近她的腹部,这真是非常俗套的画面。
但是,等一等。有了?有了!
像听到严厉的口令,所有的麦子一齐掉转头去,盯着她依然平坦的肚皮。这么说,当我们成熟、当我们变成面粉、当我们做成饺子皮,他们就会新添上一小口人丁啦。
哦,新鲜童子尿、奶香大便,有兄弟遗憾而羡慕地叹口气,我们下一茬麦子可真赶上好时候了!
不必怨天尤人,我们这一茬的运气也不算太赖。最起码,晚上很热闹!
你知道,那些连绵不断、纵横交叉的电线杆们,像富有气势的巨形蜘蛛网。每到深更半夜,这蜘蛛网便会突然抖动起来,电流声咝咝响起,接着,是喇叭里一个亢奋而疲惫的声调:各位社员请注意,立即集合,立即到大社场集合,传达毛主席最高指示!传达最高指示!
电线杆的颤抖开始传染给大地,我们能听得一清二楚,在突然的一激灵之后,各家各户床铺下面的麦秸秆们开始相互摩擦,发出睡意犹存的窸窣之声,这些麦秸秆,通常就是我们前一茬或前两茬的兄弟。人们喜欢用麦秸秆铺床,漫漫长夜,瘦骨嶙峋的身体紧紧贴着我们试图取暖。
在大喇叭的一声紧过一声的催促声中,他们开始起床,摸索着把腿伸向冰凉的裤子,用手抓一抓头发,忙不迭地就冲到屋外,生怕落在旁人后面,人们在黑暗中奔跑,惊骇的指头偶尔相触。
多么美妙的夜晚,为了抄近路,无数双脚踏入麦田,从我们身上践踏过去。——别替我心疼,你们难道不知道,贴着地面的麦子是最不怕踩的,越踩我们越会长得快、长得绿、长得肥。啊,太舒坦啦,那些泥巴鞋,高一脚低一脚,纷乱地,仓促地,像小鼓点一样敲打,像拳头一样按摩,踩一下,我们就挺一下,一边快活地呻吟,真是无与伦比的享受!
最高指示?那是什么,我们不管,但真的,请来得再多一些吧,最好每天,都让他们在黑暗中慌乱地一路小跑,在我们的身上富有节奏地踩踏……
社场上,人群慢慢地聚拢在一起,煤气灯照得大家的脸色分外白净。最高指示还没到,人们就像我们麦子一样,沉默地站得整整齐齐,先朝主席像深深地鞠躬,接着齐声背诵此前接到的各条语录,一边暗中整理扣错的纽扣或穿反的鞋子……有人自作聪明地在年轻男人耳边解释:最高指示,正在从北京出发,一级一级,一级一级,走楼梯一样,正往下面走……
年轻男人无心关心那从北京楼梯一直走下来的“最高指示”,他把手悄悄地放到小媳妇已经微凸的肚皮上,试图传递某种安慰与鼓励,哦,真可笑,他以为他的手是无所不能的电线杆吗?没有用的,年轻女人正在大口喘气,两眼绝望地上翻,徒劳地想要抑制突然涌上的呕吐感。
当喇叭里突然宣布最高指示已到,她终于一张嘴巴,吐出晚饭所吃的红薯稀饭,薄而透明的汁液在煤气灯下变得五颜六色,穿过所有社员的头顶,一直抵达黑洞洞的大喇叭,形成一个极其优美的弧线。
彩虹。
我对旁边的麦子耳语,它立刻心领神会,把关于这一奇景的定义交头接耳地传达下去。太美了,我们这一茬真赶上了个好时光。
有一天夜里,最高指示传达完毕,人们乌鸦般慢慢散开,有人打出半个哈欠,又小心地用手接住,要把剩下的半个带回被窝。漆黑的夜,走动的人群没有影子,像是一把图钉,一枚一枚地向前移动,每到一处黑黝黝的房屋,就有几个人停下,悄无声息地进去。
而老女人,跟着家里人进了屋之后没多久,等到四周鼾声响起,她又重新拉开门出来了!这真奇怪,我们几乎全被惊醒:她想干什么?
老女人走路的样子非常奇怪,好像屁眼里插了根棍子。她一扭一扭地向我们走来,走到我们中间。十二月的麦田,板寸头一样,庄严肃穆,暗中妖娆。
她一路走一路扭着头东张西望,没关系,没有人,全都跟死猪一样睡着呢,除了我们麦子,没有人看见你,你只要告诉我们:你想干什么?
老女人不说,她伶仃的小脚从田埂边开始丈量:一步、两步……八步。
换一个方向,这下我们懂了,所有的麦子都张开小嘴,优美地齐声合唱:一步、两步……八步。
这样,从东往西八步,从南往北八步,两个八步的交界处,黑咕隆咚当中,老女人从怀里摸出一把小铁铲,开始挖洞,她的手抖抖索索,几个兄弟由此遭殃,被挖得身首异处。
挖洞做什么?麦子们疑惑地交头接耳,难道,今天晚上所传达的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给了她什么特别的灵感?
嘘,别急,往下看嘛,我真不喜欢兄弟们这种沉不住气的模样,好像什么世面都没见过似的。
瞧瞧,好戏才刚刚开始:挖完洞,那老女人开始解裤子。
看上去,她要小解了?这太不符合逻辑了,她床头,不就有个红漆的陪嫁马桶吗?算了,不管那么多,这不是可以白看一下女人屁股嘛!众小麦一个个美美地张开嘴巴,准备迎接热乎乎的甘霖,像是漫长冬夜当中的一小份夜宵。
但是,不,情况有变化。——屁股是看到了,却没有夜宵。老女人的大腿紧张地绷着,接着,从私处,她掏出一个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小手绢。
哦!我知道了!天哪,世界上所有的麦子,没有哪株会有我聪明!
我知道了,她准是想在地点种下点什么!就跟当初高扬着手撒麦种一样,她是来种什么东西了!那小手绢里包着的一定是什么稀罕种子。
果然,在把小手绢包袱放进洞中的最后一瞬,老女人停住了,她犹犹豫豫地打开手绢,打开一层,还有一层。
我趁机迅速地瞥了一眼,在两层手绢中间:妈呀,是两枚金戒指,黄灿灿的!把整个黑洞洞的麦田都要照亮了似的。瞧瞧吧,这个富农老女人,还真狡猾呀,家里都抄成那样了,竟然还给她藏下两枚金戒指!
老女人嘴中念念有词:土地老爷,这是我家最后的东西了,是我们的结婚戒指,家里怕放不住,你替我先收着,等过了这阵,我再来讨还……土地老爷呀,我没别的指望,一是留住这两枚戒指,另一个呢……是让我抱个孙子!
这是什么话!这个时候,还在念叨孙子,太可笑了。再说,她怎么单单就把戒指托付给土地爷呢,把我们麦子当什么了?白吃白喝吗?明明埋在我们身子下面,将来要靠我们关照的,却招呼都不跟我们打一个,反去跟那八竿子打不着的土地爷作揖,这算怎么回事?
我们激动得窃窃私语继而大吵大闹,欲表忠心,要替她做守卫,但她毫不理会,只低头默默地把手绢放进洞里,然后又忙活着把土重新填平,并找到那几株早夭兄弟的残骸,把地面粉饰一番,最终才摸着黑走了。
现在,她走路很轻松,不扭屁股了,当然,我们也不再目送她了。说实话,她真让我们生气。
哼,种戒指,还要抱孙子,她想得可真美。
小媳妇的肚子慢慢大起来,她的呕吐症状自动消失,反之,她变成了一个胃口太好的女人。每天下午,晚饭还遥遥无期着呢,凛冽的寒风中,她会跑到田里转来转去,像逛商店那样,眼睛四处滴溜溜地打量,但这个时候,能打量到什么呢?她看看我们绿绿的秆子,眼光失望,甚至暗含怨恨,这真让我们百思不解,我们哪里得罪她了?
当她的眼光流转到田埂边上,那说不上漂亮的眼里突然又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几乎是情意绵绵了,她艰难地蹲下去,两只脚难看地往外叉开,大肚皮快要坠到地上,她不管不顾,用手飞快地往深处拨弄,指甲里很快塞满泥土,裤管上全是泥灰,但最终,她手里多了一块瘦瘦的白萝卜!或者,被铲去半块的红薯!
这就算是伟大的收获吗?瞧瞧她那轻浮劲儿!小媳妇像是胜利者一样扫了我们一眼,一路咯吱咯吱地啃着就回去了。
哎呀,就算是孕妇又怎么样呢,她真缺乏常识,真目光短浅,等着吧,等到那天,她会明白的,比之那些粗俗的红薯与萝卜,我们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冬去春来。我们现在开始蹿个子了,挤挤挨挨,比肩接踵,有些发育早的家伙甚至暗中抽起了青涩的穗子,软绵绵的穗芒像是婴儿的胎毛,弯曲着一点点舒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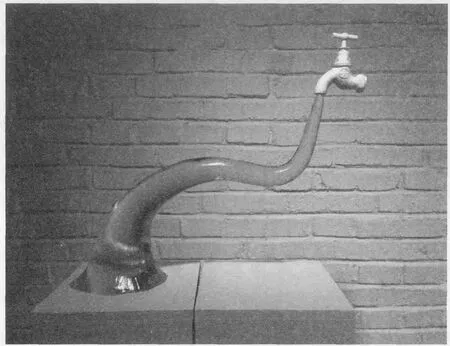
玻璃是纯净的、通透的,如凝固的水。当“玻”从水龙头里流出,驻留的不仅是时间,更是那份纯净之美。名称:随“玻”驻留作者:黄喆材料:玻璃种戒指
而这时,玉米呀、油菜呀、芝麻呀、蚕豆呀,万生万物都在四周直喘粗气,眉来眼去地日生夜长。每年的春天都这样,整个大地都春情勃发,拼命勾引着男女老少,扑到它的怀抱去吮吸浓稠的乳汁。
但这几年情形有点不同,人们似乎不像从前那样钟情于大地了,他们总在成群结队地忙着别的,拿着小红本背诵,往身上别金灿灿的像章,在胳膊上缠红色的布条,对着一张画像反反复复地早请示晚汇报。一到晚上,还聚集到社场的大谷仓里开大会开小会。其中的一些倒霉蛋,比如,老男人老女人,作为村子里最标准的富农,总会被拖出来万夫所指、千人唾面,他们被牛车拉着,头像夜晚的向日葵那样垂到地上,后面跟着一大群人,敲盆击罐,蔚为壮观。
老女人的日子很不好过,她的家与院子,都被抄家的人掘地三尺,翻得都可以撒种子长粮食了,戒指呢?你的金戒指呢?人们指着她大声质问。
她的头被压到裤裆里,但我们可以瞧见,她那满脸的鼻涕眼泪里,竟然还有一丝小小的得意呢。是啊,她一定是想着她种在我们麦地里的那两枚金戒指,嘿,她准以为自己聪明极了!
天气终于捂燥起来,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好的日子。
雨水一阵一阵,我们巧夺豪取,争抢着吮吸水分与肥料。
烈日一阵一阵,我们随之转绿变黄,芒刺在一夜之间变得坚硬刺人。
热风一阵一阵,我们翻滚着此起彼伏,像满腹心思的人,千言万语无法开口。
收割季节几乎是掐着指头就要来了,“麦子争青打满仓,谷子争青少打粮”,有急性的人开始磨起镰刀,月光下,镰刀反射出寒凉的光。这光,一下刺到老女人的眼了,半夜里,她两条腿都抽起筋来,弯缩得像烧熟的虾子。
挑了一个月色模糊的夜晚,老女人开始绕着我们转圈子,像杂耍演员走场子似的,转了不知多少圈,把我们的眼睛都看花了。转什么呢?哦,明白了,现在的我们,长高、长大了呀,她的小脚没法踏进麦田,什么从东往西八步、从南往北八步。哈哈,她没法数了,她找不到地方了!我们咕咕咕笑得前俯后仰,这下可有热闹看了。那可爱的小花手绢儿呀!
老女人脸色白了又红,红了又白,脸上的肉一跳一跳,但她比我们想的要聪明一些。她的两只金莲忽然有了主意,健步如飞地奔到附近的河滩上,一下子拖来两根长长的竹子,平放在地上,分别在上面走了八步,做上记号,然后,力大无穷地把这两根竹子往我们头上交叉着一搭,大汗淋漓的老女人眯眼盯着两根竹子的会合处,抿着嘴笑起来:是了!
像一个初学游泳的人走在水中,她奋力把我们往两边拨开,我们头顶的芒刺一定弄得她又酥又痒,还沾了她一身的麦花儿,但她奋不顾身,坚定地一直走到两根竹子的交界处。然后,像母鸡那样庄重地蹲下来。
老女人开始向下挖去。这是收割季节的大地,泥土干燥而坚硬,我们的根部紧紧纠缠。——算了,一丝恻隐之心闪过心头,我跟兄弟们使使眼色,我们松开脚下的根,让她的双手得以顺利进入泥土,摸索那条美丽的花手绢儿。
像在水中取鱼,井中捞月。往东摸,往西摸。往南摸,往北摸。几乎把我们的根下都摸了个遍,她的手与胳膊,忽然像橡皮筋那样,拉得无限长了,我敢拿我的脑袋、也就是我的麦穗,跟你打赌,她已经摸到田埂的四边了,并且已摸到隔壁的田块,包括隔壁的隔壁,她无限拉长的胳膊已经摸遍这一整块麦田了。
但是,没有。她根本就摸不到那条美丽的花手绢儿了。
哦,我的土地爷呀,我的天老爷,我的阎王爷呀,快告诉我,我的戒指到哪儿去了……老女人口中胡乱念叨着,一迭声地追问,头几乎要把埋进地里去了。
瞧,她又把我们给忽视了,土地爷、天老爷、阎王爷都有份儿,她为什么就不能问问我们呢?她怎么就不动动脑筋呢?种下去的东西,怎么可能还在原地摸得到呢,它早生根发芽、破土而出、开花结果了呀,这个蠢女人!
咯咯咯,所有的麦子都笑得花枝乱颤,肚子发疼,但我们就不告诉她,谁叫她不问我们呢。老女人继续伏在麦田深处,像青蛙准备冬眠,她死命地贴近泥土,鼻子眼睛嘴唇上全都沾满泥灰,那笨拙的模样,真把我们逗乐了。
月光在我们的头顶慢慢移动,偶尔有云朵轻佻地飘过,这样的月色之下,美美睡上一觉会特别地养精神,谁都明白这个诀窍,尤其是快到收割期,这时的麦子,就像出嫁前一个月的娇娃娘,绝不能熬夜,否则,哪里来的精神气儿,哪里来的颗颗饱满……行了,睡吧,不能老这样盯着老女人吧,由她去挖吧,就算她真的变成青蛙也没关系,反正等天一亮,她就会回家去的,她会跟别人一样,把镰刀磨得亮亮的,再搽上一层油,等着最高潮的收割期。
真没想到呀,等我们重新睁开眼,一边伸懒腰一边睁开眼,那老女人还趴在我们中间呢。
难不成在麦地里睡了一夜?我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嗬!可真有趣儿,这老女人,浑身到处都挂着金戒指呢!她用我们的身体——麦秸秆,黄得恰到好处的麦秸秆,卷成了一个又一个金灿灿的戒指!想不到,老女人那个干瘪模样,居然还是心灵手巧的呢,瞧那些麦秸秆戒指,还真是像模像样呀。
哦呀,我们一下都激动极了、自豪极了,世界上,谁知道我们麦秸秆还会有这样奇妙的用场吗!真是太棒了,谢谢你,老女人,你虽然又老又丑,成分是富农,还这样愚蠢疯癫,可是,我们麦子是最讲良心的,好就是好,孬就是孬,这回子,我们谢谢你!
我们群情振奋,热泪盈眶,几乎是赏识地看着她。
老女人这个早晨看上去真不错,完全像一个成语:穿金戴银。她把戒指戴在大拇指上,戴在中指上,套在每一个脚趾上,还挂在胸襟的一排锁扣眼上,总之,我们看不到她了,我们满眼看到的都是耀眼的金戒指!
老女人也跟我们一样欣喜若狂,满身的戒指呀,她看了这个又看那个,爱不释手,心满意足:找到了,我找到了。
清晨的阳光有着蛋黄般的柔和色调,温情脉脉地照着老女人。
可能正是在那些麦秸戒指的挑逗下,我们一下子完全成熟了,硬硬的芒尖有的开始脱落,而高天上,却极不配合地开始布满乌云,远处传来雷声隆隆,这可不得了,“麦收有三怕:雹砸、雨淋、大风刮”,人们一下子紧张起来,把红宝书与红袖章暂且放到一边,所有的镰刀在当天就开始出生入死,咔咔咔地把我们齐脖子斩断。
——不,我们一点不疼,我们乐意着呢,我们个个儿都伸长脖子在等待这个瞬间,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记住的纪念日。
哎呀,如果麦子也会喝酒、也能喝酒,而不是被人们酿成酒,我们真该喝点美酒才好!真该喝得酩酊大醉才好。风光的日子就要来啦,收割之后,经过脱粒与碾磨,我们会从木讷的麦穗一步一步变成亲切的白面,变成各种吃食,人们会用充满感情的语气提到我们,用含情脉脉的目光注视我们,会黑天白夜地惦记我们,会用牙齿与舌头颠来倒去地亲吻我们,我们会变成全世界的宠儿。
老女人一开始也是下地的,但她一下地就用麦秸秆折戒指,折得满地都是,被人们在脚下踩来踩去,她见了,就要鬼哭狼嚎地叫:戒指,我的戒指!
搞什么名堂?这不是混工分吗!人们就把她拖回去,让她跟小媳妇儿待在一块儿,那小媳妇,肚子正大着呢,人却越发地伶仃,像瓜秧上结了个硕大的冬瓜,她整天嚷饿,老鼠似的,总在家里四处翻箱倒柜。老女人却是熟视无睹不闻不问,只小心地抱着她的一团戒指,像老猫衔着新生的小猫,神情诡异地东躲西藏,每隔一会儿,就张罗着替戒指们另换一个隐蔽的地方,真十分忙碌了。
收割后的大地,像癞子头,深一块浅一块,难看极了,幸好还有麦秸秆——我们留在大地上的下半身,干燥柔软,体态轻巧,妇女们一把一把地弯腰收拾,散发汗味的乳房反复地垂向大地,那无力而无知的风情,令我们百看不厌。
现在,麦秸秆们被堆成一个又一个的圆形麦垛,带着稍尖的顶点,像大团大团的新鲜牛粪,在初夏的晚风中散发出令人馋涎欲滴的干草香。妇女们一边擦汗一边抬头欣赏麦秸堆,脸上留下道道褐色印迹,她们浑然不觉,只笑嘻嘻地嘲弄老女人:瞧瞧,这些麦秸秆,能给她做多少戒指呀,够全世界的女人戴了!
但那成为笑料的老女人现在不做戒指了。要知道,她终于学会动脑筋了,她现在想明白了,她埋下去的戒指,跟麦种子一样,结戒指了:那两只戒指,在泥地下的那些日夜里,它们先是像冰一样化成水,又像水一样变成气,然后,慢慢从地里升出来,升到半空,升到我们的麦穗里,长成一串一串,躲在麦穗里。等到碾磨脱壳时再恢复原形,重见天日,她会收获到像麦粒一样无穷多的戒指。
这完美的推理给了老女人以强大的动力,她天天坐在大队社场上,没日没夜地盯着我们被割下来的麦穗,盯着从脱粒机里出来的麦粒,盯着麦粒压碎后变成的面与糠……她那样目不转睛、一丝不苟地看着我们,像看着性感的男人,把我们从衣冠楚楚看到赤身裸体,从镇定自若看到面红耳赤。哦,你信不信,我们被她看的!哦,太刺激了,太高潮了。
有人认为这疯婆子大概是要搞破坏,也有人认为她可能是饿坏了,总之,为了让她远离伟大的革命生产成果,或者,是出于对她疯癫的歉疚,有人称了几斤白面,记到她家账上,把她给打发回去了。
就在这里面吗?戒指就在这里面吗?老女人大声地扭过头询问,人们不理她,只管用力地把她往家里拖,像拖一个不省人事的醉汉子。
哦!白面!
脸色萎黄的小媳妇老远看到老女人,一下子伶俐地站起来,好像她肚子里面装的只是气球,而不是一个快要足月的婴儿。她两只泪水涟涟的眼睛忽然学会了拐弯,老女人走到哪里,她的眼光就拐到哪里,老女人在屋子里绕来绕去,她的眼光也就绕来绕去地织成了一张花纹精美的薄地毯。
小媳妇,你这会子该识货了吧,跟你常吃的那些瓜呀豆的比一比,它们算什么?看看我们,看看这又白嫩又细腻的面,多么高级!绝对精华!冬去春回,披星戴月,迎风纳雨,饮露食霜,我们是白白受苦的吗?我们图的还能是别的吗?
小媳妇真聪明,她一下子明白我们的意思了,瞧瞧她的眼睛,她看到的不仅是白面,还看到了白面的七十二变,烙饼、馒头、花卷、饺子、面疙瘩、面耳朵……哦呀,全在空中飘来飘去,像下起了一场白花花的漫天大雹子。
老女人拎着面粉袋,左三步右五步,前两步后六步,像蜜蜂在跳它们谜语般的舞蹈,她跌跌撞撞,寻寻觅觅,真真假假,最终成功地摆脱掉小媳妇视线的跟踪。在茅房后找到一小块不为人知的空地,黑黝黝的泥土上,除了虫子与苍蝇,除了落叶与狗尾巴草,再没有眼睛盯着她了。
好极了,老女人兜底提起袋子,把面粉一股脑全都倒到泥地上,细细地一层层翻寻拨弄。“我的戒指呢,我的戒指呢,你们快出来呀。”
黑的土,白的面,在老女人双手的揉弄下,慢慢的,那一小块地,成了混沌而富贵的灰色,叶片与草籽点缀其间,像是精心设计过的斑斓图案。
真长见识呀,这老女人,她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奇妙的旅程,这样,当我们从种子变成面粉,竟又可以与大地重逢了。如此富有创意的结局,对麦子王国来说,前不见故人后不见来者。哇哈哈,真是躬逢其盛,何其幸也!
突然,我们听到一声尖厉的叫声,几乎要划破所有人的耳膜。我知道,那是小媳妇的声音,看来,她会拐弯的目光终于找到老女人了,并为眼前奇异的画面所震撼。
这声尖叫,像是一根迅速燃烧的炮仗引子,它引爆了小媳妇的大肚子,一汪清亮的羊水几乎应声而出,顺着小媳妇的裤管流淌下来。仓促之中,有人抓起一大把麦秸秆往小媳妇身下塞去,天哪!羊水,我们小心翼翼地凑近了闻闻,发现它散发出麦芽糖一样甜津津的味道,这是个好兆头,会有喜讯从天而降的!
一些妇女开始进进出出地奔忙,小媳妇继续尖叫,一边涕泪交流,不知是想念那些消失在泥土中的面粉,还是为她腹部持续的绞痛。年轻男人和老男人都从地里赶回来了,家中人满为患,厨房里,我们被塞进灶膛,变成粉红色的火焰舔着锅底,热烫烫的开水咕嘟嘟沸腾起来。
老女人天真无邪地在一边袖手旁观,眼珠在每个人的脸上搜寻破绽,偶尔小声嘟囔一句:我的戒指……那许多戒指,肯定都被你们收割了去,在你们的白面里,你们吃面条时会卡到,吃馒头时会咬到,吃花卷里会呛到……
小媳妇单调漫长的号叫,突然在高音处戛然止住,像悬崖勒马,她四周的女人们却一齐闹哄哄地叫唤起来:好了,出来了,是个小子,瘦小子!
消息被一层层往外传,外面地上蹲着的老男人与年轻男人站起来,木讷地重复:是小子,瘦小子!
满地乱跑的儿童们拍起手无意识地叫喊:是小子,瘦小子!
老女人抬起她红肿的眼睛,鹦鹉学舌般也跟着嘟囔:是小子,瘦小子!
突然,她的小脚快速地挪动起来,双臂有力地拨开那些忙得披头散发的婆娘,一直冲到小媳妇跟前,在小媳妇疲惫张开的双腿间,她看到了那湿漉漉的粉红肉团,等不及旁人阻挡,老女人手疾眼快,一把伸过手去,没轻没重地拎起来,在蜷曲着的下肢间,她看到了男婴的小雀雀。
哦!老天爷呀!我抱孙子了!
老女人忽然间两眼清澈,像水洗过的天空,她稳当当地抱起肉团,重新拨开人群,像冲过千军万马,一直冲到灶膛。她跪到地上,捧起一大捧最黄最松的麦秸秆,富有技巧地拼命揉弄,把我们的身体揉得绵软而芬芳,然后,才小心翼翼地,爱怜地,喜悦地,擦拭起男婴身上的黏液与血水,一边口齿清晰地大声吩咐呆立着的众人:去,熬红糖粥,去,染红鸡蛋!去,扯红棉布!
众人这才如雕塑般复活,僵硬地四处走散,却见老女人不知从何处掏出一个最为精巧的麦秸秆戒指,努力地噘着嘴巴,跷着不成样子的兰花指,把它套在男婴的小雀雀上,大小刚刚好。
(二〇〇七年)
【作家自述】
那些饥饿的夜晚
那时候晚上总在写小说,不上网、不微博、不视频、不饭局、不夜生活。——那时候的晚上就是写小说。
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挑三拣四。像个仆人一样,脾气好极了,只要能写,只要有个故事,有个想法,哪怕只是一个小白线头,就使劲地抽出来,要做成一件覆盖天地的大衣服。总像被命令指定了一样的,坐在电脑前,两眼雪亮地写个没完没了。写成什么样都面带傻笑,那时候是个快活的饿孩子,能吃多少就写多少,写多少就吃多少。
现在胖了,讲究了,挑剔了,这个不想写,那个不值得写,这个没有审美创造,那个有主题缺陷,这个太轻巧,那个又太装。胃口越来越可悲越来越艰难了。
有人怀念年轻与貌美。有人怀念强壮与性欲。不,我只怀念那死去的饥饿感。但这并不代表饥饿时期的产品就一定是好的,就像你在饥饿时让你眼馋并流口水的那些东西。回看早期的东西,总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有的发作太过,有的空无附依。但它们是必须存在的,必须捏造和蒸煮出来的,而且可能还卖不出去,前一天晚上我们自己做出来,第二天晚上又是自己把它们给吞下去。
《种戒指》一看就是那种跑动之中的写作,急迫而充沛,手势夸大地颠来倒去,尽可能变着花样。这是畅意也肆意的写作。小说发出来,像一粒激动的石子进入不激动的湖面。它沉入了,伴随着制造与诞生的那些夜晚一起沉入和死去了。
能有这样的机会,再把这石子捞出来,湿漉漉地打量一番。好。哪怕随后,它仍旧会被扔进湖底,扔回那些饥饿的夜晚。
赏 析: 弋 舟
《种戒指》写于二〇〇七年,距今七年的光景,长吗?似乎不,但也算不得短了。令我惊讶的是,在这样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里,一个饥肠辘辘的写作者,便会有了厌食终日的危机。鲁敏的自述写得惊心动魄,如果说我们这个栏目试图能够对初学写作者有所启迪,那么,她的这个自述便不啻为一堂优质的文学课。在这里,鲁敏几乎是在赞美写作之事最初的那份颟顸与恣肆,那份不知餍足、吞吐万象的胃口,让人觉得即便面对的是块石头,你也会不管不顾地扑上去先咬一口再说。鲁敏给这个状态找到了“饥饿”这个词,那么是的,如果你也有志于写作,你现在感到“饥饿”了吗?
这个短篇,恰恰写的也是“饥饿”。当满地的作物扎根于纸上,我们感到的却是弥漫的、闹腾的“饥馑”。这就是小说艺术不可或缺的那种张力,指东打西,影射比附,它能够以丰盈来诉说贫瘠,以富足来讲述匮乏。对于荒诞的着力捕捉,从来是现代小说的强项,鲁敏在七年前就已经深谙此道,她瞄准的那个年代,恰是铺陈荒诞的沃土,她以作物的态度扎根其上,辅以“生殖”这样的砝码,粗鲁乃至粗鄙地于沃土之上野蛮书写,实在是元气充沛。不错,找准地界,明确态度,懂得加码,善于放大,就有可能写出一个漂亮的短篇。
小说中麦秸秆扎成的那些戒指,令这个短篇霎时散发出金灿灿的光芒,此为小说家在“种戒指”这个意象之下的第一个炫技。结束时,小说家让一枚麦秸秆戒指套上了婴儿的小雀雀,这一笔,不啻是鉴定一个小说家想象力的根本性标志,由此,鲁敏完美地证明了她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的能力。——在炫技的背面,抵达了更为苛刻的艺术准则;那就是,除了炫技之外,她还有情怀令沸腾的一切归于安宁。
在我看来,是否能够和紧张的世界达成某种更高的谅解,才是衡量一个小说家的最终标尺。
这个短篇令我兴奋,我甚至想问问鲁敏:她干吗不让那个初生婴儿的小雀雀上,从娘胎里便套上那枚灿若黄金的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