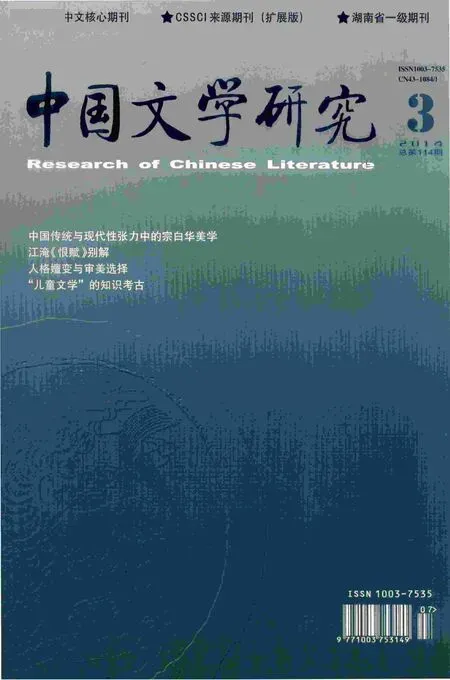论古典诗学中的内外辩证及尊古传统:以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序》“古淡”论为例
何 跞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1)
诗学的发展总会有一定的规律和原理,受其影响往往会产生一些普遍的批评现象,用以衡量诗歌的高下优劣,中国古代的诗歌及诗学批评也不例外。在中国古典诗学中,这些原理包括诗歌艺术中的思想情感内容和语言形式各自的内部有着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而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又会产生内外之间的辩证关系,还有在面对古代诗歌时因陌生化原理和文化认同而产生的尊崇古人,甚至将古作经典化的尊古现象。它们有时候同时体现于一种诗学表述中,以看起来感性模糊而内涵意义却十分丰富的一个风格范畴囊括了诸多诗学原理,如“古淡”。元代方回所编的《瀛奎律髓》是一部选诗评诗的诗学著作,体现了他自己在对待和学习前人之诗时的诗学观点和扬弃取向。清代纪昀作《瀛奎律髓刊误》,对其中某些问题进行了批驳,并在《刊误序》中首先谈到其“矫语古淡”的问题。纪昀对这个小问题的论辩,却折射了诗学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古淡”这一诗学上的风格范畴,本身含有矛盾和辩证统一的关系,而这种辩证统一关系的核心则是诗学的内外关系,它贯穿于诗歌创作及整个的诗学发展演变过程中,并生发出关于尊古的命题。
一、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序》“古淡”论中的矛盾及辩证统一
诗学批评中往往存在一种辩证统一的矛盾,由此引起关于诗美程度、价值高低和肯否褒贬的诗学评议及论争。清代纪昀在《瀛奎律髓刊误序》中有关于“古淡”的一段论辩,即体现了诗论中的这种矛盾及辩证统一。他说:
一曰矫语古淡……夫古质无如汉氏,冲淡莫过陶公。然而抒写性情,取裁风雅,朴而实绮,清而实腴。下逮王、孟、储、韦,典型具在。虚谷乃以生硬为高格,以枯槁为老境,以鄙俚粗率为牙龈,名为尊奉工部,而工
部之精神面目,迥相左也。是可以为古淡乎?古淡是一种颇具褒义色彩的诗歌风格,甚至被标为“高格”“老境”。按纪昀论诗之意,古淡即为一种“高格”与“老境”。“高格”指诗歌立意之崇高、尚大和审美之高雅;而“老境”是诗歌艺境之流丽成熟,它们都是基于整体上的优劣高低及稚熟衡量,对诗歌给予的一种较高评价。纪昀言“夫古质无如汉氏,冲淡莫过陶公”,他将“古淡”分析来论,“古”即“古质”,“淡”即“冲淡”,前者主“质”,后者主“冲淡”,且尊汉诗为“古”,陶诗为“淡”,极力褒扬“古淡”诗风。
纪昀接着解释汉、陶高出众诗之因,即其“抒写性情,取裁风雅”能“朴而实绮,清而实腴”,这其中就有一种辩证的矛盾。“朴”“绮”言诗歌艺术的色感,如人之服饰朴实或绮丽;“清”“腴”指形感,如人之形体清瘦或丰腴。“朴”与“绮”,“清”与“腴”本是对立矛盾的。“朴”“清”是指诗歌语言,其句词形式及语辞内容的朴质及清简。而这外在的诗歌语言整体所表达的诗歌意向、意境,其所代表的作者精神状态和他的意志取向,却是丰“腴”而“绮”丽的。因为诗人有一股饱满的热情,一种性情中人的诗性热情,随之而来的则是人情本身所具有的自然自发之美,以及人情之善的美感,其诗作则是包孕了美与善的自然自发的真实诗情之曝露。纵然他的创作意图中可能添加了矫情或者功利的机心,但其所写之情却是真实的人情,也就是人之常情,因而也具有真善美的意味。这就使得其诗作也如同人物实体一样,赋有色彩之“绮”与形态之“腴”。因而被纪昀隐含地标为“高格”“老境”的“古淡”实际就是“朴而实绮,清而实腴”,是融合了两种矛盾对立的风格的。而这样的矛盾之所以能融合在诗歌的整体中,是因为一方所主的是诗歌外在的文学形态,一方所主的却是诗歌内含的精神境界。内外的风格虽然不一,甚至迥然相异,互相矛盾,却能融合统一于诗歌艺术的整体之中,而取得一种很高的艺术成就,形成一种典范诗风,这就是诗歌中内外矛盾的辩证统一。
另外,此处“古淡”被析为“古质”“冲淡”。“质”则宜“朴”,“淡”而会“清”。同时,“质”言质地,有充实的质容,所以“质”本可以容“绮”。“淡”言味道与清浊之形象,“淡”品诸味,“清”照众形,因而“淡”亦可以照“腴”。所以,“朴”“绮”和“清”“腴”这两对矛盾最后还是辩证地统一到“质”“淡”概念中,形成“古淡”的诗歌风格。
而以“古”替“质”,则是因上古初民之诗往往有质淡的特点。古时初民的情感具有浓郁的自然真切和自发的意味,甚至脱离了创作机心。这种情感具有人情本身的自然之美和人情之善,因而能达到诗的真善美高度,成就一种诗美的典范,也即是“高格”“老境”。然因初民之诗往往缺乏语言技巧,也无华丽的意象入诗,即景兴情,口语成诗,不假雕饰,因而在外则如人之形貌,色“朴”而态“清”,在内却如人之精神,浓郁之状“绮”而且“腴”。
古人之诗往往因为内“绮”“腴”外“朴”“清”而呈现出“古淡”清朴之象,后世诗作继承其外形而忽略其内质者则流为纪昀所言的“生硬”“枯槁”“鄙俚”,形神皆“淡”,因而为诗家所批。只有外在的刻板模拟,而无内在的精神传接,则“朴”“质”将入“生硬”,“清”“淡”应入“枯槁”“鄙俚”,是无变化,亦无辩证的统一。同样都尚“古淡”,同样都本于“古淡”内在“朴”“清”的特点,“汉氏”、“陶诗”及“杜工部”之诗能转而“实绮”“实腴”,方回(即虚谷)却循而“生硬”“枯槁”“鄙俚”,因而为纪昀所批,谓其为“矫语古淡”,即非真古淡。这其中的原因纪昀其实也说清了,因为“汉氏”“陶公”能“抒写性情”“取裁风雅”,而方回却与“工部之精神面目”“迥相左也”,其实就是失了“性情”“精神”和“风雅”。
二、诗学中矛盾和辩证统一的核心——内外关系
在上面对关乎优劣评判的诗歌风格及其矛盾统一特点的分析中,其实有一个决定性的关键因素在里面,那就是关于内外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内容和形式之别,也即诗情与诗形之辨。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是诗歌美学的一条核心的原理。在内需要深致的情感、思想、意志,需要诗人精神内容的丰厚,诗歌情思意境的丰实,总之是文学内容的丰腴;而外在的语言形式,也即载情之体则可以多种多样。
1.内在诗情的矛盾统一
这其中有不变与变的区分。先谈内在,不变者为诗情的充实存在。诗情可以是多样的思想感情、多种体悟和意旨,然必须要是自然深致的,浅薄的或者说没有情思意志体悟的则不行。内在诗情的浓淡深浅往往决定诗歌的境界高下,韵味浅深,并成为诗歌优劣评判的一个标准。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元好问《颖亭留别》“白鸟悠悠下,寒烟淡淡飞”,简单的诗语外形,用语自然,内在却悠然自得,看上去是一种淡然的诗情境界。然这种淡然并非真的诗歌情悟之淡,诗感之薄,而是悠然恬淡情绪的一种浓烈生发,是一种融情于物的整体感悟的高级呈现,体现了以人的意识在意念中融汇感悟自然物象的力度和深度,因而能成为一种很高的诗歌境界。在其背后其实隐含并融合了作者基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及对物事肯否评判和爱憎倾向,对自己所喜所爱者的执着认同和深致情感,这些都是诗人情悟境界的基本组成部分。“白鸟悠悠下”看似无情绪,实际却有着大情绪,蕴涵了作者深在的崇尚自然高雅、厌弃世俗的趣尚,其心境的恬淡,以及对自然的亲近体悟之深。决定其境界高下的诗情包括情绪、心态、感觉、观念、意志等,以及其程度的深浅。这些形而上的内在诗情必须要在诗作中存在,而且要充实丰厚,这就是诗学中不变的原则。而诗情的腴实程度,与诗歌境界的高低及鉴赏的优劣高下,则成正比。这反映在诗学批评中则是情志高下之别,意境高下之分,优劣之争,最后甚至归于人品高低之议。《文心雕龙·风骨》就论到:“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总之,关于内在的诗情,不变的是它在诗作中的必需存在,而变的则是其深厚程度和多样的内容。
2.外在诗形的矛盾统一
关于外在的诗形,也有变与不变之分。变者是其多样的形态,不变的则是形式多样背后所遵循的一定的诗学审美原理。诗形多样包括诗体样式、篇幅结构、平仄押韵、语词排布,以及诗歌语词所指示的独体意象和整体境界的不同。纪昀所谈到的“响字之说”,其所批方回的“每篇标举一联,每句标举一字”及“后来纤仄之学”“刻镂锁事以为巧,捃摭异字以为异”,都是局限于诗歌语词形式的翻新变化。其说见下:
其选诗之大弊有三:一曰矫语古淡,一曰标题句眼,一曰好尚生新……
“朱华冒绿池”,始见子建;“悠然见南山”,亦曰渊明。响字之说,古人不废。暨乎唐代,锻炼弥工,然其兴象之深微,寄托之高远,则固别有在也。虚谷置其本原而拈其末节,每篇标举一联,每句标举一字,将率天下人而致力于是,所谓温柔敦厚之旨,蔑如也;所谓“文外曲致,思表纤旨”,亦茫如也。后来纤仄之学,非虚谷阶之厉也耶?赞皇论文,谓譬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人生境遇不同,寄托各异。心灵浚发,其变无穷。初不必刻镂琐事以为巧,捃摭僻字以为异也。
虚谷以长江、武功一派,标为写景之宗。一虫一鱼,一草一木,规规然摹其性情,写其形状,务求为前人所未道,而按以作诗之意,则不必相涉也。《骚》《雅》之本旨,果若是耶?是皆江西一派先入为主、变本加厉,遂偏驳而不知返也。
而注重诗歌语词所指示的内容的,则如“一虫一鱼,一草一木,规规然摹其性情,写其形状,务求为前人所未道。”需要说明的是,纪昀对这两种都进行了批判,称前者为“标题句眼”,后者为“好尚生新”。然对“标题句眼”,其所批的并非诗人注重诗歌的语词形式,而是他们刻意关注于诗形而忽略了诗歌的情志内容,是“置其本源而拈其末节”,致使“温柔敦厚之旨,蔑如也”,“文外曲致,思表纤旨,亦茫如也”,只注意诗歌外形之变,而忽视了诗歌内在因“人生境遇”而起的“寄托各异”和“心灵浚发”的“其变无穷”。而“古人不废”的“响字之说”,却能有“兴象之深微,寄托之高远”,所以“暨乎唐代”的“锻炼弥工”能成就其艺术高峰,为纪昀所赞。对“好尚生新”,其所批的也并非追求新的语词物象本身,而是在此过程中失去了“作诗之意”,使其“不必相涉也”,是形式对内容的“先入为主,变本加厉”。这都是诗人过分追求诗形的多样翻新而忽略诗歌内在情志的消极艺术效应,也恰好证明了诗歌形式多样的本质。另外,诗形多变现象背后也有一定的美学规则束缚,并非杂乱无章的变化,也非任何形式的语言都可以组合成为诗歌,成为艺术,这就是外在诗形的不变的因素。明代竟陵派一味追求“幽深孤峭”,在语言上走向极端,而被清代诗家如钱谦益斥为“诗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岳归堂集》提要云:“天门钟惺更标举光新幽冷之词,与元春相倡和,评点《诗归》,流布天下,相率而趋纤仄。有明一代之诗,遂至是而极弊,论者比之诗妖,非过刻也。”清代末期民国初年的诗人受西学的影响,以西方语词,甚至英语入诗,为中国传统诗家所深恶痛绝。如黄遵宪《伦敦大雾行》以中国的旧体诗写西方建筑,以西方的物事语词入旧体诗,也只是作为一种诗学变革的现象,印迹在诗学发展的历史中,标示着旧体诗向新诗的过渡,而并不具有多高的艺术价值。“诗界革命”也并没有真正改变旧体诗的原本写法,只是引发促进了新诗体式的诞生。中国传统的旧体诗有其本来的诗学规律和原则,太过地超出其写作范式,就不成为旧体诗歌了,而变质为另一种诗歌样式,不在中国古典诗学的讨论范畴之内了。总之,我们讨论的中国传统诗歌,也即旧体诗,其诗形的多样性是在其自身范畴内,遵循传统规则和审美规范的多样。
3.内外之间的辩证关系
内在诗情需要深厚的存在但因人而异,因为人心非一,所历不同,情志相别,体悟亦相异;而外在诗形可以多变但也要遵循一定的诗学审美规律。诗情与诗形各自形成一个矛盾着的辩证统一体。
而内外之间又存在一个大的辩证关系。从整体上将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诗情与诗形作一个比较,则发现内不主变,外则主变。因而在宏观的整体感悟式的诗论中,诗歌内在的情志差别往往被忽略,而以笼统的“言志”“缘情”“载情”为不变的准的。而外在诗形的定则,或者说不变的因素亦被淡化,其差异则为人们大力论争,而形成风格、派别之争,如宋代“江西派”“江湖派”,明代“公安派”“竟陵派”,其差异多体现于文字风格。内不变而外变,这又是一种矛盾着的辩证统一关系。其实“内”“外”这两个概念本身就包含有不变与变的意义取向,它们本身即有辩证的因子在其中。内者为实质、核心、精神,往往不变;而外者则为表象、外在、形态,必然是多种多样。在内如此,在外非然,内情腴实饱满,而外形清朴多样,然它们统一于诗歌之内,这就是一种辩证的矛盾。这种内外的辩证关系普遍地影响了诗学中的优劣评判,往往形成一种包含“而”字转折的辩证诗评。上面所举纪昀诗论“朴而实绮,清而实腴”就是如此。另外如《文心雕龙》中《物色》篇言“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凡摛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隐秀》篇言“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亦同此理。说明一点,辩证的诗学批评普遍存在,而其实质大多还是关于内外诗情与诗形的,因为内外两个范畴本身就构成一种辩证的矛盾关系。宋代江西诗派讲求“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明代公安派袁宏道兄弟提出“性灵”论,讲“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些诗论主张的核心还是关于语言形式和诗歌内容辩证统一的问题。
具体到风格论上,内在诗情需要丰实,这是不变的;而外在可以绮腴,也可以清朴,这是变化多样的。因而在诗学中就形成一种普遍的批评倾向,即强调诗情,表述为“温柔敦厚之旨”、“汉魏风骨”、“寄托”、“独抒性灵”,凡是没能蕴涵情志的,则予批判。如诗语绮丽香艳,诗情亦无深致,甚至为文造情的作品,常常沦为下品。在诗情腴实的前提下,诗形的风格则大致分别两路,一向朴实,二向绮丽,诗人和诗论家各从所好,互相论辩。有内实而外清者,“古淡”之风即其代表;有内外皆腴实者,如唐诗“兴象玲珑”“不可凑泊”,也是一种艺术的很高境界。说明一点,诗歌由古诗的古淡到唐诗的“兴象玲珑”、“寄托深远”,其实体现了载情之具的由粗略到精致的发展,而诗歌语言形式本身也必然经历由朴到绮的先后过程,后人学古复古,而且提倡古淡之风,实际又是对绮丽诗风的一种反拨。朴绮并无优劣之分,然却有出现的先后之序。
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内在腴实外形清朴的风格比较常见,这就形成一种普遍的辩证的诗论。在许多关乎诗歌风格优劣的品评中,其风格实质有一个“而”字转折的往往是优秀的诗歌。因为“而”字将诗歌外在的朴简转折到内在的充腴上,最后还是符合“言志”“缘情”“寄托”“风骨”的基本要求。另外,外在诗形的清简朴实更能衬托出内在诗情的丰腴充实,这跟以有限之言以盛无限之情的艺术效果是一样的,精简浓缩的往往会更加具有感染人的艺术力量。有着矛盾而内外辩证统一的,即外“朴”而内“腴”者,往往是“高格”,予以肯定;而内外皆承接为一种风格的,具体说就是外“朴”内无物者,则通常流为下者,被予批判。纪昀论中“朴”“清”风格分别走向“实绮”“实腴”和“生硬”“枯槁”“鄙俚”即说明了这个问题。后者未能领会“古淡”的实质内容,只承袭了“朴”“清”表象,而内质都失,最后反而走向了其不好的极端,变成了“生硬”“鄙俚”。
三、中国古典诗学的尊古传统
从横向的学理视角来分析,“汉”、“陶”及“杜”诗能融合矛盾风格之两端,为真正“生硬”“枯槁”“鄙俚”之诗,也即外形朴简而内在无物的诗通向内外皆实之诗的一个中间状态。而以纵向的历史眼光来看,它也是上古某些诗歌(或者说口语)向唐代玲珑大象、美轮美奂之诗的一种过渡。说明一点,上古一些诗作其实大多可能只是口语,在当时并不为诗,只因后人尊崇古作才名之为诗,而在当时人眼中并不具有后人所论的诗美,后人所欣赏的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陌生感、文化积淀和历史崇仰。这就涉及到一个传统的诗学论题,即尊古的论题。
中国历代的诗学论争中都或隐或显地存在复古与反古的问题。而这个论争首先是因后代之诗、诗人与诗学都是接续前代而来。先有历史前后,承接关系,然后才会有学古、崇古、复古的问题,才会有反其潮流而动的反古。贯穿这个过程的,很明显其实还是一个重视古人之诗与诗学的问题,并在历史先后承接的事实中必然存在着。后人对古人和古人之诗,及古人之诗学,必然有一个面对的过程。不管是学习模仿,还是批判吸收,或是对话论争,甚至全盘否定,都是一个提上议程而不可回避的问题。后人即使能回避言古,却也在事实上回避不了受古人之诗与诗学的历史濡染的事实。而正是这个由历史先后顺序决定了的先存在后被影响的关系事实,决定了古者的先在地位和历史影响。它必然先就存在,必然影响后人,因而不论承认与否,肯定还是否定,复古还是反古,后代的学者与诗人们都在意识深处认可其先在的历史存在和地位,这就是一种潜意识的重视古者,表现出来就是一种尊古传统。其实反古现象正是尊古思想存在的有力明证,它是尊古风潮过盛而引起的一种反弹。尊古传统影响于诗学就产生了人们对诗的预定审美,以至于“古”成为褒义词,成为一种大的诗学审美范畴,甚至成为一种涵容多样诗风的特殊风格。这种预审美、预评判其实包含了两方面的美学原理:一是陌生化效应,二是文化审美效应,这是因久远历史酝酿和文化积淀附着而产生的。两者都是关乎审美心理的。
其实上古之诗并非就是诗歌美学的最高标的。美的疆域是多样且无限的,美的标准,审美的眼光、心理、心态也是不一的。最美和完美往往是人们带着一定的审美心态,对符合美的规律的美的对象的自主拟画和期许。古人之诗多是自然而出,因为语言技术的不成熟不发达而显得简朴稚拙,在当时受众和评诗人的眼中,或许就是当时语境下的一种“生硬”、“枯槁”、“鄙俚”。如载于东汉赵晔所编《吴越春秋·越歌》的上古《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另如上古《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其中多用“兮”字。《诗经·郑风》中《野有蔓草》篇“清扬婉兮”用“兮”字。屈原《离骚》则大量使用“兮”字。“兮”可能本为当时的口语和语气词,如现代汉语中的“啊”“呀”,但在后来,“兮”被文言化、诗化,附着上浓厚的文化意味,而成为一种古雅的雅辞。它被专门用于诗中,用以增强诗的古雅之气,甚至因之而形成一种专门的诗歌体裁,即以“兮”字为标志的骚体诗。而《离骚》本是屈原诉说和抒情之语,在当时可能相当于郭沫若《天狗》、《站在地球边上放号》一类激情荡发之作,然而除了其深巨的情志内容,却也因对后人来说相对陌生的“兮”这样单字古辞的语言样式,逐渐被美化,被尊尚,而成为骚体诗之尊。这就是一种由陌生和距离带来的诗美,而其中还带有文化审美因素的推动和刺激。古诗中的人、物、地名,这些实际的历史存在经过积淀之后,往往会附着上某种审美色彩。如“燕赵”具有慷慨悲凉之感,“秦汉”具有古朴苍凉之意,“巢由”具有隐逸高古之味,这与典故的效应是一样的。而除开诗歌中这些名物实词所带有的文化意味,诗的语辞本身和语辞样式也有文化审美的因子。如上面所论的“兮”字,在后代就标示古雅。而带有“兮”字的句式本身,也具有古雅之气。另外如《诗经》的四言句式,其用词的方式顺序,如用“有美一人”,而非“有一美人”,还有其连绵双音,重章叠唱的诗歌结构,无不标征着“温柔敦厚”的风雅色彩。再者,诗人本身在历史的传承中往往也被附着上文化的意味。如屈原是忠君爱国的典范,标示一种传统精神,其“香草美人”的笔法也成为诗歌的传统而赋有文化意味。李白是飞扬自由精神的代表,杜甫是忧国忧民的典范。而提到陶渊明则会联想到隐逸自然,提到萧纲萧绎则是浓艳流丽。文化的承接带来一种在该文化影响圈内的普遍认同,这种认同在接触诗歌之前就已经存在,这种预认同总是会引起后人对前人之诗潜在的预价值判断和预审美。
因为人们对上古社会现实及上古语辞的历史陌生感,以及古代社会经过历史积淀后而产生的厚重文化意味,或者说因为后人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文化情感,古诗人和诗歌具有了高出当下的意味而被后人所 尊奉。这就是诗学中尊尚古制的传统及其原因,这种尊古传统是基于审美的心理效应之上的。
综上,“古淡”这一感性浑大的诗学命题,其中隐含了诗学中一些基本而重大的问题。古淡之“古”征示了诗学中的尊古传统。而古淡之“淡”不是一般的淡,而是有着丰实涵容,这又体现了诗学中一种普遍的矛盾及其辩证统一关系,其背后又触及到核心的关于诗艺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古淡”作为一种诗歌风格,是内在深厚而外在朴质素淡的,它可以作为有着内实外虚辩证特点的诗风的代表和典范。比如《二十四诗品》中所言的“冲淡”“洗炼”“含蓄”“清奇”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古淡”除了内含深致情思外,还有着历史的意味,因而在淡的形式之下,更有着“古”的内容,包括因古的陌生和文化而带来的多种意指和厚重韵味。一“古”一“淡”皆体现了诗歌美学中的一些核心规律和原理,“古”“淡”结合形成一种审美范畴和美学风格,自然就有其丰富的内涵。因而“古淡”最终成为诗人们所学习追崇的一种诗美典范,成为众诗家所推崇并标高的一种风格境界,被给予很高的评价。
〔1〕(清)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序〔A〕.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孟二冬.陶渊明集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3〕(金)元好问.元好问全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范文谰.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宋)李昉、徐铉等.太平御览〔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汉)刘向.说苑〔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