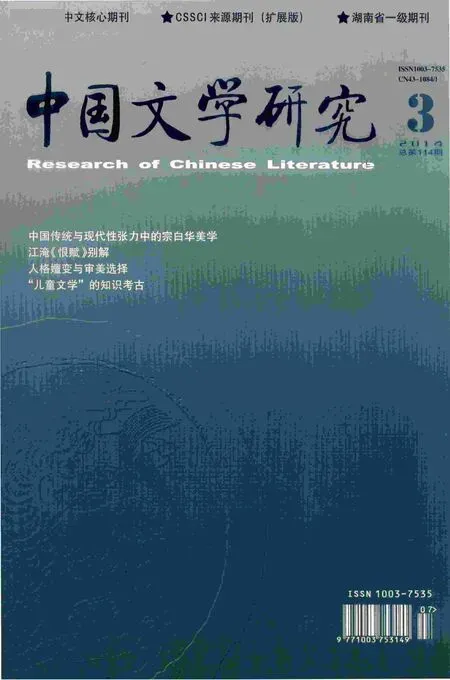《雅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
厉盼盼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圣经是人类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经典,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雅歌》素有“歌中之歌”之美誉,堪称圣经文学中独放异彩的奇葩。《雅歌》通过它的审美价值取向、情感表达方式,影响到中国现代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等诸多方面,从而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异质资源。与之相应,深受《雅歌》影响的一系列诗歌的出现,极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从而产生了民族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交融的景象。从目前笔者收集的资料来看,业已发表的一些论文和专著主要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同程度上涉及到《雅歌》,却存在着明显不足,尤其是中国现代诗歌对《雅歌》的接受与过滤方面的相关研究比较滞后,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和深化的可能性。
一
《雅歌》在中国深受青睐,究其原因,不仅因其文本自身的独特魅力,也和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雅歌》毫不避讳身体的魅力对恋人的吸引,诗行中不加掩饰地欣赏、赞美着人体的每一部分肌肤之姿,歌颂美的态度不是将灵与肉全然分开,而是在肉的描写中贯通了观念的、精神的东西,使世俗之爱带上了神圣的品质,“他所以成他的伟大,因为他是出于内心燃烧着的真挚的情感,和生命力的热情的行动。”《雅歌》里田园牧歌似的生活不能不令新时期的新青年心驰神往,伊甸园般浪漫的爱情故事更令他们羡慕不已,当读到“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歌8:7)的诗句时,不能不引起情感的共鸣。周作人认为这是“真挚的男女关系的极致”,朱维之也认为《雅歌》“在写恋情的诗歌方面,全部古代诗作无出其右者,对于两性爱情表现的大胆,对于两性肉体美描写的露骨,比东西方古代的诗作都超过了”。沫沙甚至感慨道:“这样朴素,美丽,热情的恋歌拿我国诗经中的风和雅相比,绝不会比任何一首弱;而比我们后来诗词中的情诗,却要泼辣生动得多。然而“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者更是没有。”在《雅歌》中,女性不是人类罪恶产生的根源,不是劣等的“第二性”,更不是孤苦的单相思,而是沉浸在“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歌2:16)的和谐幸福生活中,因此,“《雅歌》是对《创世记》2-3章的注解,失落的伊甸园在《雅歌》中又重新得到了”。
《雅歌》有着原始艺术的纯真和不加雕琢的天然情调,这种顽强、热烈,甚至赤裸的生命力和情欲正是返璞归真的心理状态的展现,对此,郭沫若欣赏不已。郭沫若一生写了许多热情洋溢、大胆直露的作品,他说:“恋爱,是人生之花,是自有生以来迄未来永劫,永不凋谢之花,所以歌颂恋爱的诗,也是永不腐灭,永有生命的诗。一部新约可以烧毁,只有所罗门的雅歌是不能烧毁的。一部五经三传可以抹杀,只有国风之诗是不能抹杀的。他们是植根人性之最深部,不到人类灭绝,歌颂恋爱之诗是不能绝种。”他仿照《雅歌》写了一首缠绵悱恻的情诗,即:这首被无数人引用又屡受抵毁的名诗——Venus8〕(P93):
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着一个酒杯。/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会使我时常沉醉。/我把你这对乳头,/比成着两座坟墓。/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
诗人写这首诗时正值他与日本姑娘安娜热恋之际,诗歌对爱情的热烈表白,对恋人身体直接大胆的描写,想象奇特,构思精巧。“爱与酒杯”化用了《雅歌》中的“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歌1:2)以及“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口如上好的酒”(歌7:2-9)的意象。郭沫若受《雅歌》的启发,把“乳房与坟墓”组合在一起,联想十分丰富,是对“我要往没药山和乳香岗去,直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歌4:6)一句的精心镶嵌与巧妙移植。新诗对身体叙述的第一次高潮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身体与精神密不可分,身体的革命与思想的解放、个性的张扬紧密相连,对身体的大胆描述包含对旧道德、旧观念、旧传统的反叛。许多人对爱情的大胆真挚的表达,无疑是对传统旧道德的冲击,而直接描写被传统道德框定为“非礼勿视”的身体,在当时更是惊世骇俗。这首诗写于1916年,后收入作者第一部也是代表性的诗集《女神》(1921年出版),可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新诗的可喜收获。
在《雅歌》中,现实世界各种迷人的景色构成了诗歌的主旋律,给诗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诗行的字面意义(现实世界)和比喻意义(诗性世界)在彼此的转换中得到不断强化。迷人的爱情故事丰富了诗歌的内容,从而使意象形式与爱情故事充满了张力,形成诗性世界与真实世界的互动,令诗歌呈现出动态的审美特征。《雅歌》新奇的语言及浪漫的叙事风格,吸引了众多诗人的模仿,章衣萍谈及《雅歌》对自己的影响时说:“我最爱读圣经中的《雅歌》,于是不知不觉地做了许多小诗,自己觉得思想与形式全变了,但这些小诗现在是不能刊出来的,因为中国现在正是‘法利赛’人得意的时代。”
《雅歌》“是希伯来抒情诗发展的顶峰,是一束鲜艳的奇葩”,“其清词丽句像新倒出的香膏,比醇酒还香甜。”诗人黎焚熏以“《雅歌》——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为正副标题,诗歌写道:
我说,阿秀,你的眼睛真好看,这么大,这么亮。我把你的眼睛比作窗,或者是一幅镶着金边古国暗绿的风景画,走在其中觉得很忧郁……春天里,百花盛放,草木滋长,我们的苦难的生命,也该有着它新的光彩,和新的历程啊!那些多情的花朵,斑鸠的悦耳的鸣,和香馥的流水的笑声……阿秀,到田野里去吧!到那神秘的灌木林里去,让我告诉你一点爱情和春季的秘密,还要给你说一个有趣的故事。
顿呼(Apostrophe)是对不在场的第三者直接发出呼语,表达出强烈的感情,以激起读者的共鸣。这种修辞格在《雅歌》中出现的频率极高,而且贯穿始终。诗人黎焚熏巧妙地借鉴了《雅歌》中的顿呼修辞手段,描绘出恋人之间深厚的感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诗人与恋人一起到田野里,到林丛中去,像倾听大自然一样倾听爱情,探寻爱情的真谛,一如《雅歌》里热恋的人儿深情的呼唤:“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歌7:11-12)。古往今来,虽然爱情的主角不同,但是对爱情的表达何其相似。
当然,对《雅歌》的喜爱与模仿本无可厚非,但是,像《关于爱》之类的诗:
关于爱我已无话可说/爱我的女子苦涩如耶路撒冷/我爱的女子香甜如黎巴嫩/她们何其遥远/她们何其遥远/我的爱人放下水罐离开了岸边/我的爱人赤脚而身子纯洁/她的眼睛如池边的鸽子/她的双乳像惊慌的小鹿/她们何其遥远/她们何其遥远
诗人不顾异质文化的差异性和国人审美心理,把恋人生硬地比喻为“耶路撒冷,黎巴嫩”,刻意模仿《雅歌》中的诗句“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歌5:15),“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歌5:4),不免有故作高深,过度修辞之嫌。且诗句“她的眼睛如池边的鸽子/她的双乳像惊慌的小鹿”袭用了《雅歌》中的诗句“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歌1:15),“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歌5:12),“你的两乳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歌4:1-5),“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歌7:3),无论诗歌意境还是遣词造句都落入了《雅歌》的窠臼,无非是拾人牙慧,当然谈不上创新了。
二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文学发展中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特殊政治文化语境对文学现象和作家心态的生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而形成时代语境与政治焦虑下的典型心态与人格命运。
艾青的诗歌以紧密结合现实、富于战斗精神的特点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又以精美创新的艺术风格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收获。诗歌《火把》描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的集体行动中受到教育、坚定革命信念的故事,既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又洋溢着浪漫主义激情。艾青承认:“《火把》中的‘一个声音在心里响’那一节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是从《旧约》中‘雅歌’里来的。”为了表现唐尼急切与恋人相见的复杂心情,《火把》第十二节,每一段都用“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开头,两段中间用“我举着火把来找你”一句来过渡,这种反复的句式,大大加强了抒情的气氛,其情节便受到了《雅歌》中苏拉密女寻找良人的启发。在若干年后,当艾青谈及《火把》时,仍对《雅歌》情有独钟,他说:“我这是受了《圣经》中《雅歌》的影响才这样写的。《雅歌》就是歌中之歌、最高级的歌的意思。”艾青在暮年参加了苏联第十三届青年联欢节晚会,当他看到公园里无数青年男女随乐尽情起舞时,热烈的气氛唤起了诗人年轻的心,趁着诗情的涌动,一口气写下了《写在彩色纸条上的诗》,该诗的副标题是:“为别人写的诗,为年轻的情人们写的诗”,并注明是“雅歌体”,可见艾青对《雅歌》的喜爱之情。
七月诗派诗人阿垅的诗歌《无题》用语克制,却撼人至深,完美体现了唐湜所言的“有生命的高突”。诗歌写道:
不要踏着露水——/因为有过人夜哭。……/哦,我底人啊,我记得极清楚,/在白鱼烛光里为你读过《雅歌》。/但是不要这样为我祷告,不要!/我无罪,我会赤裸着你这身体去见上帝……/但是不要计算星和星间的空间吧!/不要用光年;用万有引力,用相照的光。/要开做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诗歌以夜哭始,以凋谢终。“不要踏着露水——/因为有过人夜哭”,既渲染出一幅凄清的别离意境,又彰显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把出行路上的露水想象成离人的眼泪。诗人由此想起昔日在“白鱼烛光里”为爱人读《雅歌》的情形,沉浸在曾经幸福的回忆之中。《雅歌》所昭示的爱的力量与意义,早已净化了诗人的灵魂,诗人因对纯粹之爱的理解和彻悟,已进入一种内心坦荡光明的圣界,内心趋于一种极致的神性纯粹。因此,诗人坦然宣告:“但是不要这样为我祷告,不要!/我无罪,我会赤裸着你这身体去见上帝”。诗人自觉的批判意识和自省精神,充分彰显了可贵的文人风骨。“白色花”不仅是纯洁爱情忠贞不渝的象征,也是诗人洁白无瑕的品格的象征。全诗主题在此得以升华,充满了柔情与悲壮的色彩,不仅感情真挚厚重,而且风格也实现了隽永与炽热的统一,其内涵超出了情诗的范围,成为灵魂与人格的剖白。
诗歌不会拯救世界,但是诗歌能够迫使灵魂进入最后的逃避领域,能够肃清最后的残余,能够暴露灵魂的不完善,及其在充满罪和悲剧的世界之中的处境。绿原因胡风一案的牵连被投入秦城监狱,在漫长的囹圄生涯中,他并末沉沦倒下,而是在精神上保持着一种高贵的站立姿态,遂有了这首充满战斗力的名篇《又一名哥伦布》。绿原用诗歌语言雕塑了一位中国20世纪的思想探寻者——哥伦布形象。与历史上意气风发的哥伦布不同,他的出行没有欢呼和赞美,更没有鲜花和掌声,他被迫“告别了亲人/告别了人民,甚至/告别了人类”。与哥伦布更为不同的是,他的“圣玛丽娅”/不是一只船/而是四堵苍黄的粉墙/加上一抹夕阳和半轮灯光/……这个哥伦布形销骨立/蓬首垢面/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凝视着千变万化的天花板/漂流在时间的海洋上。诗人孤独地走在寂寞的时间之海、禁锢在黑暗封闭的牢狱之中,在无边无际的孤寂与沉默中,圣经是他唯一的寄托,《雅歌》中幸福的爱情是他永远的安慰也是永远的期望,诗人只能凭借想象力来穿透时空,以固执的理想抵御孤独,反抗绝望。诗歌采用对比的方式,以巧妙的构思,朴素的语言,表现了现实的悖谬和生存的苦难,体现了苦难中的坚守与诗性的超越。
诗人何其芳读到《雅歌》,想到了现实的无奈与苍茫,辗转难眠,于是有了《夜歌(二)》这首诗。诗歌以“我的身体睡着,我的心却醒着——《雅歌》”为题记,写道:而且我的脑子是一个开着的窗子,/而且我的思想,我的众多的云,/向我纷乱地飘来。诗人化用诗句“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歌5:2),以苏拉密女在爱情面前辗转难眠为喻,真实展现了自己在被改造的过程中,矛盾、困惑与追求激烈地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反映了一个走到革命队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诗人的思想转变过程。”诗人清醒地懂得一个真正文人所应该坚守的使命,文学对政治的依附必然带来文学主体性的丧失,在主流话语的大潮中自由主义文人必然要遭到边缘化的厄运。怎样在文学与政治间寻求一个平衡,诗人在这个困境中不断地痛苦挣扎,却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的途径,因此,这首诗是特定政治语境下人性蜕变的心灵文献。
三
海子是一位全力冲击文学与生命极限的诗人,他在山海关自戕时随身带着一本《新旧约全书》。他曾说:“圣书上卷是我的翅膀,无比明亮/有时像一个阴沉沉的今天/圣书下卷肮脏而欢乐/当然也是我受伤的翅膀/荒凉大地承受着更加荒凉的天空/我空荡荡的大地和天空/是上卷和下卷合成一本/的圣书,是我重又劈开的肢体/流着雨雪、泪水在二月”。海子有着浓厚的宗教情结,《雅歌》是他较为喜爱的篇章。作为“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与真理合一的大诗”的诗人,开放的诗学视野,使他的诗歌呈现出独特的美学特征,既包涵着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想象,又兼具更深层面的对人类生命终极价值与生存状态的形而上的思考。他在汲取东方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希伯来的异质文化因素,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意义和内涵,又扩大了读者的审美视域。
海子在诗坛的语言贡献,主要体现在神性语言与新奇意象两个方面,他的诗歌语言对实体的采撷与利用,为诗人膨胀的自我抒情找到了对应物,使自我一一分散于各个原始实体中,一起奏响生命的乐章。如《谣曲》:
你的树丛大而黑/你的辕马不安宁/你的嘴唇有野蜜……
南风吹木/吹出花果/我要亲你/花果咬破
“圣经诗歌有两种最常见的结构,一是意象、概念、主题借助于一系列诗句实现的不断强化的运动;二是一种叙述运动,最常见诸于隐喻性行为的发展过程中,亦可涉及某些文字事件。”因此,“如果只是按照字面来解读这些意象,既无法读懂这些诗歌运用的隐喻手法,更无法探出其中性爱文明的深层结构”,海子的诗歌也有着同样的美学特征。在他字里行间,自然物像随手拈来,不加丝毫的雕琢与修饰,充满自然的气息和古朴的意味,呈现出野性和原生态的美。这种赞美不仅仅是作为对自然的赏鉴而存在,更重要的是积淀了深刻的心灵体验。人们在自然中寻求自身,自然成为最接近自身的心灵家园,向自然的回归也就成为向自身回归的一种途径。诗中对自然物象的描写和赞美其实就是对女性酮体的欣赏和赞美,“丛林”、“南风”、“花果”等意象已经失去了其自然属性,成为性爱文明的隐喻,进而传达出掩盖着的男女身体融和的快乐,这种快乐通过自然物象所引发的联想表述出来,而性的含义则被隐藏在明媚的自然物象之下。这与《雅歌》中“北风阿,兴起。南风阿,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歌4:16)以及“我是沙仑平原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正像荆棘里的百合花。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好像树林里的一棵苹果树;我欢欢喜喜地坐在它的荫下,它的果子香甜合我口味”(歌2:1-3)有着共同的意趣。二者的高妙之处在于“文章通过比喻象征手法将女性美及男女的肉体吸引当作浪漫关系的重要方面加以表现,既避免了对爱情进行抽象干瘪描写的嫌疑,又回避了流于色情描写的倾向。”其所用喻体汇集了优美自然物象的精华,它们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象征性的,其意义不但在于本体与喻体视觉形象间的密切联系,也在于两者价值意义的联系。而象征与隐喻的距离越大,所产生的心理张力越大,美学上的愉悦也就越大。
走进《雅歌》的世界,扑面而来的是玫瑰花和百合花的馨香,看到的是柔情蜜意,男欢女爱,听到的是真挚热烈的爱的呼唤,处处充满盎然生机,张扬着生命的莫大欢喜。热情奔放的语言风格,优美的田园牧歌情调,唯美圣洁的爱情,使《雅歌》散发着诱人的浪漫主义魅力。学者梁工认为《雅歌》“没有一点宗教意味,而以优美的词句、丰富的想象和巧妙的譬喻,细腻地描写男女恋人的美貌及其彼此慕悦、依恋、思念的感情,流溢出犹太人欢快、健康的情趣和对甜美婚姻的热烈追求”。然而在海子笔下,爱情只是一种灾难和虚妄,这位“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理想主义诗人体验到的唯有爱的苦果,美好的爱情在他笔下被解构无遗。他在《葡萄国之西的话语》中写道:
也好/我感到/我被抬向一面贫穷而圣洁的雪地/我被种下,被一双双劳动的大手/仔仔细细地种下/于是,我感到所罗门的帐幔被一阵南风掀开/所罗门的诗歌/一卷卷/滚下山腰/如同泉水打在我脊背上/涧中黑而秀美的脸儿/在我的心中埋下。也好/我感到我被抬向一面贫穷而圣洁的雪地/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是我的棺材,我是你的棺材。
苏拉密女“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棚,好像所罗门的幔子”(歌1:5),“是沙仑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歌 2:1),是“女子中极美丽的”(歌 1:8)。海子笔下“极美丽的”女子也有着如苏拉密女一样“黑而秀美的脸儿”,只是诗人没有所罗门那样幸运地得到心仪的女子,只能叹息:“我感到所罗门的帐幔被一阵南风掀开/所罗门的诗歌/一卷卷/滚下山腰/如同泉水打在我脊背上”。整个爱情也却并非发生在“葡萄发芽,石榴放蕊”的春天,而是白雪皑皑的寒冷冬天。情人并非相偎相依在“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椽子”(歌1:16-17)的“伊甸园”,而是死亡之墓。爱情、死亡、唯美、神圣,这些震撼心灵的诗歌元素,在海子诗歌中经过奇妙组合,交相辉映,产生了极大的艺术张力。海子的诗歌有一种动态的叙事功能,体现了神性与诗性的超越,这与圣经诗歌所追求的“诗行中有一种趋于强化的叙述发展势态;这种‘水平’运动经常通过一系列诗行,甚至一首完整的诗,向下投映到某种‘垂直’运动中。这意味着圣经诗歌被关注的是一种向着某个终极目标运动的动态过程”有异曲同工之妙。“你是我的棺材,我是你的棺材”,这种刻骨铭心的表达印证了诗句“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歌6:3),“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歌8:6)。这首诗不能不说是海子爱情悲剧的投影,也是他走上不归之路的预示。
平行体是《雅歌》的重要表达方式,包括叠义平行体(P.Synonymus)和反证平行体(P.Antitheticus)。叠义平行体是将诗歌第一行的意义,以不同的言词重新咏出,或用一种类似的意义来完成第一行的意义。反证平行体与前者恰恰相反,其中的第二行用反托的词句,来完结第一行的意义。海子的诗歌完美体现了这一艺术特征。如:《十四行:玫瑰花》
玫瑰花 蜜一样的身体/玫瑰花园 黑夜一样的头发/覆盖了白雪隆起的乳房/白雪的门 白雪的门外被白雪盖住的两只酒盅/白雪的窗户 白雪的窗内两只火红的玫瑰谷/或两只火红的蜡烛……热情的蜡烛自行燃尽/两只叮当作响的酒盅……热情的酒浆被我啜饮/在秋天我感到了 你的乳房 你的蜜/像夏天的火 春天的风 落在我怀里/像太阳的蜂群落入黑夜的酒浆/像波斯古国的玫瑰花园 使人魂归天堂/肉体却必须永远活在设拉字/——千年如斯/玫瑰花 你蜜一样的身体
海子通过反复吟咏意义相同或相近的意象或情感,将内心的感情坚强而有力的表达出来,形成了回环往复的诉求气势和重章叠唱般复沓的艺术效果,从而增强了语言的音乐美与节奏美,实现了内容形式之间隽永与和谐的统一。因此,《雅歌》与海子诗歌的特征要求读者不能囿于聆听重复的想象性意图,而要从诗行的细微之处寻求新东西,因为“言说中的任何重复都有其重要性。”
余 论
周作人讲道:“圣书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可以分作精神和形式的两面”,具体而言,基督教作为宗教,对一国文学的影响,大抵可以分为:一是为文学创作提供素材和内容;二是为文学创作提供可资借鉴的艺术表现技巧;三是为文学创作赋予宗教信仰意识。《雅歌》作为圣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的异质资源,中国现代诗歌中对它的接受与过滤主要体现为:一是对《雅歌》的语言移植与形式渗透;二是对《雅歌》所体现的爱情及爱欲的认同与体现;三是对《雅歌》主题的颠覆与全新阐释。中国现代诗歌对《雅歌》的接受与过滤的过程,是异质文化与主体文化相互碰撞、冲突与激荡的过程,其结果是外来文化(文学)为主体文化(文学)所改铸,发生变形,尔后融入到主体文化(文学)之中,进而产生创造性叛逆,因而可以从中透视出中外文学接受和影响的方式和限度。因此,“在世界宗教名著中,圣经作为现代,甚至是当代中国诗歌一个重大的灵感宝库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雅歌》作为圣经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内涵已经融入到了中国现代诗歌的百花园中,不仅曾经而且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1〕摩尔登.圣经之文学研究〔M〕.贾立言译,上海:上海广学会,1936.
〔2〕周作人.谈龙集集〔M〕.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27.
〔3〕朱维之.外国文学史(亚非部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4〕沫沙.圣经与文学〔J〕.青年文艺.1943,1(3).
〔5〕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A〕.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6〕Phyllis Trible.Depatriarchalizing i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J〕.JAAR1973,Volume41.
〔7〕郭沫若.雨丝〔J〕.心潮.1923,1(2).
〔8〕郭沫若.郭沫若经典作品选〔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9〕张泽贤.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1920-1949〔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
〔10〕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 圣经、次经、伪经、死海古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1〕黎焚熏.雅歌〔J〕.文艺杂志,1943,2(5).
〔12〕北野.马嚼夜草的声音〔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3〕艾青.爱情选集第三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14〕周红兴.艾青研究与访问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15〕艾青.旅行日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16〕阿垅.阿垅诗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17〕绿原.人之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8〕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9〕周扬.何其芳文集·导言〔A〕.何其芳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0〕海子.海子诗全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21〕(美)罗伯特·奥特.古希伯来诗歌的特征〔A〕.梁工译.圣经文学研究〔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2〕李炽昌,游斌.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 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3〕梁工.诗歌书·智慧文学解读〔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24〕梁工.基督教文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25〕L.A.Sonnino.A Hand Book to Sixteenth-Century Rhetoric〔M〕.London:Routledge,1968.
〔26〕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27〕(斯洛伐克)马利安·高利克.《圣经》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从周作人到海子〔A〕.李燕译.中国现代文学论丛〔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