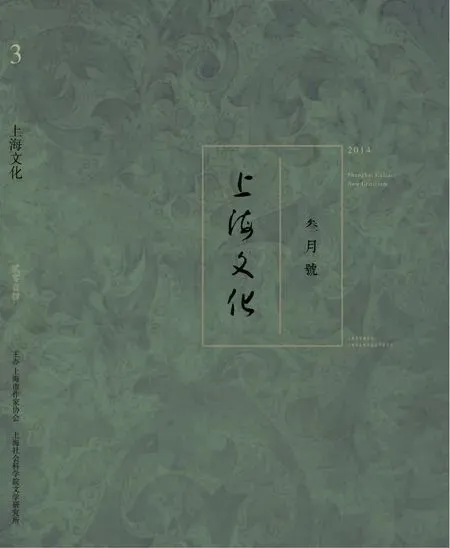“开始”在哪里?
安德鲁·班尼特 尼古拉斯·罗伊尔 李平 译
“开始”在哪里?
安德鲁·班尼特 尼古拉斯·罗伊尔 李平 译
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已经开始过了?
一部文学文本是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问题引发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中一系列根本性的思考。文本开始于作者在他(她)的稿纸上写下第一个字符,或者在电脑键盘上敲下第一个单词的时候呢,还是开始于作家对一篇小说或一首诗歌有最初设想的时候,抑或开始于作家的童年时代?我们能否说文本开始于读者捧起作品的时候?文本是从它的标题开始呢,还是从所谓文本“主体”的第一个单词开始?
我们将尝试着从一首诗歌开始。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伟大史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1667)是从退回到开端开始的:
关于人类最初违反天神命令
偷尝禁树的果子,把死亡和其他
各种各色的灾祸带来人间,并失去
伊甸乐园,直等到一个更伟大的人来,
才为我们恢复乐土的事,请歌咏吧,
天庭的诗神缪斯呀!您当年曾在那
神秘的何烈山头,或西奈的峰巅,
点化过那个牧羊人,最初向您的选民
宣讲太初天和地怎样从混沌中生出;
那郇山似乎更加蒙您的喜悦,
下有西罗亚溪水在神殿近旁奔流;
因此我向那儿求您助我吟成这篇
大胆冒险的诗歌,追踪一段事迹——
从未有人尝试摛彩成文,吟咏成诗的
题材,遐想凌云,飞越爱奥尼的高峰。
弥尔顿诗歌的开始还以其他的方式动摇了所有简单化的“开始”或“开端”的概念
这个非同寻常的开始包含了关于“开始”的各个方面。从主题上看,诗句开头写的是亚当和夏娃“最初”违反天神的命令,从而“把死亡和其他各种各色的灾祸带来人间”。但它也是这首诗自身的开端:它使我们确信,这样的写作计划是第一次被尝试(“从未有人尝试摛彩成文,吟咏成诗的题材”)。这样开启一首诗,对于弥尔顿来说,就仿佛登月迈出了一小步……然而不同的是,因为传统上认为诗歌发端于灵感的凭附,而诗中又有祈求诗神缪斯赐予诗人写作灵感的句子,所以这个开头也是这首诗歌自身的开端。但由此也产生了关于“开始”的奇怪的悖论:灵感作为诗歌的起源,反而出现于诗歌的文辞开始之后。弥尔顿诗歌的开始还以其他的方式动摇了所有简单化的“开始”或“开端”的概念。诗歌不仅谈论到开端(亚当和夏娃偷吃伊甸园中的智慧果),而且还写到未来回归于这个开端之前的时间(“恢复乐土”):一种既是新时代的开端也是先前状态重现的时间。
这个“开始”算不上是开始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它不断地使我们退回到其他的文本——弥尔顿提到了摩西(“那个牧羊人”)。根据教义,他曾向希伯来子民“宣讲”创世的故事,换句话说,他撰写了《旧约全书》开头的几章。在这个意义上,弥尔顿诗歌所恳求和呼吁的缪斯便是一个间接的缪斯了。与其独创性的声明相反,诗歌的开头复述了其他人的话,让人联想到许多别的开端。“关于人类最初违反天神命令……天庭的诗神缪斯”,重复了诸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那样的经典性开端的传统表现方式;“太初”则重复了《约翰福音》的开头(“太初有道”),等等。最后,特别是让诗句中的主要动词“sing”直到第六行才出现,弥尔顿移植了自己诗歌的开端。
然而,无论弥尔顿诗歌的开始有多么复杂,至少它尝试(或假装尝试)在特定的开端而不是在中间开始。从中间发端是另一种开始的方式,这种方式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但丁的《神曲》:
正当我们人生的中途,
前方的大道已经消逝,
我迷失在一片黑森林之中。
这里至少有三个不同的中间:“我们人生”的中途、黑暗森林之中、叙事的中端。但丁将人生、旅程和叙事三者融合在一起,暗示了以这样一个处于中间的时刻为开端所带来的异乎寻常的恐怖。尤其是诡异的“我迷失”三个字,暗示了重新发现和重新找回自我的魔幻般的惊惧。但是但丁的开始或许也是在说明,并没有绝对的开端——只有奇特的开创性的中间。旅程、人生、叙事从来不是真正的开端:所有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开始以前都已经开始过了。但也并不是说,没有“开始”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毫不介意。没有开始,那当初我们是在何方?没有开始,文本又在哪里呢?
“开始”所引发的悖论在劳伦斯·斯泰恩(Laurence Sterne)的《项迪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Gentleman,1759)的开头,就已经机智地表现出来了,该小说叙事的开端同时也是生命的开端:
由于我的父母对于我的出生负有同样的责任,我真希望我的父亲或母亲,或者他们俩在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那时候充分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将带来多么可观的后果就好了。他们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创造一个理性的人,也许还有他的快乐的构成、身体的温度,还有他的天赋、他特有的心智类型,甚至他的全部命运。这些思量可能会扭转他们高潮时的体液和性情。相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如果他们能及时权衡和思考这一切,然后再继续相应的进程,我一定会被调整,并以一种与读者可能见到的形象完全不同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认的真理”),但同时又讽刺这个19世纪早期英国中产阶级上层男士所认可的真理未必一定是普遍有效的。在对书中所用方言进行“说明性”解释之前,马克·吐温(Mark Twin)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1885)是以一则“通知”开始的:
这个开头简直就是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诗《这就是诗》(This Be The Verse,1974)那个模棱两可的开头(“他们操出[fuck you up]你,你妈咪和爹地”)的喜剧版。项迪抱怨,在他思想的形成期,他的父母总是考虑其他事情,他害怕自己的整个生活因而都被毁掉了(has been fucked up)。小说数页之后,他的叔叔托比评论说:“我的项迪的不幸,自他呱呱坠地之前九个月就已经开始了。”《项迪传》极好地处理了如何结束自传这个棘手的问题:这种体裁的文本是从来不可能穷尽其自身的,因为它所叙写的生活不会比写作者的生命跨度更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自传都不曾有结局。但是,《项迪传》也是关于怎样开始——如何在开端开始——以及我们是怎样开始的文本。
如果说开始总有一个语境,因而总是由发生在它之前的事情所决定的,那么《项迪传》的开始则表明,它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开始决定了以后发生的事情。与其他类型的开始相比较,这是真正的文学——开端像许诺一样,预示着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许多文学名著开端的力量之所在。简·奥斯汀(Jane Austen)《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1813)的开头显然是明确的:“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就为整部小说搭建起了一个舞台。主题是结婚,语调是反讽。奥斯汀赞扬普遍主义的价值(“举世公
通知
那些试图寻找本故事动机的人将被起诉,那些试图从中寻找道德寓意的人将被驱逐,那些试图寻找情节结构的人将被枪毙。
以作者名义
奉军需官G.G.之命发布
这里,机智和困惑同时扑面而来,小说的开头既是入口也是屏障
这里,机智和困惑同时扑面而来,小说的开头既是入口也是屏障。这就好像在读这样的句子——“不要读这句话”,因为它既承认读者试图在故事中寻找动机与道德因素,然而又喜剧性地阻止这样的阅读。在那句著名的开篇语“管我叫伊斯梅尔吧!”之前,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莫比·迪克》(Moby Dick)或者叫《白鲸》(Whale),则是按照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所称的一系列的“副文本”来构建的,即通过目录、题词、(单词“白鲸”的)“词形变化”和(数页关于鲸的)“引文”来构建的。讽刺性的支支吾吾和卖弄学问,与自信的夸夸其谈混合在一起,构成了整部小说的特征。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奥兰多》(Orlando,1928)在题词、序言、目录和插图说明之后,是这样含糊不清地开篇的:“他——即使被某些时髦的装束加以掩饰,其性别也不容置疑——正在切开一个悬挂在梁上的摩尔人的头颅。”这个句子以一种奇怪的不确定的语调,描述了一个不确定的人和不确定的性别,暗示了主人公与砍头和阉割的某种联系,小说就这么开始了。似乎不喜欢将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处理,这个起始句微妙地削弱了关于性别身份的习常观念。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的《好兵》(The Good Soldier,1915)的第一句话“这是我所听到的最令人悲伤的故事”也充满了激动人心的魅力。这是那种一部小说再也不可复得的句子。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追忆逝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那个轻描淡写的开头,就暗示了并不存在唯一的开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地就躺下了。”一种对逝去韶华的慎重反思,一种亲密接触的感觉,一种习惯与重复的力量,是普鲁斯特这部长达三千页的小说的特征。
以上这些例子表明,文学“开始”的特性之一就是,它们从来不是单一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莫比·迪克》和《奥兰多》,展示了围绕“副文本”的多样性开始,但其他的开始也不乏例证:《好兵》既有故事自身的叙述,也有对故事叙述的叙述(似乎没有比它更伤感的其他故事了),而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开头则给人一种叙事是以重复开始的感觉,因为没有哪个单一事件可以被说成是小说的开端。
使得文学文本的开始多样化的途径之一,是采用副文本——标题、副标题、献词、题词、引子、“通知”等等
正如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的,使得文学文本的开始多样化的途径之一,是采用副文本——标题、副标题、献词、题词、引子、“通知”等等。一个经典性的例子可能是T.S.艾略特(T.S.Eliot)《荒原》(The Waste Land,1922)的开头。在读到艾略特这首诗的首句之前,我们便遭遇到由一系列多语种写作造成的障碍。先说它的标题吧。这首诗的标题像其他所有标题一样,处于一种介乎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以《荒原》命名该诗,似乎除了外部原因,同时也是该诗形式方面的需要。“荒原”,既与某个地点抑或某种困境——比如1918年以后的欧洲——有关,也是对一片奇异的土地(land)的命名,这片土地是艾略特的诗创造出来的(就像真的荒原一样,整首诗充满了过去时代的残迹、破碎的记忆与话语引文)。接着,我们遭遇了拉丁语和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体的希腊语:“因为我在库梅亲眼见到大名鼎鼎的女先知西比尔被吊在一只笼子里,孩子们在问她:‘西比尔,你要什么?’她回答:‘我要死。’”作为题词,这段引文也可以说既位于诗歌之内,也位于诗歌之外,既是对该诗的一种评论,也是该诗自身的一部分。接下来的困难,是作者用意大利语对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称谓:“卓越的匠人。”庞德作为编辑,曾为艾略特的许多诗歌定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艾略特诗歌的合作伙伴。即便这个称谓,其实也是一种引用,它来自但丁《神曲》中的《炼狱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既是艾略特诗歌的一部分,又不是该诗的一部分。最后,这首诗还有一个副标题,“一、死者葬仪”,它也是借用了英国圣公会宗教葬礼仪式中的说法。然后,我们便看到了诗歌开头的句子:
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
从荒地里培育出丁香,
将记忆和欲望混合,
用春雨拨动沉闷的根芽。
但事实上这几行诗依然是对乔叟(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约1387-1400)中另一首诗的开头的模仿与重构:
当四月的甘霖渗透了
三月枯竭的根须和茎络,
触动了生机,
使枝头涌现出花蕾。
以这些或其他的方式,艾略特对自己诗的开端进行了移植。这首诗的开始不再是第一次落笔或第一次敲击键盘。通过互文性(包括引文、典故、参照和仿效)的有力作用,艾略特的诗歌表明,与唯一性、可限定性、稳定性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独创性的开始概念,其实是非常成问题的。如果追问艾略特的诗歌是在什么地方、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会牵涉到作者身份、文本和读者,最终,甚至普遍意义上的西方文学传统等一系列问题。
《荒原》对起源及其移植问题的重视似乎是非同寻常的。但是这个开端所探索的互文性的种种效用,事实上对一般的文学文本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说,文学文本总是依照语境或传统,并且在语境或传统之内进行构建的。在其著名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1919)中,艾略特主张,“没有哪个诗人或艺术家可以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意义”,相反,他的重要性是由诗人“与死去的诗人和艺术家的关系来决定的”。一首诗、一篇小说或一个剧本,与先前的文本完全没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真的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的话,这个文本的作者就不得不创造一切。这就好比不依赖任何现成的语言,而是从零开始去发明一种全新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互文性(被移植到别的文本的原创性的东西,其实也移植了其他的文本,等等。换言之,它消解了存在纯粹的或直接的原创的固有观念)对于文学的机制至关重要。没有哪一部文本能脱离其他文本而形成意义。任何文本,都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谓的“过去引文的一种新的编织物”。
艾略特的诗歌表明,与唯一性、可限定性、稳定性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独创性的开始概念,其实是非常成问题的
两个最具吸引力和绵延不绝的关于文学文本的神话都与它们自身的起源有关。第一个神话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在任何阅读中,最重要的是读者心灵与作者心灵的相通。这种观念作为“意图谬见”(intentional fallacy,即这样一种错误的信念:作者意图是作品“真正的”和“最终的”意义,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去了解这个意图)的一个例证(见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Wimsatt& Beardsley]的同名著名论文),在过去半个世纪己经广为人知了。但是,假如我们不能够按照一部文本呈现给我们的样子去把握它的开端的话,那我们要找出推动一个文本的思想起源,其难度之大就可想而知了。作者知道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吗?它们是真实的思想(神志清醒的、一贯的、连续的)吗?当我们读到《荒原》的开头时,我们读到的是谁的思想?是艾略特的思想,还是乔叟、庞德、佩特罗尼乌斯或但丁的思想?如果诗人声称诗歌来自“灵感的激发”,那么这些思想还能算是诗人自己的吗?第二个流行的神话是,个体的读者被赋予了首次阅读文本的优先权。按照这样的神话,所有的文学批评都会毁坏个体阅读的初始经验。从前(就像这类神话所表示的)我们可以阅读一部小说(比如夏洛蒂·勃朗特或者J.K.罗琳的小说),并且拥有一种完整、纯粹而没有受到批评性思考和其他复杂情况污染的阅读经验。不过,尽管我们经常谈到存在着某种只经得起一遍阅读的文学作品,但我们都知道,它在很多方面主要是指那些容易阅读的东西。罗兰·巴特在其著作《S/ Z》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重复阅读的行为“与我们社会的商业与意识形态习惯反其道而行”,并认为“只有那些边缘型读者(孩子、老人、教授)可以忍受重读”。教授(通常是老年人,很少会有孩子,不过两者不确定的结合也时有所见),当然也包括巴特,是向唯一或首次阅读观发起质疑的主要群体。巴特争辩道:
重读质疑如下声言:首次阅读具有原生态的、素朴的、真实的特性,此后,我们才不得不去施以“阐释”,使之理性化(仿佛有阅读之始似的,仿佛我们什么都不曾读过似的,其实,不存在什么首次阅读)。
再回过头来,艾略特的《荒原》显示了包含首次阅读在内的某些复杂性。假如艾略特诗歌的开头参考了乔叟的作品,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被合适地认为,已经读懂了“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我们曾经读过它,然而带着对乔叟诗句的印象,我们确实必须再次阅读它。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仅凭首次阅读都是不充分的。或许可以绝对地说,任何其他文学文本的阅读也同样如此:每次阅读(即便是所谓的“首次阅读”),至少部分是对已知事物或某种程式做出的反应,并受到其他人和其他人阅读经验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用艾略特的话来说,批评性的阅读“像呼吸一样不可避免”。
本书从根本上说,就是关于起源问题和开端问题的。它集中讨论了我们应当如何开始阅读、思考和写作文学文本的问题。我们尤其认为,那些不确定的起源——无论是作者、读者还是文本——没有一个是理所当然的。既不是作者,也不是读者或文本最终或恰当地构成了开端。就好像我们说“开始文学研究”(我们现在己经开始了,还是没有开始?)一样,所有的事情都开始于作者或读者或具体的文本的观念,既是很富有吸引力的,同时也是完全错误的。
附记:本文原标题为“The Beginning”,选自英国学者Andrew Bennett&Nicholas Royle的著作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 ture,Criticism And Theory
,2009年第4版。完全不同于通常的文学导论,此书摒弃了习见的块状、渐进式写法和抽象的“主义”式阐述,注重问题意识,注重从新理论与文学作品相结合的生动角度切入分析,并以主题引领的新方法来编排著作的结构,因此受到西方学界的充分肯定和欢迎。全书共分三十四个主题,尽管第一个主题是“开始”,最后一个主题是“结束”,但实际上读者却可以从任何主题进入,没有顺序的限制;而主题与主题之间又互为印证、互相补充,从而使全书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有机整体。这些主题有的是读者熟悉的(但也予以崭新的解释),而更多的则充满了前沿性和挑战性。这些主题在目录中的次序是:1.开始,2.读者与阅读,3.作者,4.文本与世界,5.不可思议之物,6.纪念碑,7.叙述,8.性格,9.声音,10.修辞和比喻,11.创造性写作,12.笑声,13.悲剧性,14.历史,15.我,16.生态,17.动物,18.幽灵,19.电影,20.性别差异,21.上帝,22.意识形态,23.欲望,24.酷儿理论,25.悬念,26.种族差异,27.殖民,28.突变,29.述行语,30.秘密,31.后现代,32.愉悦,33.战争,34.结束。❶参见弥尔顿《失乐园》,朱维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编辑/张定浩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