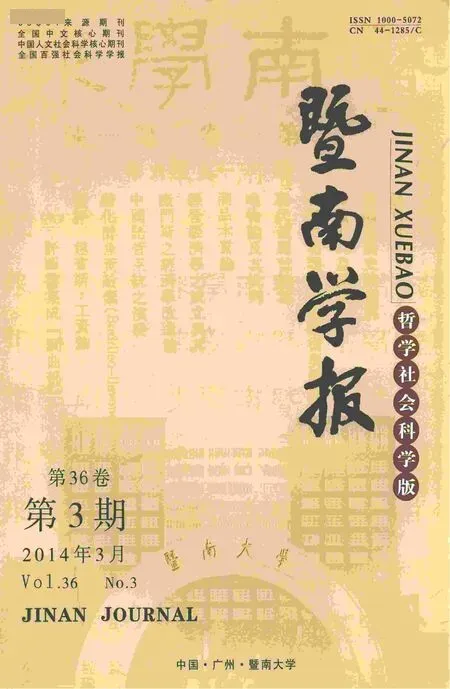明代唐诗选本中“以盛唐为楷式”之现象研究
薛宝生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高棅《唐诗品汇·凡例》云:“先辈博陵林鸿尝与余论诗:‘上自苏李,下迄六代……唯李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孤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为楷式。’予以为确论。”高棅将林鸿“以是(盛唐诗)为楷式”视为“确论”,并援其以入选本编选,对有明一代唐诗选本的发展影响深远,“以盛唐为楷式”也成为明代多数唐诗选家的诗学去取准式。而这种“盛唐楷式”又因选家们各自执守的具体标准差异而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盛唐楷式”只限于盛唐作品,广义的“盛唐楷式”则在盛唐诗之外,还包含初、中、晚唐诗歌中具有“盛唐格调”的诗。那么,这种楷式究竟确立于何时?又呈现出什么具体特征,其原因如何?选家“以盛唐为楷式”的终极目的又如何?本文试就以上问题作以解答。
一、“盛唐楷式”的奠基及初见影响
明初,高棅重申林鸿“楷式”之论,并借唐诗选本的编选来实践这种审美范式,其所编《唐诗正声》一选,盛唐诗的比例占到了50.5%,超出中唐诗近20%,初、盛唐诗选录比例超出中、晚唐诗21.2%。至此,“盛唐楷式”在高棅的选诗实践中得以落实。既然“以盛唐为楷式”在实践上得以落实,是否便意味着明代唐诗选本中“以盛唐为楷式”的选诗标准真正确立起来了呢?显然不是,这只能说是高棅在实践中将这种楷式落实到位了。事实上,在这个时候,高棅的选本还没有获得广泛的流行,也没有获得更多的支持者、响应者,尚未对明代唐诗选家及选本产生更大的影响。所谓“楷式”,只有当它被众人所效仿并形成一定影响的时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楷式”。也就是说,只有当高氏的选本真正流行起来并获得诸多选家效仿的时候,才标志着这种楷式正式确立。
那么,高选真正流行起来并产生影响,是在什么时候呢?陈国球先生认为高选的影响力是在嘉靖以后才显现的,此论良是。但是,他却以当时主文柄的名流(如杨士奇、李东阳等)论选本均谈及《三体》、《唐音》而不及《正声》、《品汇》为证据,断定高选在嘉靖以前都没什么影响力。而反对者则以桑悦及陈乔新等人的言论,来说明高选在更早些的天顺、成化、弘治年间就已经盛行了。陈氏之失在于忽略了高选在嘉靖以前小范围流行的事实及影响;后一种观点则过于扩大了高选的影响范围。事实上,高选在嘉靖以前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但这种影响范围只限于明东南部地区(即以闽地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既没有陈先生所说的那么微弱,也没有反对者所指称的那么盛行。
康麟写于天顺七年(1463)的《雅音会编序》云:“若杨士弘之选《唐音》,周伯弜攵之选《三体》,与夫遗山之《鼓吹》,高棅之《正声》,《唐诗选》、《光岳英华》等集,是皆披沙拣金,互为精密,梓行于世久矣,世之学诗者无不宗之。”
何乔新编成《唐律群玉》,自为序云:“选唐诗者数十家,惟周伯弼之《三体》、杨伯谦之《正音》、石溪周氏之《类编》,新宁高棅之《正声》,盛行于时。”
桑悦《跋唐诗品汇》:“高廷礼有《唐诗品汇》五千余首,……要其见亦仲弘之见。是诗盛行,学者终身钻研,吐语相协,不过得唐人之一支耳。欲为全唐者,当于三百家全集观之。”
弘治中进士符观编选《唐诗正体》,《百川书志》卷一九称:“《唐诗正体》七卷。皇明符观重订《唐音》、《正声》,而少加增损焉,止五七言律及七言绝三体。”
康麟言“梓行于世久矣,世之学诗者无不宗之”,何乔新言“《正声》盛行于时”,桑悦言“是诗盛行”,加上符观对《正声》的“增损”行为,从表面上看,似乎高氏的选本在成化、弘治之时已经很盛行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其一,康、何、桑、符四人都出生在明东南部地区。康麟,广东顺德人。符观,江西新喻人。桑悦,苏州府常熟人。何乔新,江西广昌人。而夹在这些地方中间的则是高棅的家乡闽地,也就是说,高选的流行范围在当时只限于闽地及周边地区,也即是闽中诗派影响所及的地方。其二,嘉靖以前刊刻高选者,张璁是永嘉人,其他如彭伯晖、黄镐、陈炜都是闽人。这就更加证实,高棅选本在当时并没有获得全国范围的认同,其推崇者亦只是闽地及周边地区的文士。其三,两种选本重刻的底本也都来自这个区域,也可为之佐证。黄镐《唐诗正声序》云:“予历仕途几四十年,遍访之尚不可得。成化庚子,承乏南都民部,而伯晖之子致政都阃。大用与予有同乡之雅,始出是编,谓先人藏此岁久,缺板尚未能补,幸为我成之,并求一言以弁诸首。”张璁《跋唐诗后》曰:“《唐诗品汇》九十卷……明年己酉,予访太史张白先生于南昌,辱示此编,实元刻本也。”其四,当时明代全国范围内盛行的选本亦如康、何等人所提及的主要是《三体》、《唐音》,这一点从陈国球先生所举的杨士奇、李东阳的话语中,也可证明。其五,《四库提要》云:“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兆於此。”即便李、何“诗必盛唐”的主张出于对高选的接受,然李、何主张所带来的影响仅限于其身前,在二人相继谢世后,嘉靖初年的诗坛风气又为之一变,如王世贞《徙倚轩稿序》所云:“当德、靖间,承北地、信阳创而秉觚者,于近体畴不开元与杜陵是趣,而其后稍稍厌于剽窃之习,弥而初唐,又靡而梁、陈月露,其拙者又跳而理性。”又王世懋云:“于鳞辈当嘉靖时,海内稍驰骛于晋江、毗陵之文,而诗或为台阁也者,学或为理窟也者。于鳞始以其学力振之,诸君子坚意唱和,迈往横历。”显然,李、何的“盛唐”论调,并未能将这种“盛唐楷式”牢牢确立起来,仅仅是昙花一现。
基于以上判断,可以确定:嘉靖以前,高棅的选本仅在明东南部地区传播、流行,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形成影响,乃为初见影响而已。所以“以盛唐为楷式”的选诗标准并没有在成化、弘治间真正确立起来。
二、“盛唐楷式”的确立
事实上,到了李攀龙主盟文坛的嘉靖年间,这种楷式才真正地确立起来。而高氏二选的刊刻情况也能支撑起这个结论。根据已知的唐诗选本情况来看,明嘉靖以前的一个半世纪,《正声》刊刻过两次,《品汇》刊刻过三次。《正声》第一次刊刻是在正统七年(公元1442),由高棅门生彭伯晖完成;第二次刊刻是在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由黄镐主持;嘉靖以后,多次重刻。从嘉靖三年华庆玄刻本到后来托名唐汝询的《汇编唐诗十集》收录本约刊刻过11次,其中嘉靖中至少刊刻过三次,分别是嘉靖三年华庆玄刻本、嘉靖二十四年何城重刻本、嘉靖三十三年韩诗刻本。《品汇》最早刻于洪武年间,今已不传。成化十三年(1477),陈炜主持第二次刊刻。弘治六年(1493),张璁主持第三次刊刻。嘉靖以后,多次重刻,自嘉靖十六年姚芹泉刊刻开始到崇祯年间张恂重订,至少刊刻过12次,其中嘉靖中就刊刻过约五次,分别为嘉靖十六年的姚芹泉本、嘉靖十七年的康河重修本、嘉靖十八年的牛斗刻本、“月到天心处”本及署名“东海屠隆长卿”的刊本。可以看出,高氏的选本是在嘉靖中才真正盛行起来的,特别是从嘉靖十六年到嘉靖二十四年,高棅的选本就被刊刻了四次。
而高氏二选在嘉靖中的刊刻高潮,恰恰是在谢榛与李攀龙等结社前后。此后,李攀龙也确立了其文坛盟主的地位,直至其隆庆末去世,时人对“盛唐楷式”的推崇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明史·李攀龙传》云:“攀龙遂为之魁,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可知,李氏论诗尤尚盛唐,这也是当时诗坛的主流思想,唐诗选家更是持论如此。孙春青《明代唐诗学》第三章专门绘制了表格,对嘉靖、隆庆年间的数十种选本和别集作了考察,得出结论:“一、李白、杜甫和初、盛唐诗人的别集、合集后来居上,成为唐诗刊刻的新热点。……二、唐诗总集刊刻的种类和数量都骤然增加,……反映着当时唐诗学领域诗学盛唐的理论动向。这说明,唐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诗必盛唐”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基于以上论述,则“盛唐楷式”在嘉靖中确立无疑。而这种楷式落实到选诗实践中,则是“选中、晚唐,必绳之以盛唐格调。”这也是持广义“盛唐楷式”的选家的共同诗学去取倾向,如李攀龙、唐汝询、李沂等选唐诗均是如此。
嘉靖以来,高棅选本的影响力逐渐显现,李攀龙受高棅影响,论诗颇重盛唐而鄙薄中、晚唐,在其《古今诗删》所选唐诗中,初、盛唐诗占77%,单盛唐诗就占了60.1%,可以说对盛唐诗的推崇几乎无以复加。在李攀龙去世后,其生前编选的唐诗选本得以付梓,出现了《诗删》、《诗选》两个版本系统,并大行于世,更助长了“以盛唐为楷式”的势头。而其更言:“后之君子,本兹集以尽唐诗,而唐诗尽于此。”陈国球先生认为:“《古今诗删》中的中、晚唐诗合共只占全数的18.9%,盛唐诗却占60.1%,可见他所谓唐诗也不是指整个唐代……而是指同遵依某些文学规范,形成某种独特风格的一种体类的诗篇,这些规范和风格都是以盛唐诗为基准。”之后,公安、竟陵曾一度主盟诗坛,宣扬异于李攀龙的文学主张,而李选的热度却不曾衰退。
后来,唐汝询选诗也承袭了高、李的路子,也即是汲取“选中、晚唐,必绳之以盛唐格调”的眼光,故其《唐诗解》选录盛唐诗所占比率为54%,所选中、晚唐诗仅占33%。明末李沂编选《唐诗援》,亦持守“盛唐楷式”,其分七体选诗,五古选杜甫80首、李白21首、王维21首;七古选杜甫35首、李诗19首、岑参11首;五律选杜甫127首、王维21首、岑参24首、孟浩然26首;七律选杜甫38首、王维7首;五排选杜甫15首、王维5首、宋之问6首;五绝选李白10首、王维5首;七绝选杜甫8首、李白14首、王昌龄11首。选诗的核心不出李、杜、王、孟、岑等人,其他作家作品入选极少。即便是后来标举“别出”之调的《唐诗归》,其所选盛唐诗占 51.8%,中唐诗 21.6%,晚唐诗 11.6% ,亦未能跳出“以盛唐为楷式”的模式。
三、楷式具体化及其原因
“盛唐楷式”从口号到落实,再到确立,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末。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唐诗选本的编选呈现出两个具体特征:即以“李杜”为中心的极则楷式与以初、盛唐名家为中心的名家楷式。在明代唐诗选本中,以李、杜为“极则楷式”是比较普遍的,在实际操作上,就是以李、杜作品入选数量居首,如高棅的《唐诗正声》、李攀龙的《唐诗选》等。特别是一大批专以李、杜为选主的选本出现,就更能说明这种“极则楷式”确实存在。据金生奎《明代唐诗选本研究》著录,已知现存的明选本约323种,李杜诗选就有64种,约占20%,其数量相当可观。在以“名家楷式”为主的选本中,其选主不仅来自盛唐,还兼及初唐,体现为一种广义的“盛唐楷式”。因其所执具体标准不同,而略有差异,大抵以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为中心,向前则兼取四杰及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陈子昂。专选李、杜诗或盛唐诗的选本自不必说,即便是通选四唐诗的选本也表现出此种倾向。兹以《唐诗解》为例,该选收诗凡1546首,作家200人(其中误收宋人两位,作品两首),所选杜审言、沈佺期、张九龄、陈子昂、宋之问、王维、储光羲、孟浩然、王昌龄、李白、杜甫、岑参、高适、常建、崔颢、李颀16位名家诗数之和为832首(其中初唐杜、沈、宋、陈、张共入选93首,盛唐诸人739首),约占《唐诗解》收诗总数比例53.8%,其他184位诗人入选作品仅714首,人均不到4首。除却李、杜之外,其他14位名家入选诗数为480首,比入选的中唐诗总数还多 51 首。可以看出,唐汝询选诗是以初、盛唐名家为主;在初、盛唐名家中,又以盛唐名家为主;在盛唐名家中,又以李、杜为尊。
而这些具体化特征,其理论上则远承司空图、严羽对唐代作家作品的轩轾之论,唐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云:“国初,主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思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夐,若清沇之贯逵;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厥后所闻,徒褊浅耳。”司空图从作家着眼,而着力标举从初、盛唐的杰出作家个体,而贬斥中、晚唐作家。其所标举的包括沈佺期、宋之问、张九龄、王昌龄、李白、杜甫、王维、韦应物,尤以李、杜为极则,也即举出了以“李杜”为中心的极则楷式与以初、盛唐诸家为中心名家楷式。严羽除了肯定盛唐诗整体成就外,也举出司空图所举的两种楷式。其《沧浪诗话》云:“以人而论,则有……沈宋体(佺期、之问)、陈拾遗体(陈子昂)、王杨卢骆体(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张曲江体(始兴、文献公、九龄)、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高常侍適)、孟浩然体、岑嘉州体(岑参)、王右丞体(王维)、韦苏州体(韦应物)。”明代选家所选名家多包含在此中,而略有损益。又云:“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此处,先云“开元、天宝”,而后单列李杜,即有尊崇之意,“李杜”前后语句中多以某个时代、某个时间段上的诗为标榜,或以数人为标榜,而“李杜”独标,即认为李、杜二公可代表一个时代,堪称典范,故云有极则之意。
选家们既然推崇盛唐,缘何又以李、杜为尊?文仲阁为张含《杜诗选》作序云:“古今推诗坛宗主者,莫不以青莲、少陵两家并称,豪迈不羁。今人读过,翩翩然凌云想者,或不能无逊于青莲,若雄壮沉厚之气,惟于少陵有独钟也。”米荣《刻全唐诗选序》云:“当时作者非一家,而后世评诗者多推重李、杜……不费斧凿而清莹自然,忧思深远而忠爱恳至,或无有愈二公,此人心之公,取予之正也。”曹学佺《唐诗选序》:“选唐诗而不入李、杜者,不重古风故也……大历以下诸公纯用才华而蕴藉少矣;贞元以下诸公,纯用工巧而古风乖矣,其病皆在不习古风也。”可以看出,以李、杜为尊,一是出于一种传统共识,即李、杜是古今论诗者共推的“诗坛宗主”,李独立卓绝,睥睨万物,杜忧思民瘼,忠君爱国;二是李、杜穷两种诗风之极,“翩然凌云”谓李诗之清新高逸,无工可见的艺术造诣;“雄壮沉厚”谓杜诗沉郁顿挫的精神气脉,后世“不能无逊”,故“有独钟”;三是李、杜诗有得于古风,即能继承《诗》、《骚》、汉魏风骨的创作传统,与之一脉相承。
此外,选家缘何又以“十二家”为代表的名家为楷式呢?黄埻跋张逊业《唐十二家诗》云:“王、杨、卢、骆沿袭六朝之习,为天赋之才,实一代声律之发硎。自是文运益昌,乃有陈、杜、沈、宋倡于前,王、孟、高、岑继于后……则十二家又唐之可法者欤?爰重梓之。”又孙仲逸序杨一统《唐十二名家诗》曰:“于时作者众多,篇章繁赘,选醇摘粹,种种相望。苛严于历下,泛滥于新宁,使务精者致憾于多,博摭者遗恨于寡,均之二集,未为折中。故总唐初四杰及陈、沈、王、孟十二人为集,上尽正始之音,中罗开元之美,外联甫、白之华,下杜中晚之渐,有唐之盛,班然备于斯矣。”黄、孙二人都提到选诗以“十二家”为中心的原因,而孙氏的论述兼及论诗中以“十二家”为楷式的原因,因而更具代表性。就选诗而言,他认为选家选本众多,且自以为能得唐诗之“醇粹”,互摭利病。前有《品汇》,后有《唐诗选》堪称佼佼者,但高选浩博“使务精者致憾”,李选苛严使“博摭者遗恨”,都不能很好地充当学诗者的楷式,故选“十二家”诗以为折中。就论诗而言,“十二家”能远承汉魏传统,为盛唐气象的代表,可以羽翼李、杜,且无中、晚之衰败迹象,足以代表唐诗艺术成就。
四、“以盛唐为楷式”的终极目的
明代唐诗选本之所以出现“以盛唐为楷式”的选诗倾向,同明代复古派论家基于文章与时高下的论调而建构起来的唐代诗歌史有密切关系,这一诗歌史则定位在与李唐国运由昌平走向极盛相表里的初、盛唐诗歌创作阶段,而排除了中、晚唐诗,这从明初宋讷、宋濂、王祎的“书”、“序”及林鸿的论诗中都可以得到验证。而明代选家以“盛唐楷式”为前提,具体到以李杜为中心,继而辅之以“十二家”,其终极目的则在于续写一种公推的经典诗歌发展史。
高棅云:“尝谓《风》、《骚》辍响,五言始兴。汉氏既亡,文体乃散。魏晋作者虽多,不能兼备诸体。齐梁以还,无足多得。其声律纯完,上追风雅,而所谓集大成者,唯唐有以振之。”
屠隆序《选唐诗》云:“诗自《三百篇》、汉魏而下,独推唐。”
叶向高《精注百家唐诗汇选叙》云:“诗自《三百篇》后,咸谓诗必汉、魏、盛唐,自严沧浪已持此论,今世之三尺童子能言之。”
黄姬水《刻唐诗二十六家序》云:“今之谈诗者,其谁不曰《风》、《骚》而下,其汉与魏乎?汉、魏而下,其盛唐之盛乎?指五尺童子而问之,亦知谈如是也。”
可以看出,从《诗》→《骚》→汉、魏古诗→唐诗(盛唐诗)薪火相承的经典诗歌史是当时士人的认识主流,且这种公推的经典诗歌发展史不仅排除中、晚唐而且是抹去宋、元诗风的。林慈序《唐诗品汇》云:“诗自三百篇而下,莫盛于唐……真所谓集大家者,降是无足取焉。”李沂编选《唐诗援》自为序云:“至盛唐洗濯扩充,无美不臻。……上可以檃栝曩贤,下可以仪型百代。谓之曰盛,不亦宜乎!至中、晚而衰矣,至宋、元益衰矣。……中、晚及宋元人皆知尊盛唐,皆知学盛唐而患不逮,乃今之人背高曾而尸祝其玄孙,忘本而逐末,取法乎下,必至风日颓、道日降。沂故不惮以衰朽余年,订斯编问世,故不得已而命之‘援’也。”引文中的“降是无足取”、“益衰”等字眼,明显地反映出选家尊唐而轻宋、元的诗学去取观念,李氏更将中晚唐、宋、元诗一概定位为“衰”,指斥为诗之“末”,甚至将其比作盛唐诗之玄孙,可见其对中晚唐、宋、元诗之鄙薄。而其对“盛唐”诗却极力称许,颇能体现出“以盛唐为楷式”这一派选家的共识。
因此,在这种公推的诗歌史基础上,明人所要做的便是径直接续盛唐格调,从而完成振起诗道的使命,即实现从《诗》→《骚》→汉、魏古诗→盛唐诗→明诗的传承跨越。谢榛《四溟诗话》卷三云:“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佚,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是夕,梦李、杜二公登堂谓余曰:‘子老狂而遽言如此。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所谓“十四家”,即李、杜与“十二家”。这是后七子谈论“楷式”的具体化(即以谁为楷式)问题时,谢氏的对答言语。首先谈到以“十四家”为法的途径,就是先编录选本(即“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佚”),而后讽咏玩味。接着托言李、杜道出以“十四家”为楷式的终极目的,即是在创作上铸就自己的风格,最终青出于蓝而自成一家,造诣上与“十四家”并驾齐驱,所谓“十四家又添一家”。也即是与“十四家”为伍、与“盛唐”为伍,从而承续滞留于“盛唐”的经典诗歌史,而不仅是模仿、接近“十四家”。选家张居仁也有类似的目的,其《唐十二家类选·小引》云:“余染指十二家已日用饮食之矣,浸假而化余之尻以为轮蹄、以为马,余因乘之而游开元、天宝间,与十二家相唱和,窅然忘吾之忧四肢形骸也。安知我之不为唐耶?十二家之不为我耶?”张氏所谓“日用饮食之”即是谢氏的“熟读”、“讽咏”、“玩味”;张氏的“安知我之不为唐,十二家之不为我”,即是谢氏的“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张氏的“与十二家向唱和”即是要与“十二家”并驾齐驱,即是谢氏的“又添一家”。可以看出,在选家眼里,“盛唐楷式”既是学诗者的师法榜样,也是学诗者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体现出一种基于特定的审美范式而又不止于单纯的崇拜欣赏,并试图超越的审美追求。以此为鹄的,所要进行的是由模仿至于谙熟而最终至于超越的诗歌创作实践,进而完成从《诗》→《骚》→汉、魏古诗→盛唐诗→明诗的经典诗歌史续写,这便是明代选家“以盛唐为楷式”的终极目的所在。
五、结 语
在明代选家眼里,“菁华毕出”的唐诗选确实具有作为“文章之衡鉴”的“楷式”意义。于是,争相为选,且都自以所选为“正”、“精华”、“绳尺”,力图为后学树立至高无上的学诗范式,如高棅《唐诗正声》、余俨《唐诗精华》、符观《唐诗正体》、徐用吾《唐诗分类绳尺》、徐统《唐诗粹选》等等。特别是通过标举“盛唐楷式”,试图使明诗从师法楷式开始,走向出于盛唐而超越盛唐的境地,从而抛开中晚唐、宋、元,续写紧承盛唐辉煌的经典诗歌史,这也是有明一代多数选家所共具的良苦用心。焦竑序《唐诗选》云:“恒自谓足以尽唐诗,乃知其精心妙会,自具别解,非唐诗果尽,要亦选唐诗者之心尽也”,其是之谓也。
[1]高棅.唐诗品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康麟.雅音会编[M].万历刊本.
[4]何乔新.椒邱文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4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
[5]桑悦.思玄集[M].万历翁宪祥刻本.
[6]高儒.百川书志[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7]高棅.唐诗正声[M].明嘉靖二十四年何城重刻本.
[8]高棅.唐诗正声[M].明嘉靖十七年康河重修本.
[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王世贞.弇州续稿[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8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
[11]王世懋.王奉常集[M].万历十七年(1589)吴郡王氏家刊本.
[12]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孙春青.明代唐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4]胡震亨.唐音癸签[M].周本淳,校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5]李攀龙.唐诗选[M].明闵氏刻朱墨套印本.
[16]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17]薛宝生.明代选家对其所选唐诗价值的定位[J].云南社会科学,2013,(2).
[18]薛宝生.唐汝询《唐诗解》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9]严羽.沧浪诗话[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0]郭绍虞.诗品集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1]张含.杜诗选[M].黄永武博士主编,杜诗丛刊(第二辑).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74.
[22]李默,邹守愚,编.全唐诗选[M].明嘉靖二十六年曾才汉刻本.
[23]曹学佺.唐诗选[M].明崇祯刊本.
[24]张逊业.唐十二家诗[M].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江都黄埻刻本.
[25]杨一统.唐十二名家诗[M].明万历十二年(1584)南州杨氏刻本.
[26]屠隆.白榆集[M].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
[27]唐诗选注[M].明万历三十三年世美堂刻本.
[28]黄宗羲.明文海[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
[29]李沂.唐诗援[M].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
[30]谢榛.四溟诗话[M].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31]张居仁.唐十二家类选[M].明万历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