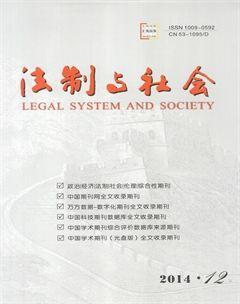朱熹的刑罚观及其影响探析
摘 要 朱熹的刑罚观是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刑罚观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刑罚合理性之论证;对“德”“刑”关系的新阐释;对重刑的推崇。朱熹的刑罚观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法制指导原则与法律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刑罚合理性 德刑关系 重刑
作者简介:卞京海,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文化。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2-007-02
朱熹的有关刑罚的观点是其法律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刑罚观与其它法律思想一样,都以其“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观为理论基础。笔者拟对朱熹有关刑罚的观点进行梳理,并对其刑罚观点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朱熹的刑罚观点
(一)朱熹对刑罚的合理性之论证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是孔子主张用道德和礼仪来教化百姓的经典表述。朱熹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认为,統治者治国理政当然首先要用“德”与“礼”来教化人民,但对于不服从“教化”或不服从“礼”的约束的人,则应该放弃教化,使用刑罚,以达到制止犯罪,维护“三纲五常”的目的。(1)在“德”“刑”与“天理”的关系上,朱熹认为,“德”与“刑”都是“天理”的表现,在维护三纲五常上是本质相同的东西。把“刑”看作是与“德”在其“天理观”体系中本质相同的东西,就是赋予了“刑”的某种合理性。(2)在“德”与“刑”的关系上,他认为,两者对于维护封建纲常伦教都是不可偏废的。他说:“若夫道德性命与刑名度数,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间,然其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则又不可得而分。” 这样,朱熹在其“天理观”的指导下,在承认“教化”与“刑罚”具有本末之分的基础上,认为“教化”与“刑罚”具有相同的作用,二者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同等重要。至此,通过(1)与(2),朱熹就在其“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体系中确认了刑罚的合理性。
笔者认为,朱熹之所以要首先论证刑罚合理性的问题,是因为在宋代之前,儒家虽然是一种外儒内法,但在对外宣传上一直以一种重“德”卑“刑”的姿态出现,如董仲舒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 《唐律疏议》更是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的法制指导原则。既然以前是卑“刑”,“刑”仅仅是政之“末”,若要使“刑”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必须从理论的层面对“刑”做出肯定的回应;(2)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需要。两者缺一不可。故解决刑罚合理性的问题既是为下面的“德”“刑”关系的阐释提供一种理论的合理性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什么要提高刑罚的地位,突出刑罚的作用。
(二)朱熹对“德”“刑”关系的新阐释
朱熹在对刑罚进行了合理性论证之后,对“德”与“刑”的关系进行新的论述:
首先,朱熹突出了刑罚对教化的维护作用,驳斥了以往重视教化、轻视刑罚的论点。他说:“如何说圣人专意只在教化,刑非所急?圣人固以教化为急,若有犯者,须以此刑治之,岂得置而不用!” 又说:“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虽尧舜亦不免。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戒,所谓‘以辟止辟。”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圣人并没有重教化、轻刑罚,圣人很重视刑罚对教化的维护作用。很明显,朱熹的这些言论,有点类似于法家的“以刑去刑”。朱熹提高刑罚的地位,突出刑罚的作用,最终目的还是在于维护封建伦常,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其次,在适用教化与刑罚时,朱熹主张两者并没有先后顺序之分。是先“教”后“刑”,还是先“刑”后“教”,必须根据维护“三纲五常”与统治者巩固统治的实际需要来确定。他说:“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无刑焉。盖三纲五常,天理各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根本也。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而其丁宁深切之意未尝不在乎此也。” 从朱熹以上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对“德”“刑”关系的新阐释已经打破了原来的“先教后刑”模式。在朱熹看来,“教化”与“刑罚”只是为维护“三纲五常”服务的,至于实施的先后顺序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处理。
(三)朱熹对重刑的推崇
有关朱熹的“德”与“刑”关系的观点,上面已经进行了论述。既然“德”与“刑”都是“天理”在世间的表现形式,并且“德”与“刑”在治国时的作用同等重要。那么,使刑罚在维护“三纲五常“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便没有理论上的障碍。实际上,朱熹关于刑罚的言论,已使他成为重刑的推崇者。他认为:“刑愈轻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长其悖逆作乱之心,而使狱讼之愈繁。” 前已论述,朱熹提高刑罚的地位,突出刑罚的作用,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常,那么,立法者制定残酷的法律,司法人员在执行刑罚的过程中即使造成“伤民之肌肤,残民之躯命” 的后果,也是正常的、合情合理的。不仅如此,朱熹还大力主张恢复肉刑,他认为;“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奸,而其过于重者则又有不当死而死。如强暴赃满之类者,苟采陈群之议,一以宫剕之辟当之,则虽残其肢体,而实全其躯命,且绝其为乱之本,而使后无从肆焉。” 从朱熹的言论可以看出,其主张恢复肉刑的原因是既可以“全其躯命”又可以“绝其为乱之本”,避免出现“不当死而死“的情况。表面上看来,朱熹恢复肉刑的原因似乎很正当。其实不然,朱熹主张恢复肉刑的本意是要借助刑罚的威慑力量,首先是使作乱者失去作乱的根本,其次是震慑其他社会成员,也就是最大限度的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作用。
除了从正面主张重刑之外,朱熹还通过驳斥“轻刑论”的途径来证明其重刑的合理性。他说:“今人说轻刑者,只见所犯之人为可悯,而不知被伤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盗杀人者,人多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为无辜,是知为盗贼计,而不为良民计也。” 朱熹认为轻刑论者是只考虑犯罪者,而不考虑被害者是无辜的,忽视了被害者及良民的感受。又说:“杀其人之所当杀,岂不是天理?”“如残贼之事,自反了恻隐之心,是自反其天理。” 按照朱熹的理解,犯罪者实施犯罪行为,是他们自己违反了恻隐之心,违背了天理,杀了他们是天理所要求的。换言之,轻刑论者同情犯罪者同样是违反了天理,那么轻刑也就同样不符合天理。
(四)小结
以上是对朱熹的刑罚观的论述。朱熹为了适应当时高度集权的政治的需要,也为了应对尖锐的阶级的、社会的矛盾,对儒家粗糙的“天命观“进行了系统化的哲理思辨,创建了自己的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朱熹的刑罚观乃至他的其他法律观念是其哲学思想在法律方面的必然逻辑结果。笔者想要强调的是,朱熹论对刑罚合理性的论证,对“德”“刑”关系的新阐释以及对重刑的推崇,都是出于维护“三纲五常”和天理的需要。他的理学为他的刑罚观及其他法律思想提供哲理支撑,而其刑罚观又在实践中强有力的维护着其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天理观,从而使朱熹的思想在中国封建后期的意识形态领域牢牢的占据着统治地位。
二、 朱熹刑罚观的影响
朱熹对“德”“刑”关系的新阐释以及对刑罚地位与作用的重视,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法制指导原则与法律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对封建社会后期法制指导原则的影响
众所周知,宋代之前的法制指导原则是“德主刑辅”,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成文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开宗明义的讲:“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德主刑辅”的核心是“重德”,强调道德教化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首要的与主体的地位;而刑罚只是起一种辅助作用,虽然并没有否定刑罚的必要性,但显然有贬低刑罚作用的倾向。但是, 如前所述,出于维护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需要,在其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理学指导下,朱熹对“德”“刑”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并且同时强调刑罚在治国中与教化的同等地位与作用。受他的这种刑罚观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指导原则由宋代以前的“德主刑辅”發展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刑弼教”。“明刑弼教”一词并不是朱熹创造的,而是古已有之。《尚书·大禹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仕,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 后人将其概括为“明刑弼教”一词。但是,在宋代以前,“明刑弼教”思想既没受到思想家的重视,更没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统治者的统治并没有受到过分的挑战,用道德教化仍然能够维护其统治的合理局面,根本不需要强调刑罚在统治中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明刑弼教”毕竟与传统儒家推崇的“德主刑辅”有明显的区别。虽然“明刑弼教”是受制于并最终服务于“德教”的,但是“明刑弼教”的核心含义是“重德而不轻刑”,强调的是刑罚在治国理政,尤其是在维护封建礼教方面发挥更大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基于此,朱熹对“德”“刑”关系的论述,对刑罚作用的强调,为“明刑弼教”思想从“默默无闻”走向“历史舞台”畅通了渠道,其代替“德主刑辅”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法制指导原则也就是必然的和合情合理的了。
(二) 对封建社会后期法律实践的影响
上已述及,朱熹的刑罚观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法制指导原则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此之外,朱熹的刑罚观还深刻的影响着封建社会后期的法律实践。概括的说,在朱熹刑罚观的影响下,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法律实践的“重刑化”倾向更加明显。笔者认为,这种影响带有很大程度的必然性。(1)朱熹本人就是重刑的推崇者,主张恢复肉刑,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主张“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 作为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主张自然会影响许多统治者的治国国策。(2)“明刑弼教”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法制指导原则,而“明刑弼教”往往与重刑主义有着联系。因为首先“明刑”的目的是为了“弼教”,刑罚的运用获得了道义上的支持。既然如此,只要是有利于“弼教”,刑罚过重也是合理的,元明清时期肉刑的复活,凌迟刑成为法定刑罚,便是有力的证明;其次,“明刑弼教”为君主维护其政治独裁与思想专制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明清时期“文字狱”的盛行便是明证,君主往往打着“弼教”的旗帜,对挑战其专制统治的文人,滥用法外酷刑,甚至株连九族。宋代以前,“重德”的立场对重刑有很大的抑制作用,所以,虽然各朝代刑罚总体状况仍然偏重,但是从秦汉至唐代,刑罚仍然呈现出由重到轻的趋势,尤其是唐律有“得古今之平” 的美誉。但是宋代以后,由于受朱熹的刑罚观的影响,不管是立法实践还是司法实践,都有十分明显的重刑化倾向。
注释:
孔子. 张燕婴译注.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6.13.
陆费逵. 四部备要·子部·朱文公文集·卷七0.上海:中华书局.1936.11.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95.23.
[唐]长孙无忌等. 刘俊文.唐律疏议.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2001.2009.
陆费逵.四部备要·子部·朱文公文集·卷一四.上海:中华书局.1936.1.
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11.212.
陆费逵. 四部备要·子部·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七.上海:中华书局.1936.22.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2712.
孔颖达. 尚书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2.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2689.
[清]纪昀,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