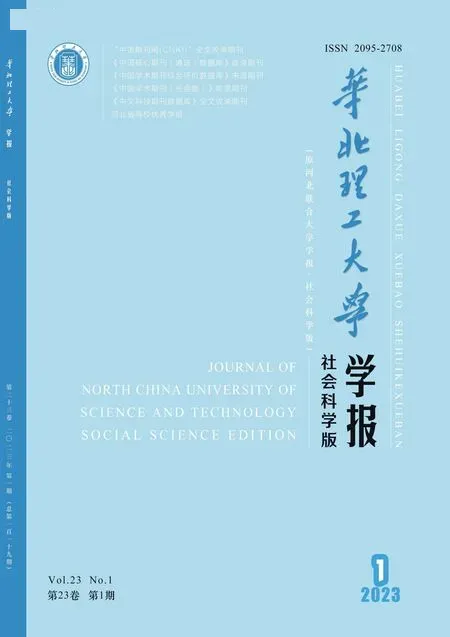重刑主义本体论
陈新委,王震
(吉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一、重刑主义缘起
当今社会,关于重刑的讨论不绝于耳,学者们认为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均在不同层度上有着 “重刑” 的倾向。只是对其核心概念—— “重刑” 的解读少之又少,对当今很多国家呈现的重刑立法倾向所隐含的刑法指导思想—— “重刑主义” ——的论述更少。重刑主义自古有之,其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而重刑的历史可能更加悠久。随着历史的发展,直至清末沈家本修法之前的历史时期均有着(传统)重刑主义的倾向,所谓的 “德主刑辅” 只是重刑下的一种 “优美” 修辞手法,是 “礼法交融” 现实状况下的粉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步入近代以降,民主自由主义的逐步觉醒和发展,重刑主义的现实反映在一定层度上有所减弱。但是近些年,由于恐怖主义的猖獗、贪污贿赂犯罪频发等原因,一些国家的立法及刑事政策普遍呈现重刑的倾向,重刑主义又回到或称为活跃在当代世界舞台。与之相关的刑法理论层面如敌人刑法、风险刑法及积极主义刑法观等是否是重刑主义披上神秘面纱的 “卷土重来” 亦未可知。更为关键的是,何为重刑主义或者说以前的重刑主义概念是否仍旧适用于今日之社会,是否应该存有新的概念释义对当代的重刑立法或刑事政策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尚无定论。
重刑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也必不从属于某一个时代或个人。其是由四个汉字所构成,其概念(内涵及外延)必然会随着时代发展、文明进步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充盈或部分剔除,从而呈现新旧不同的两种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前后两者毫无关联,相反却呈现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式的传承性或沿袭性,只是为了减少误解,将重刑主义分为传统重刑主义与修正重刑主义。但本文始终坚持,修正重刑主义更多的是对重刑主义内涵作时代性解释,不可避免的也会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通过对传统重刑主义的历史梳理及结合时代性,尝试对传统重刑主义进行重新解释,构建当代适用于部分领域立法、执法指导思想新的重刑主义——即修正的重刑主义。
二、传统重刑主义梳理
重刑主义内涵与外延的文字描述具有历史性,也就意味着对于重刑主义的具体概念、具体表现和特点应当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相对应,而不能以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其予以考察。同时,重刑主义也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一些内涵和表现具有古今通用的表述,如死刑。在本部分主要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考察古代重刑主义的具体表现,反思其当时存在合理性与不合理性。
(一)概念界定
重刑主义是一种法律思想,其具体的内涵要根据限定词 “重刑” 概念及所处历史阶段所确定。有学者认为,重刑指中国古代刑法中的严刑峻法的制度与思想;[1]也有学者认为,重刑主要包括不应当入罪而入罪、不应当施加刑罚而施加以及应当施加轻刑却施加重刑。[2]可以看到后者关于重刑概念的界定具有当代的特色,而不具有古代法制的历史性特点而难以认同。从主体角度而言,虽然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案件评判角度也可能呈现重刑的倾向,由于古代礼法合一的现实状况,将重刑主义的思想概括包含有社会民众思想会使得重刑主义的外延过于宽泛,也缺乏研究的可能性,故其主体不包括普通大众,而只能是国家机关。
因此,就传统重刑主义而言,重刑主要是指古代法制所呈现的严刑峻法,重刑主义是指在有权机关法制过程中所呈现的严刑峻法的 “态度” (包括入罪态度、刑罚态度及执行态度)。具言之,由于我国古代的法律呈现诸法合体的立法模式,其并不存在今日法律部门,也不存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划分,对于其具体表现的研究容易出现 “大杂烩” 的论述,需要结合当代刑法研究的成果,将其具体划分为三个维度,即入罪层面、刑罚层面、刑罚执行层面,对其分维度、分层面的研究便于古今对照,梳理古代法律所呈现的具体表现从中或借鉴运用或批判反思。
(二)传统重刑主义的历史梳理
1.入罪层面
入罪层面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从犯罪圈的角度即何种行为或侵害结果可以入罪方面梳理古代法制所呈现的重刑倾向,如罪及无辜、言论治罪。
(1)罪及无辜。其是指对于无辜或者说与案件毫无关联之人定罪处罚的连带责任处罚制度,即株连。其包含血缘株连(缘坐)、地域连坐、职务连坐等。连坐制度实质上是根据与犯罪人有关的血缘、职务、地域等因素确定扩大处罚范围的连带惩罚制度,具体对于被连坐人是否判处刑罚、处以何种处罚均有法律明文规定。如《唐律》规定 “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小字:子妻妾亦同)……没官。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 可以看到,缘坐制度中因犯谋反、谋大逆罪名而被连带的被连带人根据血缘关系的由近至远刑罚呈现由重到轻的趋势;年龄上,对其子以16岁为界限,以上则被判处绞刑,以下则没官;性别上,承担重刑罚的为男性,女性所判刑罚与与十五岁以下同。
通过将上述《唐律》内容对比,发现连坐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将犯罪行为人与其他人(被连坐人)通过一定的因素(如血缘、地域等)联系起来的联结作用,对于被连坐人是否进行处罚以及如何处罚则由具体法条进行规定,也就是说连带制度所起的作用是一种确定(扩大)处罚范围的制度,其本质上不能起到明确确定刑罚的作用。因此,该制度是扩大了入罪的范围并不是具体的刑罚执行,其属于入罪层面的内容。当然,本文所论述部分并没有穷举所有该制度的古代各朝代的所有法条,但观察亲属连坐(缘坐)、官吏职务连坐、邻保连坐等具体表现形式[3],其实质内核均为 “连坐” , “连坐是群体共同法律责任”[4]——即一人有罪、非犯罪关系的而有其他关系的无辜人均需承担责任的本质属性却是不容更改的。据此,可以认为连坐制度均属于入罪层面。
(2)言论治罪。其是指单纯以言论即可对说话的人进行定罪处罚。与当代的言论入罪具有本质不同,当代言论入罪需要具有对法益的侵害或者侵害危险,如日本刑法的伪证犯罪就要求 “虚假陈述等有侵害裁判以及惩戒处分这种国家审判职能之公正的危险”[5]。我国古代言论治罪并不需要具有侵害结果,甚至不需要造成侵害的危险。
文字是内心所想的外在承载方式,我国古代各朝统治者对于语言、文字的态度是不同的。如唐朝杜甫在其《兵车行》中对唐玄宗穷兵黩武之举的批判未获罪,宋朝洪迈认为唐朝人的诗歌针砭时弊无所避讳[6]。而由于言语或文章获罪的规定与实例也多有之。如《大清律》规定 “凡骂人者,笞一十。互相骂者,各笞一十。”
具体案例最为人知的当属 “文字狱” 。文字狱自古有之,我国最早的文字狱为公元前548年齐国史官因客观书写历史而被权臣崔杼杀害,至北宋典型的文字狱有进奏院案、乌台诗案、刘挚书信案、黄庭坚碑文案等。[7]文字狱在明清时期发展至 “顶峰” 。整体来看,文字狱是统治者从思想文化领域禁锢文人的思想,稳固自己统治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手段却将本不应该纳入刑法规制范畴的行为纳入进来,过度扩张了入罪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处所指的言论治罪不同于 “言论治重罪” ,从关系上讲二者是时间顺序的不同或者是所属的刑事诉讼程序阶段的先后不同,前者是指对于不应当入罪的行为而纳入刑事法律的规制范围,其回答的是否要纳入刑法评价范围的问题;后者是对于言论入罪以后对其判处较重的刑事处罚,所关注的是入罪以后判处什么样刑罚的问题。
2.刑罚层面
我国古代封建王朝在具体执政过程中崇尚报应主义,民众也多信奉因果报应。古代各朝代基于报应主义思想,即便是和平时代,其所制定的刑罚也大多较重,死刑众多、肉刑发达、言论治重罪、轻罪重罚等。以死刑为例,在清朝刑律改革之前,死罪就有840条。[8]
肉刑发达,现在一般将五刑分为奴隶制五刑和封建制五刑,前者是以肉刑为核心的刑罚(种)。苗民制五刑,劓、刵、椓、黥、大辟,前四者均为肉刑。根据文史资料,在商代墨、劓、剕、宫、大辟的五刑已有记载,到西周五刑适用较为普遍。[9]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严重原始、野蛮色彩的肉刑在汉文帝时期被废除而逐步趋向文明。[10]其后有的朝代依然规定有肉刑,但汉文帝废除肉刑举措的进步性不可否认。
在四个肉刑当中,前三个为耻辱刑,指产生羞辱效果的刑罚[11];后者是一种 “反映刑”[12],即对犯人犯罪时使用的身体部位直接加以伤害的刑法。
耻辱刑以墨刑为例,其是指对犯罪行为人面部刺字的一种刑罚,后期该刑种逐步扩大或变种发展为刺字法。在清朝规定已达完备,详细规定了墨刑的适用范围、刺字的范围、刺字的内容、对于部分罪名的初犯及再犯刺字要有所区分等,直至清末法制改革才彻底予以废除。[13]该刑种在执行以后,在古代医疗技术、条件不发达情况下,该犯罪标识是难以通过科学医疗手段予以抹掉,是一种终身的耻辱标志。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大多数人生活范围有限,犯人一旦被刺字,其在生活范围内的社会评价会形成否定评价,一生都难以改变。即便在一些情况下脱离了现有的生活范围而到达新的地方,其身体上的刺字所附带的否定评价也难以在新的生活环境改变。但是事极必反,对大量的犯罪人适用该刑,特别是当身边人大多被刺字的情况下,势必在会导致该罪的社会否定评价影响——耻辱刑的耻辱感降低,难以发挥其刑事惩罚效果。
反映刑以不能再犯同一种罪的理念对犯人去除第一次犯罪的 “工具” ,如以手盗窃断其手。具体到宫刑而言,《尚书正义》记载 “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次死之刑。”[14]对男子实行宫刑的处刑方式也经历了从 “椓” 到 “割势” 的过程,其是由于时代发展、金属制品的出现而改变。[15]由最原始的击打到后期金属切割,虽然同样都很残忍,但其也 “无可奈何” 地体现了时代文明的进步。
3.刑罚执行层面
刑罚执行层面主要梳理历史上各朝代对于犯罪人确定刑罚后执行处罚刑种的具体方式和是否公开执行。包括死刑执行方式残酷、执行公开等。
我国历史上对犯人执行死刑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炮烙、焚、沈河、陵迟、支解、磔、要斩、枭首、斩、戮尸等。执行方式各异、残酷性与轻重各异,其所体现的野蛮、非人道性是需要时刻予以警惕的。
执行公开。从今日之法律角度,执行公开是一个 “优美” 的词语,只是古时所公开的内容今日看来并不 “文明” 。在这里执行公开指对于刑罚(死刑)的执行应当对民众公开。古代历朝历代对于刑罚执行的公开是威吓民众的需要。无论是执行场所的开放、参与主体的公开亦以及执行过程的公开致死刑执行具有了一定的仪式性,在一定层度上告知民众 “恶有恶报” 的理念并予以强化,其特有的仪式品性反应了 “重刑” 观念的社会基础。[16]
(三)小结
正所谓客观决定主观,上述入罪、刑罚及执行三个层面的实践都是重刑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反映与对照,是重刑主义最为真实也是最为客观的写照。当然还需要阐明的是,对于重刑主义的认知是站在当代的角度去梳理我国古代各朝代的立法、司法及执行层面,其在当时或者说在当时民众心理是否属于重刑并不具有必然性。
站在今日的角度观之,传统的重刑主义在上述三个层面都有着明显而且具体的表现,其近乎无限制地扩大入罪范围、扩大犯罪圈,严厉而又严酷的刑事惩罚以及不人道、不文明的刑罚执行方式,都是需要反思及剔除的部分。但是,其对于部分犯罪实施墨刑所体现的 “标签” 惩罚与美国《梅根法案》中的性侵犯罪人个人信息公告制度在本质上似乎暗合,韩国的化学去势(化学阉割)惩罚与宫刑似乎只是执行方式上的区别,新加坡的鞭刑与古代的笞、杖刑神似,这些也是我们需要警惕和反思的。
三、修正重刑主义构建
在结束封建统治,步入近现代社会以来,民主、自由等思想开始觉醒,传统重刑主义似乎已经不应该有出现或适用的余地,但不可否认的是重刑主义仍旧存在于当今的国内外立法、司法及执行当中。只是部分重刑主义的内容与当代而言缺少合理性而没有了适用的余地,而且还在理论层面出现了新分类——酷刑,都在一定层度上冲击了传统重刑主义的内涵。为此,需要结合当代实际构建修正的重刑主义,为当代一些国家或地区的重刑化倾向进行理论层面的反思。
(一)概念界定
如何界定重刑主义,需要界定何为重刑,修正重刑主义与传统重刑主义又有何种区别等内容。
1.重刑的概念界定
原则上赞同前述第二种关于重刑概念的界定,其主要内容涵盖了上述入罪层面及刑罚层面的两个内容,但是却并未涉及执行层面。因此,重刑主要是指基于人道主义下的不应入罪而入罪、不应施刑而施刑、应当施加轻刑却施加重刑以及应该秘密执行而公开执行。
2.修正重刑主义概念界定
修正重刑主义是指以人道主义为指导,在符合刑法基本原则前提下,立法者、司法者及执行者对于部分具有法益侵害或侵害危险的犯罪行为(如危害国家、恐怖主义犯罪及严重人身侵害等)相较于其他犯罪行为在入罪层面、刑罚层面及刑罚执行层面等阶段(以下简称 “三层面” )秉持的从严、从重处理的思想、 “态度” 或理念。
3.修正的重刑主义与传统重刑主义的联系与区别
二者在内涵与形式上具有相通性,即二者都是针对一定的犯罪所持的从严、从重的处理理念,都涉及刑事领域的各个阶段。
但是二者更多的是不一致性。首先,本质不同。修正重刑主义是人道性(主义)的产物,而传统重刑主义缺少人道本质。从报应论的角度来讲,我国古代的法律规定与实践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行刑的等价性奠定了古代法制的整体基调,其所制定的剥夺生命、毁损身体、剥夺性行为能力、体罚、剥夺人身自由等刑法都具有合理性及正当性,但是其却忽略了人道性(人道主义)对刑罚报应性的修正作用。所谓人道性要求给犯罪人以人道待遇、不剥夺其作为人所不应受剥夺的权益,从制刑角度上述的前四种刑罚都不具有人道性。[17]刑罚人道主义是刑事政策的重要内涵,也是刑法适用的一项基本价值观,同时也是对国家刑权力运作所提出的一个道德义务。[18]故而可以说,人道性(主义)是对我国古代坚持刑罚报应观念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修正,同时也对当今各国进行上述 “三层面” 阶段相关活动时,必须时刻注意在符合报应观念的基础上是否符合人道主义的本质要求。
其次,修正的重刑主义具有法定性。就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3个基本原则是当代我国任何机关在进行刑事活动都不得违背的原则,自不需多加赘述。而传统重刑主义由于皇帝至上,皇帝凌驾于法律至上,自然在一定层度上会出现对法律规定的冲击和破坏。
最后,两者的适用范围不同。修正的重刑主义并不适用于所有犯罪,其适用范围应当有所限缩。基于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标准,首先应当排除自然犯的适用,其只能适用于部分法定犯。由于自然犯具有悠久历史与民众的法道德或朴素法感情之间结合呈现 “礼刑交融” 的现实情况,民众对于此类犯罪在日常生活中对其罪状耳濡目染的具有认知并融合进自己的道德评价。换言之,经过多年的发展,自然犯罪的立法大多趋于稳定,法条的规定、刑罚的配置形成普遍认知、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司法实践数据支撑,对于此类犯罪就不应当予以改动,甚至大范围加重其法定刑。而对于法定犯由于时代的快速发展其内涵也在一定层度上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变,甚至部分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于这类犯罪在 “三层面” 阶段可以引进重刑主义。而传统的重刑主义则不然,如连带制度。
(二)酷刑修正下的重刑主义
1.酷刑概念
有学者认为,酷刑指通过对人身体或身体的特殊部位的摧残,使受刑人感到痛苦、死亡或人格丧失尊严来达到承接目的的刑罚,也即(中国)古代酷刑。[19]
酷刑指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之人唆使、同意或默认他人,故意对实施对他人肉体上和精神上产生巨大痛苦的行为,[20]且法定的刑罚皆不是酷刑。即国际公约所确定的酷刑。
2.具体修正
酷刑始终是全人类应当反对的一种刑罚,无论如何都应当予以反对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古代酷刑,还是国际公约所确定的酷刑概念,都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但由于本文重刑是对一国刑事法律规定的审视,与国际公约的酷刑关联性较弱,在本部分的酷刑主要指古代酷刑。
从古今对比角度来看,由于这些刑罚或刑罚执行方式本身所具有的残酷性、非人道性而为现代文明所抛弃。按照该定义,古代刑罚及执行方式——墨、剕、宫、笞、杖以及死刑执行方式、执行公开等属于酷刑的范畴。
对传统重刑、古代酷刑以及修正重刑主义的定义予以梳理并将三者进行对比得出结论,修正的重刑主义脱胎于传统重刑,而又对古代酷刑有所摒弃和抵制,其本质内核才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和当代适用性。换言之,抵制古代酷刑所呈现的 “恶法非法” 理念对传统重刑进行改造,修正的重刑主义内涵也理所当然的内含抵制古代酷刑的基本要求和理念。当然,由于酷刑定义本身所具有的地域范围限制,国情不同造就认知理念不同,立足于我国国情及我国历史传统,通过域内外刑事法的对照,对当代部分国家或地区在刑事法当中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规定和适用古代酷刑的立法或司法予以警惕(而非完全否定),提出酷刑对重刑的修正路径。
酷刑对重刑主义的修订体现在立法前、立法后各个阶段。具体来讲,在立法前,域外立法是否适用于我国、是否应当在我国进行立法规定而进行法律移植,以国外 “化学阉割” 的规定为例,其能否适用于我国应先审视其本身是否属于酷刑的范畴,如果认为该刑罚属于酷刑,则不应当规定与适用;如果不属于酷刑,再思考其是否属于重刑的范畴。在立法后,虽然某一规定已经经过法定程序写入法典当中而具备了合法性,但是还需审视其是否属于酷刑。如果属于酷刑,应当及时启动修法程序予以废止;如果不属于酷刑,则应在重刑主义范畴内思考其具体的应用与实践。
因此,对于某一法律规定,酷刑起到甄别及剔除的作用,酷刑作为重刑的 “鉴别员” 而存在。换言之,修正重刑主义在具体实践落实过程中都是在排除酷刑基础上的具体适用。酷刑的存在与否或者说是否符合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修正重刑主义与传统重刑主义的核心区别所在。
(三)修正重刑主义下的 “三层面” 分析
修正重刑主义对部分犯罪行为人应当从严、从重惩罚,但是其应当坚持基本的当代刑法价值、理念与原则,其相对于传统重刑主义在 “三层面” 坚持不同的原则与理念,分述如下:
1.入罪层面
犯罪行为应当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或者社会危害性,完全没有侵害结果或者侵害危险的行为不得入罪。另外,需要坚持罪责自负原则,没有实施危害行为的人,不得将其作为犯罪嫌疑人,不存在罪名上的 “莫须有” 。
2.刑罚层面
在预防主义的修正下,传统的、对等的 “以眼还眼” 的同态复仇理念不应再适用于今日之刑罚。应当摒弃耻辱刑、身体刑,反映刑中应抵制肉刑、慎用死刑。国外一些国家规定的 “化学阉割” 刑罚,虽然有的将其表述为 “性犯罪者性冲动的药物治疗” 手段,但是其以身体本身作为处罚结果承载者的刑罚仍旧值得警惕。
3.刑罚执行层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刑罚执行应当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秘密性,鲁迅先生笔下 “蘸人血馒头” 的愚昧封建的事情不应再出现。另外,在刑罚执行方式、方法上应当人性化,关于死刑的执行方式自清朝光绪帝以来逐步走向文明,而后逐步确立枪决执行方式,再到逐步走向注射死的执行方式。同时,上述肉刑、身体刑的执行方式也随着刑种的废除而废除。
四、总结
传统重刑主义与修正重刑主义的区分更多只是为了表述两者所具有的区别性,也是为了表达二者所具有的时代传承性,而不是为了将他们进行割裂。为重刑主义 “正名” ,从理论上为当代刑事立法及刑事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对部分犯罪所秉持的 “重刑主义思想” 具有合理性、正当性。诚然,我国历史上的重刑主义思想及实践,其所体现的残酷性、非人道性应当予以剔除。当今世界各国刑法、刑事政策在不同层度上所体现的重刑(化、趋势)需要正确认识和甄别其内容,不应当一概予以否决,需要将当今时代与古代的 “重刑” 进行不同的理解,不可等同。
修正的重刑主义本体论,是在反思古代重刑主义具体表现出的残酷性基础上,结合当代域内外立法实践所进行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回答。其回答了在当代何为重刑、何为重刑主义的基础上,以酷刑这一 “先锋甄别员” 对当代刑事立法、司法进行鉴别、保留与剔除,发挥修正重刑主义在当代入罪、刑罚、刑罚执行层面所具有的科学指导性。修正人们所秉持的重刑主义 “妖魅化” 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