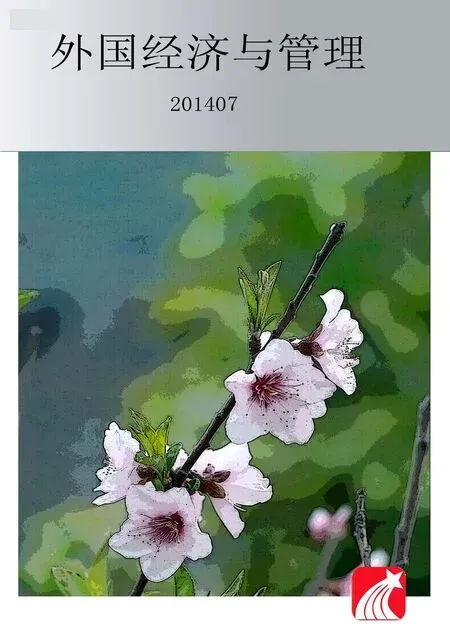流动性转移与永久性迁移:影响因素及比较
——基于上海市1446份农民工样本的实证分析
程名望,史清华,许 洁
(1.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92;2.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52)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持续进城务工,为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陈钊和陆铭,2008;蔡昉,2010)。以是否有户口伴随为根据,可以将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分为两大类。没有户口伴随的为流动性转移①流动性转移也被一些学者称为非正式迁移、短暂性迁移或“候鸟式”迁移(杨云彦,1996;姚婷等,2013),本文不严格区分这些称谓,并统一采用流动性转移这一概念。,有户口伴随的为永久性迁移(杨红,1999)。就现实情况看,转移者以流动性转移为主,永久性迁移比例极低(姚婷,等,2013)。因此,研究农民工的流动性转移和永久性迁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差异,对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乃至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和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做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一些成熟的理论和广为接受的实证结果。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因素。Lewis(1954)、Fei和Rains(1961)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之间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及由此决定的工资率差别导致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迁入城市。Jorgenson(1961)从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认为,农业剩余和消费结构变化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根本原因。Todaro(1969)、Harris(1970)重视“预期收入”的作用,认为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别是劳动力迁移的根本原因。Stark(1991)则认为相对贫困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动因,从而开创了以家庭投资组合理论和契约理论为代表的“新劳动力转移学说”。最新的研究则更多地关注于非经济因素。一是制度和政策因素。Ahituv和Kimhi(2002)、Knight和Gunatilaka(2010)的研究表明,户口与社会保障等制度因素对农民工就业选择有显著影响。二是城镇歧视因素。Majunmdar等(2004)、Démurger等(2009)、高文书和Smyth(2010)、Nielsen等(2010)强调了城镇歧视导致的不满意感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重要障碍,认为社会歧视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巨大,会对农民工形成心理困扰并产生不好的就业行为。三是子女教育因素。钱文荣和张黎莉(2009)、Goodburn(2009)、Mancinelli(2010)关注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认为生活在城镇的农民工子女面临心理健康等很多不利因素,成为农民工就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医疗与健康因素。Cros等(2008)、Yao(2010)等认为健康和被排斥在城镇医疗体系之外是农民工面临的重要问题。
通过与以上已有文献的比较,本文的创新和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学者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但已有研究并没有严格区分流动性转移和永久性迁移。而实际上,流动性转移和永久性迁移不仅在转移形式上有所差异,而且其影响因素可能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本文区分这两种转移形式并比较其影响因素差异,对于农民工从流动性转移到永久性迁移的本质性转变,以及城镇化道路的路径选择,均具有借鉴意义。第二,无论是流动性转移还是永久性迁移,必须考虑决策主体(农民工)自身的想法。因为农民工是理性的,他们会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自身或家庭的转移决策,城镇究竟要为其提供什么样的收益或福利以吸引其永久性迁入?农民工对于永久性迁入的根本诉求有哪些?倾听农民工本身的想法和诉求,将有利于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基于此,本文采用微观调查数据,以城镇化推进为目标,从决策主体(农民工)自身的诉求与行为视角进行研究。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特征分布
数据来源于2009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对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查。调查涉及农民工在沪的居住与出行、就业与子女教育、生活消费与城市认同以及相关政策执行等六个方面,共获取有效样本1446个。调查覆盖上海全部的城区和郊区,有效样本中有32.78%来自上海市中心城区,有67.22%来自上海郊区。样本就性别分布看,男性占60.58%,女性占39.42%。就年龄分布看(见表1),最大为62岁,最小为16岁,平均年龄31.80岁,整体呈正态分布状。就文化程度分布看,呈现一种以初中为中心的典型正态分布,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占12.93%,初中占49.31%,高中占17.29%,中专及以上占20.47%。就来源地分布看,共涉及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样本集中度超过20%的省有两个,一是安徽,占27.04%,二是江苏,占20.54%;若从全国六大行政区角度看,华东地区是上海农民工来源地的主体,占66.04%;其次是华中地区,占15.21%;第三是西南地区,占13.21%。

表1 样本农民工的年龄与文化程度分布
(二)研究方法
根据数据类型,本文采用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和Probit模型的建模和分析方法。首先,对于流动性迁移,由于本文调研的1446个样本是在沪农民工,均属于已经实现流动性转移的样本,无法按照“转移”和“非转移”进行虚拟变量赋值,因此采用“就业满意度”作为替代变量,以衡量其流动性转移意愿的强弱。根据调查问卷,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按5个等级进行划分,依次是“很不满意”、“不太满意”、“感觉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点量表尺度进行测量,分别赋值为“1”、“2”、“3”、“4”、“5”,代表满意程度逐渐有序升高,因此适宜于采用有序Probit模型。以就业满意度衡量流动性转移意愿的有序Probit模型的可行性及其原理(详见程名望等,2012)。
其次,对于永久性迁移,采用“永久性迁移的意愿”作为替代变量。该变量采用调查问卷中“您对将来有何设想”做替代变量,答案项中“在上海安家立业”表示有永久性迁移意愿,赋值为“1”,“有钱后返乡生活”、“学好技术去其他地方发展”等其余4个答案项表示没有永久性迁移意愿,赋值为“0”。于是,被解释变量是二元虚拟变量,适合采用Probit模型。Probit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具体可见蔡昉和都阳(2002)、都阳和朴之水(2003)等论著。根据以上变量设置,建立模型如下:

方程(1)是有序Probit模型,被解释变量是城镇就业满意度,用来衡量流动性转移意愿。方程(2)是Probit模型,被解释变量是永久性迁移意愿。X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系列影响流动性转移或永久性迁移的因素。同时引入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共有两类,一是控制区域差异,用R表示,包括“输出地(eregion)①输出地共涉及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了划分,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赋值为“0”、“1”、“2”。”和“输入地(iregion)②由于样本均取自上海,输入地的划分是基于调查问卷中的行政区域,它覆盖了上海全部的城区和郊区,其中,城区(包括黄浦、卢湾、徐汇等11个)赋值为“0”,郊区(包括闵行、松江、原南汇等10个)赋值为“1”。”两种区域变量;二是控制样本的异质性,用 H表示,包括“性别(gender)”、“年龄(age)”、“受教育年限(education)”、“婚姻状况(marriage)”和“健康状况(health)”等5个个性特征变量。i表示第i个样本,μ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流动性转移与永久性迁移的影响因素:一致与差异
(一)核心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在方程(1)和方程(2)中,对于核心解释变量X的变量选择,由于问卷调查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和繁杂,和农民工迁移意愿相关的测量项多达52项,所以不可能粗浅地把这52项都作为解释变量。针对以上情况,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该种方法也被马明等(2005)运用于就业满意度和就业意愿问题的研究。主要步骤是:应用SPSS16.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经过方差最大化旋转后,根据因子载荷矩阵(Rotated Component Matrix),得到7个主成分③由于初选的测量项多达52项,所以要不断精炼以得到最后的主成分。具体方法是:先进行第一轮主成分分析,把不显著的测量项(即因子载荷低于0.5的测量项)全部删除,然后进行第二轮主成分分析,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测量项都显著(即因子载荷大于0.5)。本文共进行了5轮主成分分析,最后精炼出7个主成分(即因子)。,将因素负荷值低于0.5的测量项目全部删去 (Price,1997),得到核心解释变量的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表2中的变量,即是经过主成分分析法精炼出来的解释变量。根据主成分方程(Principal Component Equation),计算出每个主成分的数据。在计算过程中,考虑到不同测量项原始数据绝对值的较大差异可能会对计算结果有显著影响,对涉及的连续变量按照虚拟变量的思路进行了分段处理和赋值。例如:“年龄”按照10岁一个年龄段进行处理;“月均收入”、“月均消费”、“学费”按照1000元一个收入段进行处理等。需要说明的是,参与主成分分析的52个变量的巴特利特球体检验(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值是231,其对应的相伴概率值是0.000;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值是0.723,7个主成分的累计解释方差达到56.028%,这表示本组数据具有良好的结构化效度,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表2 解释变量的主成分分析结果(N=1446)
采用以上主成分分析得出的数据,分别根据方程(1)和方程(2)建立计量模型(1)和模型(3)。同时,为了深入考察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及解释变量相互作用后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交叉变量,建立模型(2)。交叉变量包括模型(1)中显著的3个核心解释变量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3个核心个性特征变量形成的9个交叉项。在模型(3)的基础上,引入交叉变量,建立模型(4)。交叉变量包括模型(3)中显著的6个核心解释变量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3个核心个性特征变量形成的18个交叉项。以上4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3。
(二)回归结果分析
对于表3的计量回归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1.流动性迁移意愿
就模型(1)看,在选定的7个核心解释变量中,仅有“生活状况(life)”、“工作本身(job)”和“精神生活(happiness)”3个解释变量显著。这表明,生活状况、工作本身和精神生活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3大核心因素。生活状况越良好(例如较好的居住条件、便利廉价的交通等)、工作本身越满意(例如适合的工作时间,良好的工作福利等)、精神生活越丰富(例如丰富的业余生活、方便的就医条件等),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就越高,流动性转移的意愿越强。同时,“子女教育(education)”、“制度与政策(policy)”、“城市融入(integration)”和“收入与消费(income)”4个核心变量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对于短期就业而不是长期居住的农民工而言,他们更多的是关注短期利益和目前的生活,子女教育、制度与政策、城市融入等长期因素并不是其关注的核心。例如,对于“子女教育”,统计性描述分析表明,农民工最关注的是“孩子在上海上学容易办理吗”1个测量项,对于“孩子就读的学校类型”、“上学支付的费用”等测量项的敏感度都十分低。这表明,针对子女教育问题,对于仅仅是流动转移的农民工来说,其要求并不高,只要城市能给子女提供上学机会,他们就很知足了,至于就读何种学校、费用高低、教育质量如何、孩子是否适应等深层次的问题,他们並不奢求。

表3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续表
在模型(1)中,“收入与消费”这一与农民工短期利益和目前生活息息相关的变量不显著,似乎难以解释,但个案专访和统计性描述分析给出了较好的答案。就调查样本看,2009年,在沪农民工月均收入是2009.21元,低于当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月工资2728元,更低于当年上海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月工资5296元(中国统计年鉴,2010)。在沪农民工月均消费是666.71元,占其月均收入总额的33.18%,其中,食品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46.49%,即农民工的恩格尔系数是46.49%,达到小康水平①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由于仍远高于当年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37%(汝信等,2009)。由此可见,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城镇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使得农民实现了小康生活;但和城镇居民相比,其生活还处在相对贫困状态。但多年城乡差距的鸿沟很难在短时间内抹平,农民工只能接受和城市职工间存在的收入差异。农民工依旧保持着农民知足常乐的心态,对于收入和消费,他们不是城镇职工和市民比,而是跟自己在家务农相比较。较低的参照系,使得农民工对于在沪的收入有较高的满意度,从而使得“收入和消费”不是影响其就业满意度的核心变量。进一步分析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发现,食品消费在农民工生活消费中占比最大,占全部消费支出的46.49%;其次是住房支出,占17.79%;第三是交通通讯支出,占9.02%;第四是煤水电支出,占6.64%;第五是子女教育支出,占5.40%;第六是医疗支出,占4.68%;文化娱乐等精神需求的支出仅仅占0.71%。由此可见,农民工精神需求的支出比例极低。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尚未满足的需求才能产生激励作用,精神需求被扼杀的农民工具有强烈的精神需求意愿,从而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在模型(3)中,“精神生活”的系数是最显著的,其Z值在7个核心变量中最高,达10.94。该结论与Knight和Gunatilaka(2010)、伍中信和徐莉萍(2011)的研究相一致。
就模型(2)看,加入交叉变量之后,仅有“happiness*education”一个交叉项显著。这表明,首先,精神生活对城镇就业满意度的影响,依赖于教育这一变量。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其对精神生活的要求越强烈,精神生活对其城镇就业满意度评价的作用显著增强。而“生活状况”和“工作本身”2个变量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不依赖于教育水平,即无论农民工教育水平如何,“生活状况”和“工作本身”对城镇就业满意度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同时,无论男女和年龄大小,“精神生活”、“生活状况”和“工作本身”对城镇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均表现出一致性的趋势和特征。
2.永久性迁移意愿
就模型(3)看,在选定的7个核心解释变量中,仅有“生活状况(life)”1个解释变量不显著。这表明,和城镇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不同,若要选择永久性迁移,农民工考虑的因素会增多,“子女教育(education)”、“制度与政策(policy )”、“城市融入(integration)”、“收入与消费(income)”、“工作本身(job)”和“精神生活(happiness)”都将是其关注的因素。其中,“收入与消费”最显著(Z值为6.08),这表明,若要永久性地迁移到城镇,生存问题和经济因素是农民工关注的第一因素。与简单的候鸟式的城镇就业不一样,农民工对于收入水平的比较,将不再以务农收入为参照系,而是以城镇居民收入为参照系,其对收入水平的要求会显著提高,因为目前的就业收入显然不足以支撑其在城镇安家立业。“城市融入”的系数显著性排在第2位,表明若要选择永久性迁移,农民工将十分关注城市融入问题,即是不是能被城镇和城镇居民接纳,是不是会受到制度歧视和精神歧视等,将是迁移者最关注的核心因素之一,该结论与李迎生和刘艳霞(2006)、Knight和Gunatilaka(2010)的研究相一致。“子女教育”的系数显著性排在第3位,表明对于选择永久性迁移的农民工而言,子女教育及其对应的教育政策将是其关注的核心变量。
就模型(4)看,加入交叉变量后,仅有income*gender、integration*gender、education*education、policy*education四个交叉项显著。这表明,首先,收入和消费、城市融入对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依赖于性别这一变量。和男性相比,女性对于对收入和消费、城市融入的要求更强烈,对应地,这2个变量对其城镇就业满意度评价的作用更显著。其次,子女教育、制度与政策对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依赖于教育这一变量。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其对子女教育、制度与政策的关注更强烈,对应地,这2个变量对其城镇就业满意度评价的作用更显著。最后,6个核心解释变量与年龄的交叉项均不显著,表明6个核心解释变量对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不依赖于年龄这一变量。即无论是老一代还是新一代农民工,收入和消费、城市融入等6个核心因素对其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均表现出一致性的趋势和特征。
3.控制变量的影响
就区域变量看,在几个计量模型中,“输出地(eregion)”均不显著,但“输入地(iregion)”在模型(1)中是显著的。这表明,无论是对于流动性转移或永久性迁移,输出地的影响均不具有解释力,但输入地则有一定影响。就个性特征看,在模型(1)中,“性别(gender)”、“年龄(age)”、“婚姻状况(marriage)”3个变量显著,女性、年龄较小、已婚的农民工,对城镇就业的满意度较低,流动性转移意愿较弱。“文化程度(education)”变量的不显著,则表明目前农民工城镇就业仍旧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对知识和学历的要求并不高。在模型(3)中,“性别(gender)”、“文化程度(education)”、“健康状况(health)”3个变量显著。女性文化程度较高、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民工,永久性迁移的意愿更强烈。该结论和Furnham等(2002)、Clark等(2008)的研究一致;而与高文书和Smyth(2006)的研究结论差异较大。
四、结论与评述
2004-2014年,连续11个涉农“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而“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离不开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顺利转移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作为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主角,农民工自身对于迁移的诉求究竟是怎样的?这值得学界和政府深入研究和关切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城镇化推进为视角,以对农民工的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了农民工流动性转移和永久性迁移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研究发现:
(一)生活状况、工作本身和精神生活是影响农民工流动性转移意愿的3大核心因素。改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例如改善其居住条件、交通状况等;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工作,例如避免超负荷的工作时间、良好的工作福利等;改善其精神生活,例如丰富的业余生活、方便的就医条件等,将提高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流动性转移意愿。
(二)与流动性转移的影响因素不同,若选择永久性迁移,农民工考虑的因素会增多。子女教育、制度与政策、城市融入、收入与消费、工作本身和精神生活都将是其关注的因素。其中,收入与消费、城市融入和子女教育是最显著的3个核心变量。由此可见,农民工永久性迁移和流动性转移的影响因素有相同点,但差异更明显。总的来看,城镇就业是基于流动性转移的一种城镇生存状态,城镇就业满意度仅是农民工对当前就业和生活的短期评价,其3个核心影响因素(生活状况、工作本身和精神生活)有明显的得过且过、知足常乐的短期性考虑;而永久性迁移意愿是农民工对未来城镇就业和生活的渴望和预期,其3个核心影响因素(收入与消费、城市融入和子女教育)有明显的安家立业性质的计划性和长期性考虑。比较而言,相对于流动性转移的短期评价,农民工对永久性迁移的预期和评价更慎重、要求更高。因此,要促进农民工从“候鸟式”迁移到永久性迁移的转变,实现农民市民化和城镇化发展,就要适应农民工永久性迁移的要求,在收入与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城市融入等方面设计支持性的政策,特别是要尽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三)就区域变量来看,在所有模型中,输入地(迁入地)的显著性均显著高于输出地(迁出地)。这表明,首先,输出地(即农村)因素已经不是影响农民流动性转移或永久性迁移的核心因素,其核心影响因素在输入地(即城镇),该结论和程名望等(2006)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因此,减免农业税、种粮补贴、大型农机补贴、土地流转等系列农业政策,都不是影响农民工迁移的关键因素,因此也不是影响我国城镇化的关键因素。促进我国农民工永久性迁移,实现城镇化目标,其根本的动力在于城镇的吸引力。因此,政府应该从制度设计入手,尽快改善农民工向城镇迁移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制定有利于农民工在城镇安家立业的系列政策,改善农民工在城镇的生存状态、就业环境和劳动条件,应该是政策制定的根本落脚点。很有意思的一点结论是,在模型(3)和模型(4)中,输入地对农民工永久性迁移的影响不显著。随后的个案专访对该结论做出了很好的解释,即:如果条件具备(例如有良好的就业和收入,公平的子女入学,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农民工对永久性迁入城镇的意愿是强烈的,但其对所迁入的城镇并不挑剔,只要是城镇,无论是繁华的中心城区,还是较偏远的郊区,农民工都有较强的迁入意愿。此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若仅就迁移主体(农民工)的意愿来看,对于城镇化道路的选择,无论是走大城市之路,还是小城镇之路,抑或大都市圈之路,都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这使得我国城镇化模式具有较多的选择性,对应的政策回旋余地也较充分,甚至可以采取“多路共选,齐头并进”的策略,以快速推进我国的城镇化水平。
(四)就个性变量来看,性别、年龄、教育等个性特征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性转移或永久性迁移均有显著影响,表明不同个性特征的农民工在外出务工或永久性迁移决策上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因此,促进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迁移到城镇,不仅要有制度安排,更需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劳动力总体素质,增加其在城镇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性转移或永久性迁移。
[1]Avner A and Ayal K.Off-farm work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decisions of farmers over the life-cycle:The role of heterogeneity and state dependenc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2,68(2):329-353.
[2]Charlotte G.Learning from migrant education:A case study of the schooling of rural migrants children in Beij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2009,29(5):495-504.
[3]Clark A E,Frijters P and Shields M A.Relative income,happiness and utility: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8,46(3):95-144.
[4]Fei C H and Ranis G A.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9):321-341.
[5]Furnham A,Petrides K V Jackson C J and Cotter T.Do personality factors predict job satisfaction[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2,33(8):1325-1342.
[6]Harris J R and Todaro M P.Migration,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sector analysi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60):324-347.
[7]John Knight and Ramani Gunatilaka.Great expectations?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urban migrant in China[J].World Development,2010,38(1):113-124.
[8]Jorgenson D W.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J].Economic Journal,1961,(l1):213-222.
[9]Lewis W 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J].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3):139-191.
[10]Nielsen I,Smyth R and Zhai Q.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a’s off-farm migrants[J].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10,11(1):23-34.
[11]Paul C and Rhiannon T E,et al.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migrant farm worker health in conventional and organic horticultural systems in the United Kingdom[J].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08,39(1):55-65.
[12]Stark O and Taylor J E.Migration incentives,migration types: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J].The Economic Journal,1991,(101):234-254.
[13]Sumon M,Anandi M and Sharun W M.Politics,Information and the urban bia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75:137-165.
[14]Sylvie Démurger,et al.Migrants as second-class works in urban China?A decomposition analysi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9,37(4):610-628.
[15]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与公共政策方向的转变——关于中国社会保护的若干特征性事实[J].中国社会科学,2010,(6):125-137.
[16]陈钊,陆铭.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J].经济研究,2008,(1):21-32.
[17]蔡昉,都阳.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贫困假说[J].中国社会科学,2002,(4):1-7.
[18]程名望,史清华,杨剑侠.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J].经济研究,2006,(4):68-79.
[19]程名望,史清华,潘烜.劳动保护、工作福利、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镇就业[J].统计研究,2012,(10):73-78.
[20]程名望,史清华,顾梦蛟.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模型与实证[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8):20-31.
[21]都阳,朴之水.迁移与减贫——来自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J].中国社会科学,2003,(4):49-57.
[22]高文书,Russell Smyth.未来收入预期与进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对上海等12个城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6):21-33.
[23]李迎生,刘艳霞.社会政策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护[J].社会科学研究,2006,(6):100-105.
[24]马明,陈方英,孟华,周知一.员工满意度与敬业度关系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5,(1):120-126.
[25]钱文荣,张黎莉.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及其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09,(5):70-78.
[26]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7]伍中信,徐莉萍.基于企业理论的“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J].财贸研究,2011,(1):28-33.
[28]杨红.改革以来中国永久性迁移人口和流动性迁移人口的比较研究[J].西北人口,1999,(1):2-9.
[29]杨云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非正式迁移”的状况——基于普查资料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6,(11):59-73.
——基于三元VAR-GARCH-BEEK模型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