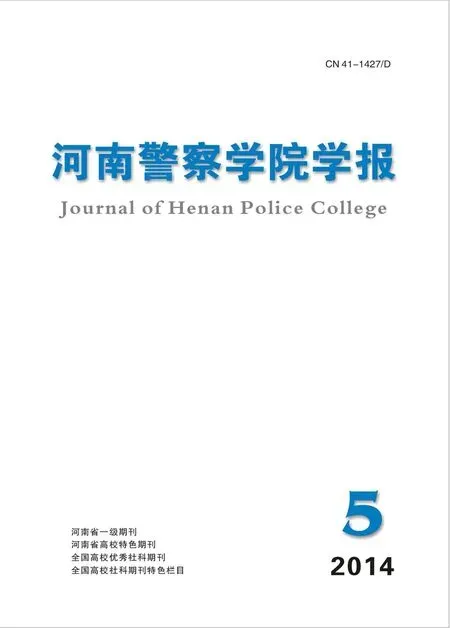论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
蔡雅奇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中国北京100144)
一、问题的提出
在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是指被害人与犯罪人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使犯罪得以发生、发展和演变并进而在二者之间产生的关系。犯罪人与被害人存在互动关系的理论学说,最早是由德国学者汉斯·冯·亨梯(Hans von Hentig)在1921年《乱伦研究》一文中提出的。他在1941年的《论被害人与犯罪人的相互作用》一文中,明确指出“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互为诱因”[1]。以色列学者本杰明·门德尔松(Benjamin Mendelsohn)则提出“刑事伙伴”或者“刑事搭档”的观点,认为被害人与犯罪人实际上是一对“刑事搭档”[2]。而在我国学者对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研究中,虽然对二者关系类型的观点分歧较大,但毫无例外地都将互动关系界定为二者之间最基本的关系,甚至有学者认为二者的关系仅为互动关系,而其他关系,如角色转换关系只不过是互动关系的一种[3]。还有学者认为虽然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关系有对应共存关系、二元互动关系、刺激与反应关系、被害转换关系、责任分担关系和刑事对立关系,但互动关系仍是二者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并且是上述关系的前提和基础[4]。
“犯罪不是单向的过程,不是一方积极加害而另一方消极被害的过程,而是一种互动的存在。”[5]在任何犯罪中,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都贯穿于犯罪发生、发展和结束的整个过程,从时间节点来看,这种互动关系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杀人犯罪也不例外。杀人犯罪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是指在杀人犯罪前、犯罪中和犯罪后这三个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并进而在二者之间形成的关系。
本文选取了H省230份故意杀人罪的判决文书,通过对其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和理论阐释,试图对杀人犯罪前、杀人犯罪中和杀人犯罪后这三个阶段的被害人与犯罪人互动关系的类型进行分析,以期揭示被害人与犯罪人这两个主体在杀人犯罪的产生、发展和结束等三个阶段各自的地位角色及其所起的作用。
二、研究样本的选取
在我国,犯罪统计特别是被害统计工作的统计资料是相当缺乏的。即使存在相关的统计数据,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全面、准确并且及时地披露。而对于杀人犯罪、杀人犯罪被害而言,由于杀人行为往往会导致适用死刑,而这些被判处死刑尤其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可能会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不会被披露,这些信息尤其是相关的统计数据,外界无法获取。
同时,通过接触杀人犯罪被害人并获取相关信息也是很困难的。例如,杀人犯罪发生的原因、被害人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被害人是否具有一定过错、杀人犯罪中双方各自的表现、杀人犯罪发生后被害人采取的态度等。毕竟,让被害人回忆复述这些消息,无异于使其再次遭受心灵上的伤害。接触杀人犯罪被害人的近亲属,可能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这种接触难的问题,导致对杀人犯罪被害人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难度增大,深度调查难以展开,“第一手资料”更是难以掌握。
鉴于本文研究存在的上述诸多困难,笔者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条件,登陆“H省法院网”,搜集了自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发布的共计364个故意杀人案件的司法文书。H省地处中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是中国大陆纵贯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全省常住人口9000余万,农业人口较多。之所以选取由H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的“H省法院网”作为本文研究的主要样本来源,是因为H省是全国范围内较少的能够在第一时间将相关司法文书直接发布在互联网上的省份,这一做法对于增进司法公开和司法民主、提高司法透明度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为了方便统计分析,笔者从这364个案例中选取了257个被害人均为1人的案例,将其余的107个案例予以剔除。在进行研究时,先对这257份司法文书进行了通篇阅读,删除了相互重叠的19份之后①之所以会出现司法文书相互重叠的现象,是因为笔者在搜集和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发现,就同一个杀人犯罪案例而言,可能有两份甚至两份以上的法律文书:既有刑事判决书,又有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甚至还有刑事裁决书。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法律文书,只是刑事判决文书,那么与之相重叠的其他司法文书只能被剔除出去。又删除了个别信息不全的司法文书,最终纳入到统计分析范围的有效司法文书为230份,即对应存在着230个杀人犯罪被害人的案例。可以说,本文对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基本上是以这230个杀人犯罪被害案例为基础进行的。
杀人犯罪往往伴随着死亡结果,这一点在笔者搜集案例和进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体会非常明显。根据笔者对H省230个杀人犯罪案例的统计,在这230个杀人犯罪案件中,共死亡139人(其中男性死亡117人,女性死亡 22人),占所有被害人的60.4%,而未死亡的仅为91人,占所有被害人的39.6%(参见图1)。由此可见,杀人犯罪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出现是很普遍的。对这一问题的交待,有利于对本文后续问题的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杀人犯罪后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部分,如果被害人已经死亡,自然不会再发生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问题。此外,如下文所述,被害人在杀人犯罪发生过程中往往会做出激烈反抗、顺应和巧妙应对等三种不同反应,而每一种反应对于最终结果的发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有的会招致更为严重的杀害,有的则成功摆脱被杀害的噩运。而这些成功摆脱被杀害噩运的被害人,则仅限于上述未死亡的91人。

图1 杀人犯罪被害人是否死亡、死亡者的性别及其各自比例
三、被害加害双方多以熟人关系为主是杀人犯罪前双方互动关系的主要特点
在杀人犯罪发生前,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交往关系。当然,这种交往关系既可能是长期的,如亲朋好友、商业伙伴等关系,也可能是短暂的。当然,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完全不认识的情况也是个别存在的,但所占比例非常小。以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亲疏远近为标准,并结合对H省230份故意杀人判决文书的调查统计,可以发现,被害加害双方多以熟人关系为主是杀人犯罪前双方互动关系的主要特点。
(一)双方是熟人关系
根据笔者对H省230个杀人犯罪被害案例的统计分析,在这230起杀人犯罪中,犯罪人与被害人完全不认识的仅有4起,只占所有杀人犯罪案件的1.7%。相反,98.3%的杀人案件中,被害人与犯罪人都是相互认识的。当然,认识的程度各有差别,有的是非常熟悉,如配偶、家庭成员、亲戚、朋友、邻里等,还有的仅仅是几面之交而已,如双方是执法人员与相关被执行人的关系(参见图2)。但无论如何,杀人犯罪发生之前,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多以熟悉为主。

图2 杀人犯罪发生前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情况
以往的研究也能证明笔者的上述结论。我国有学者在对400个杀人案件进行分析之后,得出如下结论:78.15%的杀人案件发生在熟人之间,仅有21.15%的案件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而在熟人关系中,情人关系占22.16%,夫妻关系占16.19%,朋友关系占 17.12%,邻里关系占 16.19%[6]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司法行政部门于20世纪60年代对962名杀人犯所做的调查发现,杀人犯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以熟人关系居多,完全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杀人犯罪并不多见(参见表 1)[7]。

表1 台湾地区杀人犯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
国外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依据美国联邦调查局1992年发布的《统一犯罪报告》,杀人犯在犯罪前与被害人认识的比例为78%,其中家庭成员占26%。①转引自任金钧:《被害者所引起的杀人犯罪》,载《警学丛刊》,1997年第1卷,第76页。还有学者对美国社会杀人犯罪的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人际交往关系进行了专门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参见表2)。②转引自任金钧:《被害者所引起的杀人犯罪》,载《警学丛刊》,1997年第1卷,第78页。
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原本是熟人关系,但后者却选择杀人行为这一极端手段作为解决双方之间关系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人的杀人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泄愤报复、忍无可忍、事情败露之后的灭口,等等。根据笔者对H省230个杀人犯罪被害案例的统计分析,在这230起杀人犯罪中,犯罪人的杀人动机为“泄愤报复”的共有126起,占所有杀人案件动机的54.8%,比例最高,因“家庭琐事”和“夫妻感情纠纷”而引发的杀人犯罪行为紧随其后(参见图3)。

表2 美国杀人犯罪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人际交往关系

图3 犯罪人实施杀人犯罪的动机
在熟人之间发生的杀人犯罪被害案例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杀人行为,格外值得关注。上文所列的关于家庭成员之间发生杀人犯罪的相关数字及相关比例,足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道理很简单,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家庭成员之间的杀人犯罪行为,比一般的杀人犯罪行为所带来的心理、伦理上的冲击更大。其中,夫妻间的杀人是家庭成员间杀人犯罪最多的种类,其被害人以妻子居多。仅1984年,美国发生的夫妻间杀人犯罪中,妻子被害的占2/3,丈夫被害的占1/3。③转引自任金钧:《被害者所引起的杀人犯罪》,载《警学丛刊》,1997年第1卷,第79页。美国犯罪学家唐纳德·凯内菲克(Donald Kenefick)也指出:“家庭是女性最危险的场所,每年大约有400万女性受虐,平均每四天会有一人被殴打致死。”日本的研究也发现,男性被害于各种关系中,而女性多被亲属、亲戚(55%),男朋友、情夫(35%)所杀害[8]。
夫妻间的杀人犯罪行为以及父母子女之间的杀人犯罪行为,是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互动关系的集中体现,也往往是这种互动关系的结果。杀人犯罪行为往往起因于家庭纠纷,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纠纷和冲突长期存在,在一次次纠纷中逐步升级到以被害人被杀害为结局。
从我国每年发生的诸多杀人犯罪案件来看,发生在熟人之间的杀人被害现象并不少见。①可参见:《山西吕梁杀害4家7口凶犯落网 因琐事报复杀人》,http://society.people.com.cn/GB/42733/12877178.html,访问日期:2013年11月24日。在这些犯罪被害事件中,被害人往往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过错。根据笔者对H省230个杀人犯罪案例的统计分析,被害人有重大过错和轻微过错的为191起,完全无过错的仅为39起,占所有杀人案件的17%。被害人具有轻微过错和重大过错的案件数量则分别为179起和12起,分别占所有杀人案件的77.8%和5.2%(参见表3)

表3 被害人是否有过错及其比例
在这191起有被害人过错的杀人案例中,既有言辞激烈的行为,也有相互厮打行为和挑衅侮辱行为,还有事前的诋毁散布谣言行为,等等。当然,在被害人自身是婚姻中的第三者或自己有第三者的情况下,被害人的过错更是明显(参见图4)。因此,被害人需要为自己的被害承担一定的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
(二)双方仅仅是一面之交关系
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虽不是熟人关系,之前并无往来,但仅因一面之交,例如仅仅因为一次摩擦或争执而结怨,最终导致杀人事件的发生,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这种杀人犯罪基本上都属于激情杀人,被害人往往对杀人事件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例如激怒犯罪人、刺激犯罪人等被害人过错(参见前述图4),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因此而免除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仅有一面之交但被害人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仍然发生了杀人犯罪行为,是非常不幸的事实。这种被害人实为无辜被害人。在无辜被杀的情况下,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并无任何恩怨,但却成为杀人犯罪的被害人,这种情况非常值得人们深思。从犯罪原因上看,犯罪人可能是出于报复社会的动机而对无辜者下手,也可能是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殃及无辜,等等。特别是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多起系列杀人案件中,很多无辜者成为杀人犯罪的被害人。

图4 被害人过错在杀人犯罪发生前的表现形式
四、被害人在杀人犯罪中主要采取激烈反抗的行为来处理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杀人犯罪实施过程中,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也会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从而推动或影响杀人犯罪发生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被害人一般会有激烈反抗、顺应和巧妙应对等三种不同的反应,而这三种不同的反应导致被害人自身的最终命运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根据笔者的实证研究,在杀人犯罪进行过程中,被害方对犯罪人采取激烈反抗的举动,是双方互动关系的主要特点。
(一)激烈反抗
即被害人在杀人犯罪发生过程中对犯罪人进行对抗、反击的情况。
在杀人犯罪实施过程中,被害人的激烈反抗,是其面对危险的本能甚至是必然的反应。被害人的激烈反抗,往往会导致三种后果:(1)成功威慑住犯罪人,导致杀人犯罪的未遂;(2)被害人招致更为严重的杀害,从而导致死亡等严重后果的发生;(3)被害人向犯罪人发生转化,最典型的即为防卫过当中的犯罪行为。
根据笔者对H省230个杀人犯罪被害案例的统计分析,在这230起杀人犯罪中,被害人采取激烈反抗行为的共有136起,占所有杀人犯罪案件的比例高达59.1%。其中,成功威慑住犯罪人的为27起,招致更为严重的杀害的为89起,向犯罪人发生转化的仅为20起,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9.9%、65.4%和14.7%(参见图5)。通过这一数据,可以得出两个结论:(1)在杀人犯罪发生过程中,被害人采取直接甚至激烈反抗的比例非常高。当然,这与被害人面对杀人行为发生时的慌乱、无助甚至手足无措的状态有直接关系。(2)激烈反抗的结局更多的是招致更为严重的杀害等后果。
(二)顺应
即被害人在杀人犯罪发生过程中对犯罪人进行顺应和服从的情况。在杀人犯罪发生过程中,被害人的顺应可以分为主动顺应、被动顺应和表面顺应三种:(1)在主动顺应的情况下,被害人彻底放弃了抵抗行为,这自然有助于杀人犯罪的顺利实施,从而导致自己的最终被害;(2)当被害人明知自己正在遭受杀人行为的侵害,由于各种原因不得已而服从于犯罪人的意志时,只得被动顺应。被动顺应也往往会导致死亡后果的最终发生;(3)当被害人表面顺从犯罪人,实际上与犯罪人进行“周旋”,从而寻求逃脱被害的机会和可能,此即为表面顺应。表面顺应的行为如果“周旋成功”,被害人就能够摆脱杀人犯罪的侵害,但如果“周旋失败”,反倒可能激起犯罪人更为激烈的报复行为,从而导致死亡结果的最终出现。
根据笔者对H省230个杀人犯罪被害案例的统计分析,在这230起杀人犯罪中,被害人采取顺应杀人行为的共有41起,占所有杀人犯罪案件的比例为17.8%。而在这41起案件中,有15人“成功摆脱”最终被杀害的噩运,所占比例高达36.6%(参见图5)。可以看出,与采取激烈反抗行为相比,被害人采取顺应行为更能避免最终被害后果的发生。
(三)巧妙应对
即被害人在杀人犯罪发生过程中与犯罪人进行巧妙“周旋”和灵活应对的情况。在杀人犯罪发生过程中,被害人巧妙应对的方式有许多种,如佯装妥协、假装给家人或朋友拨打电话、拖延时间、唤起犯罪人的“良心”等。无论采取哪一种行为,被害人都是为了尽可能拖延犯罪人的犯罪时间,从而为摆脱被害争取有利的时机。因此,被害人具有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是很重要的,只有临危不乱,才能不被情绪和形势所左右,理性判断犯罪事态,根据形势的变化积极应对。
就后果而言,被害人的巧妙应对要么能成功地摆脱被杀害的后果,要么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功,最终惨遭杀害。但这种巧妙应对的行为至少可以延缓犯罪被害时间、有效摆脱犯罪侵害,因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根据笔者对H省230个杀人犯罪被害案例的统计分析,在这230起杀人犯罪中,被害人采取巧妙应对的共有53起,占所有杀人犯罪案件的比例为23.1%。而在这53起案件中,有29人“成功摆脱”最终被杀害的噩运,所占比例高达54.7%(参见图5)。可见,在杀人犯罪等暴力犯罪突发时,冷静应对、巧妙周旋、尽可能地拖延犯罪时间,对于降低被害的风险和概率,还是有作用和价值的。

图5 被害人在杀人犯罪发生过程中的反应类型及其后果
五、被害人对犯罪人的行为进行告发应成为杀人犯罪发生后处理双方互动关系的最好选择①由于本文研究的样本主要来源于H省的230份故意杀人犯罪判决文书,而这些文书中并未披露杀人犯罪发生后这一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相关信息,因此,本部分无法以相关数据做支撑,而主要采用思辨研究法,特此说明。
这里的杀人犯罪后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关系,是指在杀人犯罪中并未死亡的被害人,在杀人犯罪发生后与犯罪人发生的关系。如果被害人在杀人犯罪中被犯罪人直接杀死,或者日后不治身亡,则与犯罪人之间不可能再有互动关系。当然,遭受杀人犯罪侵害的被害人的亲属、朋友及其单位等间接被害人,也可能甚至必然与犯罪人之间发生各种关系,限于篇幅,这种间接的互动关系暂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在杀人犯罪中并未死亡的被害人,在杀人犯罪发生之后,往往会采取如下几种行为,从而进一步与犯罪人发生着互动关系:
(一)告发
即被害人通过报案、举报等方式,希望犯罪人受到应有的法律处罚,从而伸张自己的权利,并期望获得有关赔偿或补偿。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向司法机关告发,有助于节省案件侦破的司法成本,减少司法办案的时间,并使被害人能够从司法机关获得更有利的保护。被害人学的研究表明,被害人在被害后是否会以告发的形式寻求司法机关的帮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利益衡量原则”(又称“支出与收益考量原则”),即被害人通过衡量其报案与不报案、容忍犯罪行为给自己带来的各种收益和由此所支付的金钱、精力等物质、精神方面对价之间的比例关系,来决定是否采取告发的行为[9]。
鉴于杀人犯罪的非亲告罪性质,在告发行为发生后,必然会引发司法机关的介入。因此,在随后的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害人与犯罪人将继续发生控告揭发、出庭作证、被害赔偿等互动关系。当然,被害人的告发行为也可能会招致来自犯罪人的更为激烈的报复,从而使自己再次成为被害人。因此,如何避免这种悲剧的再次发生,不但取决于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双方综合力量的对比,更取决于有关单位特别是司法机关能否对被害人实行及时有力的保护。但无论如何,都应看到,告发都是最值得提倡和鼓励的方式,是被害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最佳形式。
(二)容忍
即被害人由于对方势力过于强大、顾及个人声誉等原因而采取不做声张、忍气吞声的做法。被害人在遭受杀人犯罪行为侵害后采取容忍的态度和做法,同样是基于上述“利益衡量原则”作出的抉择。因为,被害人可能会发现,在告发启动刑事司法程序之后,自己将不能退出该程序。而且,在该程序中,被害人可能极不情愿乃至“被迫”地履行很多配合义务:配合侦查机关调查的义务、配合检察机关起诉的义务以及配合法院的出庭义务,这些义务的履行不仅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在漫长的司法程序中还要反复重述杀人犯罪行为发生时的场景和过程,这对被害人而言无异于一种巨大的心理折磨。而如果不报案而采取一定的避免与犯罪人再次相遇的容忍措施,在被害人看来,或许可以尽可能地忘记与犯罪有关的情境,尽快恢复生活的平静,重启往日正常的生活。
就后果来说,遭受杀人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采取容忍做法,可能为自己换来短暂甚至永久的宁静,司法机关对杀人犯罪人所采取的“官方行动”及其后果,对于被害人来说,可能都不是最为重要的,也不是其最为关心的。当然,被害人的容忍也可能为自己招致来自犯罪人的更为残忍和不仁道的报复,从而使自己再次沦为被害人。
(三)报复
即被害人不通过告发的方式,而是直接对杀人犯罪人进行报复。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其心理是非常复杂的,其中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希望尽快对加害人实施报复甚至复仇。这种极端的对犯罪行为及其后果的否定举动,实际上源自于其强烈的排斥心理。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胸中燃烧着复仇之火的(被害)人对(报复)动机问题根本不感兴趣,他只有一个念头:点燃复仇之火的事件已经发生。他的满腔怒火甚至会一股脑地发泄于无生命的东西、动物和因无知、过失或无意损害他的人。”[10]尤其是对于遭受杀人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来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一朴素的同态复仇心理和情绪,在其内心深处体现得更为明显。
被害人在遭受杀人犯罪行为侵害后所实施的报复行为,就其对象而言,可能不限于原犯罪人本人,还可能包括与原犯罪人有关系的人,特别是原犯罪人的近亲属。就报复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而言,可能是相对较轻的后果,也可能是相当严重的后果。在后种情况下,被害人的复仇意识往往非常强烈,目的非常明确,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地实施其报复行为,作案手段可能会比较残忍。这实际上是被害人向犯罪人的角色转换,即此罪中的被害人变成彼罪中的犯罪人。被害人向犯罪人发生的角色转换,是双方之间一种较为特殊的互动关系。犯罪与被害是侵害与被侵害的关系,在这种侵害与被侵害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犯罪人与被害人的角色发生相互转换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在被害与犯罪之间所观察到的联系是相当出人意料的,无论被害是直接获得的还是间接获得的,是实际的还是想象的,是个人的还是共同的,已经成为被害人这一意识不仅为犯罪提供了诱因和借口,还提供了必要的合理性和中立性,从而使潜在的犯罪人可能克服任何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包括道德抑制和刑罚威慑等。这些动机和借口能够把被害人转化为一个毫无怜悯之情的加害者。”[11]
笔者认为,由于杀人犯罪是严重侵犯公民生命法益的犯罪,也是各国刑法中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因此被害人在杀人犯罪之后所采取的上述容忍和报复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事实上,由于杀人犯罪在我国并不属于亲告罪,被害人通过上述方式来处理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实际上是对国家司法权威的一种挑战,也是对司法机关对杀人犯罪进行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刑事审判等司法活动的一种干扰。因此,通过告发的形式,使司法机关介入杀人犯罪案件中来,通过正常的刑事诉讼程序解决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唯一的正确做法。
六、结语
本文主要通过对230份故意杀人犯罪判决文书的实证分析,试图揭示杀人犯罪前、杀人犯罪中和杀人犯罪后三个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通过本文的论证和分析,既可以看到杀人犯罪本身的暴力性、残酷性和巨大的社会危害性,也可以看到杀人犯罪得以发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非简单地仅仅归结为犯罪人主观上是多么的“恶”。因此,对杀人犯罪必须进行全方位的犯罪预防和被害预防,既包括个人预防,也包括家庭预防,更包括社会预防。
与此同时,通过本文的研究,还可以发现,在杀人犯罪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被害人过错这一因素,是大量而普遍存在的。正是这种过错的存在,刺激、诱发、促成甚至直接推动了杀人犯罪的产生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杀人(犯罪)的被害人塑造了杀人(犯罪)的犯罪人”。①Joseph E.Jacoby(ed),Classics of Criminology ,Long Grove,IL:Waveland Press,1998:26 ~27。换言之,被害人过错与杀人犯罪的最终发生和发展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这在杀人犯罪前和杀人犯罪中两个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有些杀人案件中,被害人的过错促使犯罪人临时产生了犯罪决意,而在另外一些杀人案件中,被害人的过错则强化了犯罪人已有的犯罪决意。
但是,笔者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加害—被害双方互动关系这一犯罪学、被害人学领域的传统理论,在转型社会时期的众多杀人犯罪案件面前,在“戾气弥漫”的当下,是多少有些苍白的,甚至是“力不从心”的:越来越多的灭门案件的涌现、被害方一点点轻微的举动都可能引起犯罪人特别激烈的反应、无辜被害人数量的增多、毫无征兆的无辜被害现象的层出不穷,都难以再简单地用“互动关系、被害人过错”等传统理论加以阐释,理论与实践至少不再是那么的“严丝合缝”。因此,犯罪学、被害人学也面临着如何革新理论和提升实践适应性的严峻问题,研究者在此方面任重而道远。当然,这些问题只能另文研究了。
[1]李伟.犯罪学的基本范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4.
[2]许章润.犯罪学(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45.
[3]霍建中,韩文.论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J].河北法学,1999,(1).
[4]张建荣.论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J].青少年犯罪研究,1996,(8).
[5]白建军.罪刑均衡实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4~75.
[6]高维俭,查国防.故意杀人案件中加害人与被害人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7]杨士隆等.暴力犯罪:原因、类型与对策[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170.
[8](日)诸泽英道.被害者学入门——间接被害化要因[J].隆霁译.青少年犯罪研究,1997,(3).
[9]申柳华.德国刑法被害人信条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72.
[10](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M].张乃根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722.
[11]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