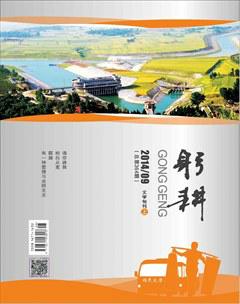生长地
毓新
生长地无疑比较幸运,名字竟然跟共和国首都的老称谓“北平”读音全同,只不过生长地太乡野太卑微,便知趣似的在第二个字符前加了恰如其分的偏旁——陇中“会宁县行政区划图”上,其东南角被标识为“北坪”的便是。
北坪者,朝北小平地,僻静尕庄子也,四围山壑环拥,左前沟谷纵横。山壑无任何特色,陇中高原司空见惯,山肌尽为黄土,不掺半粒沙石,生百草,生杂树,生菜蔬,生谷物,小路顽强执拗地盘绕其上,穿梁过岨,与遥远的外界相通相联;沟谷渗淌潺潺溪水,纤细如蚯蚓,扭曲似麻绳,却有东流入海的坚韧志向,经年累月锲而不舍,也滋养了沟谷无限生机。
大多数孩子从光屁蛋开始混起。光屁蛋在母亲温暖的怀抱,吸吮丰满乳房,感知新奇人世;光屁蛋站在雪光掩映的窗前,朝屋外红红的“阳婆婆”喊唱示好:“……五九六九,光屁蛋娃娃拍手!”光屁蛋跑田野挖辣辣,挖嫩胖——辣辣和嫩胖为至今不知其名的植物,辣辣根白味辣,嫩胖根红味甜,春天羞怯怯探两片小叶出土时挖吃最可口了。光屁蛋在沟谷热热的绵黄土中溜坡坡,满头满身糊遍汗泥,不小心蹭破手脚皮肉,赶紧抓一撮黄土撒在鲜血淋漓的伤处,嘴里念念有词:“金土土,银土土,今日不好明日好!”光屁蛋满庄道狂追乱跑,所过之处鸡飞狗上墙,遇父母心情不好,会在光屁蛋上惩罚两记红手印——父母心情有点捉摸不透,假如光屁蛋撒野太猛遭受意外惊吓,又会在夜深人静时分拿上光屁蛋的衣服去庄道安抚,声调奇特如梦如幻:“娃吃饭了!——娃喝汤了!——娃不害怕了!——”这样的举止,在多年后学习楚辞等古代典籍时似乎曾欣赏过。
疯着疯着不能再疯了,光屁蛋们被穿上缀满补丁的衣裤,送入只有一沟之隔的村学里识字认数,唱唱画画。但教室跟书本哪能缚住刚裹了衣裤的光屁蛋啊,大家跳校园花坛捕捉蜜蜂,放在教室玻璃窗内,看小生灵如何瞎飞乱撞穷折腾。大家拿墨汁涂了彼此的嘴脸,课间站讲台上扮包爷吼乱弹。大家抓来小菜蛇偷偷塞进女孩的书包,表面若无其事地坐一旁静候女孩尖声大叫。大家放学路上更整得不可开交,爬树梢掏鸟窝,攀崖壁捕花鼠,跳菜园偷萝卜,聚路畔甩扑克,最刺激的,莫过于分伙干打仗:抢占有利地形的一伙,拿大小不等的土块作手榴弹,扔向冲锋而来的“敌人”,口中“轰隆隆”炸个不停;遇上特别勇武的主儿,连中数弹不知自觉“牺牲”,只能逼你冲出去肉搏了;假如不幸被俘虏,投降最叫人瞧不起,即便衣袖破损,鼻青眼肿,被揪伤耳朵或反剪双臂,也宁求玉碎不可瓦全……纯真无忧的时光,珍藏了品味不尽的回忆!当然玩耍之外,也相跟母亲探望舅姥爷,伴随父亲领取救济粮,伙同姐姐打理家务事:清屋扫院,沟泉取水,铲猪草,拾柴禾……纵使寒冷的冬季,也在节假日提柳条筐,拾羊粪,拣树枝。用小脚丈量、用小手抚摸生长地每寸肌肤——那珍珠般随心所欲藏身于山洼的羊粪蛋,一小堆便是一份心跳的惊喜,与那些被冷风吹落的干树枝,经小手折成寸段,放灶塘吧嗒嗒扇几风箱,硬气的焰火直舔锅底。锅里的形势总不很好,或面糊糊或菜团团,拖累肚腹常叽哩咕噜大合唱,古老苍凉,激情悲壮。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在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中说:“凡人都有他的自然地位,这个自然地位的高度不是自尊和才华所能确定的,而是儿童时代确立的。”我贫穷而快乐的童年,为其“自然地位”涂抹了多么朴素坚韧的底色。
小学升中学,已跃跃欲试离开生长地,变成了住宿生,但柴米油盐仍源源不断从家里背。最初吃自炊,黄泥巴堆垒的小火炉,三五根劈柴烧顿饭,烟熏火燎,十指黑污,流出的是眼泪,收获的是成长;后来学校办了大灶,上顿下顿玉米面坨坨玉米面粥,一看见灶房清汤寡水的门就胃里泛酸。因此家里背的馍馍一点舍不得浪费,即使热天生了霉变——生长地称食物霉变为“丝起”,“丝起”即“起丝”吧,多艰辛创意浪漫的说法!馍馍“丝起”,表面先起淡蓝菌毛,渐渐朝纵深漫延,轻轻掰开,菌丝更不绝如缕,细心将表层的霉变剔除,泡开水里将就着吃,吃闹肚子者屡见不鲜。正因为此,节假日回到家里,秕糠杂粮野菜干饼,只要母亲做的,只要锅里出来的,就半根葱,咬一粒蒜,甜美和幸福感油然而生。节假日还参加农业生产,由于体力关系,常被分配在跟母亲年龄相仿的小脚大妈一组,刈除杂草,收割田禾,打碾秋场……生长地的每架梁,每溜沟,每条路,每道坎,都摸爬滚打得跟自己的手掌一般熟悉。大妈们身上有泥土的气息,有母亲的味道,有母亲的风格,在至今仍倍感亲切的唠叨中,练劳动技能,学生活态度,习处世之道,还通过大妈们藏藏掖掖的言谈,隐约感知生长地男女间不少隐秘。中学毕业那年的暑期特别长,从骄阳似火的六月延至阴雨霏霏的秋季,已快成年的我,跟生产队的糙男人们一起挑麦,挖地,积肥,放牧,脏活累活没商量,吼秦腔,说脏话,抽旱烟,捉虱子,放响屁,在皎皎明月夜驱田鼠,直裸裸听男男女女更多的昂扬事,听得惊心动魄,想入非非。终于在一个天碧如洗的上午,接到陇中某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意识到自己居然确实成功地跳出了“农门”,变为“吃皇粮”的公家人,再也无法按捺内心的冲动,烈马似的在生长地的山洼里狂跑一气,才携带满身黄土,像模像样的男子汉那般,昂首挺胸步入了外面无边精彩的世界。
从此如生长地那韧劲十足志向非凡的潺潺溪水一样,终于真正离开那块贫瘠而富有的热土,用父母的话说,变成老家亲戚了。但亲人之所在,祖先骨殖之所在,家园之所在,让人魂牵梦萦无法释怀。并且遭世事烟云炝染越久,这种感情越发纯真淳厚:那梦一般盘绕在山壑间的小路,路一般扭曲在沟谷中的溪水,水一般流淌在村落上的炊烟,烟一般飞扬在庄道边的尘雾;那“炕气”浓烈的小屋,味道独特的杂吃,古韵犹存的方音,朴实厚道的习俗;另如大伯炕头的罐罐茶,大姨膝旁的针线筐,侄女辫梢的蝴蝶结,外甥脚丫的黄泥巴,甚至鸡鸣狗吠驴嘶牛哞……都冷不丁会在现实当中,或梦境之内,焕发出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氛围,如窖藏的美酒,似新启的甘醇,让人沉迷留恋难能自已。
生长地有种叫串根白杨的树,初栽在土壤里的时候无论何等纤细,都会栉风沐雨一天天成长,长到干高枝繁根深叶茂了,会由根系“串”生新苗,几年之间围绕母树成片成林。若在草木萌动的春季,斩断任意小苗的根系移栽别处,小苗依然能一如既往生生不息,慢慢营造新天地。只是有一点,无论串生出的树林如何扩张,其根须永远血脉似的纠结着初生的方向。人的生命多像这白杨树啊,不管你长得翅膀多硬多强,远离生长地千里万里,天涯海角漂洋过海,生儿育女七老八十,功成名就光景熣灿,都永远无法从根本上绝断与生长地盘枝错节血浓于水的联结。
树的根系在土里,人的根系在心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