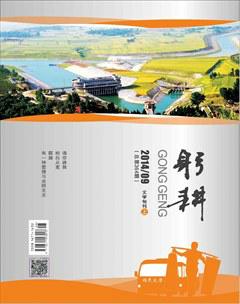我永远的栎树家园(外一章)
◆ 韩华仁
三十多年来,我回老家不下百次。虽然村口的那两棵老栎树已经消失,但在我的感觉中,她们仍高高地挺立着,对我诉说着什么。而当我站在村口,向她们生长的地方望去,那片已经长满杂草的空阔,撒满了我的惆怅。
那两棵老栎树是村庄最高大的树。我不知道她的年龄,村里人也不知道是谁种下的,人们知道的是,有一个叫西大山的小山村,小山村前长着两棵大栎树,老栎树上缠绕着小水桶粗的葛花。当一个外村人想到我们村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老栎树,因此我们村就成了“老栎树那个地方”,村上的人就成了“老栎树那个地方”的人。总之,栎树已经用气势构建出了一种形象;栎树已经成为村庄的标志。
我记事是从母亲的乳房开始的,甘甜的乳汁与温暖的怀抱,让母亲的形象更加美丽,而我在外边的记事,是从那两棵老栎树开始的,她们的高大与以及树冠营造的无限神秘,让小小年纪的我像小大人一样,坐在露屁沟的柳木椅子上,看着老栎树出神。有时候,母亲的神秘与老栎树的神秘,交织在一起,在偶尔的失神中,竟让我看着母亲想到老栎树,看着老栎树又想起母亲。
也许树木随便长在什么地方并不随便,老栎树长在村前,有着树与人说不清的机缘。树与人都是在泥土中讨生活的,一个树种就是一个家族,一片树就是一个树的村庄,一棵高大的树就是一座高宅大院,一片森林就是一座树的城市。树在树的村庄里生活着,人在人的村庄里生活着。不过,很多时候,树在人的村庄盖起了绿色的房子,人在树的村庄盖起了灰色的房子,人与树就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子里,人树同居便是乡村最常见的日子。我们那儿的山里有不少古树,但大多离村庄较远,就感到外气了,她们有的是神秘与故事,却没有亲切。好在老栎树长在村前上地的道路旁,人们早出晚归都要从她们身边经过,她们庞大的身量,不可能不吸引人们的视觉;走进树下,尤其是夏季,一种带着清香的凉气就会向身子里渗。在割麦与割稻的燥热中,很多人会在伸腰偷懒的间隙,凝视一阵子老栎树,便感到心里好似轻松了了许多。
在两棵老栎树中间,一口石头圈起的井,石头上满是青苔,石缝中长满了一撮一撮的凤尾草,它们守候着井的古老,过滤着从叶缝筛下的枯叶、花瓣与光点,然后收藏在井水里,等待铁箍水桶从井里拎出。每天早上,家家户户都会担着水桶到井上打水,在窄窄的土路上一条条水线,一头通往家家户户,一头通往老栎树,好似岁月在村庄与老栎树之间留下的记号。
我小时候家境贫寒,清霜白露,姐姐就要起来搂柴,而我一直身子虚弱,母亲怕我不成人,总是让我干轻活或玩。有时候我会随放牛的伯伯上山拾柴,我没有力气,背不动太多的柴,拾的就很少,也就有了玩的时间。但更多时候,我则在老栎树下玩耍。在老栎树旁,有一条小河。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河。它只是我感觉中的河。因为仅仅是一条沟,平时没有水,但每当大雨,山洪暴发,就会有满沟子的水。如果不是连阴雨,河水马上会干,留下亮在小水坑的小鱼让我扑捉快乐。河沟宽不过一丈,细沙也不过半尺厚,但这是我平时见到的第一个沙滩。我在沙滩上,划着,挖着,扒着,躺着,把时间埋进沙子,再扒出湿润的趣味。后来我在大河边大海边见到了数不清的大沙滩,美丽辽阔,但这些沙滩只是沙滩,却永远没有小沙滩上的梦幻感觉。
两棵老栎树本来相距有好几丈,一棵粗大的葛花却把她们联系到了一起,我想不明白的是,一根葛藤从西边那棵老栎树一丈高的地方,为什么会竟横着伸向另一棵,就像一座藤蔓编织的天桥,从远方看去,就像连到一起的两座房子,住着两户人家。
我是一个爱花爱树的人,在我的感觉中花花草草决不是庭院中的陪衬,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都是原野上的独立住户,在岁月中用叶与根营造着自己的家庭环境与气候,在阳光雨露中收割着她们的理想,那些在春天随意绽放的花朵,很可能就是植物在过自己的节日。
栎树在我们那里是一种低调的树。她们叶片窄小;好似对开花这样的大事也不感兴趣,仅在枝梢上挂一些不起眼的青穗;结出的橡子总是藏在茂密的叶片中,等待微风吹落。树木们都会在深秋用叶片争奇斗艳,栎树却不好张扬,在秋霜中土黄,等待着冬天的寂寞。而在我们那里的山坡上,最多的就是栎树,在人们眼中仅是一把柴火。
然而,那两棵老栎树却在漫长的时日中一点点增加着岁月的厚度,她们张着嘴的老皮好似在讲着遥远的故事;庞大的树冠摇动着风,让我感到夏天的凉风就是从树中刮出的。葛花没有自己的主见,这种藤蔓十分随和,在离村庄不远的一个坡嘴上,因为没有树木,一棵葛花便随高就低,整整占领了一个坡头,一根根不在路数的藤条在坡头转来转去,以至于连小孩也害怕进去出不来。在老栎树树根长着的葛花与老栎树一样古老,好似他们之间有什么亲戚关系,老栎树完全放任葛花的攀援与缠绕,有的葛藤已经深深地勒进树枝的肉里头。老栎树长多高,葛花就攀多高,在老栎树的顶稍上,仍随风摇摆着葛花富有弹性的嫩条。
老栎树与葛花好似有着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或者是老栎树收养了葛花,从此就成了一家人,那些过分的缠绕或许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正是栎树与葛花浑然一体的结合,不但为我们的的村子增添了无限的神秘,还因她们宏大的美丽让我们村名声远扬,在那个缺一少吃的年代,竟然有人在葛花开花的时候凑空来到村前观看。
每年三月,两棵老栎树便是满树葛花花,远看是一片淡蓝淡紫烟云,在烟云中晕染着娇嫩的褐红小叶片;一串串花朵的风铃摇动着春天;在无风的阳光中,自带着微风的大树向原野飘散着一种独有的清香;成千上万的蜜蜂、黄蜂、很多说不清名字的瓢虫、金龟子,在树冠上蹿飞;一片“嗡嗡”声模糊了世界,掠过耳轮的清晰的“嗡嗡”声又让世界清醒;大大小小的鸟不停蹿飞、降落、鸣叫,她们好似按耐不住惊喜的心情;花瓣花萼在太阳的光线中纷纷飘落,好似天女散花。走进树下就走进了一个声色的氛围中,走进了一个生命的乐园里。
那时,树是集体财产,葛花又特别好吃,如果葛花再兑上鸡蛋炒,就是难得的美味。每年初春,村里人就会盼望着葛花花开采花去。等到生产队长一声令下,在淡淡的曙光中,在藤条与花缝中,就会钻进男男女女几十人。他们大多把箩筐用绳子拴在树上,一只手抱着树枝,一只手拿着木钩子,在闲话笑声里采摘着欢快。泼皮的娃们则攀上葛花柔软而结实的藤条,往花堆里钻,身子随风颤悠悠地摇摆,在大人的吆喝中,不一会就摘半箩筐葛花。有时,藤条上面的树枝“噶嚓”一声断裂,藤条哗啦啦下坠,满树都是惊呼,但藤条却不会断,藤上的娃还在笑呢。有时,一阵风过,小媳妇头上的花手巾,随风而去,在小媳妇的咦咦声中,人们便笑,说还以为是只花鸟呢。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老栎树还是在我的不知不觉中消失了。那时我到县城上学,我穿着母亲亲手为我做的千层底鞋,棉布肉扣布衫,枯瘦如柴,弓着脊背,立刻成为嘲讽的对象,而我则蜷缩在心灵的角落里自卑。在我幼小的荒凉中,我对老栎树产生了无限的怀念,老栎树才是我真正的家园。但当我期末回去时,老栎树却没有了。我站在院子里,往门前老栎树处望去,因没有老栎树的遮挡,眼前便成了光秃秃的山坡。整个假期我都魂不守舍地在井旁转悠,感到村庄就暴露在荒凉贫穷之中,第一次感到村庄的破烂,落后,了无生机。
三十多年来,我到过无数的地方,走过数不清的道路,有时候我却感到,如果把我的人生路线画一张图,好似就是老家与县城的一条连线,我一直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路上,因而我不能算是一位道地的城市人,也不是一位乡下人。我只能走在没有归宿的路上。虽然我常年居住在城市里,我却更喜爱乡村的生活。然而,随着那两棵老栎树的消失,我的乡村就走上了消失之路。村庄是用房子建立起来的,但从建立的那一天起,房子就开始一点点陈旧老化,最终必须扒掉新建,新建的房子与老房子就失去了联系,村庄就会成为一种不可久远的记忆。然而树的村庄却在老梢上长出了新枝,岁月化作了清晰的老皮,树成为一种活着的记忆,连贯着的情感。
那两棵老栎树才是我家园中的永恒。我失去了我的家园。
家乡巨变的背后隐痛
这些年我每次回老家,就会感到家乡巨大的变化。
我小的时候,种地靠犁,一个队有没有实力,多少头牛是一个重要指标。牛除了犁地,还能攒粪。喂牛需要大量的草。荒坡无水涵养,仅仅春天头茬能割,到春末就成了硬梗。因此割草都是溜着地埂水边,这些地方有限,常常是你割了他割,草刚刚能够用手攥着,就被割去,地埂水边割得光秃秃的。
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粪少,就得积肥,在土厚草多的地方用锄刮,然后堆到一起用黄土封住沤肥。还割“青芽子”,就是捡树叶多的嫩枝嫩毛子割,然后积肥,或铡碎撒进稻田里直接增加水田肥力。
那时,柴火是一项重要的资源,一天三顿饭,家家要冒烟,那时冬天特别冷,还要烤火,用柴量特别大。好在我们那里出门就是山,山上是从清末就开始养植起来的蚕坡,是漫山遍野的栎毛墩。为了喂蚕,栎毛要间伐,就是隔一年砍一次。栎毛是好柴,火旺烟少。但很多家舍不得烧,都担到街上换了油盐钱。所以家家都拾柴。叶子青的时候,上山割毛子,放在石头上晒干,冬天栎毛叶落了在栎毛墩下搂柴。有时候山上搂光了,就找白草稠密的地方用锄刮掉再搂。虽然柴不太好拾,但山场面大,还能拾来。而山下的人家没坡,总为柴火发愁。他们总是到冬闲的时候,一拨一拨人到我们门前的山上拾柴,一挑一挑往家里担,弄几大捆子用架子车往家拉。
那时,盖房子用的檩条椽子,娶媳妇用的家具,老了人的寿材,都是山上地头砍的。你砍他砍,大树早没有了,哪棵树刚刚长大一点,就会有很多人打树的主意。剩下几棵歪脖子老树,也做了菜墩。
那时的坡,割割,砍砍,搂搂,刮刮,没有什么大树,草也少得可怜,地常常一片土白,要不是那些栎毛撑着,要不是草能“春风吹又生”,真不知道乡村会变成什么样子。
可就是在那个树木野草难以长大的年代,门前的小河却总是日夜唱歌,西山的黄蓓草坡春夏翻滚一坡绿浪,冬天厚重一坡红霞,门前坡上的石根草棵间有拾不完的地衣,那是做蓑衣干饭的好菜。尤其是门前的那条一大步就能跨过的小河,从来没有亏待过我的童年。那时我身体虚弱,没力气干活,但逮鱼摸虾却是我的拿手好戏。我经常与姐姐一起下河,从山根小河的源头,到下面的水库头,小河也就是二里多地,我们经常可以捉到螃蟹小鱼小虾黄鳝泥鳅大半盆子。有时还能逮到老鳖。一旦下大雨涨水,没有住点,我就急不可耐,等雨停水落,门前那条平时没水的干沟就会上来很多泥鳅小鱼,等水想要断流,泥鳅小鱼就困在一个个小水坑里,任我捉去。在坡根有一个常年不干的小水库,一到夏天我就三天两头到水库里洗澡,而在洗澡前我与几个娃们会先悄悄来到库边,偷看水库边石头上老鳖晒盖,突然一声叫喊乱扔石头,下得老鳖慌忙滚进水里。
遇到干旱,小河也有断流的时候,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水坑总是保持着小河永久的记忆,在断水处的几个石头或小灌木的乱根处,螃蟹会打一个个小洞,留下一片醒目的新沙,好似它们能感到河水不久就会再来,因而不急于往不远处的水坑里搬家。有的菜地紧挨河边,在河里挖一个大坑,水立马源源不断渗出,就可以浇菜了。
那时青蛙也特别多,尤其是春天,稻田,河里,水坑,湿地,院外下雨后的水坑,都有青蛙的叫声。晚上,青蛙的鸣叫由近及远一层又一层,感到乡村是属于青蛙的,人住在乡村是来听青蛙叫唤的。而坡上,也是从房前屋后一直连到远山,到处都是蝈蝈们不舍昼夜的鸣叫,让你感到山野是属于蝈蝈的,人住在乡村是来听蝈蝈叫唤的……
有时候我感到奇怪,自然生态的能力是建立在完美的植被上的,可老家的植被已经破坏得不像样子,但却仍有着神奇的复苏力量,尤其是那条小得不能再小的小河,没有什么树木,那来的源头活水?
这些年随着村里人口的外迁,生活水平的提高,土地不再是人的命脉,牛羊几乎没有了,没有人割草了,偶尔有一两头牛,别人不要的稻草已经喂不完了,偶尔割草,出去门到处是溜腰深的草,三下五去二就是一大箩头;很多农村人烧上了煤与液化气电器,拾柴的少了,偶尔拾柴,就在门口的坡上专找标直的栎树枝砍,一会就是一大捆子;盖房用水泥钢筋,娶媳妇不再找木匠做家具了,做着不但费事,做出来也赶不上潮流,老人的寿材要柏木香椿与鬼柳,而且讲究尺寸,用小树拼凑的棺木,会让人笑话,而这些树种的大树我们那里已经没有了,寿材都是买的,再不用砍树了;上地是各种各样的化肥,不积肥了,再也没有人刮地皮砍青毛子了。过去养蚕是一项很大的收入,现在人嫌劳累收入少,再也没人喂了,栎毛也就不用间伐了,不用砍柴了,栎毛坡慢慢变成了林子;过去的坡边地,沙包地,小片地,已经没人种了,成了杨树林,甚至有的好地也种上了杨树;都外出了,留下的孩子很少,很少的孩子,忙着看电视玩手机,没人捉泥鳅钓青蛙了……
每次回老家,看着老家人烟稀少,房子破败,路满杂草,总为老家的荒凉哀叹,老家要在时代中失落了。每次回老家,看着山野一天天茂盛,又为生态的好转感到安慰。但让我想不到的是,今年回老家,坡根那个从没有干过的水库从春天栽秧时开始干枯,水库底白亮亮的,裂着四指宽的口子,全条小河连一个水坑也没有,完全成了干沟。今年遇到了几十年不遇的干旱,属于极端天气。但小河并非今天在极端天气的暴死,而是一条河流慢性死亡在今天的终结。
几年前,有亲戚需要螃蟹治病,两个人在小河扒了一晌,仅扒一个螃蟹。当他们告诉我的时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按理现在很少有扒螃蟹的,螃蟹应该更多了,根据我的经验,螃蟹是钻洞的,逮到的永远只是少数,我小的时候,有时几乎天天下河,螃蟹总是有的。几年前我曾走进我梦想中的小河,忍不住跳进河水里,河水里一条鱼没有,用手去摸一个个石根,一个小虾也没有,河水仍然流着,但已经不再是小鱼小虾的家园,是河背弃了它们,还是它们放弃了自己的家园,让我感到很难理解。
几年前栽秧的时候,我回了一趟老家,人们正在栽秧。然而,在一块块注满水的稻田中,聆听许久,才有偶尔的一两声的蛙鸣。在我的印象中,每年栽秧的时候,正是青蛙繁殖季节,叫得最起劲儿的时候,青蛙,土蛤蟆,癞蛤蟆,气死蛤蟆,药蛤蟆,争着叫唤,常常几个人在稻田栽秧,一圈一圈叫声围着,干累了烦了,便感到聒耳,用泥巴往远处砸,叫声突然停止,田野宁静出空阔,但挖泥的手尚没洗净,一声蛙鸣起,到处蛙叫声。
小时我喜欢地衣脆脆而独特的味道,每当小雨过后,地衣膨胀,就是拾地衣的好时候。地衣长在稀疏的小草间,平缓的石头边,多的地方就会一个挨着一个,一会就捡半筐子。我总感到这种生命藏着什么秘密。我见到的植物都有根,即使蘑菇木耳灵芝也要扎根才能生长,独地衣无根,就搁在地上,慢慢就长大了。这些年回老家,心想,现在没人搂柴了,地衣应该更多了,我知道哪些地方多,但却仅偶尔发现一两个。这也让我迷惑,过去生态破坏,地衣很多,现在生态变好,地衣却少了没有了。
我们村一直没有麻衣雀(喜鹊),只有到秋季的时候,从大山会飞过来成群的山麻衣雀,没几天就又不见了。每次从山下回来看到路边有很多麻衣雀窝,就为山里没有麻衣雀感到遗憾,长辈讲,麻衣雀是平原的鸟,它们是不进山的。山里还有很多灰色的松鼠,村里却从来没有过,长辈讲,松树是深山动物,它们是不进村的。但这些年,我们村口的杨树上却有好几窝麻衣雀,松鼠在村子里的树上上蹿下跳,完全不把人放在眼里,它们专偷麻衣雀的蛋喝,麻衣雀报不成窝,但却没有走的意思,松鼠也没有走的意思……
生态变好了,人却走了,人走光了,没人的老家还是不是老家?人走了,生态就变好了,生态变好了,河却干了;河还没有干的时候,鱼虾没有了,水坑仍睁着眼睛,稻田仍长着谷子,青蛙却不叫了,田野成了哑巴,没有鱼虾与青蛙的原野还是不是原野?
人到城市找家去了,那些动物的新家又在何处?
这些有悖常理的现象总是让我感到困惑,好似在自然的背后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改变着自然的秩序与走向,而我在城市的生活中,看着住在楼上楼下相互不认识的人们,看着木着脸盯着手机的人们,我感人类的背后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秩序与走向。有时候对这个问题想得多了,竟然害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