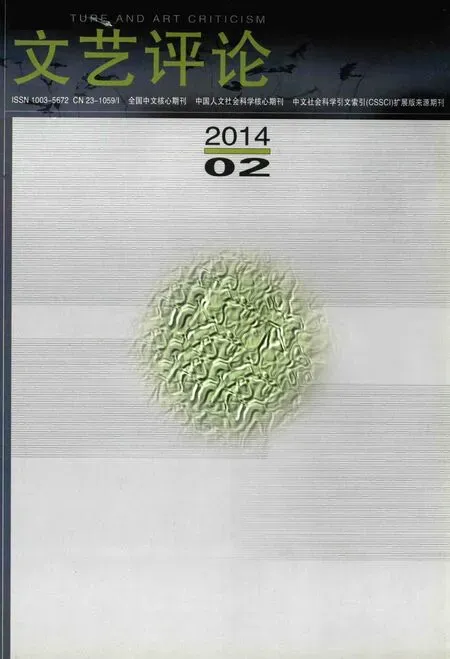偏安时代士人心态及文化意义——以东晋和南宋为例
段春杨
东晋和南宋两个王朝是极具代表性的偏安政权,均由前代统一封建帝国急转直下进入偏安时代的,外族的入侵迫使统治者退守半壁江山,社会的剧烈变动直接带来文人心态、审美趣味等诸多方面的变异,从这个角度讲,东晋和南宋比其他偏安王朝都更加具有典型意义,通过对比同处于偏安时代的士人在心态上有何相同或相异,反映出怎样的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却无人触及过的课题。
东晋和南宋时期的“士人”所代表的群体有所不同,美国汉学家包弼德曾说过:“作为一个描述社会成分的术语,‘士’在唐代多数时间里可被译为‘世家大族’,在北宋可译为‘文官家族’,在南宋时期可译为‘地方精英’。”①他的表述是局限于公元600年至1200年之间,而事实上“世家大族”亦或“门阀士族”是由汉末三国时期开始崛起,到了东晋已经达到了鼎盛的阶段,因此“世家大族”的称谓更加适于东晋士人群体,东晋的“世家大族”和南宋的“地方精英”都是当时掌握文化知识权利的阶层,他们是决定当时审美文化发展水平和趋向的主导力量,故本文所说的“士人”在两个时代的差异并不影响论题内容的探讨。
一、内向超越型文化心态的外在表现
中国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一个内向型的民族文化心理。原始儒家“士志于道”的伦理价值取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带有高度政治化的原则规范所强调的都是通过人的自身修养来规范外在行为;魏晋时期思想解放所追求的个体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带来了内向型文化意识的空前发展;般若佛学所讲究的“物我两忘”的精神追求,同样体现了内在心灵的自由。偏安政权建立之前的社会动荡对思想文化领域造成的影响是持续的,甚至波及到社会政治相对安定的整个偏安时代,这时期的士人心态在内向型民族文化心理的总体格局下,实现了内在自我的超越,突出地表现在远离政治中心和审美情趣的日趋雅化两个方面。
特殊的政治环境,为内向型的文化形态实现超越创造了外部条件。南宋诗人林升的著名诗句最能说明偏安时代统治集团的生活状态:“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统治者在他乡异地依然可以歌舞升平、苟且偷安。这其实对有志之士的刺激非常之大,偏安士人面对国家疆土的失守,对少数民族的节节退让,报国无门的他们渐渐丧失了恢复中原的信心和愿望,在心理层次上,大汉民族的优越感日益萎缩,进取精神渐趋消弭,这时,中国传统文化造就的内向保守型的文化心态所发挥的作用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处于偏安时代的士人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心灵的归宿、精神的家园。魏晋以来由生存危机和信仰危机引发的社会“离心”效应②在东晋时期继续深化并呈现出新的特点,东晋士人继续着由西晋而来的玄言清谈,虽然在渡江之初曾对西晋的乱亡有过短暂的反思,也曾认识到玄言清谈给他们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但这种反思很快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湮没在朝廷上下一片苟安的状态之下,东晋一朝形成了上下一致的偏安心态,没有形成举国一致的北伐恢复中原的愿望,在当时享有很高声誉的王羲之两次阻止殷浩北伐最能代表东晋士人的偏安心境,朝廷中有人主张北伐却屡遭反对也充分证明了偏安的心态已经成为东晋士人的普遍心态。东晋的世家大族,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主导者,国家的失守并不影响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他们仍然可以在江南重建庄园,可以继续西晋以来形成的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过分优越的特权为他们创造了耽于享乐、追求潇洒风神的条件,在留下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成就的同时,远离了政务,也与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渐行渐远,他们遵循着“不避世的逸民和不艰苦的隐逸”的原则,“在他们的立场上,并不是避世不避世的问题,而只是要问将心情置于何种境地的问题。”③东晋士人将心情置在对宁静闲逸的人生理想的追求上,而对政治则普遍采取一种消极避退的态度。南宋士人在心态上延续了北宋以来强烈的忧患及危机意识,自唐代科举制度建立并逐步完善以来,更多知识分子参与到国家政治中来,孔孟强调的“学而优则仕”到宋代真正地得到实现并成为士人难以摆脱的生存方式,因此这时的士人已经不是东晋时期仅仅局限于世家大族的狭小范围之内,他们有着慷慨悲歌的淑世情怀,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丝毫没有忘记国破家亡给他们带来的沉重打击,偏安的心态在南宋时代是统治者才有的,并没有覆盖到整个的士人阶层,报国无门带来的灰心和绝望才是这一时代文人的共同心声。因而相对于东晋士人对政治的主动避退,这时期的士人对政治的疏离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因素使然,政治和社会形势渐渐消磨了他们的进取心和社会责任感,面对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正义和良知并未完全泯灭,他们忧时伤世,却无力挽救处在危机中的国家,向心灵深处寻找安慰成了士人普遍的情感取向,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想内心世界的开掘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偏安环境造就文人更加突出的内向型文化心态也表现在审美情趣的日趋雅化上,这实质上也是偏安士人与政治疏离心态的延续和发展。东晋士人在事功上无进取之念的偏安心态,使得汉末以来的自由觉醒表现为更加彻底的心灵解放,外在表现为对宁静高雅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从中获取精神上的满足,这相对于西晋士人的对世俗物欲的追求显然更进了一步,东晋名相谢安冷静自若的指挥千军万马,王徽之雪夜访戴都以东晋特有的潇洒风神、高雅的精神境界成为名士风流的千古佳话,这种特殊环境造就的特殊的思想文化,为后世提供了一个美的境界。然而这种美是建立在衰落动乱的时代里,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如果考虑到其时的半壁江山,考虑到中国士人忧国忧民的固有传统的话,那么这种高雅情趣所反映的精神天地,便实在是因而东晋闲雅的审美情趣是狭小心地的产物,是偏安政局的自慰。”④这种审美趣味的追求是想摆脱社会剧烈变动带来的压迫感、紧张感,高雅情操下面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东晋士人是中国士文化里特殊的一群,他们的心态是内向型文化心态的特殊表现。南宋的“雅”则主要表现在“地方精英”在文学创作上的骚雅精神。科举制度在宋代的完善,使读书与为官构成了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他们既是文人又是官员,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文化的领航者,因而说此时士人的审美趣味集中并突出地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是不为过的,而词作为南宋最具代表性的美学样式,它所表现的审美追求在当时无可替代地反映了审美文化的主导倾向。“骚”与“雅”来自两个不同的审美思想体系,洪兴祖《楚辞补注》载班固《〈离骚赞〉序》解释了“骚”的本义:“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⑤南宋词中的“骚”与此意相契合,侧重作品立意,并拓宽了词在表现上的宽度和广度,“雅”来源于《诗经》的“风雅”传统,侧重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含蓄委婉。南宋词的“骚雅”体现了“屈骚”与“风雅”两种体系的结合,既表现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也表现出与社会价值的融合,通过托物寄情、抒怀言志曲折地表达对国家政治的关注,这与南宋士人忧患内敛的文化心态相一致,南宋词对“骚雅”精神的追求,既包含了对个体人格的张扬,也有社会群体意识的表达,这是在民族危亡的偏安时代对前朝已经突出的“风雅”精神的新发展,“雅”中所体现的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对讽喻传统的继承则是宋人总体内敛的文化性格的外在显现。
两个偏安时代表现出同样鲜明的内向超越型文化心态。东晋士人在对自我内在精神气质的塑造上超越了西晋士人对现实物欲的满足,南宋士人则在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上对北宋士人以词来抒写私人生活环境实现了内在的超越。在各种条件下深入到自我的情感世界中来,在中国文化史上,东晋和南宋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却是最为典型和深入的。
二、偏安时代士人心态的思想根源
由追求外在事功转向关注自身价值,是东晋和南宋两个偏安王朝共有的心态转型。“哲学是时代的灵魂。”⑥文人心态的变化自然与社会政治变动有内在联系,更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东晋和南宋的思想文化领域都处于重大变化时期,雷海宗曾在《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中将中国历史以东晋太元八年、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为界分作两大周,他的理由是,前一周的中华文化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代,后一周的中国文化在血统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单纯的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即一个综合的中国。他还认为宋代的三百年是一个整理和清算的时代⑦。雷海宗以文化为视角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正说明了东晋和南宋在这个分期中的重要地位,两个朝代正处于本体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入侵而动摇,最后又由本体文化进行整理清算的两端。在对前代哲学思想的怀疑否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两个带有思辨性的哲学思想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肯定内在心性、强化自我价值。
汉末和魏晋前期,没有了过多统治上的束缚,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和开放,原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提倡的一套价值观念随着汉王朝的分崩离析而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否定,对外在权威的质疑促成了内在人格的觉醒,玄学经由以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之后,又由郭象进行了集大成的发展,到东晋时期玄学义理的论辩和探讨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成熟的状态。这时,般若佛学大量涌入,并摒弃了原来依附于玄学的“佛以玄释”的状态,开始正式以独立的哲学姿态出现,由与玄学交织互渗,逐渐向佛学理念和佛学精神方面转化。僧肇的“性空说”重视人的内在精神修养,扬弃了魏晋玄学追求人格和自我的超越而建立了一种精神本体论。玄学虽然避世却并不否定人生,佛理更加重视人的内在精神的修养,玄学与佛理中同样强调的与自然融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获取灵感,获得心灵的解放,从而摆脱人事的羁縻正符合东晋士人政治避退的心理,狭小的生活范围,偏安的心理状态为带有思辨性的哲学思想发展内在心性的理论创造提供了必要条件。般若佛学引导着“东晋士人从西晋士人的纵欲转向追求宁静的精神境界”⑧玄学中“任自然”的思想又是他们不能摒弃的,于是东晋士人所追求的宁静闲雅的精神境界依旧是立足于人间的,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远离政治却不可以远离世俗生活,因而与政治疏离之后的士人只能向心灵深处寻求解放。正如雷海宗所说,自东晋开始,中国便进入综合文化的时代,并且外来文化的成分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著名文化学者余英时也曾说过:“自魏晋至隋唐这七八百年,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⑨外来文化夺取中国本位文化的统治地位的现实渐渐地又引起了思想家们的怀疑和反思,于是从唐代中后期开始,复兴儒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时至南宋遂有代表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理学家们“欲夺回久已失去的精神阵地”⑩,如果说东晋的玄释合流,是在对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否定和怀疑基础上产生的对外来文化的认同,那么南宋理学的建立则是对自身旧有价值观念的扬弃,吸收外来文化中对内在精神世界的肯定而开辟出的新天地。于是发展一套本位文化的心性论提上日程,由“外王”而转入“内圣”成为重新确立民族本位文化正统地位的必然之路。在南宋,以创建书院和社会讲学为显著特色的新儒家伦理已经逐渐深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强调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实质上是先秦儒家提倡的“士志于道”的伦理价值取向的强势回归,既然在哲学思想上强调心性,那么内向保守的文化心态便是充斥于南宋的普遍性的心理状态,在心理上的责任感受到政治上的强烈挤压而无法实现时,向心灵深处寻找安慰便是文人创作的常态,东晋时期的心灵解放,在这里已经转变为在文学创作上向内心世界的深入开掘。
两个偏安时代的不同的主流哲学思想同样强调内在心性和精神,决定了代表当时审美文化主导地位的士人在心态归属上的共性。东晋对玄理、佛理的探讨与创新使东晋文化充满着哲理思辨色彩,南宋程朱理学通过对“内圣”的强化和对前代哲学思想的总体性反思,同样凸显了理学的思辨性。处于这两个时代的士人虽然受到不同时期的不同哲学思想的引导,但隔代相望的两种思潮均未脱离中国古代整体的内向超越的文化型态。
三、生命意义的发现与生命意识的强化
东晋时期心灵解放的文化意义在于对生命意义的新发现。对生命的关注并不始于东晋,汉末以来,伴随着对原有意识形态的否定和怀疑,产生了以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关注为表征的人的觉醒,人们开始了对生存问题的思考:“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繁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货值得怀疑的,他们并不可信或并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⑪而这种对生命的关注仅仅是生存危机给人带来的朝不保夕的畏惧感、恐怖感,只有在真正“摆脱人与自然冲突的羁绊,并确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命结构”的基础上,“自然外物第一次作为审美对象存在,而不是作为生命忧惧的对比物”⑫这时生命才第一次具有了意义。人们第一次以平等的姿态认识到人生以外的客观外物同样具有价值和意义,相对于短暂的人世豪华,自然山水的美才是永恒的,从山水中获得了灵感,把强烈的生命意识移植于山水之中,这与东晋士人的偏安心态和闲散的生活环境结合得非常完美,在这里,自然山水“作为避世求独乐与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发挥作用”⑬。如果说西晋以“金谷宴游”为代表的文人集会活动只是将山水作为他们享乐生活的一种点缀,那么东晋偏安的环境滋养了这种审美情趣并将其上升为一种带有强烈主观意识的山水审美意识,而且已经成为东晋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便是王羲之著名的《兰亭集序》,它表达了人对自然生命的敏锐感受力,与宇宙万物相通,将对人生短暂的喟叹上升为一种宇宙的哲思。在“快然自足”之余,“不知老之将至”,“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山水情趣中的迁世之悲,到这里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历史情怀,一种超越了生死的“宇宙品类之感慨”,这是前代士人从未感悟到的。
在南宋,当哲学思潮引导着士人以理性之思融入深微痛楚的表达之时,当内向型文化心态表现为空前地肯定个人价值之际,由时光流逝所形成的伤春、叹时、嗟老等意识逐渐凸显出来,叹老嗟卑、伤春悲秋的生命流逝的意识在南宋业已发展成熟的词的创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作为南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审美样式,已经不仅仅是北宋时期作为吟风弄月、抒写私人生活的载体,情感容量已较前代大大拓展。较之其他文本词是更加贴近生命主题的表达方式,节序词、悼亡词、咏物词在南宋的大量出现就是表达强烈生命意识的最好例证,“丰富的时间意象,比较朦胧的生命意识被拓展成多维的存在性思考。”⑭这里的“多维存在性”包含了节序词中通过季节现象反观生命,如辛弃疾《汉宫春·立春》:“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寒雁先还。”时光转换,朱颜渐老,愁之将至;花开花落,岁月匆匆,徒增惆怅。包含了悼亡词中通过咏叹有缺憾的爱来思考生的存在,如史达祖《寿楼春·寻春服感念》:“谁念我,今无裳”、“身是客,愁为乡”斯人已去,留给生者的只有孤独和飘零。也包含了咏物词的托于他物寄托作者盛衰兴亡之感,如王沂孙的两首《齐天乐·蝉》,第一首:“梦短深宫,向人犹自诉憔悴。”寄身世之感;第二首:“余音更苦,甚独抱清商,顿成凄楚。”托遗臣之愤。时间的流逝、空间的变幻与个体生命的对垒表达了人对外物乃至自身生命无法掌握的迷惘,表现出一种时代性的忧郁和迟暮感。这种“多维存在性”的生命意识,是对仅仅局限于私人空间的个体生命的思考拓展为前所未有的生命意义、个体价值的理性之思。
时代文化上的思辨精神使东晋和南宋诗人对生命的关注多了一层理性的感悟,在永恒与短暂、自然与人生、时间与空间的对比转换中了悟人生,实质上都以自我心灵情感的流动为归依,在充满颓废悲观的消极感叹中,表达对人生的执著与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