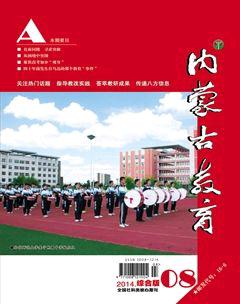台湾游学纪行
杨东平,男,1949年9月生,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著名教育和文化学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数种理论著作和书籍,发表论文30余篇,在我国教育理论界和知识界有一定影响。主要作品:《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4年)、《最后的城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学问中国》(教育部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文汇出版社,2003年)、编有《教育:我们有话要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
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按:今年4月下旬,随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等5个教育NGO(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考察台湾的教育改革和社会组织,将感悟和心得发表于此,与各位分享。
1994年4月10日社会各界要求教育改革的大游行,被视为台湾教改的起点。20年后实地考察台湾的教育改革,感到台湾教育虽然与大陆有相似的背景和一些相似的问题;但就教育的整体面貌、教育治理和公共政策而言,已经大不相同。行前我们讨论过“410大游行”的主要推动者黄武雄先生所著《台湾教育的重建》。这的确是一种重建,寓教育重建于社会重建之中,是在自下而上、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社会建设过程中逐渐完成的。
以我们参加的“均优学习论坛”为例。论坛由“国家教育研究院”、地方政府教育局以及教育类NGO共51个单位共同举办,共设置42个议题,今年是第五届。位于新北市三峡区的“国教院”风景优美、设施完好,居然与NGO共同举办论坛,免费提供会议场所和住宿,实在是超越我们经验的。事实上,由教育行政体制独任治理的传统已成过去,这里没有体制内外之分,大学教授活跃在各个NGO之中,公办学校的老师同时是教师会的成员,政府官员、教师、家长都是平等的参与主体。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治理,已经形成学校行政、家长会、教师会三足鼎立的常态。我们遇到的校长、幼儿园园长,无不十分自信地侃侃而谈,对学校共同经营的架构和自己的职能角色十分明白。
论坛的议题,除了“PISA国际教育评比的迷思”、“走向网络时代的学习”、“芬德教改对台湾的启示”等较宏观的话题;多为涉及教学、课程、教育实验的微观议题,如“维基百科在大学教育中的应用”、“教师的灵性与情绪增能”、“法国小孩不考选择题?”、“家长自主教育与实验教育”、“自学与共学教育”、“课后照顾玩英语”等等。还有一些则是台湾独特的话题。台湾从2014年9月起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称“十二年国教”,成为当前重大的教育议题。由于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劳工和新娘已在人口构成中占有相当比例,出现了“台湾的东南亚教育”的议题。而“大学退场解决之道”、“以公民行动推动校规修改”、“十二年国教与社大平台”等议题,显示的是台湾教改的社会参与维度。
大陆最为重视的教育公平议题,如农村教育、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教师队伍待遇、小升初择校等等,在台湾好像不是问题,已经获得制度性的解决。教师与军人、公务员一起,历来属于享受优惠待遇的“军公教”群体。“偏乡教育”(农村教育)受到应有的对待,农村小型学校的调整撤并有严格的程序和评价方式,分为“一般指标”和“特殊性指标”两部分,后者包括“是否原住民学校”、“该乡镇只有一所小学”等,具有重要影响力。我们所到的南部乡村学校,基本都是100个学生左右的小规模学校,学校设施完好、教师配备充裕。原住民的山区学校、离岛学校,教师工资标准比普通学校要高2%~10%,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
最能反映治理现代化的,是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回应来自教师、家长和社会的诉求,教育体制具有很好的吸纳性、弹性和柔性,各种政策、规定、立法是可以商量和改变的。社会组织的主要参与方式,就是与时俱进地推动各种教育修法。典型如在公办学校之外、实行不同教育理念的“另类学校”的合法化,以及通过“非学校形态教育实验”的修法,将“在家上学”合法化。
政府的教育责任不仅体现在“十二年国教”,也体现在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台湾的幼儿园实行学前一年免费,对经济困难家庭每年补助1.2万元(约合2400元人民币)。对占总数约5%的有学习障碍的学生,经甄别实行特殊教育,学校有专门的教师编制和预算。对占学生总数15%~25%的“学困生”,由政府提供经费实行课后补习(每周三次,每次两节课),对学生免费,叫做“补救教育”。遍布台湾城乡的“社区大学”简称“社大”,是在教改运动中应运而生的,它与我们理解的成人学历和非学历教育不同,是一种社会教育,旨在通过“知识解放”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和社区营造。社大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财政。
人们最关注的是台湾教改20年成败与否的评价。当年“410 大游行”提出的4个基本诉求,“广设高中大学”早已实现,今天的现实是2300万人口的台湾,有175所高等学校,录取分数不断降低,出现“考不上大学也难”的局面。“实行小班小校”的诉求也早已实现,法律规定小学的班额不得超过29人。批评者认为这并非政府善治,而是由于“少子化”的现实。可是,在中国大陆同样少子化的过程中,“小班小校”的目标从没有出现;相反,各地致力于集中规模办学,乃至打造巨型学校、“航空母舰”!第三个诉求是“推动教育现代化”,包括重视个体参与、强调个体差异、尊重各族群的主体性,改善教育品质,增加民众的自由选择。第四是“制定教育基本法”。应当说这些目标已大致实现,当年“教育松绑”的诉求也已基本实现。我们看到的台湾教育,已经实现了“正常化”:政府、学校、老师各安其位,做自己该做的事,学校像学校,校长像校长,老师像老师。同时,也已经实现了教育治理和教育价值层面上的现代化,学校实行以学生为中心、善待儿童的教育,废除了体罚。随着实现九年一贯制课程、改革联考制度,中小学的教育环境已经比较宽松,出现丰富多彩的教育实验和多元化的教育格局,小学基本没有升学、考试的压力,学生学习比较生动活泼,课外补习主要是在初中以上阶段。
我们在台期间,台湾的政治大学完成了新一轮校长遴选;新竹清华大学的校长遴选也刚刚完成,显示这一制度已经平稳和成熟化。基本程序是由相关人士组成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从初选的多名候选人中经评鉴最后入围3名,进行几轮的公开演讲和教师投票,胜出者报“教育部”批准当选。
对教改成败,黄武雄先生的评价是成多于败。问题主要是在扩大教育机会、教育公平的过程中,政府的承担不够,落入了经济主义的市场化轨道,2/3的高等学校是私立学校。而学者和民间对台湾教改乱象的批评,集中在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上,如取消联考制度后新的入学选拔制度的设计;取消中考实行“多元入学方案”产生的问题;实行“师资多元化”导致的教师队伍质量的参差不齐;推行“建构式数学”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实行“十二年国教”可能对职业教育、高中精英教育产生的影响——高中实行义务教育的一个重要价值,是淡化高中的明星学校;快乐教育可能降低学业水平;教科书开放导致的混乱情况等等。
在“均优学习论坛”上,教育部前部长、心理学家黄荣村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教改与学力的恩怨情仇》,以几次国际评鉴的结果说明教改并没有降低台湾学生的学力。对此,不妨补充2012年PISA测试的结果:台北地区数学第四,阅读第八;但是,学生的作业时间和课外补习的时间不到上海市的一半!黄荣村教授另外的重要判断,是关于台湾教改的社会悖论:右派社会(低税收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制度)和左派理想(要求更多的社会福利和公平);近年因分配正日益恶化,左派思想抬头,对大学谋求多元卓越发展不利。他认为面对信息化时代和国际竞争,教育改革仍应加快;但近年来台湾社会逐渐习于安逸,改革步伐大不如前。此外,是改革的方法论,即教育改革的不确定性:许多局部的合理的政策,最终导致并不合理的结果,这恐怕是对复杂系统的改革,人类理性的局限所致吧。
此行的一个重要成效,是两岸教育改革的民间力量得以携手,树立了明确的信念:教育,两岸共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