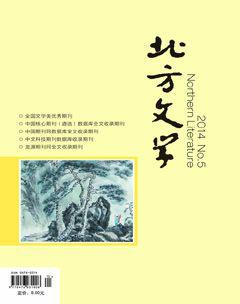魔幻现实主义的西藏本土化表达
权绘锦+李骁晋
摘 要:1980年代崛起的西藏新小说,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既源于西藏文学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潮中创新求变的内生性动力,也基于藏族传统和民间文化与培育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拉美印第安及黑人文化的相近、相似与相通。借助阿来等当代作家的个人性创化,不仅对当代文学意义深远,也为如何处理外来影响与本土转换,有所启示。
关键词: 魔幻现实主义;西藏新小说;本土化
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西藏新小说影响的研究,一可为当代民族文学寻求更好发展提供思路。因为只有创新求变,民族文学才能在日新月异的文学潮流中显示和确证自我;而固步自封,则不仅会导致文学生机全无,还会在日渐加剧的边缘化途程中面目模糊,甚至被忽略;二可为民族文学正确处理横向借鉴与纵向继承关系,提供思路。纵向继承是根基点,横向借鉴是催化剂。只有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才能使民族文学拥有未来;三可为民族作家准确理解全球化的多重意义有所启示。全球化是民族文学多元化与同质化不断博弈的历史性过程。民族作家只有直面、正视和顺应,吸取外来影响,以之观照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历史传统与文化心理,实现全球化、民族化与个人化之间的合理调适,才能具备走向世界的可能。
按照传统的观点来看,真正具备现代性意义的藏族文学,实际要从西藏新小说的崛起作为标志。而1980年代崛起的西藏新小说,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有着密切关系。这既源于西藏文学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潮中创新求变的内生性动力,也基于藏族传统和民间文化与培育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拉美印第安及黑人文化的相近、相似与相通。阿来及其《尘埃落定》对于当代藏族文学意义重大。通过对其与魔幻现实主义关系的解析,为民族作家如何处理外来影响与本土转换,应当有所启示。
一、西藏新小说与魔幻现实主义
纵观整个西藏文学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拥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绚烂的文化宝藏,但作家文学并不发达。建国之后,西藏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这“对于西藏藏文传统文学来说,无论从文种方面,从意识形态、思想感情、表达方式和表现内容等各方面,都是一种全面性的本质性的脱胎换骨。”[1]从整体上来看,从建国初到1970年代末,涌现的作家作品虽不少,但文学创作手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题材上多围绕西藏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展开。而西藏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面貌、宗教民俗,藏族独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范式,并没有反映出来。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作家在时代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下,采取高度政治化的书写姿态,而民族的自我认同和民族的自觉意识都未能得到凸显。
到了1980年代,在创新求变和改革开放的时代与文学背景下,西藏文学开始突破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度约束,寻求文学突破口和内生性的动力。这一时期的西藏作家们,一方面,向内发掘民族文化传统本身的“特质”,另一方面,也对当时国内流行的各种西方现代派横向借鉴,由此,西藏新小说应运而生。
如果说西藏文学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潮中的“自我发现”与创新求变,是其寻求国内外有益成果的内在动因的话,这一时期引进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恰好为西藏文学的创新求变提供了思路。单从流派的角度来讲,魔幻现实主义指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于拉丁美洲的,借助某些具有魔幻色彩的事物或者现象,以想象、象征、夸张、荒诞、变形等描写手段,以此来反映拉美特殊现实和历史的文学形式,是拉丁美洲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
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在拉丁美洲“发展成当今世界文坛上具有一定影响力又别具一格的文学流派”[2],与该地区的山川地理、人文物态、社会历史不可分割。地理上,绵延起伏的安第斯山脉,浩渺宽阔的亚马逊河流,地形辽阔的墨西哥高原等等,相对封闭而又神秘奇特的自然地理,为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空间;宗教文化上,古印第安文化的原始信仰和万物有灵观念,西班牙、阿拉伯等外来文化的传入,多种文化的冲突、碰撞、交流与融合,为拉美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资源;历史上,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和外来文化入侵,使得许多拉美作家借助夸张变形的人物形象和独特混沌的情节结构,来实现对本民族独特社会文化的观照与认同;艺术审美上,一方面,他们积极寻求适合表现本民族社会历史的文学语言;另一方面,他们大胆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技巧,最终形成以夸张、奇特、神秘、荒诞等为基本叙事特点的“魔幻现实主义”。
西藏新小说学习和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契合点,在于二者地域、文化、信仰、人文等方面的种种相似。从文学的接受主体方面来看,西藏在自然地理、山川物态、原始宗教等方面与南美洲的相似,使得它拥有着吸收借鉴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神秘奇特的自然地理:西藏自治区坐落在青藏高原的主体部位,地势陡峻的群山,冰雪覆盖的峰巅,星罗遍布的湖泊,亘古不化的冰川,奔腾不息的河流,垂直分布的植被带等等;其次,神佛弥漫的宗教文化。物活论、万物皆有灵魂的本土信仰与原始思维,和公元7世纪中叶传入的佛教,长期的宗教斗争和相互渗透、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再次,人文精神上,藏族人信仰群体之力,并拥有着高度艺术化的内心世界,随处可见的玛尼石堆、迎风招展的五色经幡,日常生活中的面具、服装、饰品等,都可以看出他们极为艺术化的一面;并且,西藏拥有着大量的民间故事与神话传说,这些故事和传说为西藏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取之不尽的传统资源。
总的来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西藏的传播与接受,西藏文学自身创新求变、突破表达的需要,是其寻求借鉴有益文化资源的内在性动力,而二者之间由于地域、文化等方面的相近、相似产生的“共鸣”,则是借鉴和吸收的契合点。也就是说,西藏作家们对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横向借鉴,是西藏文学自身创新求变与魔幻现实主义能够极好地传达出西藏本身的神奇、神秘和神韵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这“是西藏出现魔幻小说热潮的原因,也是西藏作家置众多外来文学于不顾,而单单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情有独钟的原因。”[3][P129]
二、魔幻现实主义的西藏本土化表达
虽然西藏作家接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比内地作家早的多。但西藏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群体亮相”[4],则是在1985年6月,《西藏文学》重点刊出的“魔幻小说特辑”。该期《西藏文学》刊载了扎西达瓦、色波等五位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不仅以不容小觑的创作成就展示了西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成就,受到了国内外的巨大关注;也为全球化语境下地域性文学的自我认同与发展、民族文学的纵向继承与横向借鉴关系提供了思路。
魔幻现实主义对西藏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西藏作家们并不是单纯地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作,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观照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因素,表达自己对于世界、人性、生命的体悟和反思。正如《西藏文学》“魔幻小说特辑”的编后语中所说,“不是故弄玄虚,不是对拉美亦步亦趋。魔幻只是西藏的魔幻,有时代感,更有凝重的永恒感。”[5][P]这种融入了作家民族观和世界观的本土化表达,不仅使作品带有浓郁的地域民族色彩,更使作品的审美内涵和表达力度大大提升。正是基于此,西藏魔幻小说一出生便广受注目。
不过,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在西藏“异军突起”之后,作家们很快分道扬镳。一部分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日渐减少,如金志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仅仅停留在1980年代,而色波自《星期三的故事》之后再未见到其魔幻现实主义之作;一分部作家在魔幻的同时转入叙事模式和文体上的创新实验,注重精神探索,如扎西达娃的“虚幻三部曲”。这些创作,个人化的实验性比较明显,在探索文本多种可能性的同时,不免晦涩难懂;还有一部分作家如阿来等,则立足于藏民族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精神内涵和文化积淀,吸收借鉴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和表达方式,实现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复杂观照和独特诠释。某种程度上讲,本土化特征最为鲜明。这在阿来小说的神秘叙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endprint
阿来作品中神秘叙事的艺术魅力中的神秘叙事,首先体现在神奇叙述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上。其魔幻现实主义创作与本民族的社会历史、宗教文化不可分割,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天火》一文,小说以自然火灾和政治“火灾”的交织,叙写代汉藏不同文化背景、思维观念的矛盾冲突,极具表现力度。
其次是根植于民族文化特质,对文化场域的“再发现”。阿来1980年代的神秘叙事,既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也受到当时中国文坛寻根文学的影响。作家发掘本民族的精神文化特质,在作品中展示出人性深层的麻木、愚昧的劣根性。《阿古顿巴》中,阿来将西藏民间传说中聪明、机智、富有正义感、四海为家的传奇人物,塑造成一个出身于富裕庄园,沉默寡言的孤独者。他离开庄园,寻找智慧和真理,并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惩恶扬善,声名远播。然而,这样一个智慧人物,却无法拯救人性的愚昧与麻木。他遇到一群毫无希望、等待被拯救的村民,并使这个濒临灭绝的部落重新强大之后,他们却认定阿古顿巴是不存在的;他救了一位失去儿子的瞎眼老太婆,把对方当母亲供养,但她却极度自私贪婪;在种种劣根性面前,阿古顿巴孤独地离开了这个无法拯救的部落。
再次,书写与表达的本土化。阿来的神秘叙事中,以种种神奇描写体现出西藏本土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藏民族特殊的心理结构。《鱼》表面上写藏族人“我”的一次钓鱼经历,内在展示的却是藏族传统文化禁忌对人的控制以及人对这种禁忌的反抗。在藏族饮食中,是忌讳吃鱼的。小说中写到扎西和“我”负责钓鱼,在“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禁忌”之间,身材魁梧的扎西把装有鱼饵的罐子交给“我”,避开对民族文化的违反。“我”则试图作一些挑战:从一开始期待鱼不要上钩,到钓到第一条鱼后萌生强烈的犯罪感;从鱼纷纷上钩的极度恐惧,到仇恨它们的慷慨赴死,让“我”在罪恶感中无法自拔;“我”选择继续钓鱼,直到用完鱼饵,听到鱼发出咕咕的叫声,并没有丰收的喜悦,而是在风雨大作的草滩上痛哭一场。正是激荡在“我”内心和精神深处的文化冲突和对抗,将看似普通的钓鱼场景写得惊心动魄。
此外,感到死之将至的索南班丹老人,走到牧场寻找被他放生的白马。一个轻盈的身体(即他的灵魂)就从他坐在地上的沉重身体中“走”了出来(《灵魂之舞》);猎人达戈得癫痫病,口吐白沫,发出动物般的哀叫,村人认为是他杀了太多猎物惹怒山神的结果(《达戈与达瑟》)等等。总之,阿来的神秘叙事,“都植根于他所熟悉的深远而悠久的藏族社会历史生活, 他借助那些充满诗意的清新而空灵的文字去书写这个古老而神秘民族的历史和文化”。[6][P107]也就是说,阿来的神秘叙事,以藏文化为基础,以魔幻现实主义为表达方法,建构了一个复杂而又神奇的文学世界,传达出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和独特的文化精神内涵。
三、《尘埃落定》:作为一种范例
在众多西藏式魔幻小说中,阿来的《尘埃落定》无疑是将魔幻现实主义创作与西藏本土文化历史结合的典范。这部初版于1998年的长篇小说,自问世之后就震惊文坛,至今被译成十六种语言全球发行。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的评语是:“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颇多通感成分,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
从文本的结构层面来看,《尘埃落定》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来营造故事氛围。围绕着罂粟的种植,麦其土司和汪波土司之间,由双方的巫师、门巴、喇嘛做法,念动咒语驱使冰雹;在罂粟花战争中失利的汪波土司,采用巫术诅咒,使麦其土司三太太央宗肚里的孩子死掉;迟迟不敢动手的多吉罗布,因鬼使神差飘落在他身上的寄魂衣,感受到神秘力量的推动,完成了复仇使命;傻子少爷到行刑人家里去参观得病,门巴喇嘛诵经作法为他治病……对作家而言,如何最大限度地展示神秘独特的藏族土司制度,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无疑提供了最恰当的表现方式。文本中这些亦真亦幻、神秘莫测的魔幻色彩描写,不仅反映出藏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神秘的精神思维模式,而且这种别开生面的叙事模式与技巧创新,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度。
从文本的文化层面来看,《尘埃落定》以藏族文化为中心的情节安排,表现出该民族所特有的生活状态、生存方式、文化伦理和审美范式。文本以藏地风情、土司制度、官寨文化,藏族各阶级人民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活动为着眼点,以细腻灵动的笔触演绎了藏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规模庞大构造精细的官寨,等级森严的土司制度和文化,穷奢极欲的土司家族生活,独特奇异的行刑制度,巫师、喇嘛、门巴等特殊群体,美丽的藏区草原风光……藏族作为一种与内地生存方式有较大差异性的民族,其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尘埃落定》中均得到较好的体现。
从文本揭示的历史背景来看,《尘埃落定》以独特的眼光视角和敏锐的历史感知方式,史诗性地展开藏民族生活和生存的画卷。《尘埃落定》叙述的是军阀混战到解放战争这段特殊历史时期。作品选择了以傻子的视角来叙述土司制度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盛而衰,最终瓦解的历史。对生活在边缘藏区的土司们来说,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是鸦片大量种植带来的无尽利益和无休止的战争,最终,粮食的极度缺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在“聪明人”相互勾心斗角,扩大罂粟种植的时候,麦其土司家的傻子二少爷“我”却预见般地种粮食,并开放贸易市场,促进边地贸易的发展;贸易市场带来了各种新鲜事物,方便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梅毒等传染源,土司们在欲望无休止膨胀之后,也断送了自己的“根”;最终,“红色汉人”与“白色汉人”之间的战争,打破了这里原本封闭自足的社会生活,土司制度瓦解,土司领地被汉族政权占据,并成为汉文化的边缘地区。
“我借用异域、异族题材所要追求和表现的,无非就是一种历史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认同,即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和普遍的人性指向。我把这概括为跨越族别的写作。”[7]《尘埃落定》观照藏族社会、历史、文化、族群等各个方面,并将这种地域民族的独特性以纵向的历史脉络和横向的世界眼光来理性看待和审视,再以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和独特的视角叙述出来,不仅使西藏文学真正传达出本土神韵和精神内涵的特质,也使得文本超越了地域民族的局限,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大放异彩。
当然,两种不同文化的“结合”与“对接”过程是极为艰难的,在“外来影响”与“本土经验”之间无法取得平衡,就会出现一系列难题:如创作本身的中途夭折或者断断续续;一味追求宗教的神秘性而出现回避或者脱离现实的倾向;在追求创新求变的同时陷入晦涩难懂的叙事“迷宫”;对地域民族认同与全球化语境的处理失当等等,这也对当下的民族文学正确处理横向借鉴与纵向继承关系,为民族作家提供准确理解全球化的多重意义以及思考民族文学的健康发展路径,有所启示和借鉴。
总而言之,作为“西藏文学在20世纪最为耀眼的一次灵光闪现”[8][P395],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下的西藏新小说,是地域民族文学的纵向继承与外来文学影响的横向借鉴合力的结果。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文学的多元化与经济技术的同质化,作为两翼,伴随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地域民族作家不可能独立于全球化之外,只有在观照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历史传统与文化心理的基础上,吸收借鉴有益的外来文学影响,实现全球化、民族化与个人化之间的合理调适,才能具备走向世界的可能。
参考文献:
[1]马丽华:《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01月.
[2]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1987年5月.
[3][4]曾利君:《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5]《西藏文学》,1985年06期.
[6]张智勇:《浅析阿来小说作品中的宗教文化》,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8(1).
[7]阿来:《历史深处的人性表达》,中国文化报,1998-03-31
[8]徐其超、罗布江村:《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权绘锦(1970-),男,汉族,文学博士,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李骁晋(1990-),女,汉族,兰州大学文学院12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