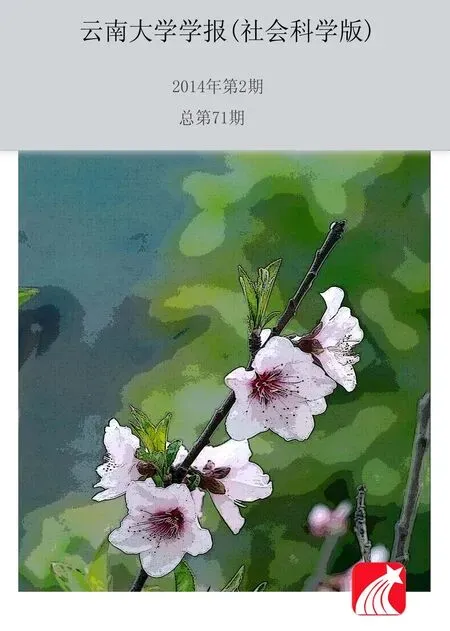北宋诗歌比喻模式的演进
张一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比喻是诗歌中的一种重要技巧,不但凝聚了诗人的才思,更反映了作者的审美。笔者曾提出“比喻模式”这一概念,证实了“比喻模式”可以作为鉴定诗人、时代风格的有效工具,并论述了汉唐之间比喻模式的消长轨迹所反映的审美风格的变迁,但尚未论及比喻模式在宋代的发展。北宋紧承唐代诗学高峰之后,同时也是宋诗史上新声迭起、光彩夺目的时代,分析北宋诗歌的比喻模式,不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那些诗学巨人的审美倾向,更能完善对诗学系统发展的描述,帮助我们在更长的时间段中审视诗歌审美发展的趋势。因此,本文对北宋数位重要诗人的比喻模式展开了分析。
一、 前期研究的回顾及北宋 诗歌比喻模式发展概貌
笔者根据对宋前诗歌比喻的研究,曾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的诗人早在《诗经》时代便已习惯使用比喻;永明诗人创造了新的比喻类型,即齐梁式比喻,此前固有的比喻类型则为汉魏式比喻;根据两大类比喻所占比例的不同,一个时代或一位诗人的比喻模式可以被鉴定为汉魏模式或齐梁模式,比喻模式反映其审美倾向,齐梁模式越明显,则齐梁化程度越高;盛唐至晚唐的诗歌呈现齐梁化程度加深的情况,元和时代是唐诗比喻从汉魏式变为齐梁式的转折点;唐代诗歌的齐梁化程度整体上高于唐前,即盛唐高于汉魏,晚唐高于齐梁,但在初盛唐之间诗歌的齐梁化程度曾一度下降,即盛唐诗歌的齐梁化程度低于齐梁诗歌。
具体说来,诗歌的齐梁化程度是通过以下规则判定的:以自然物为喻体的比喻(如“麻衣如雪”),为汉魏式比喻,以人类(包括其身体局部、品德、诗文创作)为本体的比喻亦均属汉魏式比喻,在永明以前,绝大多数比喻都是这一类型;以人工物为喻体、同时本体不为人类的比喻(如“澄江如练”),为齐梁式比喻,这一类型在永明以后迅速兴起;汉魏式比喻倾向于崇尚自然美,齐梁式比喻倾向于崇尚人工美;一位诗人使用齐梁式比喻在其所有比喻中所占百分比定义为R值,经检验,R=33为汉魏模式和齐梁模式的分界点,汉魏、盛唐诗歌的R值普遍小于33,可归为一类,齐梁、中晚唐诗歌的R值普遍大于33,可归为一类,R值越高则齐梁化程度越高;汉魏模式与重天份、重表现的诗歌时代相联系,齐梁模式与重学力、重再现的诗歌时代相联系。*相关文本分析及数学验证,参见张一南:《汉唐诗歌中两种比喻模式的交替演进》载于《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
另外,笔者在对个体诗人的研究中还发现,同一位诗人,随着年龄增长,其作品的R值会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所谓“齐梁模式”,其实就是“晚期模式”。从实际情况来看,“晚期模式”同样适用于一个大的诗歌时代,一个诗歌时代越接近尾声,其R值越高。*见张一南:《从比喻模式看流寓经历对诗人成长的影响》,收入2012年《流寓文学与文化会议论文集》,待刊。
根据以上经验,我们只要选择几位最有代表性的北宋诗人,分析其作品中的所有比喻,计算其R值,即可大致得知北宋诗坛整体的审美倾向及其发展趋势,较为精确地标出北宋诗歌在自然与人工、天份与学力、表现与再现、早期与晚期之间的倾向程度。
笔者在考查宋前诗歌比喻模式时,是选取每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几位诗人,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宋诗篇帙比唐诗更为浩繁,作者众多且水平参差不齐,故精选代表诗人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选定代表诗人时,大致以陈植锷先生《宋诗的分期及其标准》[1]一文中北宋部分的论述为依据。以王禹偁、《西昆酬唱集》为宋初即“沿袭期”的代表;以欧阳修、梅尧臣为欧梅时代即“复古期”的代表;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为元祐时代即“创新期”的代表;以陈与义为北宋末年江西诗派即“凝定期”的代表。在实际研究中,笔者发现“复古期”与“创新期”之间比喻模式的差异小于其内部的差异,故将“复古期”与“创新期”合并,统称“北宋中期”。另外,宋初“晚唐体”以姚合贾岛为学习对象,长于白描而几乎不用比喻,故虽有很大影响,但不作为本文论述的重点。
笔者对以上诗人的全部比喻进行了分类统计,得出了每位诗人的R值。同时,为了便于同宋前诗人进行比对,笔者为每位诗人选取了一位R值与之相近的宋前诗人作为对照,以便直观地标明每位北宋诗人的晚期化程度相对于宋前诗歌系统的大致位置。遂制成表1:

表1
在表1中,“对照组”列除特别注明者外,均为唐人。
通过表1,首先可以看出,宋人的R值普遍很高,所有人都超过了33,即汉魏模式与齐梁模式的分界点,亦即高于除李白杜甫以外的所有汉魏、盛唐诗人。且其中R值小于40者仅欧阳修一人,R值大于40且小于50,即相当于齐梁水平者,仅苏、黄二人,其他人均为R值大于50,相当于中晚唐水平。正如唐诗整体的R值水平高于六朝诗,北宋诗整体的R值水平也高于唐诗。这说明,如果以大的诗歌阶段为单位观察,则中国中古时期诗歌的R值是呈总体上升趋势的。也就是说,从六朝到唐,再从唐到宋,中国诗歌越来越趋于晚期风格,呈现重人工美、重学力、重再现的发展趋势。
其次,还可以看到,在北宋诗歌内部,R值并非是均高或直线升高的,而是呈现从高到低、再从低到高的曲线,与从初唐到晚唐的情况颇为类似。在北宋中期,可以按R值较高或R值相对较低将诗人分为两类,这也与盛唐到大历之间的情况小有差别。宋初的高R值为直承晚唐的高R值而来;北宋中期的两类诗人是在探索不同的审美路线;北宋末年的高R值则是重归晚期风格的结果。
具体说来,就R值而言:宋初白体的代表王禹偁与其效法对象白居易具有可比性,但比白居易更晚期化,更突出体现了元和时代的特征;《西昆酬唱集》实际上已经接近晚唐齐梁诗风的极端典型温庭筠;欧阳修与李白类似,处于汉魏诗风与齐梁诗风的分界点上,在北宋诗人中最尚自然,最有古风;梅尧臣则类似韩愈,仍然坚持人工化的路线;年辈稍晚的王安石于绮丽中求新异,人工化程度可比李贺;苏轼在北宋诗风中稍近自然,但也吸收了元和时代的成果,人工化程度与盛唐时另辟蹊径、开元和先声的杜甫相近;黄庭坚相当于一般齐梁诗人的水平,比中晚唐诗人自然,也比其他北宋诗人自然,与苏轼一样相对复古;陈师道仍受到元和诗风的影响,晚期化程度相当于李商隐;陈与义作为北宋王朝的最后诗人,在喻体的使用上颇为倾向于柔美,甚至不曾为惨痛的亡国经历所打扰,其R值相当高,与同样经历了磨难的晚唐香奁诗人吴融巧合,同时也与齐梁式比喻的开创者、永明诗人谢朓巧合。与在唐朝类似,齐梁比喻模式在宋朝又经历了一次与汉魏模式的竞争,最终都占据了上风,回归了永明的原点。
仅凭数字或许只能极为粗略地勾勒出北宋诗歌比喻模式的演进轨迹。事实上,每一位对诗学演进有所贡献的诗人,都曾独立地用心探索,创造出富于个人特色的佳句,其中当然也包括新颖的比喻。为了解宋代比喻模式的演进是如何借助每一位具体诗人的努力而发生作用的,我们仍然需要细致地进入文本。
二、 宋初对前代比喻的极度因袭
宋初三体实际上直接承袭了晚唐诗风,这一点已成为学界共识。从比喻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宋初三体的比喻模式都各自与其效法的晚唐流派十分接近,甚至大多是照搬效法对象创造的比喻。因此,可以用“极度因袭”来概括宋初三体比喻的使用状况。
王禹偁是宋初白体的代表人物。白体本是元和诗风的一大流派,而元和诗风相对于大历诗风的突出特征就是R值的急剧升高。在这个突出特征上,王禹偁比白居易本人走得还远,白居易的R值仅为51,而王禹偁达到了58。
与白居易相似,在王禹偁的齐梁式比喻中,有一部分是以华贵的金玉锦绣、美丽的女性形象为喻体,即典型的齐梁式比喻;另一部分则是以质朴甚至鄙俗的日常用品为喻体,即元和诗人新创的齐梁式比喻。前者的例子如:
野花媚宫缬,芳草铺碧紬。(《月波楼》)
绣被堆笼势,臙脂浥泪痕。(《商山海棠》)
绿萝供组绶,清籁献笙竽。(《五老峰》)
又如:
槛外澄江练不收,窗中远岫眉初印。(《送姚著作之任宣城》)
在缅怀谢朓时,将经典的齐梁式比喻“澄江静如练”完整地化入诗中,又将谢朓的名句“窗中列远岫”化为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正是齐梁人和晚唐人很喜欢的“山如眉”的比喻。将这两句单独抽离出来看,实际上就是两个最典型的齐梁式比喻。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曾以赋《窗中列远岫》一诗在科举中成名,王禹偁在化用了“澄江静如练”的典故之后,能想到以谢朓另一首诗中的句子“窗中列远岫”作对,恐怕与其对白居易作品的熟悉不无关系。
有趣的是,王禹偁还经常使用一种元和诗人很少用的比喻,即把鄙俗、缺乏美感的本体比作华贵的喻体,如:
鲤翻自跃金,蜗曳烧余汞。(《寄题陕府南溪兼简孙何兄弟》)
鲤鱼、蜗牛本是自然物之卑琐者,在大历以前恐怕很难入诗,元和诗人为求新变,很喜欢写到此类物事。王禹偁也以这些物象入诗,明显受到了元和诗人的影响。但是,元和诗人在写到此类物事时,却很少像王禹偁这样,将其比作金、汞等贵重之物。诗人在创造一个比喻时,总是潜在地认为喻体的诗性高于本体,将鲤、蜗比作金、汞,则仍是认为金、汞比鲤、蜗更适合写进诗中,这是典型的齐梁式审美特征。也就是说,王禹偁内心深处并不认为鲤、蜗之类是什么有价值的意象,仅仅是为了模仿元白,才去写这些卑琐之物,但在写的时候,又像真正的齐梁诗人一样,把它们比作了金玉等物。又如:
鲳蚱脚多垂似带,锯鲨齿密利如刀。(《仲咸借予海鱼图观罢有诗因和》)
玉堆深媿白,黛泼不如彬。(《仲咸因春游商山下得三怪石辇致郡斋甚有幽趣序其始末题六十韵见示依韵和之》)
从字面上看,“鲳蚱脚多”、“锯鲨齿密”的形象、“堆”、“泼”的字眼都绝不唯美。但如果单独把喻体抽离出来,“带”、“刀”、“玉”、“黛”却都是齐梁人很喜欢的喻体。这类现象,在元和诗歌中是少见的。
王禹偁以日常物作喻体的例子如:
峰峦开画障,畎亩列棋枰。(《春游南静川》)
火云如山暑雨歇,天地炉烘三伏月。(《谢政事王侍郎伏日送冰》)
荣枯祸福转如轮。(《放言·其二》)
这些都是典型的元和式比喻,是元白诗派喜欢使用的。
另外,王禹偁还会直接把白居易的得意比喻拿来使用,如白居易的著名比喻: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忆江南》)
以日常使用的“火”比喻“江花”,以染衣的“蓝”比喻“江水”。这是很典型的白居易式的比喻。这两个比喻被王禹偁分别化用为:
商山三月花如火,草树青葱雨初过。(《赋得南山行送冯中允之辛谷冶按狱》)
穷荒近日恩信沾,寒岩冻岫青如蓝。(《战城南》)
又如:
余霞犹散绮,新月已张弓。(《西晖亭》)
上句化用谢朓的名句“余霞散成绮”,下句化用白居易的名句“露似真珠月似弓”(《暮江吟》)。再如王禹偁的名句: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村行》)
实际上,这两个比喻也化自白居易的比喻。“荞麦花开白雪香”化自白诗“月明荞麦花如雪”(《村夜》)。白诗把荞麦花比作雪,被王诗全盘袭用。而白诗中将花比作胭脂的例子甚多,不胜枚举。可见,王禹偁并非触景生情,根据自己对现实事物的感受新创了两个比喻,而只是很熟悉白居易的比喻而已。
不过,王禹偁的比喻模式也并非白居易的翻版。比如,王禹偁很喜欢用动物做喻体,如:
春云如兽复如禽,日照风吹浅又深。(《春居杂兴·其二》)
石危蹲虎脚,松老咤龙髯。(《商山》)
罅开青虎眼,痕驳黑虬鳞。(《仲咸因春游商山下得三怪石辇致郡斋甚有幽趣序其始末题六十韵见示依韵和之》)
这样的比喻给人以险怪奇特之感。白居易从来不使用这样的比喻,反而是韩愈、李贺很喜欢用动物做喻体。由此可见,王禹偁并非亦步亦趋地模仿白居易的比喻,而是同样接受了韩孟诗派的影响。王禹偁的比喻艺术其实吸收了整个元和时代比喻艺术的特点。
同属宋初三体之一的西昆体宣称以李商隐为学习对象,但收录典型西昆体诗歌的《西昆酬唱集》的R值却远远高于李商隐。《西昆酬唱集》的R值高达77,而李商隐的R值仅为55,看起来,西昆体的齐梁化程度似乎远远超过了其师法对象。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李商隐只是晚唐齐梁诗风的一个代表,他与年辈较高的温庭筠,年辈较低的唐彦谦、吴融、韩偓等人,共同推动了晚唐齐梁诗风的形成。西昆诸子在学习李商隐的同时,未必不会涉猎晚唐其他诗人的齐梁风格诗作。而晚唐齐梁体诗人的R值是普遍高于元和诗人的,其R值大多在60以上,温庭筠甚至达到了79。李商隐实际上是晚唐齐梁诗风中偏于复古的一位诗人,他一方面创造过很多香艳的齐梁式比喻,一方面总体R值并不算高。如果把西昆体看作整个晚唐齐梁诗风在宋初的余绪,那么它与其继承对象的R值还是很接近的。或者可以认为,西昆诸子进一步强化了李商隐身上的齐梁因素,因而反与比李商隐更妖冶的温庭筠等人暗合。
从具体的比喻来看,西昆体还是以选择性地学习李商隐为主的。《西昆酬唱集》照搬李商隐创造的比喻之处甚多,如:
霓裳犹未解,绣被已成堆。(刘骘《槿花》)
将花比作“绣被”的构思,当是借用了李商隐的“绣被犹堆越鄂君”(《牡丹》),而将花比作“霓裳”,也是晚唐齐梁体诗人惯用的比喻。又如:
谁然百炬金花烛,渡袜歌梁暗落尘。(杨亿《又赠一绝》)
此诗是咏荷花。将花比作蜡烛的构思,当亦是出自李商隐《牡丹》一诗,化自“石家蜡烛何曾剪”一句,在李商隐之前,几乎没有诗人用蜡烛比喻花。而将开在水面上的荷花比作宓妃的罗袜,这个构思当是来自李商隐的“渡袜水沾罗”(《荷花》)。
甚至一些汉魏式的比喻也来自李商隐的构思,如:
雷响金车度,梅残玉管清。(杨亿《宣曲二十二韵》)
用雷声比喻车声,虽然在司马相如《长门赋》中便已有先例,但更直接的来源显然还是李商隐的“车走雷声语未通”(《无题》)。
另外,西昆诸子还喜欢用李商隐诗中的典型意象作喻体,如:
吴宫何薄命,楚梦不终朝。(刘筠《槿花》)
宝树宁三尺,华灯更九枝。(钱惟演《槿花》)
羌人自怨残梅曲,庄叟还迷梦蝶魂。(杨亿《柳絮》)
楚昭萍已剖,韩嫣弹争投。(刘筠《樱桃》)
诗人们并不仅仅是写到这些意象,而是愿意用这些意象做喻体,证明他们提到这些意象不仅仅是为了看起来像李商隐,而是真心地认为这些意象是美的,足以用来提升所咏之物的美感。西昆诸子做到了美义山之所美,这一点是与王禹偁之学习白居易不同的。《西昆酬唱集》中的比喻谈不上什么独创性,但其中反映出的对李商隐审美的极大认同和进一步强化,证明其不愧为晚唐齐梁诗风的直接继承者。
此外,以“九僧”为代表的宋初“晚唐体”多用白描,很少使用比喻,与中晚唐“姚贾体”的做法相同。故从比喻的角度看,“晚唐体”也毫无疑问的是中晚唐姚贾派诗风的继承者。
从比喻模式的分析可知,宋初三体的创造性不强,因袭的痕迹很重,对其各自模仿对象的审美都表现出极大的认同。其中,王禹偁在继承白体之余,已经掺入了韩孟诗派的审美;西昆体对李商隐的审美观十分忠诚并将其进一步发扬;晚唐体也保持了姚贾体的做法。从比喻的角度看,宋诗的创新在这个时代的确还没有开始。
三、 复古气质的“盛宋”
正如唐诗在进入王维时代后出现了R值的大幅度降低,宋诗到了欧阳修手中,也急剧地降到了汉魏模式与齐梁模式的交界点,这说明,欧阳修复古的努力,很明显地反映在了其审美模式上。比欧阳修年辈更低的苏轼、黄庭坚,也同样维持着低于元和诗人的R值,审美模式近于盛唐但比盛唐略偏晚期风格。在此前提下,几位诗人的比喻呈现出不同的个人风格,他们的努力促成了宋诗的新变,同时也呈现出复汉魏之古的审美倾向。
欧阳修似乎不太有意在比喻上用心,使用比喻的频率不高,也不曾挖空心思地创造新奇的比喻,这使得他的比喻有一种平和自然之美,与盛唐人相似。在北宋大诗人中,欧阳修使用汉魏式比喻的比例最高,他笔下的汉魏式比喻往往具有光风霁月般的疏朗,如:
乱石泻溪流,跳波溅如雪。(《八节滩》)
青天却扫万里静,但见绿野如云敷。(《百子坑赛龙》)
夕云若颓山,夜雨如决渠。(《答梅圣俞大雨见寄》)
与汉魏盛唐诗人一样,欧阳修极喜在称颂他人时使用比喻,如:
篇章缀谈笑,雷电击幽荒。(《读蟠桃诗寄子美》)
羡子年少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升。(《送徐生之渑池》)
爱君小鬟初买得,如手未触新开花。(《重赠刘原父》)
有如风轻日暖好鸟语,夜静山响春泉鸣。(《赠沈遵》)
这也是一种较为自然的审美观。这些比喻的构思虽已不时见于前人诗中,但在欧阳修写来,仍觉不失美感。欧阳修的齐梁式比喻也大多是典型的齐梁比喻,多用优美华贵之物,而不像元和诗人那样用日常物和动物做喻体,故无粗朴险怪之态,如:
仙衣霓纷披,女锦花綷縩。(《金鸡五言十四韵》)
靓容新丽一何姝,清池翠盖拥红蕖。(《绛守居园池》)
啼鸟亦屡变,新音巧调篁。(《暮春有感》)
欧阳修的比喻中已找不到追步某人的痕迹,也突破了元和以来以丑怪为美的成规,兼重汉魏的自然与齐梁的华美,表明诗人已经走出沿袭,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美了。
与欧阳修相比,苏轼创造比喻要用心得多。苏轼一生创作甚丰,使用比喻也比较频繁,共使用比喻945条,远远超过了唐代使用比喻最多的诗人白居易(766条)。苏轼创造的比喻往往形象鲜明,道前人之所未道,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汉魏式比喻的名句如: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
以人做本体,自然物做喻体,本是在《诗经》时代就很常用的最古老的比喻,“飞鸿”作为喻体也已有了悠久的历史。苏轼却将这一古老的构思进一步具体化了,写到“飞鸿”足下的“雪泥”,以飞鸿无关本体而又转瞬即逝的足迹比喻人生的痕迹,故不觉烂熟,反有耳目一新之感。这种平中见奇的比喻所在皆是,兹举几例: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一》)
“万人如海”几为熟语,但以“一身藏”搭配,陡觉形象。又如:
我梦扁舟适吴越,长廊静院灯如月。(《雪斋》)
“灯”、“月”都不过是寻常物象,但历来言“月如灯”者多,能看出“灯如月”者却少,以至于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认为“月可以当灯,灯不可以当月”。苏子此时却偏以灯当月,从世俗风光中见出自然之趣。再如:
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
以月色为水,花影为萍,将新奇与唯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苏轼非常喜欢这个比喻,曾在诗文中反复使用。这个比喻甚至被当作苏轼的标志性比喻,如宋人叶厘认为:
“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坡诗也。“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泽皆龙蛇”,鲁直诗也。*(宋)叶厘:《爱日斋丛抄》,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苏句的自然、清朗而不失新意,被用来代表苏轼诗的风格。黄句以龙蛇为喻体,是韩孟派比喻的做法,而其奇险、古拗则被用来代表黄庭坚诗的风格。这两个比喻之间的反差就足以代表苏黄之间的反差。再如:
后会知何日,一欢如覆水。(《诸公饯子敦轼以病不往复次前韵》)
“覆水难收”本是俗语,而用“覆水”比喻不可再得的欢会,却是苏轼的独出心裁。
不过苏轼更多的独创性的比喻还是标准的齐梁式,如: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其一》)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新城道中二首·其一》)
路失玉钩芳草合,林亡白鹤古泉清。(《与舒教授张山人参寥师同游戏马台书西轩壁兼简颜长道二首·其一》)
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其二》)
苏轼诗中能脍炙人口的比喻,大多仍是像典型的齐梁人一样,以华贵之物和美人做喻体。与其他小类的比喻相比,这样的比喻不但在苏轼诗中所占比例最高,而且也最能代表苏轼比喻的风格。
除此以外,与欧阳修不同,苏轼同时也擅长驾驭元和式的比喻,即用日常所用人工物做喻体,如: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新城道中二首·其一》)
将云比作絮帽,日比作铜钲,是典型的元和比喻。但在苏轼写来只觉亲切潇洒,看不到韩愈式的调侃、白居易式的俚俗或李贺式的恐怖。苏轼天才的艺术感觉,使其在继承了元和诗人欣赏日常诗意的能力的同时,能恰到好处地将其转化为易于为读者接受的美感,使读者知其趣而不觉其怪。同样的例子如: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百步洪二首·其一》)
又有以动物做喻体者如:
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守岁》)
比喻新颖,取象虽怪,却饶理趣。苏轼的比喻成功地吸收了元和之新,而淡化了其怪,显得更为成熟自然。
苏轼还尤其善于将比喻艺术与对仗艺术结合起来,将两个单看或许并不见长的比喻精心地排列在一起,获得某种趣意,如:
风梢千纛乱,月影万夫长。(《次韵子由绿筠堂》)
经火尚含泉脉暖,吊秦应有泪痕潸。(《次韵和子由欲得骊山澄泥砚》)
街东街西翠幄成,池南池北绿钱生。(《寿阳岸下》)
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戏子由》)
拙于林间鸠,懒于冰底鱼。(《送岑著作》)
君如大江日千里,我如此水千山底。(《送张职方吉甫赴闽漕六和寺中作》)
我今心似一潭月,君已身如万斛舟。(《次韵子由书王晋卿画山水一首而晋卿和二首·其二》)
也知不作坚牢玉,无奈能开顷刻花。(《谢人见和前篇二首·其二》,喻雪)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声调轻快,不乏机趣,或驰骋巧思,或游戏调侃,平易近于乐天,却更见士人心性,遂为后世小诗开无数法门。
从苏轼的比喻艺术可以看出,此时的宋人已可以自如地进行艺术创造,元和诗风对宋人的积极影响已经固定下来,而其稚拙之处已基本消退。
黄庭坚的R值介乎苏轼与欧阳修之间,这意味着他使用了大量汉魏式的比喻。但需要指出的是,从小类来看,黄庭坚使用的汉魏式比喻颇为单一,多数都是以人物或其诗文为本体,其实很少用无生命的人工物做比喻本体。与此同时,黄庭坚使用比喻也较为频繁,共用比喻801条,也超过了白居易,而频繁使用比喻本是齐梁模式的特征而非汉魏模式的特征。事实上,黄庭坚对待比喻的态度与近人钱锺书颇为相像:一方面大量使用比喻,对比喻艺术表现出浓厚兴趣,在比喻上花费了很大心思;另一方面,又把精妙的比喻艺术大多用在了对人物的描写上,大费心力地琢磨如何用一个新奇的比喻曲尽形容身边的人和事,因而大大拉低了R值。以人为本体的比喻虽然是最古老的比喻类型,但在黄庭坚、钱锺书这样的比喻巨匠手中,却往往凝聚了不少的锤炼工夫,实际仍是以学力取胜的,很难说有多少淳古的汉魏特征。因此,黄庭坚、钱锺书的比喻艺术是极为特殊的,不能简单地归为“汉魏模式”或偏于汉魏模式。兹聊举几例,以见黄庭坚以比喻写人之精心:
连营貔虎湛如水,开尽西河拥节旄。(《别蒋颖叔》)
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空。(《陈留市隐》)
吾欲超万古,乃如负山蚊。(《次韵答王韵中》)
邢子好少年,如世有源水。(《次韵答邢惇夫》)
阅世鱼行水,遗书鸟印沙。(《次韵吉老知命同游青原二首·其二》)
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鹗。(《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其七》)
顾我今成丧家狗,期君早作济川舟。(《次韵德孺惠贶秋字之句》)
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戏呈孔毅父》)
鉴中之发蒲柳望秋衰,眼中之人风雨俱星散。(《再用旧韵寄孔毅甫》)
人骑一马钝如蛙,行向城东小隐家。(《稚川约晚过进叔次前韵赠稚川并呈进叔》)
所选喻体或新奇生动,或幽默风趣,可以见出黄庭坚对诗材独特的识力,而并非一味复古,更非泛泛之言。黄庭坚独特的风格使这种古老的比喻类型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样的比喻,在欧阳修、苏轼的诗中也不难见到,只不过在黄庭坚诗中尤为多见。可见,以人为本体而在喻体的选择上下工夫,是一个时代的风气。
不过,与苏轼一样,黄庭坚最能为人们记住的比喻,仍然是齐梁式的,如:
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观王主簿家酴醾》)
这个著名的比喻以花为本体,而以男子为喻体,一经出现,就引起了众人的惊叹。仅比黄庭坚年少15岁的惠洪就曾赞叹曰:
前辈作花诗,多用美女比其状。如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陈俗哉!山谷作《酴醾诗》曰:“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若出类。[2]
同是以花做本体,惠洪认为以美女做喻体则“陈俗”,以“美丈夫”做喻体则“出类”。这大概是因为在惠洪的时代把花比作美女已经很常见了,而比作美男子的却很少,故给人以新鲜感。元和以来,不少诗人都在努力寻找新奇的喻体,也就是为了达到这样让人惊叹的效果。
其实,把美人比作花的例子从《诗经》时代起便史不绝书,但把花比作美人的历史却没有惠洪想象中的那么长远。把自然物比作人属于齐梁式比喻的极致,直到萧梁才开始被较多地使用。具体到把花比作美人,今天可见的最早的例子是陈后主的“落花同泪脸,初月似愁眉”(《有所思》)。从元白诗派开始,把花比作美人才逐渐成为一般化的比喻。惠洪举出的把花比作美人的例子即出自晚唐罗隐的《牡丹》。而把花比作男子的例子更是罕见。
不过,把花比作男子的第一人并非黄庭坚,而至少是李商隐。南宋的王楙即指出,这一联实际化自李商隐的“谢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炉更换香”(《酬崔八早梅有赠兼示之作》)[3]。其实,李商隐把花比作男子的例子还不止这一处,如他曾在《牡丹》一诗中,把牡丹先是比作“绣被犹堆越鄂君”,接着又比作“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一首写花的诗中有三位美男子作为喻体出场。可以看到,李商隐很喜欢“荀令香炉”这个喻体,两次写花都用到了,歌颂过了牡丹,又去歌颂梅花,顺便拉进了谢庄、鄂君、石崇三个美男子作陪。故“日烘荀令炷炉香”这个比喻实非黄庭坚的首创,而是从义山处“点铁成金”而来的。
细究起来,也可以说李商隐的这几个比喻还不是用男人做喻体,而只是用男子所用的蜡烛、熏炉、衣袖做喻体。但显而易见,李商隐是有意要让读者联想到几位美男子的形象,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用男子所用之物做喻体,跟用闺阁淑女的用物做喻体,终归是不同的,故可为山谷此诗的先声。宋初西昆诗派的杨亿也曾写到“尘暗神妃袜,衣残御史香”(《槿花》),也是把花香比作了男子的衣香(尽管此“御史香”本是来自女子)。黄庭坚的前辈欧阳修又曾在怡情小词《望江南》中写道:
江南蝶,斜日一双双。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
本体为蝶,而用傅粉何晏、偷香韩寿做了喻体。在这首小词里,男子本身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喻体。只不过欧阳修写的是词,无妨轻狂,故逃过了诗学家的批判而已。黄庭坚的这个比喻,也是上句写粉,下句写香,上句也是用何晏做喻体,只把下句的喻体由韩寿换成了李商隐用过两次的荀彧而已。欧阳修的这首词当是黄庭坚这联名句的又一个灵感来源。黄庭坚用男人做喻体,不但是有先例的,而且是直接用了先行者们用过的喻体,并不是开天辟地的创举。大概只因黄庭坚凭借元祐诗人对待比喻的无与伦比的认真态度,直接写到了何晏的肤色和荀彧的体香,在使用比喻时比他的前辈们更为直露、更重刻画,才引发了轰动效应。
这样离经叛道的比喻赢得的当然不只是赞扬,如金人王若虚即批评此句曰:
花比妇人,尚矣,盖其于类为宜,不独在颜色之间。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见其好异之癖……不求当而求新,吾恐他日有以白皙武夫比之者矣。[4]
王若虚认为把花比作妇人是好的,而比作男子则不伦。这个分别“不独在颜色之间”,即不是像不像的问题,而是“于类为宜”,即不能这样比的问题。所以比喻得像不像还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男子这类事物不可以做花这类事物的喻体。这说明,这个比喻刺激到王若虚的,还是本体和喻体所属分类之间的关系。根据王若虚的审美模式,男子的诗性小于花的诗性,所以把花比作男子的比喻不能成立。当然,这也应该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模式。
把花比作男子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争议,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个比喻的模式超出了一般人的审美认知。把花比作男人,就是借男人去赞美花,潜在地暗示男人(尽管只是几个特定的男人)比花更妩媚,而一般人则是天然地认为花是比男人妩媚得多的存在,所以才会对这个比喻感到惊奇甚至难以接受。
王若虚把黄庭坚以男子喻花的动机概括为“好异”、“求新”,抛除感情色彩来看,这也是说出了事实。自古以来诗人们不断地寻找前代诗人没有使用过的喻体,永明诗人发现了人工物,梁陈诗人发现了人类的身体,杜甫和元和诸子发现了日常使用的人工物,都莫不是“好异”、“求新”的结果。想必这些喻体刚刚被诗人发现的时候,也曾引起过部分读者的不适,但在后世却纷纷化为经典,供后来的诗人学习并超越。在元和以后,可供诗人发现的喻体类型越来越少,出现把花比作男子的比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王若虚认为,如果说还有比用白皙的男性文人比喻花更不可容忍的比喻,就是用“白皙武夫”比喻花了。从形象上看,同是白皙,没有什么不可以比喻花的,之所以男人比女人不可接受,武夫比文人不可接受,只是喻体在诗人选取的特征“白皙”以外的其他特征,亦即喻体的分类属性不同罢了。这个比喻得到的赞美和批评,都源于本体和喻体在分类属性上的巨大反差,而这种反差,其实是千百年来诗人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
用男子比喻花,是最为极端的齐梁式比喻,也足以代表黄庭坚在创造齐梁式比喻时标新立异的程度。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黄庭坚很少使用日常人工物做喻体,而是多用典型的齐梁比喻,如:
小鬟虽丑巧妆梳,扫地如镜能检书。(《常父答诗有煎点径须烦绿珠之句复次韵戏答》)
青山如马怒盘旋,错认林花作锦鞯。(《次韵裴尉过马鞍山》)
泉响风摇苍玉佩,月高云插水晶梳。(《观化十五首·其二》)
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其二》)
春愁如发不胜梳,酒病绵绵困未苏。(《招戴道士弹琴》)
这与欧阳修、苏轼使用齐梁式比喻的情况大致类似,而元和比喻艺术的影响显得更小。
欧阳修、苏轼和黄庭坚共同体现出北宋中期部分诗人R值较前代降低的现象,这种现象与盛唐诗R值降低的现象似有可比性,或可将这段时期类比性地称为“盛宋”。R值降低表示诗人在审美上比前代诗人更倾向于自然物,但也应看到,与盛唐诗人相比,这批诗人的齐梁式比喻仍写得相对较多,质量较好,这些诗人最为擅长、脍炙人口的比喻仍然多为齐梁式。笔者在观察汉唐比喻模式时发现,突出的汉魏模式往往出现在重表现的时代,突出的齐梁模式则出现在重再现的时代,相对居中者则出现在表现与再现并重的时代。“盛宋”诗人的比喻模式相对居中而倾向于齐梁,或可推测“盛宋”是一个表现与再现并重而略倾向于再现的诗歌时代。*关于表现与再现的交替演进规律,参见钱志熙的《表现与再现的消长互补》,载于《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另外还应看到,“盛宋”诗人已彻底抛弃了专学一家而因袭其比喻的做法,元和诗风的影响在此时也稳定下来,并开始在部分诗人的作品中与传统诗歌审美调和,甚至呈现消退的迹象。这批诗人在艺术上已经走出了一条带有复古气质的新路。
四、“盛宋”的另一种声音
“盛宋”诗风的新变不同于盛唐的一点在于,盛唐诗人R值的下降几乎发生于当时所有诗人的身上,而“盛宋”只有部分诗人的R值下降,另一部分诗人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R值,与元和诗人相近。这两部分诗人甚至并非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诗派,他们之间存在着高度的认同、密切的交往和频繁的唱和。欧阳修的密友梅尧臣、与苏轼同朝为官的王安石,与黄庭坚同属“苏门四学士”的陈师道,都属于保持了高R值的类型。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宋代拥有比唐代更悠久的诗学积淀,诗学系统更为复杂,使得诗人有了更丰富的选择,所以即使亲近的诗人之间也可以在审美倾向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与欧阳修几乎扬弃了元和式比喻而几近盛唐不同,梅尧臣的比喻明显呈现出元和特征。梅尧臣的R值与韩愈本人十分接近,且喜用韩愈式的险怪比喻,如:
龙蛇缘古木,凤鹄舞幽庭。(《雪咏》)
掉尾为旗纛,磨牙为剑铓。(《猛虎行》)
百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却回如鼻吸。(《青龙海上观潮》)
聚石如伏兵,敛敛波下立。(《过涂荆二山遇暗石》)
化虫悬缢女,啼鹱响缫车。(《至广教因寻古石盆寺》)
鬰气若甑炊,初阳如火红。(《和江邻几景德寺避暑》)
光魄纵复吐,血赤如顽铜。(《杨公藴之华亭宰》)
暗雨轻烟满室中,尘事如脂一朝洗。(《和和之南斋画壁歌》)
安知秋江水,净碧如磨铜。(《寄李献甫》)
桂林地险通椎髻,阳朔峯奇削剑铓。(《送广西提刑潘比部》)
亦多有李贺式的艳异的比喻,如:
水发黏篙绿,溪毛映渚春。(《上巳日午桥石濑中得双鳜鱼》)
南郭复西城,晓色明于甲。(《依韵和武平苕霅二水》)
秋雷石罂破,晓日丹砂烂。(《石榴》)
秋风白虎嗥,长庚光如刀。(《秋风篇》)
松间无人扫,陨叶如断鬉。(《送允从上人还庐山》)
蛱蝶未生蜂未来,赤身掩敛无金缕。(《红梅篇》)
日光亭午时,赫若镕黄金。(《次韵和马都官苦热》)
班笋迸林犀角丰。便令剥锦煑荆玉,(《韩持国再遗洛中斑竹笋》)
天如青玻瓈,月若黑水精。(《月蚀》)
与元和诗人一样,梅尧臣总是努力地寻找新奇的喻体,追求坚硬的质感和富于崇高感的形象,努力与盛唐式的审美拉开距离,不断地挑战读者的审美预期。在梅尧臣的比喻中,找不到欧阳修那样的月朗风清,而人工物的静穆、冰冷、诡异被发挥到了极致。
韩孟的怪奇诗风在晚唐并没有获得像元白、姚贾诗派那样多的效法者,宋初三体中也没有韩孟后继者的位置。梅尧臣显示出的韩孟风格,并非是直承唐风而来,而应当是自觉选择的结果。陈植锷先生将欧梅时代统称为“复古期”,当是着眼于这一时代不再直承晚唐余绪,而开始从更早的时代自主寻找诗学资源。但从比喻模式的选择来看,这个时代的共性仅仅在于“复古”,即寻找前代资源,至于寻找什么样的资源,则完全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并无一致性。欧阳修选择了复汉魏盛唐之古,梅尧臣则选择了复韩孟之古。当然,这种分别可能不是自觉的,因为就连韩孟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在复汉魏之古,而并不知道自己的审美模式其实是齐梁之甚者,故欧梅应当都是把汉魏和韩孟放在一起学习的,并不能做出区分。至于欧阳修近于真正的汉魏盛唐,梅尧臣近于韩孟,当是其各自的才性使然,并非有意为之。高R值与低R值的模式一直并行于整个北宋中期,应当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
王安石的比喻在北宋中期显得颇为特殊,他的R值虽高,却未蹈韩孟蹊径,而是多用典型的齐梁比喻,显得气质高华,设象净丽。其酷类齐梁的句子如:
金钿拥芜菁,翠被敷苜蓿。(《招约之职方并示正甫书记》)
浮云堆白玉,落日泻黄金。(《东阳道中》)
径用金玉等字做喻体,富丽堂皇。但此等句子在宋人写来,反觉夸张稚嫩,真成了“至宝丹”。这也是为什么韩孟诗派要刻意回避这种字眼。王安石连这样的字句都不回避,足见其与韩孟诗派的审美追求很不相同。
更多的时候,与真正的齐梁诗作相比,王安石的笔法又显示出宋人的老练,浓艳而不拘滞,唯美而不失自然,如:
薄槿烟脂染,深荷水麝焚。(《自白土村入北寺二首(其一)》)
把花色比作胭脂,花香比作麝香,自齐梁以来就算不上什么新奇比喻了。但这样的比喻,句法稚拙的六朝人难免会写作“深荷焚水麝,薄槿染烟脂”。身为宋人的王安石使用“名名动”句式,比起六朝人常用的“名动名”句式,便觉潇洒灵活。且以水生的荷花切合“水麝”,将“胭脂”借“烟”字以写轻薄的槿花,亦见巧意。再与原诗中的另一联比喻“溜渠行碧玉,畦稼卧黄云”搭配,引入田家风光,便又不觉甜腻,却又用齐梁比喻习用的闺阁之物与华美的“黄云”做喻体,富丽典雅,写田家偏无清寒之态。又如:
野林细错黄金日,溪岸宽围碧玉天。(《次韵舍弟遇子固忆少述》)
虽然也是用金、玉作喻体,但用“细错”消解了“黄金”的村俗,“宽围”掩盖了“碧玉”的局促,写景如在目前,宏细景物搭配有致,故显得精致多了。又如:
峨然九女鬟,争山一镜奁。(《和平甫舟中望九华山二首·其一)》)
把山丘比作发髻,湖面比作镜面,也早不是新奇的比喻了。由像发髻的山丘想到少女,把湖面的大山想象为镜奁,二者的关系处理为“争”,用以比喻山丘相聚的形态,便显得新奇,虽是把自然物比作人工物,却反而写出了动态,因而显得自然生动。再如:
大江当我前,颭滟翠绡舞。(《金山寺》)
把滔滔江水比作舞动的翠绡,纤小艳丽之极,却偏偏与“大江当我前”这样的古诗散句搭配,语态本身颇有英雄欺人之感,使人错觉诗人并非是因为只想着“翠绡”这样的喻体,而只是因为气魄宏大,可以藐视“大江”。与梅尧臣在名词上下功夫,挖空心思寻找新奇的喻体不同,王安石更擅长把炼字的功夫下在动词上,用生新的动词去组织早已烂熟的喻体。
当然,王安石也不忽视喻体的选择,他甚至可以在一首写景绝句中使用多个人工物喻体,如:
一陂焰水蒋陵西,含风却转与城齐。周遭碧铜磨作港,逼塞绿锦剪成畦。(《一陂》)
将水中的花影比作“焰”,将河港比作“碧铜”磨制的镜子,将成畦的庄稼比作“绿锦”。在看到这些地道的自然风光时,王安石脑海中反映出来的居然全是那些宫体色彩浓厚的物象,足见其审美是齐梁式的。在此基础上,王安石不肯用“似”、“如”等字眼,而是用了“磨”、“剪”等讲究的动词,给人工物以动态,弥补了齐梁式比喻冰冷呆板的缺点。
王安石诗中有不少用美女形象作喻体的例子,如:
嫣如景阳妃,含笑堕宫井。(《杏花》)
一水衣巾翦翠绡,九峰环佩刻青瑶。(《不到太初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诗攀寄》)
额黄映日明飞燕,肌粉含风冷太真。(《次韵徐仲元咏梅二首·其一》)
蝉娟一色明千里,绰约无心熟万家。(《读眉山集爱其雪诗能用韵复次韵一首》)
需要指出的是,用美女,尤其是美女的整体形象做喻体,原本是白居易的爱好。王安石诗中不乏白居易式的比喻,又如:
和风满树笙簧杂,霁雪兼山粉黛重。(《至开元僧舍上方次韵舍弟二月一日之作》)
春风过柳绿如缲,晴日烝红出小桃。(《春风》)
王安石也会用相对日常的人工物做喻体,但他的笔调一直是唯美的,没有元和时代同类比喻的丑怪粗朴。王安石的比喻中有白居易的痕迹,但扬弃了白体粗朴率意的一面,继承了齐梁诗人追求精致的精神。如果说欧阳修是越韩孟而至于盛唐,王安石是阶元白以入于齐梁,二人师法的路径不同,但在扬弃粗朴、追求精致的选择上则不谋而合。王安石虽不追求自然美,但与效法韩孟的其他宋代诗人仍不相同。
王安石的汉魏式比喻也同样清丽可观,如: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北陂杏花》)
山如碧浪翻江去,水似青天照眼明。(《泊姚江》)
浓绿扶疏云对起,醉红撩乱雪争开。(《池上看金沙花数枝过酴醾架盛开二首(其二)》)
可见,王安石也能像欧阳修一样,发现自然之美的。而且这些比喻,仍然是意象平常而动词考究。
对于得意的比喻,王安石还会反复使用。如形容女子的“颜色如花命如叶”一句,就先是用在了《明妃曲》中,又收入了集句体的《胡笳十八拍十八首》中。又如“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这一对比喻,就同时用在了《壬戌五月与和叔同游齐安·其一》和《木末》中。“缲”和“割”都是极为人工化的动作,但句意却是将丝比作白雪,将小麦比作黄云,是典型的汉魏式比喻。看得出,王安石对自己创造的这个比喻极为得意。除了这两处以外,他的“缲成白雪三千丈,细草孤云一片愁”(《示俞秀老二首·其一》)和“梅残数点雪,麦涨一溪云”(《题齐安壁》)也是用了类似的构思。
陈师道在比喻上不甚用力,一生只创作了114条比喻,比同时代的其他大诗人少得多,也没有创造过什么令人过目难忘的比喻。这大概与他耽于苦吟,注重白描,注重熔铸古语,从而不便施展比喻的创作态度有关。
陈师道诗中的比喻体现了韩孟诗风在元祐时代发生的影响。除了R值较高以外,陈师道诗中也不难见到怪奇的比喻,如:
修鳞失水玉参差,晚日摇光金破碎。(《次韵苏公西湖徙鱼三首·其一》)
黑云衔日蚕不吐。(《奉陪内翰二丈醴泉避暑》)
风叶倒垂云覆碗。(《次韵寄答晁无咎》)
南朝官纸女儿肤,玉版云英比不如。(《从寇生求茶库纸绝句》)
也有近于元白体的比喻,如:
新绿葱葱红蔌蔌,却成妆面映青纱。(《和参寥明发见邻家花二首·其一》)
高花初欲然,平荷已如拭。(《和黄生春尽游南山》)
莲剥明珠滑,瓜浮绀玉香。(《同苏不疑避暑法惠寺》)
以优美或有些世俗的人、物做喻体。韩孟诗派的比喻与元白诗派的比喻,在陈师道诗中都出现过。
陈师道的汉魏式比喻往往不太出彩,往往只是熔铸经史成言,创造一些以人为本体的比喻,如:
吟作秋虫到白头。(《和江秀才献花三首·其三》)
南阳老幼如云屯,(《寄邓州杜侍郎》)
才如得风鹢,已复触藩羝。(《赠赵奉议》)
名堕网中蝶,身随冰底鱼。(《答寄魏衍》)
生世如风花,高下亦偶然。(《奉酬应物》)
虽有时也不失形象,却都离不开古代的典籍。诗人实际感受到的是典籍中的形象,而非自然的事物。
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的比喻模式向汉魏盛唐倾斜的时候,他们身边的一批诗人在与他们并肩复古的同时,无意中选择了属于晚期风格的审美模式。他们或复韩孟之古,或复齐梁之古,而元白的风格也一直如影随形。这批诗人同样有着自己的审美追求和艺术创新,同样有力地影响了北宋诗坛,他们的审美风格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着后人对北宋诗风的判断。北宋中期的比喻模式形成了两条并行发展的轨迹。
五、 晚期风格的回归
北宋末期的诗风可以用陈与义做代表。陈与义的比喻模式呈现出向晚期风格——即齐梁和晚唐曾经呈现过的风格——回归的倾向,人工化的程度很深,并表现出柔美静穆的风格。
陈与义的R值已超过了元和,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这样的R值水平曾分别出现于六朝与唐的末期,是一种典型的晚期风格,昭示着一个诗歌时代的临近结束。陈与义一生经历过北宋灭亡的重大变故,并且也自认为这次变故是自己一生创作的转折。他曾在自己的诗中宣称:
但恨平生意,轻了杜陵诗。(《正月十二自房州城遇金虏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张家》)
认为自己在南渡后比以前对杜诗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这也成为陈与义前后期转变的标志性诗句。从杜甫、韩愈等人的先例来看,如此重大的变故足以使一位诗人的审美模式发生明显改变。但陈与义的R值无论是在北宋,还是在南渡后,都恒定在66。可以说,无论什么样的事件曾进入诗人的视野,在审美层面,陈与义其实没有受到历史变故的一丝冲击。
从最初援笔为诗直到南渡以前,陈与义一直多用典型的齐梁式比喻,如:
平林过西风,为我起笙竽。(《次韵张矩臣迪功见示建除体》)
春风所经过,水色如泼油。(《路归马上再赋》)
远峰如修眉,近峰如堕鬟。(《与伯顺饭于文纬大光出宋汉杰画秋山》)
川后不愁微步袜,鲛人暗动卷绡梭。(《次韵家弟碧线泉》)
喻体净丽,语态娴雅,表现为标准的齐梁式审美。而在北宋灭亡后,陈与义也没有像杜甫入蜀后和韩愈贬谪后那样,引入险怪、恐怖的喻体和日常化的喻体,而仍然维持了雍容华贵的齐梁式审美,如:
东风吹不断,日暮臙脂薄。(《海棠》)
微泉不知处,玉佩鸣深丛。(《山路晓》)
唯有君山故窈窕,一眉晴绿向人浮。(《火后问舍至城南有感》)
梅花乱发雨晴时,褪尽红绡见玉肌。(《醉中至西径梅花下已盛开》)
青裙玉面初相识,九月茶花满路开。(《初识茶花》)
面对流亡途中所见的景致,陈与义联想到的仍然是这些脂粉气颇重的物象,可以说与真正的齐梁诗人在审美上没有什么差别,完全见不到流寓诗中常见的怪奇恐怖的喻体。甚至在南渡后,陈与义还有不少欧阳修般风清月朗的汉魏式比喻,如:
我身如孤云,随风堕湖边。(《王应仲欲附张恭甫舟过湖南久不决今日忽闻遂登舟作诗送之并简恭甫》)
高柳光阴初罢絮,嫩凫毛羽欲成花。(《题东家壁》)
乍脱绿袍山色翠,新披紫绶佩金鱼。(《拜诏》)
从比例上看,陈与义的审美并未比渡江前更为苍老。陈与义在感叹“但恨平生意,轻了杜陵诗”的同时自诩:
久谓事当尔,岂意身及之。避虏连三年,行半天四维。……向来贪读书,闭户生白髭。岂知九州内,有山如此奇。(《正月十二自房州城遇金虏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张家》)
认为自己在流寓途中经历了在书本中无法感知的奇山异水,才对杜甫诗有了切身的体会。但事实上,陈与义的南渡诗从未像杜甫的入蜀诗那样,表现出对陌生山水的新奇感和流寓生活中的焦虑心态。由此可见,与杜甫入蜀相比,陈与义在南渡时可以说没有受到多少心理冲击,流离的苦难并没有改变陈与义对世界的感受,没有深刻地融入其生命体验中。陈与义仍然用一位学养丰富、气质高贵的北宋士大夫的眼睛,审视着南宋初年兵荒马乱的世界。陈与义在南渡后对杜甫的追忆,只不过是一位崇拜杜甫的文人在遭遇了类似杜甫的命运后,对其偶像做出的情理之中的致敬,并不能代表其艺术风格的实质性转变。从总体上说,陈与义的审美模式不但表现出极端的晚期风格,而且比起北宋中期学习韩孟的各位诗人,要雍容唯美得多,几乎看不到韩孟的影响。梅尧臣等人的人工化审美与欧阳修等人的不师韩孟,亦即宋代中期比喻模式发展的两条轨迹,终于在陈与义这里合流了。
从比喻模式看,北宋诗人普遍呈现出比唐人更高的R值,这是深厚的诗学积淀作用的结果,也反映了诗歌比喻模式演进的宏观趋势。北宋诗歌比喻模式的发展轨迹大体与唐诗相同,即开头直承前代的晚期风格,中期新变,晚期复归晚期风格。不同之处在于,北宋中期的诗歌新变表现为两条轨迹的并行:一部分诗人扬弃韩孟,向汉魏盛唐靠近,同时又保持了学力深厚的宋人风味,多出新声;另一部分诗人或师韩孟,或法齐梁,较多地继承了人工化的审美模式。这两条轨迹最终在晚期风格的复归中合流。
参考文献:
[1]陈植锷.宋诗的分期及其标准[J].文学遗产,1986,(4).
[2][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四)[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1.
[3][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 [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四十)·诗话[Z].四部丛刊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