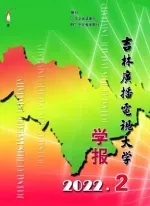《哈姆雷特》“悲剧性格论”和“延宕复仇论”的再探讨
张晓焕
(河南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河南 开封 475001)
威廉·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是世界文学殿堂里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以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不朽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亲身参与剧本的解读,从而使得主人公哈姆雷特王子的形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与国度里,始终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哈姆雷特》讲述的是一个剧情跌宕起伏的宫廷复仇故事。剧情的发展环环紧扣,层层递进,波折起伏,激荡人心。如剧中鬼魂的诏示、王子装疯、宫廷“戏中戏”、误杀大臣、死里逃生、情人之死、阴险的决斗、始料不及的惨烈结局,以及剧中穿插的精彩对话、诗歌、台词、人物思考,不时让读者或沉思、或忧伤、或叹惋。全剧可谓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由于剧中的主人公哈姆雷特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几个重要人物最后都归于毁灭,其复仇过程的曲折与代价的惨烈,都极大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这就赋予了《哈姆雷特》这部伟大的作品以浓郁的悲剧色彩,哈姆雷特也因此成为戏剧艺术舞台上最为鲜明的悲剧人物形象之一。
在近四百年的莎评中,对于造成哈姆雷特悲剧之因问题的探讨一直没有间断,其中“较有影响的观点大致有二:一,哈姆雷特的悲剧是由于哈姆雷特性格上的‘悲剧弱点’和与此相关的拖延造成的;二,哈姆雷特的悲剧既不完全是拖延的悲剧,也不完全是环境和命运的悲剧,而是各种因素兼而有之。”[1]对这两种观点,笔者却有自己不同的见解。
一、“悲剧性格论”之批判
一些人将哈姆雷特的悲剧性主要归咎于其性格上的各种弱点,如软弱、犹豫等,这种认识是很肤浅的,而且剧本中其实并无直接的证据支持这一论断。就拿剧中第四幕第三景那一场“夭折的复仇”戏——不少持“悲剧性格”观点的论者就经常将这一出戏作为确立其观点的最经典例证拿来引用——来说,当哈姆雷特的叔叔丹麦王克劳狄斯为排遣心中巨大的罪恶感而跪下祈祷时,当此之际,哈姆雷特要挥剑复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他却理智地选择了暂时赦免。个中原因,并非是软弱、犹豫的性格使然,而是由于他思想中的宗教、道德的力量阻止了他的行为。试看剧本中当时哈姆雷特的思考:“我现在就下手杀了他……然后他就直接上天堂;这就算是复了仇?”“一个恶徒杀了我的父亲,而我——父亲的独子——却保送此恶徒登上天堂;什么,这等于是成全了他;这不算是复仇。”何为复仇呢?那种干脆利落、血溅当下的快意恩仇的复仇方式并未被哈姆雷特所采纳,哈姆雷特对复仇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认识:“回鞘去罢,宝剑呀,让我寻个更好的机会:当他烂醉如泥、大发雷霆、淫榻寻欢、赌博渎神、或做其他毫无拯救可言之事时,那时我再颠他于我的足下,教他双脚朝天,一条地狱般黑恶之灵魂直归阴曹府。”在哈姆雷特心目中,复仇并不是简单地对一个人肉体的惩戒,而是要实现对其灵魂的鞭挞;不是在他灵魂升腾的时候拉他下坠,而是当其灵魂堕落之时送其直入地狱。哈姆雷特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教理念和体会的青年,他的复仇方式直接受其宗教思想的指引和规范。另一方面,哈姆雷特的复仇行为也受其头脑中的道德理想的制约:“他在我父亲未经悔过、罪恶贯盈时把他杀害;上帝对他的这笔账此时是如何的看法,除了神之外,有谁晓得?依凡人之推理,这应算是个重罪。”哈姆雷特认为,当此忏悔之时杀他,与奸王杀戮自己父亲时悍然剥夺其忏悔权利与机会的不义行径何异?套用中国先秦思想家孟子的话,不义也,故不为也。哈姆雷特在自我道德修养方面有一个崇高而圣洁的追求,他的复仇之剑在此时戛然而止,正是他自己道德心理在起作用的结果。所以,那种用性格决定论来解释哈姆雷特的复仇行为的特点是牵强的,缺乏说服力。
另外,把哈姆雷特性格界定为“软弱”、“犹豫”也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对剧本中的三个细节进行分析而得到证明。需要注意的第一个细节,是哈姆雷特在母后寝室误杀波隆尼尔的那一剑。这一剑是何其迅捷,何其果断,没有丝毫犹疑!因为,在当时那种场景下——在皇后的卧室内,有人可以合法地藏身帘幕后偷听,依照通常的逻辑来推断,哈姆雷特很自然地认定,那鬼鬼祟祟地藏于帷帐后窃听他们母子谈话的人,一定是他那位奸邪的叔叔克劳狄斯,所以他的复仇之剑果断出手,毫不迟疑地刺去,遂一击辄中。需要留意的第二个细节,是当获悉克劳狄斯的借刀杀人之计后,哈姆莱特立即将计就计,另拟了一份用于掉包的信件,指令英王“立刻把那两个传书来使处死,不让他们有从容忏悔的时间”,从而把以往的同学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送上了死路。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哈姆雷特表现得果断决绝,雷厉风行,毫无迟疑之色。第三个细节是,当哈姆莱特得知酒是毒酒,剑尖上亦涂有毒药,克劳狄斯的狐狸尾巴彻底暴露时,他知道等待已久的复仇机会终于来临,而且是今生唯一的机会了。此时的哈姆雷特已身中毒剑,命在须臾,但他没有绝望,而是在一刹那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持毒剑猛刺国王”,并“强迫重伤的国王喝鸩酒”,让这个恶贯满盈的奸王自食其果,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复仇使命。这三个例子有力地推翻了哈姆雷特性格软弱、犹豫、优柔寡断的说法。
二、“延宕复仇论”之商榷
在有关哈姆雷特的论题中,有一个经典问题,众说纷纭,至今仍悬而未决,这就是关于哈姆雷特的“延宕复仇”问题。对此问题,有从主观方面分析的,亦即从其性格上分析的,如前所论,此不赘述。也有从客观方面分析的,也就是从哈姆雷特在剧中所处的客观环境特点去发掘,认为客观因素的不利是他拖延复仇的主要原因,这一派以普劳曼、瑞特逊、克兰和魏尔德等学者为代表;第三种倾向是综合论,其基本观点是:哈姆雷特深知自己有责任改造这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可他性格中的软弱如谨慎、内向、多疑、不善行动等使他没有足够的信心与勇气来杀死克劳狄斯,因此在国王的淫威下只是被动的忍受,一拖再拖,最终酿成悲剧。对以上三种论调,笔者不做评论,只是认为有必要对“延宕复仇”这个命题重加商榷。以笔者拙见,如果“延宕”一词的含义是拖延,也就是认为哈姆雷特的复仇历程具有一再拖延的特点,那么探讨延宕的原因则是富有意义的。可如果“延宕”一词用在哈姆雷特身上原本就并不恰切的话,那探讨“延宕复仇”问题就成了一个虚假的命题,失去了探讨下去的意义。但既然“延宕复仇”已经引起广泛讨论,那就不妨随其潮流,在与之相关的层面上做一探讨。
哈姆雷特的“复仇”有其特别的内涵和方式,它与雷欧提斯的“复仇”有着很大差异,可以说两者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雷欧提斯是一个受激情支配的复仇者,政治的、宗教的、伦理的、道德的因素都被摒弃在复仇行动之外,对他来说,复仇就意味着赤裸裸、血淋淋的行动。”[2]哈姆雷特则不然。简单地说,哈姆雷特的复仇是极为理智的,它不仅须合乎人性道义的要求,也需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对他提出的隐性要求。根据前一项要求,哈姆雷特的复仇雪耻,首先需要让自己的灵魂安宁,也就是遵循上帝的原则行事,当那一个罪恶的灵魂在忏悔时,他没有刺出那复仇之剑;当哈姆雷特得到那封借刀杀人之计的信件后,他并没有怒不可遏地回国行刺国王,相反他给国王写了一封信,明确告知他的归期和安排。这样做显然是以敲山震虎的手法儆诫国王,同时也是想进一步试探国王,看他是会悬崖勒马,还是会变本加厉。换言之,哈姆雷特曾留给自己的叔叔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但遗憾的是,他的叔叔执迷不悟,怙恶不悛,终至恶贯满盈,自取灭亡。这两件事都表明哈姆雷特的复仇是在遵循道义的尺度内展开的。据此,有些学者认为,哈姆雷特迟迟不肯复仇,是因为他“不愿采取和他的人道主义理想不相符合的步骤”[3],这一说法应当得到肯定。
与道义的要求相比,后一项要求在哈姆雷特的复仇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哈姆莱特作为一位王子,一个王位继承人,他要诛杀当前执政的一位君主,就一定要有能令天下人信服的理由,也就是无可置疑的铁证,否则,他就成为世人眼里的一个篡位者,一个弑君的千古罪人。所以,为了能让他的叔叔克劳狄斯在国人面前充分暴露罪行,将“他弑我君、娼我母、挫我登基之望、并用诡计来图谋我的性命”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王子哈姆雷特这才煞费苦心想出装疯的妙计,以便暗中查证,掌握充分的证据,从而光明正大地高举复仇之剑,在全丹麦人中公开诛杀这个衣冠禽兽,为死去的父王报仇,同时也可以警诫后来人莫要丧尽天良,为非作歹。他亲自指导巡回剧团的演员以真实故事情节入剧,改编成讽隐戏剧《捕鼠器》,通过现场演出直观地探察国王的情绪反应,证实国王确实曾犯下那桩弑兄淫嫂的罪孽,也证实父亲的鬼魂说的是实情。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证据,但这还不足以让普天下的人相信。故此,他必须要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当且仅当他收集到足以令天下人信服的显赫的罪证时。正是在这一复仇思想的指引下,他以极大的忍耐力,始终不露声色,运用自己的智慧与敌周旋,最终收集到了国王谋害自己的亲笔信,致使皇后死亡的鸩酒,雷欧提斯的毒剑等包藏祸心的三大罪证,且众目睽睽,铁证如山,奸贼克劳狄斯再也无处遁形。即便哈姆雷特不出手,天下人也都认清了此贼的丑恶嘴脸,依其罪恶人人可得而诛之。纵不诛之,此人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令罪恶的灵魂无处忏悔,无处容身,万劫不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仇。毫无疑问,哈姆雷特成功了。
总之,事实并不完全像赫士列特所写的那样,哈姆莱特只“满足于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满足于他的试验成功,而不是行动起来。”[4]哈姆雷特深刻意识到,简单的复仇并不能解决人们仇恨和罪恶问题,只有心灵的忏悔和和解才是唯一出路。他的复仇首先是拯救心灵,其次才是对堕落灵魂的惩戒。哈姆莱特希望他的复仇既能获得自我思想与理智的认可,又能得到世俗的支持,为此他沉潜心志,慷慨力争。哈姆雷特是成功的,他在复仇过程中展示了的美德,成为人伦的典范,世俗的楷模。
[1]弥沙.“哈姆雷特”拖延复仇的心理分析[J].鸡西大学学报,2003,(5).
[2]胡克红.从哈姆莱特的复仇悲剧探其内心游移——重读《哈姆莱特》[J].零陵学院学报,2002,(12).
[3]乔建中等.(撰)文艺鉴赏大观[M].1989.
[4]莎士比亚评论汇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