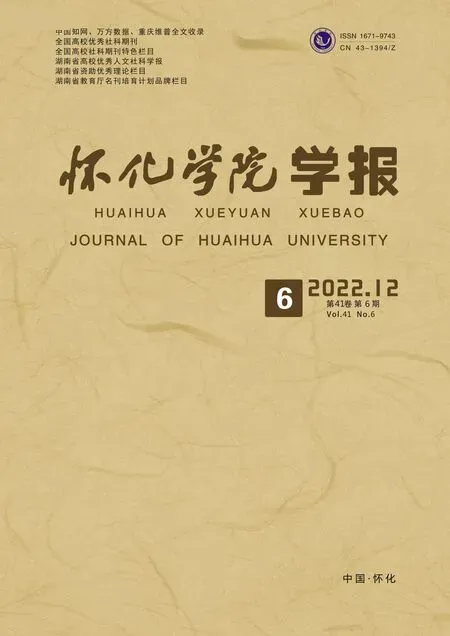论《哈姆莱特》中克劳狄斯的伪装
曾 绛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湘潭 411201)
《哈姆莱特》(行文中简称《哈》)为古今世人提供了以假面掩盖心灵扭曲的一组群像:乔特鲁德以安详贤淑的外表掩盖着她心灵的躁动和情欲的膨胀;雷欧提斯则在血气方刚的性格和骑士身份的掩盖下实施剑上涂毒的卑鄙行为;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以带有私欲的愚忠掩盖他们见利忘义的丑恶;奥斯立克则以巧言令色掩盖着他那心灵的空虚[1]230。从以上《哈》剧角色以假面掩盖下的罪行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剧中主、次人物的灵魂都是被某种欲望所驱使、所支配,从而干着罪恶的勾当,或表现出趋炎附势和厚颜无耻,或有意或无意地干出了为满足一己私欲而损毁他人的恶行。然而,利用以上人物的恶行和私欲而导演这场群丑众恶或狂欢或独舞的是极擅伪装且阴险狠毒的克劳狄斯。
克劳狄斯是《哈》剧中一切丑行生发和一切祸端滋生的根源,是一个贪婪无耻阴险狡诈的恶贼[2]477。他引诱王嫂并与之私通在先,弑兄夺位在后[3]125。为了夺取王位,他赶在哈姆莱特回国奔丧前与王嫂速婚,占据了合法继承人哈姆莱特的王位,还以群臣拥戴的名义使自己的僭位合法化。《哈》剧从第一幕第二场始向世人呈上了一个“荒淫”“狠毒”“奸邪”“阴险”的戏剧形象,一个马基雅维利式人物的代表[4]178。
克劳狄斯以血腥手段和罪恶伪装达到了他蓄谋已久的目的——坐上了梦寐以求的宝座。然而,坐在万众凝视和群臣仰望的宝座上,他如何能以假面掩盖自己犯下的罪行?能否以伪装的自我实行王权并治理多事之秋的国家?如何在灵魂的忏悔中继续他的罪恶行径?如何看待克劳狄斯的伪装行径及其政治后果?对克劳狄斯这一人物及其伪装行径和政治博弈进行文本解读,可增强对《哈》剧艺术性和政治性的认知。
一、克劳狄斯的伪装背景
《哈》剧一开始就为我们提供了一幕疑雾重重的背景:午夜时分的艾尔西诺城堡守望台上万籁俱寂、寒气逼人,如此时空使接近城堡的人不寒而栗。在如此肃杀静穆的空气里,老哈姆莱特的鬼魂连续三夜晃现在守望台上,在阴森可怖的黑夜中徘徊辗转,增加了轮值守夜士兵的恐惧。霍拉旭(Horatio)据鬼魂的频频出现做出了自己的推测:“这恐怕预兆着我们国内将有一番非常的变故。”[5]185①霍拉旭的推测向观众或读者暗示:老王之死存有蹊跷,新王对此有着重大嫌疑;如果查证老王死因必然发生系列事件,此后的悲剧终会连续发生,国家的时局会产生变故。
(一)克劳狄斯面临的动荡时局
当值哨兵马西勒斯(Marcellus)则由霍拉旭的推测联系近期自己的所闻所见,回应霍拉旭:“国家正为备战而忙乱骚动;军民在夜以继日地制造铜炮;民众议论着政府要向国外购买战具;军部正在征集大批造船工匠。”[5]185霍拉旭对马西勒斯所道出的现象予以解释:挪威王子小福丁布拉斯(Fortinbras,Jr.)趁丹麦老王新丧政局不稳,正在积极准备用武力夺回曾经失去的土地。克劳狄斯对此做出了备战和外交的两手准备,一方面动员全国军民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着准备,另一方面则采取绥靖的外交政策,派遣大臣出使挪威,向在位国王小福丁布拉斯的叔父面呈国书,并要求挪威王遏制侄儿的野心。挪威王回应来使:知情后对侄儿进行了训斥,在侄儿诚心答应悔过下,现已委任他统帅他所征募的兵丁去征伐波兰边疆一小块荒瘠的土地,并提出挪威军队借道丹麦的非分要求②。
挪威军队借道邻国事关丹麦国家安全和丹麦与波兰的睦邻关系。然而,既是“谋杀者”又是“篡位者”的克劳狄斯惊魂未定底气不足,应允了挪威军队借道边境的要求[6]43。这一退让大大损害了丹麦国家主权,民众痛感丧失了国家的尊严。依此可说:莎士比亚塑造的克劳狄斯一角既是一个令人发指的谋杀者,又是运用阴谋篡位的叛逆者,更是一个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和不幸的罪人,一个以伪装为能事的阴谋家。因此,国家、人民以及他自己正面临着严峻形势。克劳狄斯面临王兄的阴灵不远、英名犹在和侄儿的王位归属、民心所向的挑战:一是,老哈姆莱特在位时,国家强盛,称霸一方,威名远播且具威慑力;二是,按“丹麦王位继承法”,王子哈姆莱特是老哈姆莱特的血脉传承者,是继承大位的唯一人选[6]45。并且,王子哈姆莱特曾在威登堡大学读书,深受欧洲大陆人文思想浸润,拥有民主意识,心系民众。克劳狄斯与其王兄两相比照,显然相形见绌、劣势明显。马西勒斯“丹麦国体正在腐烂衰败”的言论代表了大部分民众的声音[5]240。
(二)君臣间的紧张关系
此时的宫廷充满了威胁、恐吓、欺蒙和哄骗。而克劳狄斯则是威胁和欺骗产生的来源。克劳狄斯深知“王位世袭继承”观念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7]118,如非继承,自己王位的稳固需要多方势力的支持和认同。克劳狄斯深谙伪装之道,将“众臣视为舞台下的观众”,自扮自演伪装者的角色[8]80。在他的倾情演出下,众臣为他哀悼老王“猝死”的表演所动容,为他“不得不违情逆理”,让“殡葬的挽歌和结婚的笙乐同时并奏,用盛大的喜乐抵消沉重的不幸”言辞所说服,认同他为国土统一而背负“娶嫂夺位”骂名的“担当”[5]195-196。克劳狄斯的伪装不仅避免了一场内部的“派系斗争”,而且使得王位竞争者哈姆莱特的“煽动性言论”无法奏效[8]81。在赢得众臣的认同之后,克劳狄斯巧妙地运用了“艳丽的”上衣和“宽松的”裤装,塑造身份和烘托气氛,来掩饰英明君主“猝死”和邻国军事骚扰共同作用下的混乱局势[9]。但他还未意识到的是:欺蒙和哄骗是政体“腐败”生发的土壤,是王国“迅速衰微”的苗头[10]。
克劳狄斯将连环性的欲望变成现实后,连续地大宴群臣,并默许售卖他的画像,由此助长了奢靡的社会风气和阿谀奉承的宫廷恶习。对于克劳狄斯的做法,哈姆莱特评论道:“我的叔父是丹麦的国王,那些当我父亲在位的时候对他扮鬼脸的人,现在都愿意拿出二十、四十、五十、一百块金洋来买他的一幅小照。哼,这里面有些不是常理可以理解的地方,要是哲学能够把它推究出来的话。”[5]289-290哈姆莱特评论中暗带嘲讽:老哈姆莱特的小像贵重无比,是“神圣信仰的标志”。而克劳狄斯的小像低俗廉价,是“真相被隐藏的符号”[8]80。一方面,这些恶习引发各级官吏对民众的重利盘剥、横征暴敛,贪污受贿之风盛行,民乱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另一方面,克劳狄斯默许小像四处兜售的行为带有异教崇拜的嫌疑,比哈姆莱特视父亲如同神明的做法更为教会所不容,会触发国内的政教冲突。
二、克劳狄斯的伪装策略
克劳狄斯拥有很强的“以言行事”能力,且是一位行事果断的“实干家”。他带着阴险的目的,披着伪善的外衣,运用虚伪的语言,得到王兄的信任,博得王嫂的感情,取得群臣的认可。在阴谋行径达到目的后,他试图继续采用“言语伪装”和“行径伪装”,以此应对与他对立的任何人,尤其是哈姆莱特。然而,克劳狄斯终究是一阴谋家,而非思想家,且行的是恶,用的是伪,他行事的思考缺乏逻辑,他的言语本质上是虚假的,他的行事留有漏洞。
(一)言语伪装
克劳狄斯以“一石两鸟”的伎俩既实现了“娶嫂为后”,又占据了本属哈姆莱特的王位,然而再以自认自说的“群臣拥戴”使自己的篡权夺位的行为合法化合理化,进而当众宣称,这样重大的事情事先“曾经征求意见,多蒙大家诚意赞助”[5]196。克劳狄斯深谙“同类人群”的“语言游戏”及“语言规则”,反复使用空洞虚幻的言辞掩饰残害王兄奸娶长嫂篡夺王位的罪行[11]。更有甚者,他用表面上对哈姆莱特非常关心掩盖其罪恶的心灵,要求哈姆莱特视己为父,许诺将像慈父一样给予他关爱,虚情假意地恳请他留在身边伴随左右,应允他为王位的唯一继承人。克劳狄斯“按强盗的逻辑,夺取了别人的东西,答应自己不再使用时还给别人,还将自己美化成父亲般的仁慈”[1]231,并惺惺作态地要求哈姆莱特“在朝廷上领袖群臣,做我们最亲近的国亲和王子”[5]204。然而,克劳狄斯在酝酿着杀机,就在怀疑哈姆莱特装疯时,内心已经形成铲除他的方案——送往英国,借英王之手将其处死。从克劳狄斯玩弄的两面手法中,观众和读者看到的是一幅伪装的笑脸掩盖下的凶残、卑劣和狡诈且狰狞的面孔。
“君权神授”的观念一经打破,随之而来的影响是任何民众都可质疑君主王位获得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而自拥称王。克劳狄斯深知自己的王位既非“继承”亦非“神授”,而是“窃取”,担心雷欧提斯为父报仇的举动演变成颠覆其王位的民变,他立马想到转嫁矛盾,将雷欧提斯的怒火引向他处。面对雷欧提斯对父亲死因的追问,王后为他开脱的说辞是,“但是并不是他杀死的”,减弱了雷欧提斯对克劳狄斯的愤怒,避免了一场由情绪冲动可能发生的杀戮。依靠王后为其开脱之词,奸猾狡诈的克劳狄斯顺势引导他将愤怒的矛头直指他的心头大患——哈姆莱特。雷欧提斯报仇心切,正是克劳狄斯的所需,克劳狄斯终于为自己找到了消除心中隐患的工具,他接下来想要看到的是:这件“工具”能在比剑中刺中他的“心头大患”。
因王后的指证和克劳狄斯的挑拨,雷欧提斯的复仇怒火开始指向哈姆莱特。为自己全面开脱,克劳狄斯扬言以国土、王冠甚至生命为代价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的言说不仅是其为掩盖心虚的狡诈之举,而且反映出其本性中的愚蠢。接此,他趁势以言语引导雷欧提斯将复仇目标锁定为真凶,真实目的则是:“可是他们假如认为我是无罪的,那么你必须答应助我一臂之力,让我们俩开诚合作,定出一个惩凶的方案来。”[5]420身为大权独揽的一国之君,他的言说似乎不合常理,但仔细推敲,我们从此中可再识克劳狄斯的狡诈:在王位不稳之际,他不能亲自下令拘杀王后唯一的儿子,否则,这会使他失去到手的一切并暴露他的罪恶和阴谋。借他人之手除去哈姆莱特才是克劳狄斯玩弄阴谋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是他奸佞狡诈本性的体现。
(二)行径伪装
老哈姆莱特在位时,克劳狄斯用尽心机伪装忠于王兄,伺机对其施行谋害,终于得手。在由王亲走上王位后的短暂时日里,克劳狄斯统治下的丹麦却已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猜忌的风气:克劳狄斯对哈姆莱特充满戒心,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唯恐他知道了自己弑君篡位的底细而揭露真相并实施复仇;克劳狄斯对哈姆莱特以假恩虚惠收买不成,转而动了杀机,将他派去英国,名为“追索延宕未纳的贡物”,实为一路被监视下去受死,乔特鲁德却对克劳狄斯加害儿子的阴谋毫不知情;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对所传国书的内容全然不知,结果稀里糊涂地双双命丧英伦。此外克劳狄斯还为哈姆莱特与雷欧提斯的决斗设置了三道鬼门关(剑头开刃、剑刃蘸毒、备下毒酒),以取得一石二鸟的杀人效果。乔特鲁德对克劳狄斯所设计的连环圈套全然无知,终而被害。
克劳狄斯施政伊始就在丹麦王宫大行窥探之风,哈姆莱特被他视为心头大患。他投入最多时间和最大精力去探知哈姆莱特的行踪言迹,使用各种手段探知哈姆莱特装疯中的言说行止,从而猜中他的真正动机以便做出及时应对:他应允波洛涅斯安排女儿与哈姆莱特谈话,以便掌握哈姆莱特的心理动态;接受波洛涅斯的建议由乔特鲁特找儿子谈话,以便获得哈姆莱特在充满母子亲情的交谈语境下吐露的真实心境;罗森克兰兹和吉尔登斯吞被特召回国充当密探,按克劳狄斯的旨意窥探老同学的内心世界。作为反制,哈姆莱特则以伪装疯癫作为防身之器,以使克劳狄斯放松对自己的警惕,给自己留下时空伺机复仇;他借此安排巡演戏班排演《贡扎古之死》,以戏中戏来从旁窥探克劳狄斯对剧中弑君情节的反应,从而确认了鬼魂所说为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面对怒不可遏复仇心切的雷欧提斯,克劳狄斯心理空虚、底气不足,只得自降身份,装出一副“可怜”和“无辜”的嘴脸,亲自告诉雷欧提斯杀父的真凶是谁,并告诉他哈姆莱特也在图谋他的性命,并诉说他不能以杀人罪对哈姆莱特施以惩咎的理由——他与王后乔特鲁德伪装的难分难舍的感情和哈姆莱特深受民众的爱戴。
克劳狄斯一直畏惧的不仅仅是哈姆莱特本人,而是一旦失去王后的联盟就会丧失王权,导致民心不稳、民情不安定而王位不保。雷欧提斯因复仇而振臂一呼,即唤起了民众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可能性的存在。终而,一场夹杂为父复仇和质疑君权的大规模叛乱,就降格成了一次小型贵族私仇决斗。
哈姆莱特偶然看到克劳狄斯写给英国国王的信,从而成功跳脱出克劳狄斯为他预设的第一个死亡陷阱。哈姆莱特的突然返回使得使克劳狄斯惊愕了片刻。他一边喃喃自语:“要是果然这样的话,可是怎么会这样呢?然而,此外又如何解释呢?”[5]428一边思索着自己的缜密计划何以被哈姆莱特破解的原因。狡诈的克劳狄斯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利用雷欧提斯的复仇心切,再一次为哈姆莱特设下陷阱,只需他对此陷阱稍加掩饰就可将哈姆莱特置于死地而自己还可脱离干系,达到既可蒙蔽王后又能避免引发民乱的目的。他为此庆幸:雷欧提斯的出现为自己找到了除掉哈姆莱特的工具,再一次为哈姆莱特设下了死亡陷阱。此外,克劳狄斯使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肯定雷欧提斯的高超剑术,雷欧提斯准备好了与哈姆莱特兵刃相见。
垂直运输采用悬臂式桅杆配以3 t卷扬机。将桅杆与烟囱里侧的两层操作平台的横杆固定到一块,以增强其稳定性。
在克劳狄斯提议剑斗之外,雷欧提斯内心邪恶占据上风,准备再在剑刃上涂上致命的毒药以增加成功率。克劳狄斯还吸取此前借刀杀人未遂的教训,设计了一条连环计:“为了预防失败起见,我们应该另外再想个万全之计。”他的万全之计是:“我就为他准备好一杯毒酒,万一他逃过了你的毒剑,只要他让酒沾唇,我们的目的也就同样达到了。”[5]435-436克劳狄斯奸谋的深层目的是取得“一石二鸟”的结果——为哈姆莱特挖好了连环陷阱,也为犯下引导民众暴动的雷欧提斯准备好了结局。
三、克劳狄斯伪装的后果
戏班子的到来为哈姆莱特提供了证实复仇对象的契机。戏中戏激起了克劳狄斯的惊悸和恐惧,同时激活了他的灵魂深处的人性。在克劳狄斯的意识里,“花园谋杀”又一次浮现在眼前,他为自己的罪恶行径忏悔,对自己的良心予以谴责。但是,克劳狄斯的本性是贪婪的、虚伪的和阴险的,他不会以宗教信条和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以及行为,他的欲望是永远拥有已有的利益,且心中的欲火既已燃起,就难以熄灭。
(一)政治影响
经哈姆莱特改动的《贡扎古之死》(更名《捕鼠器》)展现在艾尔西诺王庭,当哑剧情节推进到扮演琉西安纳斯(Lucianus)的伶人将一种毒液佯装滴进正在酣睡中的国王(贡扎古)扮演者的耳朵中时,哈姆莱特期望见到的戏外戏出现了:克劳斯斯惊恐万状,脸色煞白,顿然站起身来,大喊着“给我点起火把来”[5]346。此呼喊吓坏了在旁的王后乔特鲁德,和陪伴观剧的群臣,波洛涅斯喝令伶人:“不要再演下去了”[5]346。台上的毒杀情景以及伶王伶后的肉麻对白打破台下观众的平静,彻底击垮了克劳狄斯的心理防线,揭开了克劳狄斯的伪装脸孔,迫使他露出了惊恐万状的真容。哈姆莱特以戏中戏验证了鬼魂申述事件的真实存在,明确了复仇的对象,坚定了复仇的决心。而克劳狄斯在惊悸和愤怒之后,暗暗坚定了除掉哈姆莱特的决心,决定加速实施残害哈姆莱特的行动。一场复仇和反复仇的斗争拉开了序幕。
中止观剧后,克劳狄斯的心情无法平静。他下令让哈姆莱特立即离开丹麦前往英国,以中止来自他的公然威胁。此时,当年的谋杀场景浮现在他的眼前:王宫后花园的正午阳光,大树覆盖下的阴凉处所,躺着在花坪上睡熟的王兄,他憋住呼吸,悄然地溜到王兄的身边,轻声呼唤数声,见王兄未有反应便从怀中掏出那瓶罪恶的毒液,给自己鼓上劲定好神,将毒液滴入王兄的右耳……。此时,“滴毒入耳”的意象不断在克劳狄斯脑海中浮现,不断提醒克劳狄斯所使用过的蒙蔽朝臣视听的伎俩。“滴毒入耳”具有具体和抽象双重含义:一指毒药滴入老哈姆莱特的耳朵,摧毁他的身体,致使他的凋亡;二指克劳狄斯伪装的言行和托词麻痹了群臣,“使得整个王庭又聋又瞎”,政务出现紊乱,政体趋于瘫痪[7]114。《捕鼠器》演出的舞台变成了政治法庭,演员成了控诉方,观众都成了法庭上的陪审团,台上台下对克劳狄斯的所作所为进行控诉、揭露和审判。克劳狄斯不敢再往下追忆,他的心灵在震荡,他的人性在回归。
(二)伪装的忏悔
震撼之余,克劳狄斯的人性有所回归,开始忏悔,对上天坦言:“哦,我的罪恶的戾气已经上达于天;我的灵魂上负着一个原始以来的诅咒。”[5]358-359克劳狄斯此时感到用罪恶换来的王位像一朵带刺的蔷薇,感到自己所犯罪行已为天地不容,呼唤道:“我因为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而徘徊歧途,结果反弄得一事无成。”[5]359他把罪恶归为自己的堕落,向天空伸出那只种下罪恶之果的手:“要是这只可诅咒的手上染满了一层比它本身还厚的兄弟的血,难道天上所有的甘霖,都不能把它洗涤得像雪一样洁白吗?”③[5]359
但克劳狄斯的欲火不能熄灭,到手的俗物难以舍弃:“现在还占有着那些引起我的犯罪动机的目的物;我的王冠、我的野心和我的王后。非分攫取的利益还在手里,就可以幸邀宽恕吗?”[5]360他试图以祈祷来减轻罪恶感,以忏悔救赎自己,一方面安抚因戏中戏演出引发的自我良心谴责,另一方面从心理规避因罪行而衍生的惩罚。他既贪婪又现实,深知只能去拥有现在,他忏悔的言语只能“滞留在地上”,而“永远不会上达天界。”[5]363克劳狄斯不愿屈下“顽强的膝盖”向上天祈祷,他不能丢弃运用伪装和罪恶行径夺来的一切,他要继续统治这一方国民,他至死认为,只要再发动一场博弈,就能消除心中的大患,就可享受已在手中的“利益”。
注释:
①引文译文选自朱生豪先生的《莎士比亚全集》(六卷本),作者略作改动。英文版《哈姆莱特》选用汤普森和泰勒注释的阿登版(2016),并在戏剧文本引文规范的基础上做了调整,将原本的幕次、场次以及行数替换为页码。全文中引文标注对应英文版《哈姆莱特》页码。
②小福丁布拉斯率兵去争夺的是“一小块徒有虚名毫无实利的荒瘠土地”,而波兰人为保疆卫国,早已布防好了以迎击来犯之敌。征伐本无意义且代价巨大,借道只是幌子。挪威军队的真实意图在剧末得到印证:小福丁布拉斯从波兰班师道经艾西诺城堡,正值丹麦宫廷中一片惨景,他轻易获得的不仅仅是父亲当年输掉的土地,而是整个丹麦国。
③《麦克白》中有类似的话语,如:杀害了邓肯的麦克白心虚气短,带有负罪感时忏悔道:“大洋里所有的水,能够洗净我手上的血迹吗?不,恐怕我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红呢。”麦克白的此句忏悔曾是文学批评的对象,原文中的词语被语言学者作为研究早期现代英语的范例。从写作年代考查《哈姆莱特》写于1601-1602年期间,《麦克白》则为1606年,那么,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有所提升,显得更有气势。但同一意思的不同说辞也体现了人物在性格上的差异和因身份不同而行为方式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