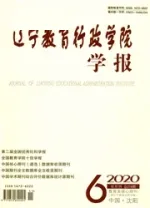宋代古文批评之论“奇”
张天骐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110034
一、宋代古文尚奇之风及相关批评的出现
整个宋代散文领域最为重要的事件非“古文运动”莫属,这场具有文学和思想两方面意义的革命孕育了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古文作家,虽然他们的风格各异,但是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一些以“奇”为尚的作家,创作了大量具有瑰奇风格的作品,这使得人们竞相模仿,从而影响了这个时代的文风,宋代的古文批评家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南宋时期关于文章之“奇”的讨论也不在少数,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奇文”并不是后代文人竞逐文才的产物,早在先秦时期,散文中就已经有了大量具有“奇”文性质的作品,其中以《战国策》和《庄子》最具代表性,《战国策》的纵横之气和《庄子》的瑰奇华丽都对后世散文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汉代的贾谊、扬雄等人也受到影响,所创作的文章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而有奇气。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逐渐被四六文所统治,古文的创作陷入低潮。直至唐代,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才让古文创作进入了一个高潮,而韩愈本人因其出众的文采,在创作上也有着“奇绝”的风格,不仅如此,他还创作过很多诸如《毛颖传》这样的“奇文”,韩愈的文法和风格对宋代古文作家颇有影响,只不过他所领导的古文运动在晚唐逐渐衰微,古文创作又一次陷入低谷。北宋时期兴起的新一轮古文运动,使得古文的创作成为文坛主流,而“奇”这一种风格以及对这种风格的讨论也开始于这一时期。北宋时期古典文章学尚未建立,也缺乏文话和文选著作,但是在一些文人书信和序跋中,已经可以看到北宋文人对“奇”这种风格的讨论,北宋文人郑獬就曾评价韩愈文章“质而工,奇而肆”,更具有理论意义的是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对欧阳修作文风格的批判:“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奇”。这首先说明了欧文的确有“瑰奇”之风,其次也能看出王安石对这种风格的称许。然而引领一代“奇”文之风的人并非欧阳修,而是以苏轼为首的三苏父子,苏洵的文风近于《战国策》自不必说,苏轼的文风也和父亲一样以“奇”为尚,南宋文人认为“子瞻文皆有奇气”。对于三苏父子对当时文风的影响,朱熹这样论道:“自三苏文出,学者始日趋于巧”。而苏轼门人也都有此风格,以致于苏轼曾以晁补之文章过分追求奇为例提醒黄庭坚对于文章之奇要采取适度原则:“凡人作文,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尔;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谓其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虽然这是苏轼对于门人“奇怪”风格的指正,但也从侧面说明求奇这种趋势在北宋已经开始。此外,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对于一味在字句上求奇求怪的作品,很多批评家都采取反对的态度,他们的评判也足以证明当时文坛确有求奇之风,只是并不是所有这类文章都可以得到认同。
与尚奇之风在北宋的流行不同的是,对于这种风格的讨论直到南宋才相对完整,这也符合理论滞后于创作的文学规律。北宋时期对于“奇”的讨论是零散的,并且为数不多,到了南宋,几乎每一部文话和选本作品中都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并形成了不同层次,尤其是《朱子语类·论文》在这个方面论述颇多,对韩愈、苏轼之“奇”有独特见解,也涉及到当时文坛尚奇的文风。可以说在南宋时期,批评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形成了辩证的思维,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二、宋代古文批评论“奇”的三个层次
“奇”这一批评概念在南宋批评家的论述里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层次,有三种不同的理论内质,即作法层面、风格层面以及思想层面,这一点在《朱子语类·论文》中体现得比较明显。通过对材料的研究发现,宋人对这三个层次的“奇”有着不同的态度。总体来说,对“奇”的崇尚和欣赏只是在风格层面,在作法层面和思想层面,大多数意见都是反对求奇的。以下是对于这种现象的具体分析。
在“奇”的三个层面中,文法层面上的“奇”是最显而易见的,这种书面上的奇是通过在用字和造句的方法上刻意追求新奇古怪而达到的,在宋代的一般文人中十分普遍,下层文人往往通过这种形式引起他人的注意,试图在官场和科场中以文显名,可以说,这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创作行为。对于在文法层面的求奇行为,大多数的宋代文论家都是持反对态度的。北宋文人杨杰就曾论及欧阳修对一味求奇之风的改变:“场屋文章,以搜奇抉怪雕镂相尚,庐陵欧阳公,深所疾之;及嘉佑二年知贡举,则力革其弊,时之道亦尝被黜”。虽然这句话讲的是欧阳修对时文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欧阳修显然对这种雕琢字句以求奇的做法是持反对态度的。苏轼的门人张耒更是对此有着精到的论述,他在《答李推官书》中评判道:“足下之文,可谓奇矣,损去文字常体,力为瓌奇险怪,务欲使人读之如见数千岁前科(蝌)蚪鸟迹所记,弦匏之歌,钟鼎之文也……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理黜者,巧为粉泽而隙间百出”。可见,他认为着力于使文章奇怪会有害于理,实不可取,接下来,他又以水为例提出了他所认同的文章之奇:
怒之为雷霆,蛟龙鱼鼋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而水初岂如此哉,是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沟渎东决而西竭,下满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见其奇,彼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之文也。六经之文,莫奇于易,莫简于春秋,夫岂以奇与简为务哉?势自然耳。
张耒以“沟渎之水”比作刻意雕琢求巧的把戏,把“江河之水”比作上古之文,以对比的手法说明了真正的奇在理到的基础上要做到自然,否则就无益于文章。这也引出了风格层面关于奇的问题,通过张耒的论述,可以看到,宋代批评家审美理想中的奇是风格上自然流露的奇,并不是仅在字句上磨炼功夫的奇。南宋的文论家基本持有和张耒相似的观点,朱熹也曾批评道:“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在遣词造句上,他反对追求新奇,然而在风格上他却提倡求奇,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文字奇而稳方好,不奇而稳,只是闒靸”。显然,“稳中有奇”是朱熹认为文章应该具有的风格。苏轼的奇文之风格往往成为后世批评家赞赏的典范,南宋黄震在《黄氏日抄·读文集》中就对苏轼之“奇绝”十分称许:“苏东坡作《韩文公庙碑》,词绚云锦,气矗霄汉,振古一奇绝也”。“《李太白碑阴记》东坡奇才逸笔,簸弄千古”。“温公德业三王佐,坡老文章万古奇”。这些盛赞之语都可以说明批评家对于这种“奇绝”文风的欣赏。苏轼之奇,并非通过雕镂词句得来,而是“只平易说道理”,“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由此可见,宋代文章批评界对于奇的批评是辩证的,并不是一味地崇尚求奇,也不是对此全部否定,而是将“自然之奇”这种风格上的奇作为典范,同时反对通过在字面上求新求僻达到的“刻意之奇”。
除了以上两方面的文章之“奇”,宋代的批评家也关注到了文章所蕴含在思想层面的“奇”,在论及这方面内容时,“奇”往往与“正”相对,二者成为具有相反意义的批评观念。所谓“正”就是符合儒家道统,能够以儒家思想为准绳,以作文为传道的手段;所谓“奇”就是所作文章带有不同于儒家之思想,所作文“有害于道”,不能阐释儒学之理。朱熹就经常以这种角度来批判三苏父子的文章:“老苏文初亦喜看,看后觉得自家意思都不正当。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欧曾文字为正”。“老苏之文高,只议论乖角”。由此观之,朱熹对于苏洵富于纵横习气的文章是不赞同的,而以欧阳修和曾巩的文章为正。他还批评苏轼道:“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对于苏辙和黄庭坚,朱熹也加以指责:“子由文字不甚分晓。要之,学术只一般”。“黄鲁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气”。之后他总结这种求奇而害正道的原因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诸公文章驰骋好异常。止缘好异,所以见异端新奇之说从而好之。这也只是见不分晓,所以如此”。朱熹的如上观点带有他自己的偏见,不见得都对,但至少可以反映当时的批评界对于“奇”与“正”的对立已有所认识,朱熹认为韩愈的文章奇却不失正,算是一等文字,当门人问起韩柳二家孰正的时候,朱熹认为柳文“不甚醇正”,而韩文为正。但同时,他又认为韩文“有险奇处极险奇”,可见,朱熹对韩愈文章所体现的奇与正的和谐是很赞赏的。而如何处理好奇与正的关系,可以用南宋文人谢谔的一句话来概括:“奇而法,正而葩”。他的这种提法被当时很多批评家所接受,分别在孙奕的《履斋示儿编·文说》和陈模的《怀古录》里被引用,足见其重要性。南宋批评家吴子良在著作《荆溪林下偶谈》中也表示认同,他认为“文虽奇,不可损正气”。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宋代批评家们普遍将“正”置于“奇”先,在思想层面,有损于儒家道统的文章之“奇”是不被认同的。
三、宋代古文批评论“奇”的理论价值
在对宋代批评理论中“奇”这一概念的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在对这样一问题上,宋人有着比较完整且辩证的观点,这一点在文章学体系尚未建立的宋代是难能可贵的。而单一批评概念“奇”有着三方面理论内质和批评角度,这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中也是比较少有的,它几乎涵盖了文章的各个方面,从风格、文章作法到思想内容,宋人为“奇”树立了正确的审美标准,也影响了一时文学好尚,在风格上对于奇的崇尚符合了文学的审美属性,使得古文的创作不至于过分平淡无味;在作法上,他们对刻意雕琢的求奇求怪进行批评,并创造了“自然之奇”的审美典范;在思想内容上,他们主张言之有物,一切以正大行之,使得北宋以来古文运动的思想得以延续。事实上,宋代批评家对于很多类似“奇”出现于作品中的现象都曾进行讨论,比如“简”、“淡”、“老”等,而这些无论是在风格上的还是文法上呈现的文学现象都是来自于宋代“古文运动”中各个古文大家所创造出的审美风范。可以说,正是由于古文运动的发展,宋代的文章学理论才能有此发展,然而也是因为有文章学的发展,古文运动的成果才能得以总结,并且继续对后世的文章写作产生影响。这样的创作与理论的共同发展与交流,让宋代文章学的各个方面能够逐渐成熟,虽然宋人未能为文章学建立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但他们对于文学现象精到的总结与评判,对风格的认识,都对元人有重要影响,从而使元人在宋人的基础上,将具有完整性体系的文章学理论框架建立起来,在这其中,既有文法论的内容,也有风格和思想层面的内容,而这一切都已体现在宋人对“奇”这一审美范畴的批评当中。总之,对于“奇”的讨论是宋代文学批评领域十分有意义的一个事件,它既能体现宋人在文章学见解上的独到,也是宋代文章学风格和现象批评的一个典型,值得人们对其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1] 王水照.历代文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北京[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 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