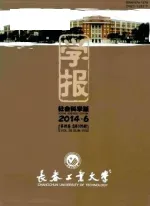从司各特《艾凡赫》看小说的史诗性
李昆峰
(贵阳中医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部,贵州 贵阳550002)
司各特是英国著名的诗人,更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史实通常是其小说的主要取材,因此,他的小说又被称为历史小说。由于他的历史小说极为独特和突出,对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他被誉为“历史小说之父”。[1]司各特的《艾凡赫》开创了西方历史小说的完美范本。他将小说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在欧洲影响深远。本文从错综复杂的民族间、民族内矛盾冲突中体现史诗性、从对犹太人的同情和理解中体现史诗性三个方面品读了司各特《艾凡赫》的史诗性。
一、从错综复杂的民族间矛盾冲突中体现史诗性
名作《艾凡赫》的故事发生在12世纪末期的英格兰,当时被诺曼征服并统治着。在各种复杂矛盾冲突的冲击下,约翰亲王弗朗·德·别夫和布里昂等贵族们同塞德利克一直就积攒着许多仇恨。[2]所以以贵族塞得利克为代表的萨克逊人始终与诺曼贵族进行着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斗争。而广大的底层人物,代表人物有绿林好汉罗宾汉,组织贫苦百姓反抗诺曼领主的剥削与压迫。在反抗的同时,贵族内部又存在着内讧,代表王权的理查王同代表割据势力的约翰亲王在进行着殊死搏斗。不惜赶走亲生儿子的塞德利克仅仅想要让两大势力之中的代表结成姻亲,却甘愿牺牲儿子的爱情,这种完全不顾及孩子感受的做法体现了封建思想的腐朽与不堪,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姻亲,没有存在自愿的恋爱情节,势必会产生巨大的矛盾。[3]文章中查理王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向萨克逊人寻求帮助,与他们结为联盟,于是,在共同的斗争对象的号召下,民族独立斗争、反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反割据强化王权的斗争终于完整地统一了起来,他们共同努力促进英吉利民族的统一。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诗性是司各特历史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也就是说,在对阶级、政治、民族、经济文化等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进行反思的过程中运用描写广阔社会生活的方式,力图将时代和社会的全貌描绘出来,从而将时代的本质特征及历史发展总趋势全面揭示出来。司各特的所有历史小说均具有这样的特征,使读者对知之甚少的古代生活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认识。
在反映民族矛盾的过程中,司各特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不列颠岛上的入侵与反入侵、剥削与反剥削的民族斗争,这些斗争发生的时间贯穿于不列颠岛从形成到现今整个过程。因为在不列颠历史上,最先在不列颠岛上定居下来的民族是萨克逊人和罗马人,在近代居民中萨克逊人属于日耳曼民族。萨克逊民族在与早先的古老民族的杂居中,倚仗其好勇斗狠的性格,逐渐成为岛上的主人,而其他古老的民族,如盖尔人、条顿人等,则成为少数民族。[4]后来,萨克逊民族在北欧的诺曼人及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入侵过程中开始了与诺曼民族的斗争。诺曼人凶猛而狡猾,萨克逊人好勇尚武,两个强者相遇,诺曼人占据了上风。之后,诺曼人一方面对萨克逊人的财物进行了无耻的抢劫,另一方面还将萨克逊人的土地强行据为己有。诺曼人通过入侵逐渐成为岛上的主人,而随着每次入侵,两个民族之间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间的融合,逐渐形成了封建的英吉利制度。特别是在1066年,诺曼人将北方征服,并向诺曼人分配没收的土地之后,不列颠岛上逐渐形成了封建经济制度,而这一经济制度是从村社演变过来的。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发展,不列颠岛上又逐渐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政治上层建筑。这时诺曼人已经掌握了英国的全部土地。[5]
二、从错综复杂的民族内部矛盾冲突中体现史诗性
萨克族和诺曼族之间进行着斗争的同时,诺曼族本身也进行着斗争,诺曼族中的皇室内部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在战争中被俘虏的萨克逊族中以塞德利克为代表封建贵族,时刻不在想着如何才能重新获得自由和独立,甚至自私的牺牲自己儿子的婚姻自由和家庭幸福作为条件交换。文中这样提到他:“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是战败的民族,害怕受到侮辱,会拼命的隐藏着他们的祖先。可是塞德利克却想尽一切办法去证实自己就是这样民族的子孙。”约翰亲王是封建反叛割据势力的代表,也是诺曼人中最可恶、最无耻的人。反叛割据势力是萨克逊人的冤家,但是他们却归顺了理查王。这就是对塞德利克的讽刺,但是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们失去了雄心。塞德利克是一个悲剧英雄,从另一个角度看,成功是必然的,因为百姓们希望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而不是取而代之的战争,理查王有着较好俘虏人心的政策,这为理查王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圣殿骑士派一直对犹太人实施迫害,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圣殿骑士布里昂·基尔勃及其所参加的教派,成为英国一种重要的民族矛盾——宗教与种族之间的矛盾。体现出司各特对历史观察的深刻入微。[6]
在《艾凡赫》中,小说还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塞德利克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司各特对历史生活进行如实再现的另一个角度就是家庭。塞德利克父子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关于萨克逊古老的传统和秩序是否要保存下来的矛盾,因此在这一家庭冲突中,那个时代的特征被毫无遮拦地再现出来:种族冲突在家庭生活中若隐若现,而民族大融合时期的民族矛盾也在个人之间的恩怨中彰显出来。
司各特作品错综复杂的矛盾还表现在:在统治阶级的无情压迫和剥削下,广大底层人们被迫沦为强盗,与官府进行着殊死的搏斗。让人意外的是,塞德利克在强盗横行的社会环境中竟然不怕走夜路。
塞德利克和阿泽尔斯坦随着一对旅客走到一片森林的边沿就要穿过林子时,行路的人开始担心这个地方很危险,因为这里群聚着很多铤而走险的人,他们在政府的压迫下沦为强盗。塞德利克和阿泽尔斯坦虽然看到天色已晚,但是却依然决定走进这片森林,因为他们认为那些绿林人是不会扰害他们的。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萨克逊族的庄户和农民占据了那些绿林人中的绝大比例,他们过着这种流浪生活,成为亡命徒的罪魁祸首是政府严酷的森林保护法,通常情况下他们还是尊重本民族人的生命财产的。
这些“强盗”,在封建贵族的残酷压迫下、在森林法的苛政下,没有一丝力量去为自己的生存加码,万般无奈下只能成批地守在森林荒地。可是,即使是这样,官府仍然不肯放过他们,时时镇压他们,逼迫他们反抗。而贵族们却会养一班可以保护自己的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地上做着“土皇帝”。[7]特别是约翰亲王等统治者,他们无耻的将自己的情绪肆无忌惮地发泄到他们身上。比如,约翰亲王在艾凡赫比武胜利后向罗文娜上献王冠时,感觉艾凡赫在武场上打败自己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因此产生泄恨的念头。他长时间地看着那个带着弓箭的农民,认为是他让自己不高兴,因此盯他的眼光也是恶狠狠的。同时对身边的卫士下命令道:“你们别让这家伙逃走了,否则用你们自己的性命抵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劳动人们俨然就是统治阶级戏弄的玩具和发泄的对象。而这种矛盾在萨克逊人内部同样存在。比如,葛尔兹颈上带着铜圈,他生来就是罗泽伍德氏家的奴隶,注定一生不自由。服从是他生来就要做的事情,他的主人像狗一样奴役着他。当他的主人塞德利克生气时,即使他接近他的主人,也要被责骂或毒打,还不如那条可以在他主人面前撒娇的狗。所以他告诉汪巴:“请你告诉主人我再也不想服侍他了,即使他用各种方法折磨我,甚至杀死我,我也不会在被迫爱戴他、服从他了。我宣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是他的奴隶了!”[8]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从前所过的日子是多么的悲惨。
文中将两大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彰显的很独到。诺曼人从来都是以高姿态去看待其他民族的,一直对其他民族存有偏见。而虽然诺曼入侵者很傲慢,但是萨克逊人却仍然坚持着本民族的特点,较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塞德利克虽然为自己儿子在比武上能战胜诺曼人而高兴,但是他觉得艾凡赫是“忤逆不孝”之辈;艾凡赫在战斗中不用本民族的“砍刀”,取而代之的是诺曼人的“长矛”,说明了他们民族的一些特质和习惯。
三、从对犹太人的同情和理解中体现史诗性
无论是萨克逊族还是诺曼民族对犹太人的仇恨已经很深,这不仅体现在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一直存在欧洲,司各特竟然无意之中把这个问题的实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司各特成功塑造了丽贝卡这一犹太女子的形象来完成对历史偏见的突破。丽贝卡不仅漂亮、重情重义,而且不畏强权、乐于助人。丽贝卡为了报答骑士的救命之恩努力劝说父亲:“你是得到过那位骑士先生的好处的,报答他一下,可千万不应该后悔。”还给骑士的仆人们回赠“二十个采荆”,劝告他们当心自己的行程,避免“丢了钱还赔上性命。”[9]这就与犹太人见利忘义的“传统性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布里昂是好色之徒,对丽贝卡进行威逼,这些龌龊的行为不仅没有使丽贝卡妥协,反而激发了她顽强反抗的精神。种种遭遇使丽贝卡心里的信仰更加坚定。被压迫的民族时刻不在遭受着灾难和无情的压迫!还体现了当时的历史现实——排斥犹太人的运动仍然在继续。
犹太人一直以来都在逃离,为了避免灾难和灾害的侵袭他们居无定所。世界各地都存在着他们的身影,因为不迁徙有可能面临死亡。他们的粮食没有固定的产量,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在流浪中想着如何积累更多的资金,因为生活是残酷的,更不要说在有战争的年代。时刻让自己充满安全感的东西莫过于金钱了。“犹太人没有人性,只知道挣钱”,这些都是欧洲人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赋予犹太人这些命运,造就了他们所说的犹太人传统的性格。[10]在这里我们应该给犹太人一个公正的申诉,他们虽然是流浪者,但是他们想要好好生活的信念却不是“流浪者”。[11]他们想要的东西比那些地主们向往土地所有权还要正当;比贵族们对世袭爵位的渴望还要正当。我们不能因为民族生活形式的相异而去排斥他们,排斥较为明显的是欧洲,而且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出现了,突出表现在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之中,对夏洛克这一人物的描写站在犹太人的民族立场上、仅仅只是理解、同情犹太人。但是在最关键的地方——对于犹太民族及其生存方式等应该如何看待,小说中却没有进行详细的描写,所以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夏洛克的性格特征还是吝啬、没有人性、只知道挣钱的形象。之所以说司各特超越了莎士比亚,是因为他站在了莎士比亚的肩膀上,看到比莎士比亚更加全面的一面——犹太人的民族性问题。司各特是在用自己塑造的丽贝卡这个美丽动人、智慧大方的女子形象冲破了传统观念。司各特敢于做这样的事情也是他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形象刻画的越深刻,对犹太人的同情就越深,司各特在作品中能够反其道而行,渊博的学识和胆略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司各特的小说在当时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喜爱和极力推崇和这点是分不开的。
[1]〔英〕司各特.艾凡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文美惠.司各特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3]韩加明.司各特论英国小说叙事[J].外国文学评论,2003,(2).
[4]张亚.稀释后的历史——司各特历史小说《艾凡赫》中的骑士精神[J].世界文化,2010,(4).
[5]万信琼.论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J].励耘学刊(文学卷),2010,(1).
[6]张宏莹.从《艾凡赫》看司各特历史小说的骑士色彩[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1).
[7]朱海霞.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观和历史叙事[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
[8]张箭飞.风景与民族性的构建——以华特·司各特为例[J].外国文学研究,2004,(4).
[9]刘凤.论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真实观[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5,(10).
[10]高萍.历史叙事中虚构、想象语境的营造[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11]黄波.饱蘸历史笔墨,圈点民族之魂——简评司各特的《昆丁·达沃德》[J].淮北煤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