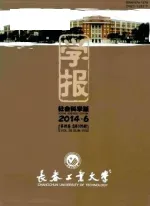品评辽代诗坛的一座高峰——从《焚椒录》看萧观音的文学成就
陈姗姗
(东北师范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吉林 长春130024)
一、萧观音其人
萧观音,是辽朝道宗的宣懿皇后,据《辽史·后妃传》记载,其为“钦哀皇后弟枢密使惠之女”,不仅“姿容冠绝”,且对诗词曲艺尤为精通,有“工诗”之才。“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1](P1205)更重要的是,她有皇后之德,抚育太子之功,足为当朝所称道。然而这样一位才学出众、德行昭然的皇后,人生结局却异常冤屈悲恨,令后世唏嘘。辽朝正史《辽史》对其记载仅寥寥数语,她的大部分人生事迹与文学作品都被记载于王鼎的《焚椒录》之中。
二、王鼎与《焚椒录》
王鼎,《焚椒录》的作者,字虚中,涿州人。史书记载其自幼好学,博经通史,为人刚正不阿,“人有过,必面诋之”。[1](P1453)王鼎于辽道宗清宁五年擢进士第,后累迁为翰林学士,寿隆初,又升观书殿学士。王鼎原本一路仕途坦顺,然其后却因“醉与客忤,怨上不知己”而惹怒道宗,[1](P1453)被杖黥罢官,流放镇州。数年后,其又因“谁知天雨露,独不到孤寒”之句博得道宗怜之而复职,[1](P1454)最终于干统六年卒。王鼎曾行史官之职,《辽史·王鼎传》载:“当代典章多出其手。”[1](P1453)有人认为王鼎一生最大的史学成就就是其在流放时期著成了《焚椒录》一书。[2](P15)出自王鼎之手的《焚椒录》是辽代留传下来的唯一一部传记性文学作品,兼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而在辽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焚椒录》一书详细记述了萧观音被诬案件的始末,可补《辽史》记载宣懿皇后诬案之不详。同时,萧观音作为辽代杰出的女作家,其作品《辽史》失载,赖《焚椒录》存之。《焚椒录》共载萧皇后作品15篇:诗4首,词10首,疏奏1篇。这些是萧观音传世的全部作品,弥足珍贵。《焚椒录》对萧观音这些作品的记载使其诗词文献得以留传,其文学才华得以彰显后世,可谓于萧观音本人,于辽代文学,乃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功不可没。
三、从《焚椒录》看萧观音的文学成就
《焚椒录》记载萧观音作品共6题15首:《伏虎林应制》诗1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诗1首,《谏猎疏》疏奏1篇,《回心院》词10首,《怀古》诗1首,《绝命词》诗1首,可谓体裁各异,题材多样。其选五律、七绝应制,言简意切,直抒豪情;取体制较长的骚体来表露自己的情感世界,酣畅真切;择词来表达女性所特有的幽怨之情,婉转缠绵,可见史书所赞“工诗”之才不虚。
清宁二年八月,辽道宗行至秋山围猎,宣懿皇后奉命随行。适至伏虎林时,道宗兴之所至命后赋诗一首,于是一篇气势不凡的七绝便在萧后口中应运而生: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
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敢猛虎不投降。[3](P506)
此口占七绝气势磅阔,道尽了大辽王朝的声威与雄心。前两句明写辽出猎阵营之浩大壮观,实则暗指威风凛凛的大辽王朝,幅员万里,表明其南征东扩之宏愿。其诗开口便道出宏旨,既符合萧观音“母仪天下”的皇后身份,又巧妙含蓄地迎合了道宗的心境与政治抱负。“灵怪大千”之句以野兽暗喻“南邦”、“东邻”之敌,并以“俱破胆”三字展示了大辽国欲争天下、所向披靡的雄威与自信。更工巧的是,尾句“那敢猛虎不投降”又与地名“伏虎林”相合。难怪道宗听罢便大赞皇后之才,喜不自禁。此诗为萧后随口应制之作,从中不难看出其才智之敏,学养之深。一年之后,清宁三年秋。辽道宗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一诗,萧观音再次应制和诗:
虞庭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
文章通鹿蠡,声教薄鸡林。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3](P506)
这首五律热情地歌颂了辽国开放、包容的文治理念。诗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作者因辽被汉视为“夷”而自卑,亦或是产生敌对情绪。她并无理会“夷”字本身所带有的文化霸权色彩,而是在“文章通谷蠡”、“应知无古今”的开阔的文化视野下,主动认同并接纳先进文化,把契丹民族纳入到“虞廷开盛轨”的中原道统之中,将君臣视为一脉,即“同志”,找到华夷合一、天下归宗的根本,即“同风”,也就是中华文化的大融合。此诗以舜周之盛世开篇,以其喻辽,颔联与颈联各承“君臣同志”“华夷同风”之题旨,尾联摘引《易经》,贺万物通泰。通观全诗,境界开阔,题旨宏大,诗律和畅,文辞古雅,开合对仗精致工巧,展示出四海同风天下一统的民族融合壮丽画卷,体现了诗人高瞻远瞩的政治气魄以及娴熟的诗学造诣。《焚椒录》亦载:萧后“婉顺善承上意,复能歌诗。而弹筝琵琶尤为当时第一,由是爱幸,遂倾后宫。”[3](P505)本来,宣懿皇后无论样貌才情都颇得道宗垂爱,可后来道宗却因“性忌”而对其厌烦疏远,这“性忌”的源头就是萧后所作的《谏猎疏》:
“妾闻穆王远驾,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几屋。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龟鉴也。顷见驾幸秋山,不闲六御,特以单骑从禽,深入不测,此虽威神所届,万灵自为拥护,倘有绝群之兽,果如东方所言,则沟中之豕,必败简子之驾矣。妾虽愚暗,窃为社稷忧之。惟陛下尊老氏驰骋之戒,用汉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为牝鸡之晨而纳之。”[3](P506)
这是一篇宛似汉儒手笔的疏奏,意在劝阻道宗远游出猎。此疏以中原帝王耽于畋猎而荒政误国的历史教训为事实根据,以汉哲智士劝谏驰骋的古训为理论依据,从心系社稷的角度出发,对辽道宗进行规劝,言辞委婉,情感恳切,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然“上虽嘉纳,心颇厌远。故咸雍之末,遂希幸御”。[3](P506)
《谏猎疏》之后,道宗对萧后疏远,萧后自然心知肚明,所以为挽回上心,其作《回心院》词十首,“被之管弦,以寓望幸之意”。[3](P506)
埽深殿,闭久金铺暗。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埽深殿,待君宴。
拂象床,凭梦借高唐。敲坏半边知妾卧,恰当天处少辉光。拂象床,待君王。
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转展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
铺翠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块。铺翠被,待君睡。
装绣帐,金钩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见愁模样。装绣帐,待君贶。
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
展瑶席,花笑三韩碧。笑妾新铺玉一床,从来妇欢不终夕。展瑶席,待君息。
剔银灯,须知一样明。偏是君来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剔银灯,待君行。
爇熏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爇熏炉,待君娱。
张鸣筝,恰恰语娇莺。一从弹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张鸣筝,待君听。[3](P506-507)
在萧观音的所有作品中,属《回心院》流传最广,徐诚庵的《词律拾遗》、况周颐的《蕙风词话》、钟惺的《名媛诗归》等对其均有收录,诸多古文学选本亦刊载此作,将其作为辽代文学作品的压卷之作。《回心院》是一组典型的闺情词,共十首,依次以扫深殿、拂象床、换香枕、铺翠被、装绣帐、叠锦茵、展瑶席、剔银灯、爇熏炉、张鸣筝十种闺阁细节起兴,层层深入,情思缠绵,通过回首往昔恩爱岁月的点滴传达出作者盼君回心的主题。第一首词运用了以景衬情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内心世界,用游丝结网、尘土作堆的凄冷场景正衬出作者冷寂孤清的遭际,进而表达出内心苦闷凄婉的心情。第二首紧承前词,以拂床凭梦的凄楚画面尽显其处境悲怆。第三首由象床写到香枕,香枕虽好,奈何“双双泪痕渗”,足见其思君盼君之意浓切。第四首采用反衬手法:一眼望见“鸳鸯对”,可堪自身无人怜。其后第五首、第六首、第八首、第九首中的“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见愁模样”、“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偏是君来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几句“皆有唐人遗意,恐有宋英神之际,诸大家无此四对也。”[3](P510)尤其是第八首,作者运用对比与拟人的艺术手法言银灯对君“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将自己的生命感受和情感体验投注到无情之物上,以物传情,含蓄委婉,却更显内心之幽怨。第十首词,是《回心院》组词的最后一首,幽怨的琴声、窗前的风雨声,其凄婉的情境恰与首词环境氛围接洽,从而使十首词成为一个整体。这十首词在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均采用三五、七七、三三的句式,各自成篇,但同时其各自在时间、动作上又具有承接性,并都归结到“待君”这一思想主题之上,意境相通,情境互融,浑然一体。
“被之管弦”的《回心院》想必动人无比,缠绵至极,然圣心是否回转我们不得而知,但萧观音此举却真正意义上为自己拉开了悲剧的序幕。正是由于《回心院》“被之管弦”才给了奸人以可乘之机,随后他们又利用萧后善史、喜文、工诗的才情,引其于手抄《十香词》后附自作《怀古诗》一首,招致大祸。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
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3](P507)
本来,这首怀古之诗在意境、格调、神韵等方面都尽得唐人怀古诗之妙谛,尤“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一句更是与“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刘禹锡《石头城》)神韵相通,“败雨残云误汉王”之句,亦被认为“议论果决,态度明断,有杜牧咏史诗之特长”。[4]但不巧的是,诗中偏含“赵”“惟”“一”三字,被奸人利用,成为了道宗赐死萧后的最后一击。道宗敕后自尽,后乞面上而不得,遂望帝所而拜,作《绝命词》:
嗟薄祐兮多幸,羌作俪兮皇家。承昊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华。
托后钧兮凝位,忽前星兮启耀。虽衅累兮黄床,庶无罪兮宗庙。
欲贯鱼兮上进,乘阳德兮天飞。岂祸生兮无朕,蒙秽恶兮宫闱。
将剖心兮自陈,冀回照兮白日。宁庶女兮多惭,遏飞霜兮下击。
顾子女兮哀顿,对左右兮摧伤。共西曜兮将坠,忽吾去兮椒房。
呼天地兮悿悴,恨今古兮安极。知吾生兮必死,又焉爱兮旦夕。[3](P509)
这是一首骚体诗,共六章三段,两章为一韵。前两章为第一段,表明其有幸贵为皇后,自尊自爱,无愧于宗庙社稷,三四章第二段写自己正待有所作为却含冤受屈,无处辩白。五六章末段写儿女左右之哀伤,但却爱莫能助。全诗结构工整、层次井然,语言慷慨刚烈、悲愤率真,为我们再现了一个自律自爱、自尊自贵、自明自悔、敢怨敢恨、无畏无愧的皇后形象。
祝注先先生曾在《辽代契丹族的诗人和诗作》一文中这样评价萧观音的文学作品:“代表了辽代诗坛的一个高峰。”[5]通过以上分析,从《焚椒录》中所载的萧观音的传世作品来看,此赞诚确不虚。萧观音的文学作品虽数量不多,但体裁各异,题材丰富,技巧娴熟,艺术风格也不拘一格,既有阳刚之美,又含幽怨之柔,集豪迈与婉约于一身,展现了北方少数民族女作家所特有的艺术情怀。可以说,萧观音的诗词作品是辽代诗坛的一面旗帜,代表了辽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其文学造诣可与蔡文姬、李清照等人媲美,亦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一道亮丽风景。
[1]〔元〕脱脱,等撰.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吕富华.《焚椒录》的史料价值探析[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3]王鼎.焚椒录[A].续修四库全书(第042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李正民.萧观音与王鼎《焚椒录》[J].民族文学研究,1998,(3).
[5]祝注先.辽代契丹族的诗人和诗作[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