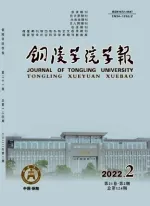GVC下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自主创新战略研究现状与趋势
刘江雪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 蚌埠 233030)
自从价值链理论形成以来,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就层出不穷,其中关于价值链治理和产业集群治理便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全球价值链是一个跨国界企业组成的组织,也是一个连接各种活动的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上,从事活动的企业可以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事的活动可以是原料的采集,产品的生产也可以是产成品的销售和服务(UNIDO,2002)[1]。产业集群顾名思义是产业集合形成的群体,具体来说是指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的企业和机构由于彼此之间的联系而集中在某一区域内,集群里包含一些相关产业和其他实体,它们共享一个竞争环境(Michael E.Porter,1998)[2]。在全球价值链下产业集群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集群的升级,尤其是对中国来说,产业集群的升级更为重要。因为,长久以来中国依靠的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较低的加工制造环节上。虽然根据比较成本优势和H-O理论,我国通过国际贸易能够取得收入的增长和国民福利的提高,但长此以往下去,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人口红利”的消失,加之存在于中国产业集群中的那种“路径依赖”和“低端锁定”效应,如果我国不能开拓除劳动力之外的其他适应当今世界需求的高级生产要素,并打破对先进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以便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上被锁定的低端位置,那么将会使我国失去集群的比较优势继而失去竞争优势。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只有自主创新才是推动一国持久发展的动力。因此,对全球价值链下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章拟综述全球价值链下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的研究动态,并分析其研究趋势。
一、全球价值链下产业集群自主创新动力研究现状
自主创新是中国特有的提法,它源自于技术创新理论,与技术创新相比它更加强调创新的自主性。以阿罗、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资本的增长率和技术创新。Cantwell(1989)[3]和Florida(1997)[4]的相关研究显示,一个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越强,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数量就越多。Branstetter(2006)[5]使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日式企业更多地是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学习继而吸收美国的知识和先进技术。Drukker是非常重视组织创新能力的学者之一,强调在多变的环境中企业唯有创新才能生存,在当今时代,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创新出新产品的能力对绩效是非常重要的。Humphrey and Schmitz(2002)[6]指出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虽然在一些环节取得了进步,但是在研发、营销和品牌等核心环节却落后于发达国家,不能很好地进行功能升级和部门升级。Bair等(2006)[7]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出口导向活动都能促进制造业升级,而只有存在于区域内部并且对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的出口活动才能起到提升产业升级的作用。
国内学者对自主创新动力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国特定环境进行的。陈朝晖(2008)[8]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动力来源于与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治理关系上的竞争。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实质上是全球价值链治理关系博弈,而这种博弈的结果就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学习与创新能力。卢宁、李国平、刘光岭(2010)[9]用1998-2007年自主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且自主创新在支撑发展能力、辐射能力和自网络能力上对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陈继勇、雷欣、黄开琢(2010)[10]为了对自主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交互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首先采取多维指标衡量来评估自主创新能力,然后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发现自主创新对FDI有积极影响,说明外商进行投资方向选择的时候,自主创新能力的强弱是他们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罗勇、曹丽莉(2008)[11]认为创新如同是国家的发展动力一样,也是集群发展的动力,一个集群要想永久生存下去必须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只有通过创新才能改变我国在GVC上的位置——从中间向左边移动,才能实现集群的创新升级。朱瑞博(2011)[12]总结国内外经验,发现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因为跨国公司早已在世界市场上构建了强备的防护措施,抵制其它企业进入利润较高的环节,一般企业若没有在创新上具有实力,是很难突破这些抵制措施,成功开辟自己的更高位置。
二、全球价值链下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自主创新优势研究现状
波特在其关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框架中指出企业因价值链功能而形成的产业集群网络中产生的创新知识、及其流通与增值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来源。Micheal E.Porter(1998)[13]认为集群的优势是:集群企业具有更高的敏感度,比一般企业更能发现客户的需求,更能开发出一些符合客户需求的经营和送货方式,同时集群更能感受新的市场机会。因为产业集群在资源、成本、专业化和区位营销方面都具有竞争优势。Asheim,Isaksen(1997)[14]指出产业集群有利于企业进行创新合作,有利于创新知识和技术在集群企业和机构间传播和扩散。Feldman(1994)[15]认为知识有编码化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前者可以由通信技术实现传递和交流,后者只有通过面对面地交流才能获得。而进行创新需要大量隐性知识,因此如果创新主体在地里上接近这些隐性知识,那么创新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Camagni(1991)[16]指出企业网络对集群发展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对集群的创新活动有重要作用,因为企业网络能促进企业之间集体学习机制的建立。Cookeetal(2000)[17]从知识移动的角度阐述了产业集群能为知识扩散和技术创新提供途径。
李大为,刘英基,杜传忠(2011)[18]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优势,即有效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长期、稳定的技术创新协作机制;企业技术创新的低成本;有效的隐性知识学习和传递的途径;有效的技术扩散渠道。郑胜利(2004)[19]他们认为,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不仅相互学习,而且彼此也有竞争,这种竞争会促使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加快创新步伐,拓展新的业务。魏江(2003)[20]认为产业集群可以划分为三层网络:核心网络、辅助网络和外围网络。这三层网络有如企业等创新主体,有如行业协会等服务机构,有如政府等监督机构,这三层网络相互作用构成了强大的集群创新系统。张平(2006)[21]指出地里上相互接近的集群企业在新知识、新观念和新技术地传播与扩散上具有优势,并且这些企业能很好地享受到知识外溢带来的好处。陈旭(2005)[22]分析了产业集群内技术创新扩散的特征及创新扩散的动态过程,得出产业集群内并非每个企业都有能力和条件进行技术创新,即使有创新,这类企业的创新对经济的影响大都是通过创新扩散来实现的。
三、全球价值链下产业集群自主创新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创新因素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Nelson,Winter(1982)[23]发现创新具有公共品属性,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创新者不能得到创新活动的全部收益。Nadiri(1993)[24]也有相关的经验结论:R&D私人回报率大于社会收益率,知识一旦创造出来,几乎都能免费使用,这对“搭便车”行为产生了强烈激励,因而政府干预也是必要的。Griffith等(2000)[25]用1974-1990年12个OECD国家的工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国内研发投入对创新的作用如同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一样,可以加快创新进行的速度,加快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瑞典地理经济学家阿歇(Asheim,2003)[26]说在一个集群内有没有公共的技术创新服务组织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是不同的。Arvanitiset.al(2009)[27]认为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等机构的合作程度对它的创新有正向作用;同时Antonioet.al(2010)[28]研究香港制造业时指出企业应与供应商和客户建立紧密的交流渠道,因为他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对产品创新与绩效有正向作用。Kaasa(2009)[29]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企业通过非贸易形式建立起的一系列关系有利于企业的创新。
国内关于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则具有广泛性。范红忠(2007)[30]认为市场需求规模的增加,在短期内能提高技术创新的预期收益,对一国技术创新有需求拉动效应;在长期则能影响市场结构,改善创新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的微观创新环境,从而对技术创新有供给推动效应。刘穷志(2007)[31]研究了公共支出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发现公共支出能有效地促进自主创新,并且存在一个激励自主创新的公共支出最优规模。王珺,岳芳敏(2009)[32]以南海西樵纺织专业镇的技术创新过程为例,考察了技术创新如何从技术服务组织向企业内部转化的过程,从理论上解释了在一个缺乏创新动机与能力的中小企业集群中,技术创新活动可以通过技术服务组织的有效扶持得以发生。韵江,刘立(2006)[33]用中国路明集团自主创新战略的成功案例分析了在中国这个特定环境下企业家远见与创新精神、历史压力与随机事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企业家远见与创新精神对于企业创新战略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历史压力与随机事件在偶然性意义上会导致企业创新出现“锁定”或“突破”现象。姜卫韬(2012)[34]从企业家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指出人际关系也是一种创新资源。企业家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够融合各种社会资源,不断创新,从而获取盈利机会的能力。张杰,刘志彪(2008)[35]指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或执行机制的缺位是我国地方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重要原因,因为它们的缺位“扭曲”地激励了地方产业集群,使它们忽视自身创新发展的重要性,而选择以代工或贴牌的出口方式参与全球商品价值链。刘炜,李郇,欧俏珊(2013)[36]采用问卷调查分析、案例分析和话语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考察了顺德家电产业集群的非正式联系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企业衍生的非正式联系、人才流动的非正式联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技术信息与知识的传递,而长期合作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非正式联系主要体现在使企业之间产生了一种技术上的共同理解和认识,能够提高企业之间技术合作的成功率。
四、全球价值链下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路径研究现状
在GVC理论基础之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方面研究了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路径。Hobday(2002)[37]针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电子产业的发展情况,研究发现这些企业在早起大都从事的是组装加工或组装活动,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模仿和吸收,最后通过技术创新构建了自己的品牌的,实现了企业质的跨越。Lee&Lim(2001)[38]认为韩国主要是通过跟随追赶、跳跃式追赶和创造新的技术这三种路径实现自主创新的。Pawan Sikka研究了印度企业自主研发的状况,认为企业应该和国家的一些研发机构建立紧密联系。因为尽管创新活动的国际化程度在不断增加,但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毛蕴诗、汪建成(2006)[39]提出基于产品升级的自主创新路径:替代跨国公司产品的产品升级、利用行业边界模糊的产品升级、适应国际产业转移的产品升级、针对行业标准变化的产品升级、加快模仿创新过程的产品升级。于开乐和王铁民(2008)[40]以南汽并购罗浮为例较深入地探讨了“开放式创新”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发现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企业自主创新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但要求被并购方知识积累大于并购方或与并购方知识积累形成互补;并购方有能力整合来自被并购方的创意,使外部创意内化为以开发新产品为特征的内生创新力量。
肖高与刘景江(2007)[41]运用企业创新理论、能力理论和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一个先进制造企业万向集团的深度案例分析,提炼出先进制造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三个关键途径,分别为:执行有效的战略领导;塑造有利于创新的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建设和完善以企业技术为核心、产学研有机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陈劲、王方瑞(2007)[42]根据创新演化理论和其他相关理论,并结合传统“熊皮特创新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针对像中国这样的技术后发国家的自主创新模式,即“拓展性破坏模式”和“突破性强化模式”。李大为,刘英基,杜传(2011)[43]认为产业集群实现技术创新包含四个阶段,即创新网络孕育阶段、创新网络形成阶段、创新大量涌现阶段和创新提升了产业集群的发展创新能力这四个阶段。张杰、刘志彪等(2007)[44]研究认为改变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创新能力缺失的关键是:解决产业集群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而解决此问题就需要改变集群内企业分工的横向依赖,进而改变集群内的分工状态,代之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纵向分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利益分配的方式继而解决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罗勇、曹丽莉(2008)[45]也提出产业集群实现自主创新应以核心企业为主导,建立这种“中卫型”的产业集群,并且开展供应链上的合作是解决创新动力的一条有效途径。
总结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第一,动因方面。国内外学者关于自主创新动力的解释大体相同,主要包括:自主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自主创新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自主创新是实现产业集群升级,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从低端环节向高端转移的关键。但中国的研究主要出发点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不利地位,打破发达国家的垄断跨国公司对我国的“低端锁定”,改变我国长期以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全球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方式,并形成一批有实力的本国跨国公司,从而发展我国的国家竞争优势。
第二,影响因素方面。国外学者主要根据创新的公共物品属探讨了政府在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加大政府的指导和调节,以及建立公共技术服务组织的重要性。同时还研究了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及产业集群内部企业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等都对自主创新有影响。我国对影响自主创新因素的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产业集群外部和产业集群内部。产业集群外部的因素有市场需求的作用,政府公共支出的投入,技术服务组织或中介机构的扶持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产业集群内部的因素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及集群内企业间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
第三,发展模式或路径。国外学者关于自主创新提升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模仿-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即通过早期为国际领先企业从事组装、加工,然后模仿、消化吸收,最后在前两步积累的情况下发展到实现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的建设,这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的角度的。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了构建国家创新系统的方式。国内的研究则相当广泛。有基于产品升级的自主创新路径,开放式创新路径,构建核心企业主导的创新路径等。
五、全球价值链下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研究趋势
综合GVC下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研究的现状,发现关于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的研究较多,尤其是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创新研究,但关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的研究则较少,这就给后来的学者提供了研究空间。研究趋势主要表现在:
(一)创新主体由企业到产业集群的转移
熊彼特开创了对创新的研究,起先学者是从企业内部对创新进行研究,认为创新就是企业自身内部的这样一个过程,即“发明-开发-中式-生产-销售”的过程。后来相继发现了很多外部因素也对创新产生影响,继而导致了创新研究“网络范式”的兴起。关于创新网络的研究最初是从国家角度开始的,但后来发现国家的创新系统更多地表现在区域的层面,这样就和产业集群紧密相关了,因此创新的研究也就由企业个体转移到了产业集群身上。
(二)高新技术产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递进
欧美国家更多地关于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的研究,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这可能与它们的国情有关,技术密集型产业是它们的主导产业也是优势产业,它们的重点当然是这类产业。但中国的国情使我们不能照搬它们的研究模式,而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际从事研究活动。当前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优势产业也是劣势产业,它占据着我国产业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对于它更好更快发展的研究就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即能弥补理论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自主创新研究的空白,又能为我国的产业发展提供指导建议。
(三)研究方法的综合广泛运用
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的研究综合了管理学,经济学等相关知识,方法也容纳了理论分析,数学建模和实证检验等。
[1]Michele Clara,Fabio Russo,Mukesh Gulati.Cluster Development andBDS Promotion:Union’s Experience in India[M].UNIDO,2000.
[2]Porter Michael E.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ofCompetition[M].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11-12.
[3]Cantwell.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Multi-national[M].Basil,Oxford,1989.119-144.
[4]R.Florida.The Globalization of R&D:Results of A survey of Foreign-affiliated R&D Laboratories in the USA[J].Research Policy,1997,(26):85-103.
[5]Branstetter.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Channel of Knowledge Spillover?Evidence from Japan’s FDI in the United States[J].Joural of Internaional Economics,2006,(68):325-344.
[6]Humphrey,J,Schmitz,H.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J].Regional Study,2002,36(9):1017-1027.
[7]Bair J,Peters,Dussel.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Endogenous Growth:Export Dynamism and Development in Mexico and Honduras[J].World Development,2006,34(2),203-221.
[8]陈朝晖.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集群创新成长战——以柳州汽车产业集群为例[J].亚太经济,2008,(2).
[9]卢宁,李国平,刘光岭.中国自主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8-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1):3-18.
[10]陈继勇,雷欣,黄开琢.知识溢出、自主创新能力与外商直接投资[J].管理世界,2010,(7):30-42.
[11]罗勇,曹丽莉.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思路[J].国际贸易问题,2008,(11):92-97.
[12]朱瑞博.核心技术链、核心产业链及其区域产业跃迁式升级路径[J].经济管理,2011,(4):43-53.
[13]Porter Michael E.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M].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11-12.
[14]Asheim,B,T. Isaksen A.Localised knowledge,Interactive Learning and Innovations:Between Regional Networks and Global Corporations[A].The Networked Firm in a Global Word.Small Firms in New Environments.Ashgate,Aldershot,1997:163-198.
[15]Feldman M.P.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Economics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1997,9(3):299-300.
[16]Camagni R.Local‘Milieu’, Uncertainty and Innovation Networks:Towards a New Dynamic Theory of EconomicSpace[M].in Camagni R.(Ed)Innovation Networks:Spatial Perspectives London:Belhaven Press,1991.121-142.
[17]Cooke P,Boekholt and Todtling F.The Governance of Innovation in Europe[A].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Competitives.Pinter,London and New York,2000.
[18]李大为,刘英基,杜传忠.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机理及实现路径[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32(1):98-103.
[19]郑胜利,周丽群,朱有国.论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J].当代经济研究,2004,(3):32-36.
[20]魏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与技术学习[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1]张平.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理论研究述评[J].科学管理研究,2006,(1):68-71.
[22]陈旭.基于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扩散研究[J].管理学报,2005,2(3):333-336.
[23]Nelson,Richard R.and Winter,Sidney G.The Schumpetirian Tradeoff Revisited[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2,72(1),114-132.
[24]Nadiri,M1 Ishaq,1993,Innovationsand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Working Paper44231 Cambridge[R].M A: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August1.
[25]R.Griffith,S.Redding and J.Van Reenen,Mapping Two Faces of R&D:Productivity Growthin aPanel of OECD Industries.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J].2000,86(4):883-895.
[26]Asheim Bjorn.T,Isaksen Arne,Nauwelaers Claire andTodtling Franz(ed),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y for Small-Medium Enterprises[M].Edward Elgar Cheltenham,UK,2003.
[27]Arvanitis,Spyros,Woerter and Martin.Firms’transfer strategies with universitiesand therelationshipwithfirms’innovationperformance[J].Industrial&CorporateChange,2009,18(6):1067-1106.
[28]Antonio K.W.Lau,Esther Tang,and Richard C.M.Yam.Effects of Supplier andCustomer Integration on Product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Empirical Evidence inHong Kong Manufacturers[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0,27(5):761–777.
[29]Kaasa A.Effect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socialcapital on innovative activity:Evidence from Europe at the regional level[J].Technovation,2009,29(3):218-233.
[30]范红忠.有效需求规模假说、研发投入与国家自主创新能力[J].经济研究,2007,(3):33-44.
[31]刘穷志.激励自主创新:公共支出效应与最优规模[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3):81-90.
[32]王珺,岳芳敏.技术服务组织与集群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J].管理世界,2009,(6):72-80.
[33]韵江,刘立.创新变迁与能力演化:企业自主创新战略[J].管理世界,2006,(12):115-130.
[34]姜卫韬.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策略研究——基于企业家社会资本的视[J].中国工业经济,2012,(6):107-119.
[35]张杰,刘志彪.制度约束、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J].当代财经,2008,(9):84-91.
[36]刘炜,李郇,欧俏珊.产业集群的非正式联系及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J].地理研究,2013,(32):518-530.
[37]Hobday M.The Electronics Industries of The Asia-Pacific:Exploit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J].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2002,15(1):13-29.
[38]Lee,Keun and Lim,Chaisung.Technological regimes,catching-up and leapfrogging findings from Koreanindustries[J].Research Policy,2001,(30):459-483.
[39]毛蕴诗,汪建成.基于产品升级的自主创新路径研究[J].管理世界,2006,(5):14-20.
[40]于开乐,王铁民.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南汽并购罗孚经验及一般启示[J].管理世界,2008,(4):50-59.
[41]肖高,刘景江.先进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关键途径与案例分析[J].科研管理,2007,(8):13-17.
[42]陈劲,王方瑞.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路径模式探讨[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29(3):49-57.
[43]李大为,刘英基,杜传忠.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机理及实现路径[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32(1):98-103.
[44]张杰,刘志彪.制度约束、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J].当代财经,2008,(9).
[45]罗勇,曹丽莉.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思路[J].国际贸易问题,2008,(11):9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