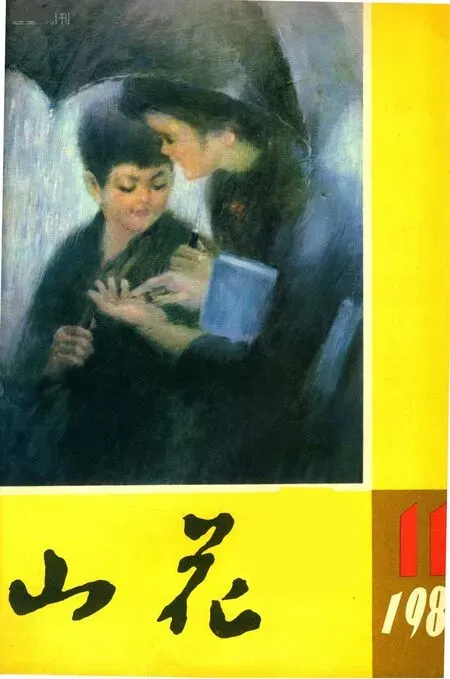时间的力场——从时间主题看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
巴赫金在谈到小说的时间形式时说过:“文学把握现实的历史时间与空间,把握展现在时空中的现实的历史的人——这个过程是十分复杂,若断若续的。”在这部小说中哈里托诺夫将两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线打乱,掰碎,混杂,密布在细节的铺陈中隐约若现,作者有意运用其独特的艺术手法给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制造重重障碍,而探究小说的时间主题无疑是越过作者设置的陷阱,进行文本解读最基础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碎片化与交织混杂的时间
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师范学院的讲师利扎温70年代撰写一篇论述20年代同乡作家的副博士论文,其中他最感兴趣的是作家波格丹诺夫。几经周折利扎温发现波格丹诺夫的真名叫米拉舍维奇,在州档案馆里去找材料时,利扎温误打误撞闯进了一间堆放杂物的屋子,意外发现了一只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里面堆满了他的手稿——红红绿绿的包糖纸。这些手稿是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笔,不同颜色的墨水在包糖纸上写的,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内容五花八门。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些糖纸上没有确切表明的日期,这些积累几十年的糖纸就像无数等待发掘的谜,谜底揭示着米拉舍维奇和他生活的点点滴滴,生活被凝聚,定格于一片一片包糖纸的碎片上,混杂在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里。连贯的生活情节被视为是怯懦的人的一种狡猾的手段,生活被认为实质上只是一堆片段,任何关联性都被视为是无意义的。伟大的孤独和全部的瞬间将看起来无重大意义的细节扩大,使一切获得了史诗般的伟大。零碎的细节才是生活唯一可以呈现的方案。文本中呈现出瞬间即是永恒的观念,一片一片的糖纸是对外在表象的联系的消解,碎片才呈现时代的印象,才是一点一滴的真实。填满时间的生命的物质创造时间的长河,对于心灵和记忆来说,永恒和瞬间无法区分,一切同时存在其中,有条有理的感觉由于与地面的相撞而破碎了,以后再也不可能重复一次。
正如糖纸所呈现的一样:这里记录的是一种思考和接受世界的方法,可能与职业上的习惯密切相关,这里积淀的和不由自主地改变样子的是日常生活中一粒细小的灰尘,米拉舍维奇用它来测量时代的丰富内容,它从内部更合乎他的心意,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纲领性言论和大炮轰鸣更容易接近。结合在一起,这粒灰尘便可描绘出它所发生的或它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轮廓。作者在叙述利扎温在研究米拉舍维奇的糖纸的过程中,又将米拉舍维奇的生活经历与利扎温的生活穿插混杂其中。对于主人公利扎温,作者直到第三章中才透漏他在州师范学院代理副教授,作者将利扎温的生活与他研究的米拉舍维奇混杂交织在一起,利扎温的生活就是围绕着米拉舍维奇展开的,在夜以继日痴迷地分拣、整理、归类,琢磨解读糖纸的过程中也展现了自己的生活糖纸将各个人物的命运与生活连接起来,使我们不得不和主人公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到处都是糖纸。
循环性与重复的时间
虽然在文本中,时间生活都被定格在片段之中,但这些片段又不完全是纯粹孤立的,而是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或者说是某种意义上的重复与循环。博尔赫斯也曾感叹:“我常常永恒地回复到永恒的重复中去。”在文本中首先展现在米拉舍维奇的生活与其小说这个层面上。小说《命运线》以米拉舍维奇一篇怪诞的短篇小说《神启录》开篇,引出了趣味横生的命运。作者在其后的篇幅中转述了自己虚构的米拉舍维奇的小说中的故事。于是,在文本中虚构的小说的主人公与小说的主人公,以及两个人在生活上的经历构成了一种重复性。另一个方面,主人公对意外发现的米拉舍维奇的一堆写在糖果纸背面的手稿进行着不厌其烦的反复阅读,在阅读与梳理的过程中利扎温无意地重写着米拉舍维奇的生活与思想。糖纸上呈现出来的个人在生活中所感觉到的意义使这两个主人公找到了共同点,于是形成了许多重复循环。不仅如此,利扎温开始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到处都是糖纸,所有人的话都曾在糖纸上出现,现在的一切变成糖纸的重写、重演、重现,直到利扎温毫无自觉意识地写下任何地方都不注明日期的笔记,米拉舍维奇在利扎温那里得到了完整意义的复写。
在文本中,生活被定格在无数重复的情节、片段和意象中。利扎温屡次为买不需要的东西排队,仿佛只是为了再现米拉舍维奇糖果手稿中的“时间面前的犯罪现场”这一场景。在这里一切有意义的行动和行动本身的目的都被重复与循环消解了,排队不仅仅是一个行动,其本身更是这一行动的终极意义。重复排队,重复米拉舍维奇,甚至重复利扎温。那只在米拉舍维奇的小说中出现被人等待的神秘人的小箱子,那一只装满了米拉舍维奇糖果手稿的小箱子,那一只卓娅唯一随身携带的小箱子,那只使阿尼娅和那个萍水相逢的魅力姑娘一见如故的小箱子,在文本中,仿佛所有人的生活都紧紧和一只小箱子联系在一起,所有人的生活都被浓缩在一只小箱子里,里面汇聚了形形色色各种人的命运线。
此外,文本中还多次出现了钟。时间以钟的形式直接说话。但在作者笔下时间不再是常规意义的,无论是教研室和厕所的门上方挂着的从不准时的电钟,还是那只不需要指针的钟表,都是与常规的钟相去甚远的,钟不再具有度量时间的功能,在这里时间已经隐退了,或者说时间已经是不被需要的了。因此文本中才会不厌其烦地响起这样的感叹:“我们整个的生活——是一年四季,是儿童的旋转木马。”
巴赫金在谈到时间时曾有这样的说法:“时间首先是在自然界中显现出来的:太阳星辰的运转,公鸡啼鸣,一年四季可睹可感的特征;所有这一切与人的生命、日常生活、活动(劳动)中的相应因素,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不同紧张程度的循环时间。”在《命运线》中,哈里托诺夫恰恰给我们呈现了这种循环,生活成了无数瞬间周而复始的重现,这让我们想起了加缪重写过的《西西弗斯神话》。在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是科林斯王,死后降入地狱,宙斯罚他推一块巨石上山,刚到山顶巨石便滚落下去,如此周而复始……在加缪的笔下,西西弗斯成为一个具思想性与背负人类历史悲剧的悲剧英雄。周而复始不顾一切地推石头上山也被视为是英雄最壮烈的抗争与战斗。而在《命运线》中,这种周而复始的行动却是抗争与战斗转而成为生活的本真,成为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不再是英雄的行为,生活成了永无休止的重复,而重复本身就是全部意义。
不确定性与陌生化
时间在无限的反复与循环的进程当中也并不是顺理成章的,在文本中存在着叙述者逻辑的反悖和自我否定。两个主人公米拉舍维奇和利扎温在文本中也存在着对话。米拉舍维奇跳出来告诉利扎温说那样在那些糖纸上试着组合各种各样的情节不是徒劳的,但是利扎温从事的这项工作却又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因为那些糖纸上根本没有明确的日期,按这样的说法,利扎温在做着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却又不完全是徒劳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荒谬的悖论。在第九章中,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了利扎温那个与米拉舍维奇有关的笔记本的分析思考,最终却因为被认为笔迹很像是马克西姆的,而丧失了一切意义。在文本中或在利扎温的生活中,米拉舍维奇仿佛处处在场而与之相关的一切却又都是无迹可寻或者说全然无法理解的,代之而来的是文本中的矛盾。无论是作者笔下还是作者借米拉舍维奇表达出来的都是未知和不确定的,从而通过一种自我否定的悖论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作者在叙述过程当中有意给我们制造了阅读障碍,使我们在阅读时面临着利扎温在整理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里的糖果手稿和探究米拉舍维奇的生活时面对同样的困境:在无限循环的不确定中找寻根本就不存在的答案。简单的、线性的、明晰的、确定的逻辑已被打破,相似相关或者毫无关联的因素被堆置在一起,毫无逻辑地并置,使原本混乱无序的文本更加的毫无头绪。
同样的陷阱出现在安东·安德烈耶维奇利扎温副博士与另外一位副博士的对话中,两个人都同样被冠以副博士的称谓,角色化个体差异性在这里被作者有意模糊了,在另外一种虚拟的对话,即利扎温与米拉舍维奇的对话中,同样也是不确定的。我们甚至无法肯定是利扎温在与米拉舍维奇对话,或是利扎温幻想出来了米拉舍维奇与自己对话,抑或是利扎温幻想了自己与自己对话……是米拉舍维奇需要被另一个人了解,接受和倾听,所以有了利扎温和他的博士论文。还是利扎温为自己塑造出了米拉舍维奇这个事业和生活中的交谈者?正如糖纸上带着翅膀的小天使一样,没人能找到答案,也没有答案,只有一条若隐若现的虚线,但却无法找到明确的归属,一切都是悬而未决的。正如文本中在教研室的那只在某一时刻显得非常准时的电钟,某个准时的时刻只不过纯粹出于偶然,因为它根本不走。确定性根本不存在,暗示和隐语也变得没有意义,因为随时随地都可能变卦。
作者的叙述艺术使整个文本和其中的人物出来的时候都给人一种第一次出场的错觉。正如利扎温在离开他熟悉的涅柴斯克一段不长的时间,重新回来时的感觉,文中作者从小习惯的小城因为离开一段时间而变得陌生,难以适应了,甚至连自己的房子都找不到以至于会敲错别家的房门。在文本中,哈里托诺夫不仅仅是通过上述的不确定性和矛盾反悖给人以陌生化的效果,叙述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小说以多条线索打碎混合相互交叉的叙述手法,本身就增加了读者阅读的难度,延长了审美感受的长度,从而达到了较强的陌生化的效果。
结 语
正如赵丹在《多重的写作与解读》中分析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时所说:“《命运线》就是名副其实的迷宫。迷宫结构的设置制造了一个意义无限开放的文本,扩大了小说的能指空间。”但“迷宫”一说并不能涵盖这部小说的谕旨所在,也不能揭示作者笔下“命运线”的真正含义。迷宫显然是这部小说所呈现出来文本结构最为简洁精准的概括,也是读完小说最深切的感受,但是迷宫却不是小说的真正含义,哈里托诺夫为我们设置了这样一个迷宫,并不仅仅是一场文字游戏,作者通过游戏,通过迷宫的设置给我们传达了对于生活的哲学思考。在作者笔下通过小说中的主人公传达出来的思考变成了生命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存在方式,世界变成一组被捣碎,排斥在永恒之外的永恒瞬间,在破碎的世界中,一切关联都是虚无的、表象的。每个个体都被认为是独立存在而又等位的。没有先后,不分高低,是自由而又平等的。这才是物质及生命应该的存在方式,才是生活的原生态。正如开篇我们所引用的小说中的话一样:“时间的力场,命运线。”我想这才是哈里托诺夫在这部小说中讨论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时间。所以才会被称为是“瞬间的汇集”。
[1]刁绍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词典[M].北方出版社,2000.
[2]阿格诺索夫.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巴赫金.小说理论[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M].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
[5]赵丹.多重的写作与解读[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