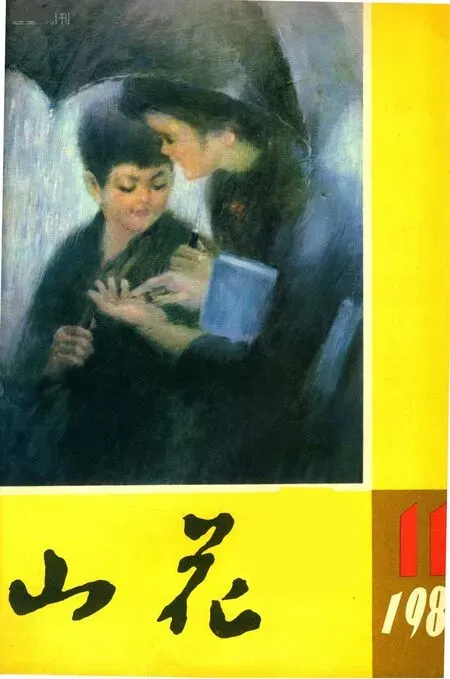语词的高蹈,抑或血肉的传奇——陈陟云诗歌读札
一
一生的足迹,要历经多少道路
才能抵达一片雪域?
一生的道路,要穿越多少歧途
才能在雪域中停止?
每一首诗都是诗人对人生的一次特定的造访,也是诗人与词语的一场难忘的邂逅。当一群语词在一首诗的篇章之中会聚在一起,便将奏响一曲情绪的和弦,便将展开一段别有意味的生命叙说。
《雪域》自一开始就设定了情感倾诉的高调。“把纯净的蔚蓝作为唯一的背景/雪域,总高于我们的仰望”,在这里,“雪域”与其说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不如说是一种精神性的符号,它规划着我们的思想图式,也提示着我们的精神视野。“雪域”是以纯净的蔚蓝为生存背景的,“雪域”的存在是一种理想化的存在,它似乎无法被我们的现实目光所轻易触摸,因而它总是“高于我们的仰望”。
由于“雪域”始终远离俗世的生存而独在,因此,“一个酷暑的下午,当我写下‘雪域'/墨迹和笔画寒光直逼/我陡然青丝白尽/眺望窗外,天空宁静,目光高远”,这样的描述便显得真实可信。“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命形式”(维特根斯坦),有时候,一个语词或许就代表着一个家园,也代表着一种生命形式,例如这“雪域”,诗人确乎将其视为一种高洁的生命形式,一种理想的存在家园——当它在诗人笔下出现,带来的是逼人的寒光和令人心神动荡的震撼力,便可想而知了。
“雪域”出现了,它带给诗人的是无边的宁静和沉寂,是杂念滤尽后的纯净。“我余生的影子,像一朵孤单的云/在雪地上逆光而行/闪亮的疼痛,消弭于马粪的余温/一所精致的木质房子,是最后结痂的疤痕”,“雪域”的现身,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它让“我”逆光而行,终成为强大的主体;它让我终老于“一所精致的木质房子”,生命得以返璞归真。“安居时刻,我眺望窗外/宁静的天空更加宁静/高远的目光更加高远”,“雪域”的出现,提升了“我”生命的境界。
每一首诗都是一次语词的高蹈,每一首诗也是一次血肉的传奇。当诗人面对“雪域”展开意义的追问和生命的寻思,我们不禁为那内心秩序的生长而肃然起敬。
二
青山不老。每年的清明,生死只一土之隔
叙述不在倾听之内,遗忘却在记忆之中
死亡之上,生命代代相传
一切生命都是面向死亡的存在,死亡是生命的一种常态,而活着,不过是生命的一种暂时的形式。相比青山大川的永在,人的生命不过如转瞬即逝的流云,随生随灭。基于此,有关生死的思考与喟叹,会始终萦绕在人们脑际,并充斥于古今中外的诗章之中。
《青山不老》也是直面生死、咀嚼存在之作。诗人以清明节为特定的时间节点,在祭奠亲人、追忆过往的仪式之中,考量生与死的内在涵义。“每年清明,是青山突起的喉结”,“喉结”这一喻体的现身,将清明所具有的生命诉说特性鲜明彰显。随后“欲言又止的哀伤”,“见证”等语词,又将清明时节生者与死者遭逢时的复杂情绪敞现出来。
“走在山中,如走在祖先坟前的一片叶子上”,诗的第二节,是对山中祭奠先人的铺叙。虽说是铺叙,但诗人并不倚重叙事笔法,而是依靠虚实相间的抒情辞章来言明。“他细数着经年雨水的痕迹”,“雨水”是一种来有影去无踪的存在,它何言“痕迹”呢?显而易见,这里的雨水,并非自然世界的真实写生,而是内心情绪的隐喻托化,“经年雨水”即曰“多年的思亲之情”。“山岚已飘十里/他收于袖口,把一生的重量担在肩上”,这是诗人所具有的中年情结的形象暗示,人到中年,责任在肩,扶着老人的佝偻,携着孩儿的踉跄,执着而勇毅地向前,这是生命之曲的最高音,也是由死亡的暗影而激发出的最浓烈的生活热情。
“叶脉的光晕,在雨滴中悬浮/擦亮骨肉深处的沧桑”,“沧桑”之云,意在呈显生命历程的久远和人生阅历的丰足,也许只有意识到人进中年之后,内心深处才会生出“沧桑”之感,这是饱经风霜的岁月“擦亮”人生的自然结果。“流水响动之处,一群少年的身影/抖如蝉翼,他们的回眸,仓促而足够悠长”,“少年”这一群体的出现,从另一角度提醒着“他”的中年身份,少年回眸的“仓促而足够悠长”,将少年记忆的特征和人生意义挑明,同时也与他的“沧桑”心境构成一种对话性关系,“少年”、“中年”与“祖先”在清明的山中聚首,回应了前述“一代代人”的代际刻画,又引领后面的“生命代代相传”之语。
生与死的距离,其实只在咫尺之间,“生死只一土之隔”,但生与死的差异又有着天壤之别,当人们将生命与死亡相提并论的时候,内心深处激起的情感波澜又是如此的壮阔跌宕,潮汐不平。“叙述不在倾听之内,遗忘却在记忆之中”,这写出了诗人有关生死沉吟的独特人生感悟,“叙述”和“倾听”的不同步,“遗忘”与“记忆”的相反相成,精彩描绘了生死考量中的超常化人生情态。这样的生命领悟里,无疑沉淀着丰厚的中年经验。
《青山不老》是中年心曲的艺术演绎,是站在中年的时间视点上对整个人生历程的全方位考量,也是不乏深意的有关生存与死亡的辩证之思。
三
今夜,躲进一个词里
在那里孤独,失眠,无端地想一些心事
在那里观照事物,获取过程
诗歌是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奇迹般降生的,语言的世界筹划了诗的世界。在诗歌的冥想世界里,一种情绪,一幕意境,甚至一个词,都将成为诗人思想的驻扎点,或者情感的栖息地,沿着词语的流向,诗歌的意趣和情怀默默酝酿而出,散逸开来。
正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习惯在夜里写作的陈陟云,此刻恰为一个词所眷顾,所有的心意和思绪都被这个词语所裹挟。“躲进一个词”,此间的“躲”别有意味,不知是诗人躲进了词语的衣胞,还是词语躲进了诗人的心怀,总之有一种庄生梦蝶的禅味氤氲其间。词是世界的符号化显现,“躲进一个词”也就意味着躲进了一个符号化的世界之中,也就获得了超逸物质世界的开放性和自由度,由此,“无端地想一些心事”,从独特的视镜上“观照事物,获得过程”,就有了极为切实的保障。
接下来,诗人要向我们展示躲进词语之中展开想象羽翼自由翱翔的精妙情形。躲在词语中想象世界,其实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重构现实人生,由此展开的想象,必然是超规逾矩、天马行空、匪夷所思的。“把鞋子穿在月亮上,让路途澄澈、透明/对应体内深切的黑暗”,这宣示的是向宇宙“借光”来驱除体内黑暗的伟大梦想;“把发音变成鸟语,牙齿便长出翅膀/咬一溪流水,噬两畔花香”,这表达的是向自然索取灵性来升华人生的内在渴求。如果说这样的想象还不够出格的话,那么诗人将继续带领你向更深远的冥想处进发,“如若意犹未尽”,这是对读者的阅读召唤,也是对自我想象力的进一步开掘,在这样的开掘之下,便有了“把眼睛守望成露珠/映照草尖上的另一颗/这苦痛的附加之物,瞬间被纯净照亮/光晕拖曳生命的本质/抵达无人可及的混沌深处”这样神奇的描述。眼睛化为露珠,被纯净照亮的目光,目睹了生命的本质,这样的想象与陈述,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奇特的想象既是一次语词的高蹈,也言说着某种传奇的人生。在上述令人惊叹的想象纷纷出笼之后,这首诗的最后几行,诗人向我们展示的想象性情境,更显得离经叛道。“或者,干脆把皮囊脱成一袭黑衣/脱去一生的长吁短叹/骨骼也是一个词,从语言遮蔽的背面/进入另一个词/在那里打坐,面壁,坚守”,“皮囊”是一个词,它可以像一袭黑衣般被脱下,皮囊褪去后留剩的“骨骼”也是一个词,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躲避场所,“在那里打坐,面壁,坚守”,或许别有一番天地。不言而喻,《躲进一个词》通篇显示着想象的超常与奇崛,进而绘制出别样的生存图景。
四
没有人会用痛苦去打扫一次心灵
没有人甘于安然而没有焦虑
街道通向墙壁
语言触碰沉默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时光总是如白驹过隙,箭也似地飞逝着。每到岁末之期,人们就会回首一年的历程,反思生活的得失,对人生作一次细致的清点。自然,岁末的清点所具有的意义是有限的,它既不能挽回曾经的过失,也无法阻止时光的继续飞逝。
《岁末》言述的正是这个独特的时间节点上,诗人内心深处的斑驳痕迹。在一年将尽的岁末里,“清点”成为了一个有强烈生命意识的主体迫切的现实行动,然而,“事物却纠缠着消失”,这无疑增加了“清点”的难度,此种情形下,“一个人走在风里,停下/茫然无措,焦头烂额”,很可能成为我们见惯的精神情态。这种精神情态的背后,掩藏不住的心理动因是什么呢?或许正是诗人所云:“没有人会用痛苦去打扫一次心灵/没有人甘于安然而没有焦虑”,曾经的时光徒自荒废,反刍岁月必定会泛起苦涩的记忆,回顾过往怎么可能会心安理得?“语言触碰沉默”,在这无言之言的诉说之中,多少杂陈的生命滋味将会泛溢而出。
岁末是旧的一年与新的一年的接洽之处,走过岁末的感觉是怎样的呢?诗人选择了“门”这样的喻体来说明。“仿佛一扇门已被关上,另一扇还未打开”,一扇门关上,曾经的岁月悄然封存;另一扇门尚未开启,即将带来的时光携带着多少神秘的气息。在诗中,“门”的比喻无疑是巧妙的,具有极为突出的表意效果,这种将时间空间化的修辞策略,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岁末”所带给人的强烈的时间意味。在旧岁已去、新岁将至的时间关口,诗人的内心并不是那样的惊慌失措,六神无主,而是在短暂的“焦虑”之后,复归于冷静和理性。“寂静来得多么及时,豁然何其美丽!”在赞叹之中,诗人迅速找回了自我,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举手,敲门/我将放弃伴随多年的行囊,和背影/让灵魂孑然一身”,放下包裹,轻装上路,用孑然独在的灵魂,迎接迅疾而来的新的岁月。这样的生命态度,是积极的,有主见的,因而值得人们赞许。
陈陟云对于时间的体悟总是独到的,他的一些诗句,如“一生何其短暂/一日何其漫长”(《梦呓》),“寻找桃花源只能逆流而上/有人耗尽一生的漫长,只为一次等待/有人只为瞬间的灿烂,不惜焚毁一生”(《暗恋桃花源》)等,都闪烁着耀眼的时间哲学之光,让人过目难忘。在《岁末》一诗的结尾,诗人写道:“年年岁末,你永远清点不了什么/该结束的终究结束/当开始的必然开始”,这是从新的角度对时间进行的深刻审视,既显示着面对现实的坦然与豁达,也体现出迎候未来的理智与信心。
“岁末”是一个表述时间的典型词汇,“岁末”又是言说人生的重要术语。在“岁末”的写照中,我们再次聆听到词语与人生的和鸣。
五
这些天,我一直在努力模拟一只瓶子
撕去标签,倒扣
把自己彻底倒空
在寺院中参禅诵佛,燃香火以寄心愿,这是尘世中人祈祷佛家保佑、求祈平安康健的极为重要的仪式。在仪式的背后,多少人将如许极为迫切的现实期待投放其中,希翼立刻得到承诺和满足。因为愿望的表达过于直接,现实的利诱呼之欲出,寺院之中的念佛诵经之事,大都缺少了超越性的宗教情怀,更多的是出于祈求延年益寿、多福多财的功利目的。
《松赞林寺》也是对礼佛参禅活动的诗意描摹,不过诗人向我们揭示的却是这一仪式中的另一番情景。“黄昏,是松赞林寺闪耀的金色,和/金色一侧高低错落的阴影/寺门依然人群涌动/如经幡轻飘不绝”,首节描绘的寺院热闹景观,为我们习见,即便黄昏已至,松赞林寺依然“人群涌动”,这里极言了此处佛名远播,香火旺盛的情貌。在这潮涌的人流之中,如果诗人接着描述自己有幸成为其中一员,由此经历了繁盛的礼佛仪式,感受了佛家境界的高妙等,那就太没意思了。诗人显然意识到如此描述的平庸和无趣,在第二节里笔锋一转,绘制出另一种参佛的景观:“此来数日,不入寺门/仅住寺旁的松赞绿谷/寺内有人诵经,拜佛,行繁复的仪式/这厢我只休闲,放松,过简单的生活”。驱车千里,好不容易来到松赞林寺,却偏“不入寺门”,仅住寺旁,不去寺内“诵经,拜佛”,只在寺外“休闲,放松”,过简单生活,这是对俗套的礼佛仪式的婉拒,也是对佛家要义的新的理解和诠释。
正因为有意避离了俗套的礼佛仪式,诗人才睹见了常人难以见到的自然生趣,也体味到他人无法体味的心灵化境。“庭前,牛羊安静,时日安好/湖边,轻风无尘,水草无语”,牛羊、轻风、水草等,各自显露着自然的生命情趣,这是为那些拥挤在寺院中祈求福禄寿的人无法窥见到的景象;“晚来静坐山岗/左手抚一轮沉日/右手托暮色苍茫”,这是真正懂得佛家旨意的人才可能进入的生存境界。在自然的描画和心灵的写真中,浓郁的佛理和深隽的禅意从诗行中涓涓流淌而出。
最后两节,诗人揭开了自己为何不入寺门,只滞留寺外的谜底。以“瓶子倒扣”的喻象来呈显自我努力遣尽沉积于心的凡念杂思,这是富于形象性和表现力的。而倒空自己之后所形成的新的主体,可以承载“松赞林寺天空下的这一片虚空”,这又显示出某种捧手可掬的佛趣来。每一种宗教说到底都是一种话语系统,宗教仪式只是这个系统中极为浅表的话语形式,因此,仅仅是仪式的接受和履行,往往很难抵达宗教的真谛。如果能不受仪式的干扰,另创一套话语系统来对接宗教话语,在秘响旁通中更有可能叩开宗教的法门,参悟其中的玄机。
寺外参禅,心中纳佛,在人群罕至的孤寂之处,深切地领受禅的旨趣,这或许是接近佛家的正途。《松赞林寺》向我们传递的,正是这种具有宗教意味的人文信息。
六
从所有的道路上撤退,退回内心
蜕下的肉身
在流光逝去的尽头耸立
坚实,优雅,而清辉四溢
生命是一次远行,生命需要不断进发,需要奋进有为,这是我们熟知的一种旨在向前的入世哲学。不过,生命中还有一种后退哲学,一种以退为进的生存之道。有些时候,理性地后退比冒失地前进,或许更有可能找回本真的自我。
《撤退》写出的是“退回内心”后的生命境况,流露出某种超离尘俗的道家旨趣。“从所有的道路上撤退”,意味着放弃主动进发的前进哲学,意味着从奔突的动物性状态返归到宁静的植物性状态,由此,一个人顺理成章地变为“一棵沉默的树”,便在意料之中了。这棵移变而成的树,显示着与众不同的精神状态,“每片叶子都透着光的纯然/吐出疼的芬芳”,每一个生命毛孔里都渗透着纯净、宁谧、幽然,虽然这种撤退而成的生命物种,还留有阵痛的心灵烙印,但即便“疼”也不乏“疼”的芬芳。
在人生路途,撤退是一种删繁就简,撤退是一种返璞归真。诗人接着描摹了“撤退”之后的生命样态,“语词的景观,是一片原生的开阔地/有如忘川之畔的留白/在蝴蝶纷飞中敞开”,这告诉我们,返璞归真的人生,有着更多可以言说的空间,有着更为明净的诗意,值得我们驻足和流连。而撤退之后的个体,是那样的心无挂碍,无拘无束,“风吹澄明,桃瓣褪色/只有气息的轻盈,轻如飘絮/自在,忘然,无已”。
陈陟云的诗是经得起细读的,也就是说,他的诗歌词句精炼,表现力强,每一字句都不能轻易放过,都值得仔细剖析。某种意义上说,细读既是诗歌分析的重要方法,其实也是诗歌评价的基本标准,经典的诗歌都应该是经得起细读的,经不起细读的诗,其美学价值也许都是可疑的。如果说诗的第一节是以“植物”的喻体来近距离呈现退回内心的个体展示出的生命状态的话,第二节则远距离凝望其具有的精神风貌。“蜕下的肉身/在流光逝去的尽头耸立/坚实,优雅,而清辉四溢”,“坚实”、“优雅”、“清辉四溢”,真的是繁华落尽见真淳,这褪去一切伪装和粉饰的真的自我,多么清秀和迷人。
“撤退”是一个具有力量的词语,在人生之中,“撤退”又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意志的。《撤退》一诗既是“撤退”一词的生命演绎,也是“撤退”生命状况的语言学诠释。语词的高蹈与生命的传奇,在此又一次完美聚合。
七
我只习惯于安静,简单
当生命也成为身外之物
活着,已不是负担
我们的生命行为,很多都源自某种习惯,习惯构成我们处事待物的基本思维逻辑,习惯反射出我们饮食起居的某种通常规律。当习惯渐成自然,习惯也就被我们默认为习以为常的惯例,而得不到及时的反刍与回思。不过,当我们对已成自然的“习惯”加以仔细审视和细致咀嚼时,习惯便可能流露出特别的意味,散发出诗的光泽来。
陈陟云的《习惯》便是反思“习惯”之作。这首创作于夜半的诗歌作品,一开始就直奔主题,“已习惯于半夜醒来”,在半夜时分静坐窗前,反刍“半夜醒来”的“习惯”所显露的生命滋味,一定别有一番妙义。其实,从生理学角度看,“半夜醒来”的“习惯”,或许并不是什么好的习惯,因为这种习惯,打乱了自己的睡眠秩序,损耗了自己宝贵的休息时间,并不利于身体的缓冲和精神的补养,还可能影响次日的工作状态。不过,当这种习惯被诗人以特定的视镜来窥探时,它却显示出特别的情味。“掬一把微光,洗涤脸庞/把岁月的灰尘,弹给夜色/飞鸟不飞,流水不流/只想一些寻常事物,以及融化它们的/空气和雨滴”,这是诗人面对并不良好的习惯时泰然处之、举重若轻的生命情态的诗意素描。把岁月的灰尘“弹给夜色”,想一些平常而纯净的事物,这些都折射出内心的坦然与平静。
在半夜醒来,尽管于身体而言,此习惯并不值得称许,但对诗人而言,能发现普通人平素难以发现的自然景观和生命况味,也算是上苍给他的特别的补偿吧。在宁谧的午夜,诗人听到的是“偶尔一阵蛙鸣/触碰隐约的山峦”,诗人感觉到的是“偶尔一缕风/穿透内心的石头,带着清澈的冰凉”,这些细致的物象和情景,这些生动的外在洞察和内心体验,或许只有夜半独坐窗前的诗人才能切实领受。
在夜半时分沉思“半夜醒来”的“习惯”,诗人不止体察到常人难以体察的景观,还意外捕捉到生存的某种真意。“此刻,我只习惯于安静,简单/当生命也成为身外之物/活着,已不是负担”,在“习惯”中咀嚼“安静,简单”所具有的生活蕴意,诗人吐出了视生命为身外之物时,活着不再是一种沉重负担的肺腑之言。其意是说,当我们不对自己的生命人为地强加过多的承载时,生活就将变得简单和轻松了许多。
八
所谓桃花潭,想必是桃花开在潭里
所以,把灯点到潭水深处
所有的月色都会落到潭底
以古典意象为现代精神的寄发媒介,将现代人文信息撰入古典的诗歌意象之中,进而将传统与现代巧妙有机连通,以现代人生经验来重释传统审美意象,这应该说是现代诗歌寻找艺术增长点的有效路径。陈陟云的组诗《桃花传奇》,正是实施这种连通传统与现代策略的典型文本。
这组诗由四首构成。第一首《桃花潭》,将那个活在李白诗歌中的古典意象进行了重新阐发,释放出新的人文意蕴来。首节云桃花潭边取水,此时四周景物为月光笼罩,静寂的万物井然有序,此时恰是半夜,“寺钟敲了三下”。半夜三更之时,在桃花潭边取水,是想舀起一瓢月色,还是打捞无边的静谧?总而言之,“取水”这一事项的设计是别富深意的,借助对“取水”之事的写照,诗歌营造出一种迷人的意境来。
第二节采用古词新解的方式,赋予“桃花潭”新的意义。“所谓桃花潭,想必是桃花开在潭里”,这是诗人的大胆臆测,这样的臆测显然与词语本义相去甚远,但这样的臆测又因建立在诗歌“无理而妙”的美学原则上,因而是完全可能成立的。桃花潭的新意赋予,是为下文的进一步想象作铺垫的。既然桃花会开在潭里,那么“灯火”就可以点到潭水深处,“月色”也可能都会落到潭底。
其实,前边两节所有的写照,都是为着最后一节而充分蓄势的。最后一节唯有一句,“所有尘世间的爱,都会落到潭底”,由前述的自然描摹,转移到对人类生命情态的点化,显得轻巧而贴切。尘世间的爱会落入潭底,语意多重,既可说表明了尘世之爱终将逝去的意味,又可说强调了潭水集纳了世间的爱,所以显得情深意浓。
“桃花”是承载爱的语言符号,“桃花潭”是聚集爱的曼妙空间,诗歌由此流淌出汩汩不断的感人情味。
九
十里长溪,并无桃花
一路行走,桃花只开在他的内伤里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这是唐代诗人张旭创作的《桃花溪》一诗,“桃花尽日随流水”的写意,给人带来多少关于人生的唏嘘感慨。《桃花传说》组诗的第二首也名曰《桃花溪》,不过陈陟云显然不愿遵循古诗的意义轨辙,而是另辟蹊径,再创言路,从而写出新的生命境界来。
在十里长溪穿行,却未尝见一瓣桃花,这“桃花溪”的当下情形,已不是“桃花尽日随流水”所能简单形容了,只因为“桃花只开在他的内伤里”,他的生命中已深烙下捕获爱的印痕和失却爱的悲戚。曾经沧海难为水,十里长溪一路淌流的,或许只是他哀婉的故事。
第二节直接陈述他的现实状况。“风吹三月,从背囊里/清点年华和生涯,然后卸下/留下纸和笔,还有隐忍与爱/溪水漫过他的脚踝”,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不,是“桃花红”,因为这里是桃花溪。但他没有将热情倾注于桃花之上,而是将注意力放置在自我的清理和打点之中,回顾往昔,思忖爱的历程,一切都在内心沉淀下来,将自我沉淀得如此成熟,任溪水自由地漫过脚踝,任疼痛的往事随溪水流走,此番清点之后,便可以重新上路。
真的就可以让不堪的往事轻而易举地如水流逝吗?诗人告诉我们说,恐怕不容易。最后一节写曰:“俯下身去,是否还能找回/多年前遗下的那一串泪水?”暗示了面对过去的隐隐不舍。这样的交代,为呈显“桃花溪”的繁复情绪着上了有力的一笔。
十
你来了,以复述为舟
在陶氏的虚构里,缘溪而行
桃花盛开两岸
“桃花源”是陶渊明的首创,后由刘禹锡复写,其故事色调几经变幻,先是充满浪漫和传奇,后又显出波折和戏剧性,历史的烟尘,在“桃花源”上绣出阐说不尽的意味。
《桃花传奇》第三首《桃花源》,正是对这一历史故事的现代汉语重塑,是在历史的斑驳记忆中觅求现代性的人文影踪的形象演绎。组诗的第一首以“彼处”开端,显示出空间的旷远;第二首以“彼时”起笔,意在突出时间的悠久;第三首则以“此地”为首引词,这是有意将镜头拉近的叙述笔法,以便诱导读者将历史当成现实来品读,达到更大程度的感同身受。“此地无桃三万亩/春风不来,桃花不开”,“无桃”,“桃花不开”,桃花源何从谈起?“无桃”的交代是有双重意义的:当历史曾是一片空白,后来者创业无疑会充满艰辛;但历史还很贫瘠,又给后来人大胆开拓提供了极大机会。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刘郎”就是这样的开拓者。他以复述为舟,划开了一片汪洋。他沿着陶氏的思路,让“桃花盛开两岸”,将浪漫的理想转化为灿烂的现实。那桃花如此殷红,仿佛鲜血一般,此鲜血又是前世青袍“咳出的”,可以想见付出的艰苦与辛劳该有多么沉重。
“前世的源头,匿影无踪/谁若南阳刘郎,寻而病终?”历史已成过往,而今的“刘郎”何在?其实,进取创新,开拓前行,既是古典的士大夫情怀,又是现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历史为今天树立了楷模,今人如何向历史交代,《桃花源》一诗,在这里显出了可贵的意义。
十一
把血流遍岛上的每一寸土地
桃花便在每一寸土地上盛开
《桃花岛》是组诗《桃花传奇》的最后一首,也是其中想象最为奇崛的诗章。该诗以“一百年以后”为时间标记,将此后情景的描画设置为想象的产品,从而赋予其出人意外的奇幻色彩以充分的合法性。
“一百年以后,我要坐一朵桃花/到一个岛上去/把桃瓣的碎片,葬在血脉里”,坐桃花去岛上,这交通工具可谓绝也。更绝的是,“桃瓣的碎片”居然可以葬入血脉之中,滚烫的鲜血,流淌艳丽而芬芳的生命记忆。“把血流遍岛上的每一寸土地/桃花便在每一寸土地上盛开”,如此形成的桃花岛,该是如何的姹紫嫣红,美艳无双啊!
“一个岛,远望/也是一朵桃花”,由上节所云的满岛的桃花,缩写为“一朵桃花”,桃花岛的精神,被简洁地勾勒出来。
“桃花岛”上的桃花是诗人的鲜血所喂养的,由这样的桃花所塑造成的“桃花岛”,自然有着不同凡响的精神气度和人文风采。这样的桃花岛,其传奇性无疑是最为充沛的。这样的桃花岛演绎出的,既是植物的传奇,更是生命的传奇。
十二
往事如尘
光是唯一的对话,被深藏,被宽恕,被忘记
语词的高蹈,沦陷于血肉的传奇
《前世今生》是陈陟云着力打造的一部长篇抒情诗,全诗共有九章,每一章又由九个部分构成。这里着重分析的是该长诗第三章第九部分的诗歌。
“前世今生”是生命轮回学说的简单概括,是人生剧情重演的精彩暗示,陈陟云以此为诗名,揭开了关于爱情、人生和命运的诗化演绎。“薇,圆日于喉间蠕动,渐渐消融/黄昏沉静,如壳内的蛋黄,人浸其中/深陷虚空的鸟迹划过,省略结语/内心黑暗的孤独,在一支香烟上点燃”,如同其他节次一样,诗人在这部分里仍以“薇”作为情感倾诉的对象,来展开对现实的观照和对心灵的细察。首节由时光的流逝而联想到自我心灵的虚空与孤独,情由景生,心随时动,细腻展示了抒情主体内在心迹的流变。在诗人看来,时光的流逝,是与人类主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时光一分一秒地消隐,都会在人类身上留下痕迹,于是就有了“圆日于喉间蠕动”、“黄昏沉静,如壳内的蛋黄,人浸其中”的叙述之语。
作为情感倾诉的指定对象,“薇”的身份是耐人寻味的,她或者是一株富于灵性的植物,或者是一个如植物般芬芳可人的女性,或者是诗人拟造的某种富有梦幻色彩的精神虚像。这个情感倾诉对象的设置,既使诗人的情绪表达有了确定的归宿和寄托,又让长诗在一定程度上达成某种抒情格调上的统一,因此这样的设置还是富有艺术表现力的。在第二节中,诗人向“薇”生动描摹了“独处”之时的生命境况。“独处是一种奢侈”,“奢侈”一词,意涵良多,耐人咀嚼。有句俗语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可见从俗世层面说,独处对个人来说并非理智的生存选择,不过,若从精神的向度上说,独处又是自我充分敞开的最佳时机,是思想进入深层的必要条件。一般人是无法体味到独处的妙处的,一般人也无能消受独处的胜境,所以诗人以“奢侈”饰“孤独”,是具有说服力的。在独处之期,隔世的风在吹拂着,往事的尘土在飞扬着,光和生命在频繁对话着,这些都被诗人一一感受到。而“语词的高蹈,沦陷于血肉的传奇”,意即词语与人生在互相诉说着,彼此诠释着,这是诗人此刻所深切领悟到的生命要义,正在自己心海上翻波涌浪。事实上,世上一切的讲述都是词语的自我演绎,同时也是人生的某种展示,也可以说是词语和人生的互相打开、相互照亮。接下来,诗人对时间的思考也耐人寻味,“只有钟摆的苍老,预示相爱的短暂/一生只照亮一秒,一秒几乎长于一生”,这时间悖论里含蓄着深隽的哲思,表面荒谬的造语里闪烁出某种真理的辉光。
梦呓在不断延伸,时光永不停息地流逝,尘世的嘈杂总在持续着,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不过,当“前世今生”的生命理念在心灵中驻扎,我们就有了安排自我去处的新的方案:“一灯如豆,我们入定,尽遣化身/双手合十的形体拒绝光影,清澈而透明”,弃却肉身的短暂,追寻灵魂的永恒,“我们”的生命因此得以升华和涅槃。
十三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不止是说诗歌要讲究语言取用上的恰切和精当,更是强调诗歌是对语言意义边界的挑战,是对语言潜能的最有效开发,是对语言的弹性、质地、情感色泽、内涵外延的最大限度展示。诗歌创作必须将词语的内在潜质有效激活,诗歌创作必须将现代汉语的表意空间充分打开。真正的诗歌创作,就应该是语言的炼金术,是意义的采矿机,是促成语言价值完满实现的最奇特路径和孔道。
陈陟云的很多诗歌都是对固有词汇的全新阐释,在他的作品中,情境的创设,情绪氛围的营造,意义场域的呈现,全不受词语本身原有的意义格局的干扰,而是根据自我的生命体验和形而上思考,重新打开语言的意义空间,再度开发词语的话语潜能,力图赋予现代汉语词汇新的内涵和意蕴,前述所提及的《雪域》、《岁末》、《撤退》、《桃花潭》、《桃花溪》、《桃花源》等,无不如此。可以说,通过对固有词语意义的重新赋予和话语潜能的充分挖掘,陈陟云诗歌提供了当代诗歌写作不可忽视的重要美学方案。他以富有语言学功力的现代汉语书写,有力捍卫了中国新诗的艺术尊严,为口语写作鱼龙混杂的当下语境中如何有效提升当代诗歌的美学品质做出了某种表率。
与此同时,陈陟云对生命和存在有着独特的理解,对生与死、爱与恨、恒常与流变、时间与空间等不乏富于辩证性的思考,他的诗歌显示着存在主义的哲学睿智。可以说,陈陟云的诗歌从不是某种小情小调的分行书写,也不是某种灵机一动的简单记录,而是从某个特定的情景切入,实现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窥探,对人类本体的形而上玄思。他的诗歌是有思想硬度的,是有精神重量的。在而今崇尚碎片化、消解深度模式的后现代语境下,陈陟云的诗歌显示着特别的意义,它以现代性的艺术气质,实现了对后现代的执意抵制和有力反抗。只有这样的作品再多一些,当代诗歌才可能体现出更令人满意的精神质量和思想高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