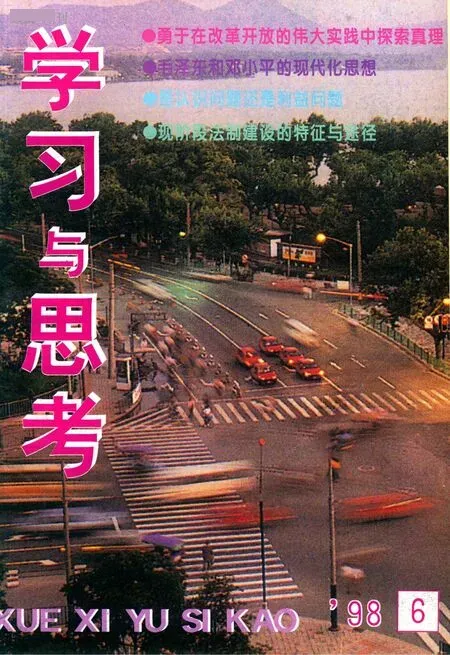勿忘列宁的忠告
□乔耀章
一、何谓列宁的“忠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缔造者。列宁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阶段,并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开始变为实践,从理想开始变为现实。列宁为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进行的十月革命既提供了意志与胆识,又提供了智慧与思想,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也为正处在千年大变局中的中国社会先进分子送来了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所谓列宁的“忠告”,本意是指列宁诚恳地劝告的话,同列宁的“政治遗嘱”相关联。列宁的政治遗嘱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部分。广义的政治遗嘱是指1922年12月23日,列宁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使他“焦虑不安”的想法和考虑写出来。到1923年3月2日,列宁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等8篇书信和文章。列宁政治遗嘱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党的建设、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民族问题、合作社、工农联盟、发展生产力、文化革命等等。狭义的政治遗嘱一般是指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该信中曾提到建议党中央把斯大林调离领导岗位。然而,本文所谓的列宁的“忠告”,既不是指狭义的列宁的政治遗嘱,也不是指列宁关于“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①《列宁全集》(第五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页。的忠告,还不是指广义的列宁的“政治遗嘱”。笔者特别想阐发的问题主要有三:其一,到目前为止,国内外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还很少有人从列宁的“政治遗嘱”中解读出本文所特指的“忠告”内容;其二,虽然列宁“忠告”的内容寓于列宁的“政治遗嘱”之中,但“忠告”的内容与“政治遗嘱”的其他内容不能等同视之;其三,列宁“政治遗嘱”的其他内容可能成为过去时,但“忠告”的内容并没有远离我们的时代而去,由此必须提醒人们勿忘!那么,列宁政治遗嘱中的“忠告”内容是什么呢?
本文所说的列宁的“忠告”内容是指在1923年1月2日列宁口授的《日记摘录》中涉及的三个自然段。由于版本不同(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高质量高水准翻译,对于完整准确地把握经典著作的思想原义是至关重要的),为说明问题起见,特引出来以便于比较:
“……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利用我们的政权把城市工人真正培养成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
我说了‘共产主义’这几个字,我要赶忙声明一下,以免引起误会或过于机械的了解。决不能把这一句话了解为似乎我们应当马上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还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这样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危险的。
不能这样做。应当从建立城乡的联系开始,决不能过早地给自己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的目标。这个目标现在是达不到的,是不合时宜的,现在提出来不但无益,反而有害。”①《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9页。
“……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我们的政权使城市工人真正成为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
说了‘共产主义’这几个字,我要赶快声明一下,以免引起误会或过于机械的理解。决不能把这话理解为我们应当马上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奠定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这样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致命的。
不能这样做。应当从建立城乡间的交往开始,决不给自己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这种事先定下的目标。这种目标现在是达不到的。这种目标是不合时宜的。提出这种目标不但无益,反而有害。”②《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
从以上引文中可解读出这样三个问题:第一,究竟由谁向谁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强调的是由城市工人或无产阶级向农村农民或农村无产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其中,可见列宁暗含着的思想是,相比较而言,城市工人或无产阶级要“先进”于农村的农民或农村无产阶级,不过,城市工人或无产阶级并不是先天的自然而然的先进于农村的农民或农村无产阶级的,要靠“培养”、才能使之“真正成为”(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又靠谁来培养呢?第二,列宁这里的“共产主义”,是有“纯粹的和狭义的”与“非纯粹”的或“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之分、之别的。由城市工人向农村无产阶级传播的只能是非纯粹的或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是纯粹的和狭义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所谓纯粹的和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第三,列宁特别强调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有条件的。如果在农村中“还没有实行”或“奠定”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就“过早地”或“马上”就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那不但无益、有害,而且还是致命的!可见,本文的所谓列宁的“忠告”正是这其中的第三点。列宁逝世90年来的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在真正的物质基础具备过程中,过早地传播和推行(当然不仅限于在农村、而且在城市以至于在一个国家)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是有害的和致命的!
二、对列宁“忠告”的理解
为了加深对列宁的这个不可忘却的“忠告”的理解,我们拟提出和初步分析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关于“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在这里,列宁所说的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248页。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有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的学说。我们通常认为,由于时代和历史使命决定,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主要是侧重于理论论证,而不是具体的实际运用,这就要求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论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理论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248页。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场景的论述中都强调一个共同的主旨问题,这就是“条件”。列宁的“忠告”中的“物质基础”就是“条件”的同义语。他谆谆告诫人们:要推行那种不讲条件、没有物质基础的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将导致一种致命的灾难。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唯条件主义”,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学说。⑥参见黄 森:《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过程》,《光明日报》2011年9月19日;田居俭:《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第7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就是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是以消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为目的的。
其次,关于革命问题上的辩证法与建设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在革命与建设的问题关系上,进步的革命能够解放或推进社会建设与进步;失当的社会建设往往会引发或导致革命的发生。在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并不必然产生关系和联系,其中,辩证法有朴素的辩证法、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等;唯物主义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机械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唯物主义等。在革命与辩证法、唯物主义以及建设与辩证法、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有着更为复杂的交互关系。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理论论证的马克思主义和实际运用的马克思主义两个部分有机统一时,势必要在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上提出、研究分析和回答革命与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条件论”的理论论证逻辑,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方文明国家同时发生,并以此为信号(这也是一种条件),带动东方相对落后的民族国家实现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穿(有别于“跨”)越式发展。然而,这一理论设想在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领袖们那里被简单化、教条化、机械地固化甚至庸俗化了。1899年2月,伯恩施坦因其所编写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全面“修正”及其以后的影响而赢得了民主社会(修正)主义鼻祖的称誉。他们以“民主”作为“前提条件”而站立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对立面而反对这种革命。对此,列宁在《论俄国革命》一文中,指出他们的学究气,他们迂腐到了极点,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革命辩证法是一窍不通,一点也不理解。①《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9-691页。列宁进一步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赶)上别国人民呢?”②《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是,首先有资本主义的建设成果为革命创造了前提——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伯恩施坦等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歪曲并庸俗化了这一逻辑),这是一种革命问题上的唯物主义;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逻辑是,在特殊的国际国内的条件和形势下首先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种革命问题上的辩证法。这在当时好似一桩难以判断是与非的历史公案,但是如果在今天比较公允地看来,当年,伯恩施坦及第二国际领袖们的主张较为符合西欧的情势,而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的实践行为则更符合俄国的国情。从特定意义上说,列宁与第二国际领袖们及其在俄国的代表们相互间的论战缺乏一定的公约数。然而,列宁所直面的是俄国冷酷的现实,他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他领导俄国人民不失时机的从革命的辩证法转向了建设的唯物主义,我们从他的“忠告”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对此,笔者称之为是在革命与建设关系问题上“首先和然后历史发展序列的颠倒”③参见拙文:《学习列宁关于经济方面的政治思想保证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试论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苏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关于十月革命方式的思考》,《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试论列宁的社会主义》,《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再次,关于列宁“忠告”的历史见证。列宁对建设俄国需要什么样的物质基础问题关注最早,最为重视。早在1918年春就提出了苏维埃当前任务问题。先后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两个著名的公式:一是在1918年提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二是1920年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两个公式强调三个问题:第一,特别强调国家政权优位,体现首先夺取政权的革命辩证法逻辑的延续;第二,特别强调发展高度的社会生产力,体现然后建设的唯物主义逻辑使然;第三,特别强调新生苏维埃共和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发生积极的经济关系,体现对外开放、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唯物主义辩证法逻辑创新。但是,由于帝国主义联合的武装入侵,这两个公式预设没能进入实践程序,并被迫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对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平息国内叛乱,巩固苏维埃政权起到了保障作用。但其弊端随着战争结束而暴露出来,引发部分工农群众不满,导致1921年2月喀琅施塔得暴动。直面严峻的形势,列宁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勇于创新,探索解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思路。1921年3月俄共(布) 十大通过了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决定。但是,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以后,新经济政策很快就被废止了,以1925年4月俄共(布)十四大确立斯大林“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为标志转向了“斯大林模式”。今天看来这一转向,正如列宁当年所说的是有害的和致命的。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以后,引发了人们对斯大林模式的历史性反思,更有甚者,还引发了一股怀疑和否定列宁的历史功绩,及十月革命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声浪。国内学者的反思是比较公允的、全面的,如张全景对苏共失败原因概括为: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并且认为现实原因是主要的。①张全景:《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3期。李慎明则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有多种原因的,主要有三类: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军事威胁与争霸;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苏共领导人长期脱离人民群众、腐败、背叛,并认为这是主要的。②参见李慎明:《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人民论坛》,2011年第37期。然而,笔者却认为其中的历史原因、失误和弊端是更为重要的。其中偶然中有必然,从特定意义上说,正因为没有汲取列宁的“忠告”所富有的智慧,才成为日后苏联亡党亡国的不可忽视的源头、基因(DNA)及内因依据。
三、列宁“忠告”的历史性启示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相比较而言,对列宁的“忠告”比较陌生,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对“斯大林模式”却比较熟悉,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也更加深远。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内外环境下,我们党并不知晓列宁的“忠告”,虽然没有复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嫁接”了“斯大林模式”,探索性地走出了自己的路,虽然取得了奠基性的成就,但也犯下了影响后来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带有某种“基因(DNA)”性质的错误。对此,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思认识是不对称、不平衡的。最早对此有比较清醒认识的是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身患重病的他忠告西哈努克、乔森潘、英萨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犯过错误,我们必须为此造成的后果负责。我冒昧地提醒你们,不要期望通过一场大跃进就能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必须小心谨慎,明智行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共产主义道路。如果你们抛弃这种谨慎和共产主义的常识,那只能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灾难。”③张寿春:《周恩来病重期间告诫西哈努克什么》,人民网,2013年6月9日。周恩来这段话既是对我国接连发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严重“左”倾错误的深刻反思,更是忠告兄弟党避免重蹈覆辙的金玉良言。如果说,对于当时的苏联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列宁的“忠告”属于预见,那么周恩来的忠告则是中国铁的事实。
列宁曾经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④《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郑重的党。重温列宁的“忠告”,直面复杂的中国现实,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从头(1949年或1956年)做起的历史进程。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主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曾有过一次评价,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39-140页。笔者认为,邓小平的这些话也是一种忠告。从特定意义上说,邓小平的忠告,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对列宁“忠告”的历史性回声。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实质上是对“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性传承,是可适应整整一个时代的长期战略,而非权宜之计。
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征途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暂时距离“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远”了些,但距离为解决民生问题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则日益趋“近”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