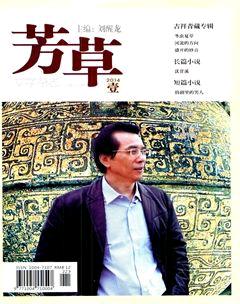走往何处[十二首]
那只曾在我的窗台坐过的鸟
有一天我遇到它正在采一朵花
它把自己插在一簇粉色的三角梅里
躬着身,深深地深入那团耀眼的花丛
我不确定它要一朵花干什么,只看见了它在为一朵花用力
它像一个挖掘者,在用探镐
像一部法律的起草者,在用键盘和打字机
像一个捕气球的小女孩,伸出手臂高出的部分
它的样子,已经完全不是鸟,而是花丛的一部分
而下午,它依然在那里
仿佛已在那儿成家,仿佛
那花丛已是它的花园
任何人,都不能在它呼吸的地方采花,直至枯萎
同样的夜晚,我又出来在门口的空地上散步
我又想起了那鸟,那花,那姿势
那灯苗一样的眼神
我以为它已经离去了,我又去看看它
高大的棕榈树下,那花团仍在,它也仍在那儿
只是换成了另一种姿势
蹲着,显示着它对于那美的永久的拥有和护卫
然而我走上用手抚摸并触动它,它已不动,不再用那眼神看我
我们已经没法继续交往
我已经不能问它死对于它意味着什么,对我意味着什么
已经深夜了,我想借着夜晚的光埋葬了它
但天上的光已不足够我在大地上安葬一个服从自然的朋友
獾来自哪里
肯定不是它的洞穴。也不是来自它的公路。一只獾
在夜间来临,看不清
它的容貌,也听不到
它的声音。一只獾
闪动着
獾的颤动、獾的称号
一种动物的神秘
和神圣、造物主的
理想与怪癖
一个手艺上的错失
和一次嘴唇上的误读
一只獾
负载着獾的名字、獾的稀少、獾的夜色、獾的传记
不去征服,也不去洗刷任何事物
有别于生物学的笔迹
不同于植物学的根须
来自一片树林、一块田地、一个漏洞
它浑身湿漉漉的,田畴间转动的
脖颈,湿漉漉的
我们看见它,跟上它,写下它陌生的
名字,空白的
面容,周围起伏的灌木
被手指出、密实的茎叶
湿漉漉的
火山轶事
上一周,我在一片空地上制造一座火山
我在那片空地上给那座火山打草稿
在草稿上写上火山的思想和目标
在后面注明了火山喷发的日期和名字
上一周,岛上台风刚过
下了三天的雨
我乘公交车去了三趟医院
有一次,我半途下来
到无人的田野上独自走了一会
在那里
我看到了一只灰色的鸟
和田野上那些零星隆起的墓堆
它们让我想到了我的火山
它的火和它喷发的样子
让我想起了火山由于燃烧
而让大地布满了灰烬
因为喷发
却留下了眼睛一样敞开的山口
上一周,我在这片空地上
就这样整天为一座火山打草稿
我在这座火山的周围不停地转来转去
我感到我的脚都热了
我停了下来
后来我想火山早已在人类漫长的历程中喷发过了
人们早已学会了
在秋日的林中拾捡那些坠落的橡果
我已经不能用疾病和火山来赞美这个忧伤的世界
我的提问
我问父亲
为什么红薯支撑我们,却不赞成我们
我又问他
为什么人死了,要像红薯一样
我问他,人能走多远
如果开着一辆拖拉机
我问他,世界上还有几辆拖拉机
除了从黑暗中驶来的那一辆
我问他,秋天了
人们摘下了向日葵的種子
为什么要把它高高的茎秆撵出门外
我问他,鬼魂像蜜蜂
还是像蝴蝶
是围着路旁的杨树,还是菜园里的菜叶
我问他,是否也会有那么一天
我在黑夜里劳动,而你静静地坐在一旁
我问他,你为什么默不做声
沉默意味着一条道路还是其他的什么
我问他,等你老了
是否还会记得这个田块,这个我们赢得食物和黑夜的地方
一九八零年的深秋
在一片刚刚收获的红薯地里
我问我的父亲
天空上群星涌动
空气中传来浓浓的霜气
父亲正在把满地的薯秧
一堆一堆拢在一起
我坐在火堆旁
烤一个冰冷的红薯
火堆旺旺的
我看着火堆里的火
在心里问我的父亲
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爱
我当时还不知道那就是爱,而以为只是我对他随意的提问
麋鹿
在机场候机楼的门口我们相依而立
我抽烟,你把烟灰弹进一旁垃圾箱明亮的碗盂
我移动手,你把手放在手渐渐移动的地方
在同一座机场的候机楼门口我们已如此分别四次
飞机起飞了,你启动了马达
你在暮色中沿着海岸驱车回去
我在云层上看着你一米一米离去
你犹如一只故乡真实的麋鹿而我犹如
一只异乡的孤鹰
我看着你,每一次,我都看到了清晨你向我的水杯里倒水时
水使你明亮的样子
每一次,我都感到我接近了天穹,而这力量
来源于大地上人类心灵中那忧郁的幸存之物
如此安宁的一天
哪一天才有如此的安宁
我坐在一棵木桩上,看着远处的天空
已经暮晚了,天幕整洁而阔大
好像从没有谁在那儿飞翔
也没有什么从那儿降落
一只蝴蝶的颤动,引起了空气自身的呼吸
一只不见身影的鸟儿,发出了手中的书卷上同样的鸟鸣
有人说,我们祷告吧,为那海面上沉去的桅帆
为那田畴中弯腰捡起的岁月与奇迹
你已经老了,白发苍苍,站在灯与光的深处
你如此高大,为我说起灵魂和孩子,准备好水和温热的晚饭
陶潜的诗
昨晚,我读了一首陶潜的诗
我猜测他写这首诗时正站在上顶上
我想那座山,并不高,是一座无名的山
但是可以看到山东的那些果园
和秋日的枝头上灿烂的苹果
我想他肯定是把那些苹果
认作是中国的少女与灯
才写了这首关于故乡的诗
他肯定是病了,一个病人
到了山顶上,不写诗
就会孤独
踩着潮湿的鹅卵石,朝孤独的尽头使劲走去
出门之前你要数数你的黍子和羔羊
出门之前你要数数你的黍子和羔羊
让它们也数一数你
睡觉之前,你要亲亲你的暖瓶和水壶
让这些温暖的物件
也亲吻它们的主人和亲人
到了田野上,你要向着那些谷物挥挥手
也冲着那轰鸣的收割机挥挥你的手臂
让那铁家伙,开得慢一些
来得慢一些
在路上遇到了那些玩耍的孩子,你要停下来
看一看他们那白绿相间的校服
盯着他们的眼睛出一会儿神
如果刚好喷着热气的铺路机
拖着黑黑的柏油缓缓驶过
你也不要敌视它,你也要赞美它
你要记得,凡是被你赞美过的事物
都会更加坚固,更加长久
你所赞美过的数字、路人、朋友,都至今爱你,至今活着
我要走往何处去
天黑了,我要走往何处去
是走向坡下已经亮起夜灯的快餐店
还是走到对面技校的清冷的食堂去
(为了抵抗饥饿,我前天已在那里买了饭卡)
是沿着公路随便走走
再省掉一顿晚饭
还是顺着公路一直跨海走回故乡去
天黑了
鸟儿已经不再啼叫
草丛里只有秋虫起伏的演奏
我站在离它三米远的地方
听到它像一只古瓮,又像一把胡琴
不论是什么,都调子艰涩发出长长的哀音
我想我还是哪里都不去吧
就这样站在原地
等天再黑一些,我就去看那位黑眸子的朋友
我的朋友住在山的另一侧
去看他
要经过一道阴森幽僻的峡谷
他坐在那里,召唤我
来吧,客人,来吧,狮子、游牧人,来吧
可怜的江非,穿着漆黑的袍子后背上贴着黑色邮票的人
天黑了,我的朋友吹着口琴流着泪
给你
给你,这凄美的一日
给你,兰波
这个卷头发的乡村里来的去非洲的军火贩子
给他一整个马赛港
从最炎热的沙漠里
运回最温暖的棉花
但不给他女人
这将耽误他的一生
给他一瓶康师傅矿泉水
别让他说
人是另一个
给我说你曾经见过他
他还在热带写诗
将热的太阳
和火
运到北方
填进空空的冰箱和母亲的灶膛里
给他这好聚好散的日子
这倒霉与辅音
但不要给他女人
这将耽误他的一生
大海
大海,今天我看你
像个丢失了机票的孩子
回不了水星的故乡
还像个不会说话的孩子
心里只有一个孤独的思想
也不是不会说话
是你的话
无关人类
是你有话
不说给人类听
也不说给我听
大海,人类太多
你只有一个
今天我又独自
坐在岸上看你
看见你心里只有一句话
用水埋着
不知道该说给谁听
弯曲
已经二十年了
我没有见过我父亲
哭
也没有再见过他
站在庭院的过道里
抽煙
一个人
把烟灰磕在自己的鞋子上
我的父亲
待在某个中国的乡村
他已经成为一个中国老头
我每年见他一次
或者三次
他也同样见我
有时候,我们只是对面坐着
有几次,他走
我送他离开
在银灰色的
电动三轮车跟前
父子轻松地相望一眼
已经不愿哭
或者已经哭不出来
但我总想父亲再哭一次
像二十年前的样子
一个父亲
抱着已成年的儿子
身上发出无力的抽搐
犹如树在
弯曲
而我也想问问父亲
已经老了
时日不多了
如果还剩下了最后一天
他会干什么
他不会回答
但我知道他的答案
而他也同样会问我
而我的回答是
如果还剩下了最后一天
我将用来维修我的骨头
如果不维修骨头
我将用来
维修房顶
如果房顶是好的,没有漏雨的
迹象
那么,我将用一天的时间
来维修我的坐姿
我将维修一朵菊花的
眼
如果眼
不是最后的熄灭之物
我将让眼看见
这株植物
在向地面弯曲
这是我
不是我的父亲
但我知道这不是我
而是我的父亲
(责任编辑: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