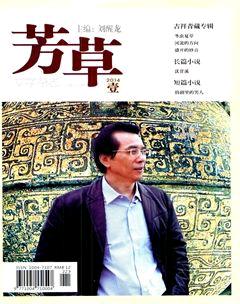妮卡
维克多·佩列文
此刻,当她微弱的气息再一次消于世上,散于云天之间,随着春日的寒风而逝,我不时将目光从膝头上那部如硅化砖一般厚重的蒲宁小说书页上移开,望向墙上,那里挂着偶然存留下的她的相片。
她比我年轻许多,命运偶然让我俩相识,而我并不认为是自己的优点召来了她的眷恋,简单地说,我对她而言,借用生理学术语,只是刺激剂,用来引起那些始终不变的生理反射和生理反应,即便让一个头戴学究气小圆便帽的基础物理学家取我代之,或是某个贪腐官员,或者任意某个准备鉴赏她黝黑的南方姿色,以此减轻她异国他乡的生活压力的路人。当她把头埋在我胸口,我会缓缓抚摸她的香颈,想象另一只手也曾在这温软的弧度里——纤细白皙戴着骷髅戒指的手,或者猥亵多毛配着蓝色手表的手,同样慢慢向下滑去——并觉得这样的更迭并未触动她的灵魂。
我从未以全名称呼过她——薇罗妮卡这个单词于我来说是一个植物学名词,并唤起对于一种南方白色花朵般令人窒息的气味的久远童年记忆。我以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将就,她无所谓,对于言语的音韵她毫无辨别力,而对与自己同名的那位有翼无头的女神更是一无所知。
我的友人都不喜欢她。或许他们知道,即便慷慨地——哪怕是几分钟——将她接纳到自己人的圈子里,她也只会无人问津。但圈外的妮卡傻兮兮的尝试行为,就好似铺路的工人期待着从来往行人那里得来感激,对她来说周围的人仿佛是一个个会说话的立柜,以莫名其妙的原因出现在身旁,又以同样不可理解的缘故消失不见。妮卡不关心别人的感觉,但本能地猜测到了他们对自己的态度——当有人来访时,她越来越多地起身走进厨房待着。表面上熟人们并未对她无礼,但当她不在一旁时也不掩饰对她的轻视,不言而喻,没有人对她平等以待。
“你的妮卡是怎么回事,看都不愿看我一眼么?”他们中的一个讥笑问道。他没有意识到,事实正是如此,而他古怪且天真地认为,妮卡在心灵深处为他预留了一整座画廊。
“你完全不會驯服她们,”另一人在酒后猛吐真言,“要是我,一个星期就驯得她服服帖帖。”
我知道,他精通于归整物件,因为他的妻子驯服他这样做已是第四个年头了,但在生活中我越发不愿去做什么教导者。
妮卡并非对舒适漠不关心——她病态般的始终出现在我想要坐的沙发椅上——但家中物品只存在于她还在使用它们的时候,之后便消失了。大约因此,她实际上一无所有,我有时在想,这便正是原始共产主义者试图建设的样子,努力的同时并不知道将来结果如何。她不顾虑他人的感受不是因为性情恶劣,而是没有意识到这些感受的存在。某次,她将立在橱柜上的一只老旧的库兹涅茨瓷糖罐打碎了,一小时后我冷不丁扇了她一记耳光,妮卡就是不明白她为何受此体罚,跳起来跑开,而当我上前道歉时,她只扭过脸去沉默不语。对妮卡来说,糖罐只不过是一个闪亮材料制成的塞满纸的锥形器皿,而对我而言——是一个存储了我毕生现实存在证明的储蓄罐:从某个早已不存在的笔记本上扯下的小纸条,记着一串我从未拨打过的电话号码,一片未撕去票根的电影票,一张小相片和几页没写满的药店处方。我对妮卡心怀愧疚,不知所措而笨拙地请求原谅,前言不搭后语又矫揉造作:
“妮卡,别生气了。破烂对人拥有古怪的影响力。扔掉某个碎裂的眼镜便意味着认可,从镜片后观察到的整个世界被永远抛在了身后,或者,反之亦然,出现在了日益迫近的死亡国度……妮卡,如果你明白我说的……往日的残片就像是锚,将灵魂与已逝去的钉在一起,从那里能见已不存在的,和通常人们深藏心底的,所以……”
我从手掌下望了望,她在打哈欠。天知道她在想什么,我的话没有传进她美丽精致的脑袋里——就像是在与她臀下的沙发讲话,同样毫无结果。那天晚上我精心侍弄她,但她依旧冷如冰山,仿佛我滑抚她身体的手与散步时划过侧身的树枝无异——彼时我俩还出去散步。
我们每日厮混在一起,但我再清醒明白不过,我俩不可能真正走近彼此。她甚至不知,即使是在她柔软地蜷在我身上时,我可以心在别处,全然忘记她的存在。本质上,她十分庸俗,各种诉求是赤裸裸的生理需要——填饱肚子,睡足好觉,以及为了良好消化所必需的足够爱抚。她整日窝在电视机旁打盹,也不瞧一眼电视,只是海吃——顺便说说,油腻的食物是最爱——热爱睡觉,我记忆中从未有过她看书的场景。但天生丽质和青春年华赋予了她虚幻的灵性,她的生理存在闪耀着高度和谐的光芒,自然天成的气息让艺术无望地在其身后追逐,我开始觉得,她单纯的命运是真正意义上的美丽和明澈,而所有我生活基础的一切——只是臆造,甚至是别人的臆造。一次,我妄图得知她如何看我,但从她那里得到回答的尝试被证明是徒劳的,而我偷偷翻阅的日记本也未曾动过。
猛然间我发现,她的世界让我兴致盎然。
她有久坐窗前眺望下方的习惯,一日我驻足她身后,一手轻扶她的后颈——她轻轻颤抖一下,没有避开——我试图猜测她在看什么,看到的对她意味着什么。眼前是寻常的莫斯科院子——几个在沙坑里挖掘的孩子,用来挂起地毯除尘的单杠,一套用红色钢管焊接的帐篷骨架,圆木制的玩具木屋,垃圾坑,球门以及路灯。最让我压抑难受的是那个红色帐篷骨架——也许是因为幼时某个灰蒙蒙的冬日,一本硕大的、向古老文化致敬的民主德国图册上,猎人追猎猛犸象的情形将我的心灵碾至吱嘎作响。这是一个惊人坚韧的文明,曾经存在于西伯利亚某处,几千年历程中完全不曾改变——住在用猛犸象皮蒙墙的半球形小屋里,屋子骨架与现时庭院中的红色结构物在几何学上精确一致,只不过并非钢管,而是猛犸长牙拼接而成。图册描述的是谋生的猎手——浪漫的字眼,顺便说一句,和脏兮兮的家伙绝无相似之处,他们每月一次将鲁莽的大型动物引进竖有尖刺的陷坑——图画十分详细,我在惊异中了解了许多细小的日常生活细节、风景和人物,并作出了我生命中第一个逻辑推断,该作者毋庸置疑是做了苏联的俘虏。自那时起我便觉得,这些耸立在几乎每个大院的半球形骨架,变成了养育我等文明的声声哀叹,她的另一声长叹化为了一群陶瓷小猛犸,散落在苏联全境数以百万计的小卖部里,喃喃呓语从千年的黑暗中延至未来。如果我们的祖先另有其人,譬如特里波利耶人①——不是的黎波里②人——四千年前耕种畜牧,闲时用石头雕刻超大臀围的小型裸女塑像——这些塑像,现称“维纳斯”,存世颇多,除此之外,特里波利耶人引以闻名的还有他们严谨规划的木屋集体农庄。农庄内有宽敞的大路,所有房屋外观完全相同。现今在我和妮卡观察的庭院里,遗留下的就会是这个文明精确表示出方向的圆木小屋,那里会呆坐着一个穿胶鞋的小姑娘——但看不到什么小姑娘,双目所及只有一双不时轻轻晃动的淡蓝色靴筒。
天啊,我怀抱妮卡想到,我本来有这么多可以讲述,比如沙坑,比如垃圾坑,比如路灯。但所有这些让我极度厌倦的将成为我的世界,无处可逃,因为意识就像苍蝇,会粘上任何双眼视网膜所触及的影像。而妮卡却对这必然的损害完全免疫,譬如垃圾箱上的火苗和一七三七年莫斯科大火的对比,或者一边打嗝一边呱呱叫的肥壮的超市乌鸦与古罗马皇帝尤里安提到的预兆之间的相对关系。只是为何她性情如此?尽管妮卡彻底处于我的掌控之下,我对她的不可捉摸的内心世界的短暂兴趣已渐渐清楚,似乎这种渴望摆脱并转变了此前我脑中轰鸣奔驰的思绪,并使之彻底脱轨。实际上,已许久未有新鲜事发生在我身上,站在妮卡身边,我希冀着能体验某些崭新的生活和感受。当我凝望窗外自省时,她只是简简单单地看着那里的事物,她的神智绝没有唆使自己回望过去或神游未来,只满足于现在。我已然弄清楚问题不在于真实存在着的妮卡,而在于自身的整套思想,在我眼前出现的,一如往常,将来亦然,是她形体的表象,而坐在半米远处妮卡本身是无法企及的,恰如大钟楼的尖顶。而我再次感觉到肩上毫无重量却难以忍受的孤独重压。
“你瞧,妮卡,”我边走开边说,“对于你为什么盯着院子和你看到了什么,我毫无兴趣。”
她看了我一眼,又转向窗户——想必她已然习惯了我的反常行为。再说——虽然她从不承认这点——她对我所说的一切漠不关心。
我从一个极端冲向另一个极端。在确信她的浅绿双眸中——纯粹的光学作用——有蹊跷后,我决定去了解她的一切,对她的喜好被我毫不掩饰的轻视所冲淡,认为她不会注意到。但很快我察觉到,她对我们毫无交际的生活心生厌倦,变得爱抱怨和神经质。时值阳春,我几乎整日呆坐家中,她也只好陪着打发时间,窗外芳草萋萋,薄雾一般铺满天空的云层外,比平日大了一倍的太阳模糊地闪耀着光晕。
我记不清她第一次自己出门散步是什么时候,但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萎靡不振地放弃了与她同去的念头,我平静地准许她离开。并不是厌烦了她的陪伴——而是我逐渐开始以她一贯对我的态度来对待她了——就像对待圆凳,窗台上的仙人掌或者窗外的云朵。通常,为了保存上一次带来的幻觉,我只送她到电梯门口,嘴里喃喃两句含糊不清的告别辞就调头,她从不乘电梯下楼,而是悄无声息得一路碎步跑下楼梯——我心想,这其中没有一丝卖弄风情,她是真正如此年轻和精力充沛,宁可用三分钟轻松地脚不沾地地奔下楼梯,也不愿耗费同样的时间待在漆成刺眼黄色又嗡嗡作响的,还洋溢着尿臊气和后朋克乐队歌曲的棺材盒子里。(顺便说一句,妮卡对这个乐队毫不感冒,对摇滚亦然——我记忆中唯一引起她兴趣的,是那首《动物们》中,卡车喷吐着云团般的烟雾驰往前线,还未被鲍里斯·格列边希科夫③收买为爪牙的歌手,心事重重地嘶吼。)我好奇她会去往何处——虽不至于尾随监视,但已足以让我在她走后几分钟手持望远镜走上阳台,我从不欺骗自己我在做什么好事。她简单的行走路线沿着小径延伸,穿过长凳,贩售饮料的小亭和订货处的螺旋楼梯,然后在一座十六層高楼处转弯——在那尘土覆盖的废弃空地后便是森林边缘。接下来我跟丢了她——天啊!——我多么希望能在几秒后重新见到她,但已无可能。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只是不想再做自己,也就是说停止存在——这是我国自杀系统中最温和的形式。
英语中有这样一句谚语——每个人的柜子里都藏着自己的骷髅④。某些东西干扰了善于思考的英国人理解其终极真理。最糟糕的是,这副“自己的”骷髅并非指的是财产权或者将之隐藏起来的必要性,而是指“自己私人的”,这里的柜子——婉转表示躯体,哪天柜子消失了,骷髅便会掉出来。我从未想过在那个我称之为妮卡的柜子里也存在一副骷髅,从未想象妮卡可能的死亡。她所有的一切都与这个词背道而驰,她是生命的浓缩,就有如炼乳一般(一个冰冷的冬日傍晚,她光溜溜地走出雪花覆盖的阳台,忽然一只鸽子落在栏杆上——妮卡屈膝蹲下,怕惊走了它,一动不动,我欣赏着她黝黑的后背,猛然惊讶地意识到她全然不觉寒冷,或者干脆忘记了。)因此她的死并未使我产生特别的印象。她不过是没有触及我意识中涉及感觉的部分,未成为情感事实,也许这种特殊心理反应便是造成我所有行为的原因。当然,我没有亲手杀了她,但却是我推动了不可见的命运车轮,使之最终追上了她,是我开启了漫长的一连串事件,致使链上最终一环成为了她的灾厄。额头扁平且毛发低垂,满口流涎的爱国者——她命中所见的最后画面——是她的死亡的具体化身,仅此而已。笨拙地搜捕凶手,每一纸判决书都能找到合适的刽子手,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屠杀的同谋,世上万物皆交织在一起,因果关系无法还原。谁知道坦桑尼亚儿童遭受的饥荒,是不是只因为我们在地铁里给某个凶恶的老太婆让了座位?远见和责任的范围紧贴彼此,所有的原因最终都会走入未知,走向创世之初。
已是三月天,但天气仿佛仍驻足于列宁时代。窗外如水兵黑色呢制夹克的大雾笼罩着,行纳粹军礼似的生锈起重机的轮廓勉强可见,近处的建筑工地上联动机槌桩的声音犹如阿芙乐尔号的舰炮。当桩子被槌入地下后,轰隆声沉寂下来,雾中传来酒醉的对话和叫喊声,其中一个颤抖的男高音尤显突兀。接着传来咣当的铿锵声——这是在拖行至新铁轨。而后槌击声重新响起。当天色渐暗,气温稍降,我坐在被妮卡躺得失去弹性的沙发对面,开始翻一本加兹达诺夫的书。我有朗读的习惯,即便她从未聆听,我也并不觉得委屈。妙处在于,我允许自己用口吻语调来区分某些段落。
“她绝称不上内向,但若想知晓她迄今的生活轨迹,她爱什么,不爱什么,对何事感兴趣,看重别人什么品质,与哪些人交往,就必须长久与她相识,或亲密地心灵接触。我没有机会听她亲自描述自己,虽然我跟她谈论各式各样的话题,她通常只是默默听着。好几个礼拜后,我对她的了解只比最初几日稍增而已。然而她没有任何理由向我隐瞒任何东西,仅仅只是因为她的矜持,这让我无法不心生疑虑。当我向她询问什么,她不愿回答,而我对此始终心存惊奇……”
让我始终心存惊奇的另有其事——如果细想,几乎所有的书本,所有的诗句,都是为妮卡而作——仿佛她是不可名状的,她的聪慧和俏丽是艺术家无解的玄妙谜题,即便最智慧的心灵向这沉静而无法理解的绿色双眸发起猛攻,竭尽全力想要排除这不可见,甚至说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真正无法逾越的——障碍,即使是杰出的,在最后时刻用多愁善感的主人公护住自己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⑤,也只会残余两只忧愁的眼睛和一根一尺长的阳具(稍后我会解释他在异国他乡写就的那部著名长篇小说)。
“她缓缓穿行在醉鬼之间,从未有同伴,孑然一身,”我在半梦半醒间低声呢喃,反复思索这穿越百年的,映射无数迥异心绪的沉默,“那里有长毛的希腊式沙发,肆意涂鸦的墙……”
我趴在书上睡着了,醒来发现妮卡不在家中。很久前我便注意到,妮卡每天夜里会出去一阵子。我以为她是需要一些睡前运动,或者是和傍晚聚集在大门前路灯下的其他妮卡们进行交流,总有人会在那里用录音机放着音乐。似乎她有一个叫玛莎的朋友,棕色的毛发,伶俐活泼,我有几次见到她们在一起。我没有丝毫反对意见,甚至还会为她留门,免得她撞见我在昏暗走廊里跟踪她散步的勾当。我经受的唯一情绪就是嫉妒,因为世界的某一方又从身边逃离了——但我从未想过与她一同前往,明白自己的陪伴会是多么的不合时宜。我未必会对她的交际圈感兴趣,但仍旧会稍觉懊丧,她有她自己的圈子,而我不可进入。当我从梦中醒来发觉独自一人时,忽然想要下楼在大门口的长凳上抽支烟,我决定如果看见妮卡,无论如何也不可表明关系。站在下驶的电梯里,我甚至在想象她看见我的神情,哆嗦一下,但注意到我的冷漠后又转向玛莎——不知为何我认为她们会坐在旁边的长凳上——继续她们轻声细语只有彼此能懂的谈话。
楼前空无一人,我突然不明白先前自己为何确信会遇到她。长凳旁泊着一辆深棕色的奔驰——有时我注意到它停在隔壁街上,有时在楼前,但从记住的号牌上可以辨别是同一辆——车牌上有“ХРЯ”或者“ХАМ”⑥。从二楼传来静悄悄的音乐声,草丛在风中轻摇,雪突然间都不见了,就快到夏天了,我想。但天气依旧清冷。当我转身走进楼内,一位坐在门岗处形同枯萎玫瑰的老妇向我投来不满的目光——已经要锁门了。上升的电梯中,我思索着这几位曾是旧时积极分子的退休老人,坚守着这个正在枯死的全民岗位的最后嫩枝——从他们悲剧式的专注度可以看出,他们无法将之苟延许久,又无人可以转交。在楼梯间里我最后深吸了一口,打开楼梯门去扔烟头,便听见某种古怪的声音从下方院子传来,从栏杆上俯身探头,我看见了妮卡。
心智敏锐的人可能会认为,她特地挑选此处——与住所两步之遥——是为了获得一种特殊的满足,凌辱家园得来的快感。我不以为然——这对妮卡而言太过繁琐,但我所见到的唤起了自身本能的厌恶。故障路灯闪烁的灯光下两具疯狂交合的躯体,对我来说就像活生生的缝纫机,而尖叫声很难认为是人类的嗓音——就像没润滑的齿轮的吱嘎声。我不知道看了多久,几秒还是几分钟。突然间我看见了妮卡的双眼,而一只手自己抓起了垃圾桶生锈的铁盖,刹那后它已轰隆着贴墙而下,向她头顶落去。
想必他们被我着实惊吓到了,拔腿便跑,而我也弄清楚了是谁和妮卡在一起。他住在同一栋,有几次电梯断电时在楼梯上碰见过他——无神的双眼,淡色的胡须,一副充满自尊的模样。一次我曾见到他端着这幅架子在翻垃圾桶,我从旁经过,他抬起头仔细地打量我,当我上了几级台阶,而他确信我不会与他争抢后,身后再次响起在土豆皮中翻找的沙沙声。我早就猜到妮卡早晚会被他吸引过去,猜到她会喜欢这种类型,完全意义上的动物,她自己都不敢与之月下同行的种类。其实,她就本身而言是独一无二的,我一边开门一边想,如果我细瞧,她就好似一件完美的艺术品,问题不在于她而在于我。一切我所见到的美丽都被禁闭在我心里,因为那里竖着一支音叉,我用它不可言喻的音调来校准所有其他事物。在与外界打交道时,我始终认为自己就是自己,而周遭世界是一个由不同弧度的镜子组成的系统。我在想,我们都被安排成只能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细微至每个个体每个场景,以取代真正展示给我们的事物,就像亨伯特⑦将邻居家窗边露出的一只圆润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手肘,当成是小妖精的膝盖。
妮卡当晚没有回家,而是第二天早上,彼时我已经反锁全部门锁出城去了。兩周后返回时,迎接我的是门岗的红发老妇。她向另外三位在围坐在她桌边的老太使使眼色,大声宣布说,妮卡来过几次但进不去屋,而最近几天没有出现。老妇们好奇地打量着我,我快步走过,但对我某些道德面貌的评论还是在电梯旁追了上来。我感到不安,因为完全不知道去哪里寻她,但我相信她会回来的。事情繁多,直到晚上我也没想起妮卡,夜里电话响起,门岗的老妇公然决定参与我的私人生活,告诉我她叫塔季杨娜·格利高里耶夫娜,而她刚刚看到妮卡在楼下。
眼前的柏油路变黑了——下着毛毛细雨。大门口有几个小女孩伴着有节奏的叫喊在跳皮筋,皮筋高至她们的脖颈,她们竟然能够奇迹般地用脚挂上。风将一只破塑料袋吹过我头顶,不见妮卡的影子。我弯过转角向楼后的树林走去。我不知道这是往哪里走,但确信会遇见妮卡。当我走到空地前的最后一栋时,雨差不多停了,我转过屋角。她站在那辆深棕色的下贱奔驰前,车停得纨绔霸道——一只车轮轧上人行道。车前门敞开着,窗后一个身穿华丽条纹夹克长得像年轻斯大林的人正在抽烟。
“妮卡!嗨,”我停下说道。
她看了我一眼,就像不认识。我弯下腰将手撑在双膝上。人们常对我说,她这样的,不会被原谅,但我从未当真——可能是因为之前她原谅了我所有的欺侮。坐在奔驰里的人嫌恶地转向我,微皱眉头。
“妮卡,原谅我吧,啊?”我努力不去注意他,低语着去拉她的双手,一边苦闷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是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因为需要而钻进圣彼得堡大门,见到跑来躲避严寒的姑娘立刻站起身来伸双臂而迎,让我稍觉欣慰的是这样的对比未必会浮现在妮卡身上,或是那个已然在挡风玻璃后呲起金牙格鲁吉亚人脑中。
她垂下头,像是在犹豫,突然间我从某个无法明辨的细节中明白,她即将走向我,离开这辆贼脏的奔驰,以及那个用发动机罩颜色的双眼直勾勾死死盯住我的司机。而几分钟后我会携着她当面经过自家大楼门岗里的老太婆,我已在脑中对自己发誓,再也不让她一人去任何地方。她应该走向我,这再明显不过,就像淅淅沥沥又落起了雨,但是妮卡忽然躲向一边,而身后传来惊恐的孩子的叫喊:
“停下!我说,站住!”
我回头一望,看见一只壮硕的牧羊犬从草坪上安静地向我们飞奔而来,它的主人,一个戴着硕大帽檐鸭舌帽的小男孩,挥舞着项圈大叫道:
“爱国者!回来!到我这!”
我清楚记得这漫长的一秒——草上疾驰的黑色物体,扬手似要痛抽某人的小小身影,几个驻足向这边观望的路人,还记得当时一念闪过,觉得带美式鸭舌帽孩子都讲的是边境难民营的黑话。身后响起尖锐的刹车摩擦声和某种女人的尖叫,目光所及不见妮卡,我便知道发生了什么。
汽车——类似低档拉达车,后窗上沾满了鲜艳的贴纸——再次提速,想必司机受到了惊吓,即便他没有罪责。当我跑上前去时,汽车已经消失在转弯处,眼睛余光注意到狗正跑回主人身边。周围不知从何处冒出几个行人,兴致勃勃地注视着潮湿的柏油马路上一摊鲜艳到不自然的血迹。
“真是恶棍,”身后一个带格鲁吉亚口音的声音说,“滚远远的去。”
“这些人应该拉去枪毙,”另一个女声说。“什么都被他们买光了,你知道……对啊,您这样看着我干吗……哼,我知道了,您也是……”
人群在后面聚集,另外几个声音加入了谈话,但他们所说我已充耳不闻。雨又下起来,水洼中溅起的水泡缓缓浮动,就像我们的思想,希望和命运,从树林吹来的风带来了第一缕夏天的气息,完全无法言喻的新鲜空气仿佛在许诺着某些从未有过的东西。我没有悲痛,出奇的平静。但看着她无力垂下的深色尾巴,她的身体,即便死去也不曾失掉那份神秘的暹罗之美,我知道,无论我的生活如何变化,不管将来如何,都无法取代我今日所爱所恨,我永远不会站在自己窗前,怀抱另一只猫在手中。
①新石器到青铜器时期乌克兰地区的特里波利耶文化
②利比亚首都
③苏俄歌手,音乐人,摇滚教父
④意为人人都有不可告知之事
⑤俄裔美籍小说家,《洛丽塔》的作者
⑥俄国车牌一般有三个字母,此处“ХРЯ”与俄语单词公猪“хряк”相近,“ХАМ”是下贱货的意思
⑦《洛丽塔》一书的男主人公
(责任编辑: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