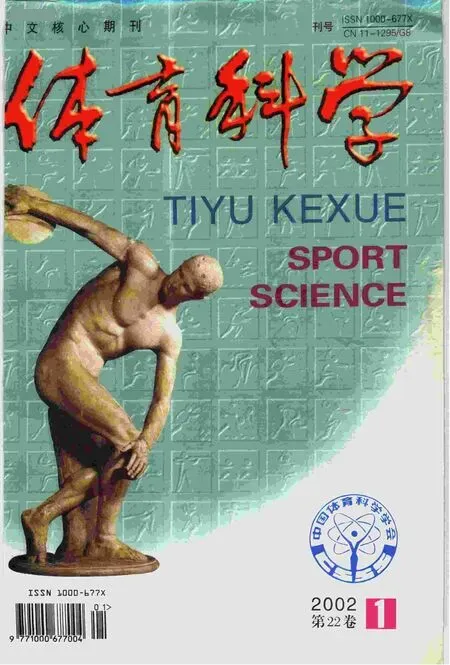先例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律适用中的指引作用探析
杨 秀 清
1 问题的提出
以历史为线索对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简称CAS)公布的裁决进行类型化考察会发现个案仲裁裁决受到先前类似裁决指引作用影响的情况越来越多。通过CAS发布的从1986—2003年的裁决结果来看,每6个裁决中仅有1个引用了先前的案例,然而,从2003年开始至今的裁决对以往案例裁决的参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乎每一个案件的裁决都参考了一个或若干CAS的先前裁决[19]。于是,有学者开始讨论在国际体育仲裁中是否存在着像英、美普通法系判例法中那样的“遵循先例原则”(Principle of Stare Decisis)[22]。有研究 以经验主义的进路开展了细致的实证考察,以2000—2010年CAS公布的所有关于田径运动兴奋剂违纪处罚上诉案件的仲裁裁决作为样本,总计23份,发现共有17份裁决在法律适用部分援引了先前的裁决,且其中只有1份运用“法律区别技术”(Technology of Distinguish)对后案与前案做出了不同判断,其余16份裁决都坚持了在前案裁决中体现出的原则或标准[8]。
上述情形是先例在CAS裁决中发挥重要指引作用的反映。那么,这种现象只是发生于CAS仲裁的纪律性处罚(非商事性质)争议中,还是也同样发生于商事性质的争议仲裁中?为何这种本不应在仲裁中出现的现象会发生?背后有什么潜在规律?是否可以认为在国际体育仲裁的法律适用中也存在着英、美法系的“遵循先例原则”?先例对国际体育仲裁的法律适用有什么意义?对像中国这样不以判例为法律渊源的国家,研究这一问题有什么价值?
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将从以下几方面展开:首先,关注先例(或称判例)在整个CAS体育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其次,按照纠纷性质的不同,把体育争议分为商事性质和非商事性质两类,分别探讨先例在两类争议的仲裁程序实体法律适用中的指引作用;再次,对先例指引作用的发生基础和效力性质进行评价;最后,挖掘它对于我国体育仲裁机制建设的价值,提出要重视构建我国的体育仲裁先例制度,以提高法律适用的水平。
2 先例是全球体育法“Lex Sportiva”中的核心要素
住所地在瑞士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于1984年由国际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组建成立,CAS的管辖权覆盖了与奥林匹克体育运动有关的商事和纪律性争议,以及其他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 of sports,IFs)或各国国家奥委会(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NOC)、各国国内单项体育协会(national federations of sports,NFs)同意提交CAS仲裁的争议[15]。基于国际体育领域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司法干预以保障行业自治的考虑,国际奥委会和各国际体育联合会通过与各级成员订立强制性仲裁协议或者将CAS仲裁条款植入体育组织章程等方式,共同构建起一种独特的国际性统一私法秩序,几乎将体育性纠纷完全置于国家法院司法管辖的直接控制之外[21]。CAS下设普通(Ordinary)仲裁和上诉(Appellate)仲裁两个并行的分支程序。普通仲裁处理的是当事人直接指定CAS裁决的争议,主要是运动员与体育组织之间或者体育组织与体育组织之间的商事性质争议;上诉仲裁处理的是在当事人用尽各体育组织内部救济后交由CAS做出终局裁决的争议,主要是不服体育组织纪律性处罚而引起的争议。CAS在机构设置上,还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一些大型国际单项体育运动项目的世界锦标赛(如世界杯足球赛和欧洲杯足球赛),设立了特别仲裁处以提高程序便利性。
与其他领域的仲裁相比,CAS仲裁庭在法律适用时对先前裁决的依赖程度非常高,以至于很多学者将CAS诸个案的仲裁庭自觉援引CAS先前裁决而累积成的实践作为已 经 出 现 “Lex Sportiva ”的 一 项 核 心 证 据[20]。 “Lex Sportiva”是由CAS在其出版的1983—1998年期间的裁决汇编中由国际体育仲裁院秘书长马修·睿布(Matthieu.Reeb)创造的一个定义尚有争议的概念[25]。我们姑且把它译为“全球体育法”。在各种定义中研究者比较认同的是,它指“适用于国际体育治理的特殊法”,是“从体育组织的实践和规则中提炼出来的一般规则,并用于体育治理”,它以正式契约为基础,其合法性来自于运动员和受它管辖的其他人自愿协议或提交体育组织的管辖权,由国际体育组织产生的法律规定和基本秩序组成的跨国自治私法秩序[20]。不管这一定义是否确切,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以先例为示范是“Lex Sportiva”的核心要素,考夫曼·科勒(Kaufmann-Kohler)认为,正是 “由于国际体育仲裁院在裁决中对先例日益增加的适用,使得一个条理清晰的‘Lex Sportiva’体系已经形成。[19]”纳夫齐格(Nafziger)甚至认为,“Lex Sportiva”可以用于专门指称CAS所创设的判例法体系,而齐格曼(Siekmann)认为,体育法的硬核可以简要地表述为“裁判者造法”(judge-made-law)[26]。由此可以看出,个案裁决在“Lex Sportiva”这一CAS的内生性规范体系中产生了聚沙成塔的效果,个案裁决的影响并不是在结案后就湮灭的,而很可能向未来扩张,对之后的类似案件裁决在法律适用上产生指引作用。
由于CAS仲裁中的程序法律适用统一为CAS住所地瑞士的法律,这里只谈实体法律适用中的援引先例。CAS《体育仲裁规则》第R45条规定了普通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问题,“仲裁庭将根据当事人协议选择的规范来裁决争议;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的,则适用瑞士法;当事人还可以授权仲裁庭依据公平和善良原则(ex aequo et bono)来裁决争议。”CAS《体育仲裁规则》第R58条规定了上诉仲裁程序法律适用的问题,“仲裁庭应根据可适用的规则(通常为处罚决定所涉的体育组织的具体规范),并辅之以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来裁决争议;若当事人没有就法律适用作出选择时,将补充适用仲裁庭认为恰当的有关体育联合会、体育协会或者体育组织做出决定时所在地的国内法,或者在给出合理根据的情况下适用仲裁庭认为恰当的法律[11]。”从上述CAS法律适用的两个规定来看,当事人的协议选择权得到尊重,但仲裁庭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可能是由于当事人没有行使选择权,或者作选择后出现某些瑕疵,或者所选择的规范本身不够明确等原因。可见,CAS仲裁庭在法律适用上的自由裁量权既包括对当事人所选规则的解释,又包括在当事人未作有效选择时自行作出决定,而先例正是在这一空间内发挥指引作用的。
3 先例在CAS仲裁程序中发挥指引作用的实践
3.1 商事性质争议仲裁法律适用中援引先例的实践——以国际足球联合会(简称FIFA)运动员雇佣合同争议为例
倚重先例指引作用的商事性体育争议多发生于个人与体育组织之间。因为,个人通常是体育组织的成员,所以,二者之间除了处于争议中的微观合同关系之外,还存在着成员加入体育组织时应遵守的章程和规则这一宏观合同关系。这种商事争议经常涉及对体育组织制定的相关条款的解释,先例的指引作用就突显出来。
下面以FIFA运动员雇佣合同争议仲裁的法律适用为例进行分析。俱乐部与运动员之间的合同常可能出于各种原因而被无正当理由终止,从一般合同法原理来看,这是一个违约行为,将涉及赔偿问题,其核心在于赔偿标准。与普通商事合同中可由当事人任意约定赔偿标准所不同的是,运动员合同多为标准合同,违约责任条款通常较为抽象,且很多相关事项常被上升成体育组织章程和规则中的规定。与FIFA运动员雇佣合同违约的赔偿标准有关的是FIFA《球员身份与转会规则》第17.1条:
“所有案件中,违约一方应当支付赔偿金。除合同另有约定的以外,违约赔偿金应按照本规则第20条和附件4关于培养费赔偿的规定,在计算违约赔偿金时要考虑相关国家的法律规定、体育行业的特殊性及任何其他客观标准。这些标准应特别包括:运动员在现行合同和/或新合同中所有的工资和其他福利、现行合同的剩余期限(上限至多为5年)、由先前俱乐部所支付的费用和产生的开支(依合同期限摊还),及合同违约是否发生在保护期内。[13]”
上述条文中提及与赔偿标准相关的3个因素应予考虑,即“相关国家的法律规定”、“体育行业的特殊性”及“任何其他客观标准”。这种抽象的规定为CAS仲裁庭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比如,“相关国家”指什么?“考虑相关国家的法律”是否构成一个法律选择条款?“体育行业的特殊性”应如何对待(赔偿运动员原所属俱乐部对他的培养而应得的利益,与保障运动员的自由流动之间常存在着一定矛盾,在如何平衡问题上常有争议)?“任何其他客观标准”与前两者相比处于何种地位,以及其中的各要素如何进行协调?第17.1条规定了一个宽幅度的标准,其中有许多元素断然无法被组合在一起,且其中还有一些可能在一类案件中适用恰当,而在另一类案件中却不恰当。
本研究不讨论这类争议法律适用的具体问题,只是说明在很多同类案件中都出现了后案援引前案的例证,比如:Soto案援引了Webster案。Webster案的争议焦点是,运动员Webster在保护期已满但是原合同未正式终止的情况下单方面解约,从原俱乐部苏格兰的哈茨(Hearts)转会到新俱乐部英格兰的维冈竞技(Wigon Athletic)后,哈茨应当获得的违约赔偿额该如何计算,以及是否应包括运动员的市场价值。CAS仲裁庭在Webster案中创设了一个对第17.1条进行解释的先例,其解释方法在之后的案件中产生了示范作用,并且该案裁决否认了赔偿额应包括运动员的市场价值,有人认为这一做法可能使该案像欧洲法院判决的博斯曼(Bosman)案件一样成为之后同类案件裁决的一个标杆[1]。此类援引先例的情形还有,Francelino da Silva案的仲裁庭参照了之前的Pyunik Yerevan案,逐字逐句引述了Pyunik Yerevan案的仲裁裁决中一些考虑“体育特殊性”的观点。以CAS的前案裁决为有力凭据的例子还有Ionikos案,案中仲裁庭多次以CAS的前案裁决为其指示依据[7]。
3.2 非商事性质争议仲裁法律适用中援引先例的实践——以国际田径联合会(简称IAAF)兴奋剂违纪纠纷为例
非商事性体育争议通常涉及体育管理和体育处罚,比如,参赛资格纠纷、比赛结果纠纷、兴奋剂违纪处罚纠纷等,一般通过CAS上诉仲裁来解决。根据CAS《体育仲裁规则》第R58条,相关体育组织的规则必然得以适用,因而同样需要CAS对体育组织的规则进行解释,先例在此也必然发挥重要指引作用。
兴奋剂违纪引起的纠纷是非商事性质的典型争议,前文提到的CAS对田径运动兴奋剂违纪上诉仲裁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援引先前裁决的案例中没有出现明显与先例相背离的情况,而在未提及先前裁决的案件中,仲裁庭都找到了裁决案件的充分的条文性依据[8]。
当确定案件中某个争点的条文性依据不足时,CAS仲裁庭对先例的依赖程度会很高。比如,兴奋剂违纪需要通过一定的药检方式来认定,但是,药物检测水平常常落后于新型兴奋剂的开发和利用,基于这一现实困境,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WADA)很难明文规定一套标准用于判断某种付诸实践的药检方式的可靠性等级,于是,仲裁庭就需要依赖先例来处理兴奋剂违纪案件中某项技术性证据认定上的争点[16]。有许多兴奋剂违纪纠纷中的被处罚人常常以做出阳性认定的药检方式尚未得到有力的科学证明为由在CAS上诉程序中进行抗辩。对此,CAS仲裁庭常常援引先前做出的那些涉及以相同药检方式认定违纪成立的裁决来予以驳回。例如,在IAAF诉摩洛哥田径协会(MAR)案(2003)中,运动员婆罗门·布拉米(Brahmin Boulami)因在赛内药检中查出促红细胞生长素(EPO)为阳性而受到处罚。布拉米和 MAR对检测结果不服,称药检方式的科学性是存疑的,且没有在国际上获得认可。CAS仲裁庭驳回了这一抗辩,依据是在CAS之前处理过的数件兴奋剂违纪案件中,都使用了这一项从2002年美国盐湖城(Salt Lake City)冬奥会时就已经开始使用的检测方法[9]。
4 对CAS先例指引作用的分析
4.1 先例发生指引作用的基础
通常,民商事仲裁裁决不具备先例价值,主要原因是实践中裁决一般都不予公开,后案的当事人难以得知前案裁决的内容,让仲裁庭去比照适用一个不公开的同类案件来进行裁决,既不实际也不公允。在某些特定领域,如国际海事领域或建筑工程领域的行业性或专业性仲裁,却比较重视以公开裁决结果为先例的形成创造条件[14]。CAS仲裁的大多数案件也都对外公开,提供面向大众的查询渠道(官网),并且,定期制作案例汇编,这为特定个案的裁决成为先例提供了可能。主张仲裁中适用先例的正当性在于,当事人能够受惠于仲裁员们的特殊知识和技能产生的劳动成果,并且对先例的依赖也有利于某个领域仲裁中法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17]。
先例在CAS仲裁体系中发挥的指引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国际体育领域存在着普通商事领域所没有的结构化组织形式,因而无论争议是否是商事性质,个案的具体情形常被认为与一个行业的整体利益有关,个案裁决往往就会被放到这种大背景下去考虑。无论法律适用的对象是由当事人选择的还是仲裁庭决定的,无论是法律性质的还是非法律性质的,无论是公平善良原则还是其他合理原则,仲裁庭在对这些对象进行解释时都会受到这种统一背景的影响,一般不会采用合同解释方法,而会统一参照法律解释方法[7]。这两种解释方法最大不同在于,合同解释方法一般是就事论事并着眼于个体,而法律解释方法更具有系统性并着眼于整体。采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就意味着,CAS仲裁的法律适用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对于特定目的的指向性,这一特定目的即是维护行业内的秩序稳定。因为不同争议的当事方往往是某一领域的同业人员,如果仲裁庭在个案中对类似情形作出的判断常常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即使能顺利解决个案纠纷,也势必会扰乱行业秩序。
行业秩序对于有相对独立性的体育领域有重要意义。行业秩序可以分为纵向的管理秩序和横向的市场秩序。体育领域存在层级分明的结构化组织形式,从历史角度看,联合会制结构是竞技体育的基本组织形式,虽然在不同的时期会因各国情况以及各种体育项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却是建立在相对一体化的机制之上的,有天然的垄断性。它的生成是自发的,先由体育运动的个体参与人自愿组成若干体育俱乐部,然后,发展出各级各类体育协会、联合会,从地区级开始,逐次扩展为国家级、国际级直至世界级[7]。一方面,从纵向的行业秩序上看,在管理中保障决策的统一和公正是重要的。比如,在CAS裁决兴奋剂违纪纠纷时,对于药检呈阳性这一事实的归责,虽然不同体育组织的规则中都普遍地确立了严格责任条款,但进行解释时遵循先例很重要,是解释为绝对的严格责任还是相对的严格责任会有重大区别,绝对的严格责任将使阳性检测结果直接构成违纪,而相对的严格责任则只是把阳性检测结果作为确认违纪的初步证据,二者对被嫌疑运动员的影响有很大不同。对严格责任条款的解释,CAS仲裁庭通常坚持绝对主义立场而形成了许多先例,但也发生过一个例外,那就是弗里兹·安纳斯(Fritz Aanes)诉国际摔跤联合会(FILA)案(2000),该案中仲裁庭认为阳性检测结果是构成违纪的初步证据并允许运动员推翻这种假定[5]。且不论绝对严格责任还是相对严格责任哪种更加合理,CAS仲裁庭都应该尽量通过援引先例,坚持在解释规则时的一致性立场,否则必然不利于世界反兴奋剂斗争。
另一方面,从横向的行业秩序上看,在市场中保障竞争的自由和公平也是重要的。比如,运动员转会问题中,在涉及违约赔偿的计算时需要考虑“体育特殊性”问题。“体育特殊性”不仅涉及要鼓励俱乐部培养年轻运动员,也涉及要减少运动员自由流动的障碍,这两个目标同样都具有合理性和重要性。当二者在个案中发生冲突时,仲裁庭不论侧重于二者中哪一者都是正当的,但更重要的是,仲裁庭应坚持通过对“体育特殊性”的综合考量而提出一种利益平衡的解决办法,并且不论在创设先例还是援引先例时都应始终如此。这种实践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便演变成为自由公平的市场秩序的一部分,个案中对它进行随意突破的任何做法,尽管本身可能有正当性,但都将对和谐的市场秩序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先例的指引作用仍是至关重要的。
4.2 先例发生指引作用的性质
4.2.1 先例是对法律适用中条文性依据的补充
关于先例能否独立地成为与条文性规则平行的法律渊源尚无定论,研究者较为保守地认为,先例只是条文性规则的补充,即当没有条文性规则或者条文性规则不具体时,仲裁庭才应依赖先例来指导个案中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而当先例与条文性规则不一致时,不应抛开条文性规则而选择适用先例。可以用兴奋剂违纪中的严格责任为例说明,在兴奋剂违纪认定中,存在着难以证明检测结果为阳性者构成违纪的主观过错的困难。在国际马术联合会的一起争议中,CAS仲裁庭首次把国际马术联合会的条文解释为绝对的严格责任(即只要发现兴奋剂检测呈阳性即认定为违纪并自动取消参赛资格)后[23],其他体育组织纷纷将严格责任条款加入其反兴奋剂规则中,于是广泛地存在着适用严格责任的裁决实践。在WADA全面完成对各个体育组织反兴奋剂规则的统一之前,也有若干体育组织的规则未对严格责任作出明确规定。Q诉国际射击联盟(UTT)案(1995)就发生在这一特殊阶段,当时UTT的规则中没有明确规定严格责任,于是仲裁庭并没有援引其他兴奋剂违纪先例中普遍存在着的严格责任的裁决实践而认定该案违纪成立,否认了严格责任已经成了一般原则的观点。而该案则导致了相关体育组织的规则增加了严格责任条款的明文规定[28]。当然,研究者并不否认随着Lex Sportiva的发展,未来CAS判例法可能成为独立的法律渊源,而只要当事人选择了CAS的仲裁,就意味着愿意接受CAS判例法来裁决争议。
4.2.2 先例不构成对仲裁庭的强制性约束——不存在英、美法中的“遵循先例原则”
CAS仲裁庭援引先例的频率非常高,即使在条文性依据足够充分时,也可能去援引先例来进一步强化裁决的权威性。研究表明,仲裁庭组成中是否有部分或全部成员来自判例法国家,并不影响仲裁庭是否做出援引先例的选择,实事上许多大陆法系背景的仲裁庭也频繁援引先例[8]。
虽然CAS依赖先例的指引作用,却不能认为在CAS仲裁中存在着像英、美判例法中那样的遵循先例原则。判例法的来源不是专门的立法机构,而是法官对案件的审理结果,它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司法者创造的[2]。遵循先例原则是判例法的生命线,它意味着某个法律要点一经司法判决的确立,便构成了一个日后不应背离的先例,即一个基于司法机关的判决而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定作为确定的先前判例,对以后的判决具有法律规范效力,应在以后的法院判案中作为法律依据得到遵循。该原则保证了判例法中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可预见性、一致性和延续性[23]。当然,在英、美法中“遵循先例”也并非绝对化,主要表现在宪法性案件中,在环境变化、适用先例存在困难和后来的案件与已有先例不一致而创设新的先例3种情况下[27],法院可以不遵守先例,但对于大多数非宪法性案件或非最高法院裁判的案件而言,遵循先例原则仍有强大的约束力。
CAS的做法不同于普通法学者所认为的遵循先例原则的实践,而更类似于大陆法系中的司法惯例(jurisprudence constante)。按照这种惯例,CAS仲裁庭通常要尊重前例的影响,但仍有自由和权力为了公正考虑而背离先前裁决。比如,在奥运会争议仲裁管辖规则的时间性要求上,CAS《奥运会特别仲裁规则》第1条规定,争议因是“产生于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或者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前10天”[10],但未规定纠纷的起算点是以申请人提交仲裁的日期为准还是以纠纷的实际发生日期为准。在这一问题上,CAS通过瑞士单板滑雪运动员斯库勒(Schuler)诉瑞士奥林匹克协会案(2006)确立了一个以提出仲裁申请日为准的先例[24],这在巴西冰上运动联合会诉国际雪车联合会案(2010)中得到遵循[12],但是,在爱尔兰拳击运动员约瑟夫·华德(Joseph Ward)诉国际奥委会案(2012)中,仲裁庭却动用自由裁量权确立了新的标准,认为应以纠纷的实际发生日期为起算点更合理[18]。在CAS《奥运会特别仲裁规则》尚未通过条文的完善来明确争议时间的起算点以前,华德案会成为供未来仲裁庭选择性援引的新先例。
即使某些个案的仲裁庭做出裁决时完全地援引了先例,但仍会明确表示不承认受到遵循先例原则的约束。比如,美国奥委会诉国际奥委会案(2004)[29],美国队获得4×400m接力项目金牌后发现,该队运动员杰罗米·扬(Joreme Young)在奥运会前有兴奋剂违纪行为而不具备参赛资格,CAS仲裁庭需要裁决美国队是否能够保留这项金牌。2000年的IAAF规则中只对个人兴奋剂违纪的后果做了取消成绩的规定,但未明确是否适用于团体项目中出现个人违纪的情形。IAAF援引了CAS先前在其他项目上类似案件中的裁决要求收回美国队的金牌,但这一主张未获得仲裁庭的支持。相反,仲裁庭援引了Q诉国际射击联盟(UTT)案(1995)中的原则,即不利的后果(处罚)应该是可以被预见的。通过坚持无明文规定就不应以任何方式产生不利于相对人的后果这一原则。CAS在本案中创设了一个先例,当无明文规定时不应将有部分成员违纪的团体所取得的成绩一并作废。另一个案例,争议起因于美国短跑运动员琼斯(Jones)在后来的一个司法程序中承认,她从2000年奥运会起就一直服用未被查出的禁药来提高成绩,而她在当时分别参加了4×100m和4×400m两项接力赛,两项分获铜牌和金牌。鉴于琼斯的违纪,国际奥委会纪律委员会决定收回这两项团体奖牌。相关人安德森(Anderson)将争议提交CAS后,仲裁庭援引第一案而推翻了IOC纪律委员会的决定,但是仲裁庭却特别强调,援引先例的原因是第一案对于第二案而言具有关键性的说服力,而不是产生了非遵循不可的拘束力。仲裁庭明确指出,它有权决定是否援引先前的同类裁决,并且它始终保留着在必要时做出与先例不同的裁决的权力[6]。
由此可见,在CAS仲裁中,援引先前同类裁决的实践非常普遍,甚至达到了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判例法的程度。但是,CAS始终没有正式承认过,在法律适用中存在着遵循先例的普遍性原则,先例只被作为选择性的法律依据。它的适用有助于完善仲裁庭裁决的理据,有利于体育仲裁机制在整体上实现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但就当前而言却并不构成对仲裁庭的强制性约束。
5 中国未来体育仲裁机制应重视发挥先例的指引作用
虽然我国目前的体育纠纷除自行和解外,主要是通过行政申诉和司法诉讼来解决,但是,这两个正式途径与国际通行的体育仲裁机制相比,在中立性、公正性、一致性、效率性或者专业性等若干方面总是存在诸多的问题。鉴于此,我国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简称《体育法》)第33条第1款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这在立法上明确了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合法性,但是,第2款“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却至今仍未落实。这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研究者认为,可以简单归纳为两方面:一是,在立法上,《体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简称《仲裁法》)存在不协调,1994年《仲裁法》颁行在《体育法》之前,其中,第2条对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规定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对不能仲裁事项的规定是“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这样的规定没有明确肯定或否定体育纠纷的可仲裁性,而我国体育行业带有较强行政化特征,这导致在体育纠纷是否可以仲裁问题上产生一些本无意义的困惑;二是,在实践中,体育仲裁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体育行业在国家的正确引导和支持下实现充分的依法自治,也有赖于我国体育仲裁专家型人才队伍在规模和质量上的成长成熟,而这些都需要一个过程。学界对如何协调我国《体育法》与《仲裁法》的矛盾、如何构建我国的体育仲裁制度进行了探讨,其中,张芳芳的《我国体育仲裁法律制度研究》一书较为细致全面,但学者们却鲜有关注我国未来体育仲裁制度的法律适用问题,更未注意先例在体育仲裁中的特殊价值。
先例在CAS仲裁中的指引作用,值得我国在构建和实施体育仲裁制度时认真研究。我国在纠纷解决实践中,像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更加习惯于从法条出发进行逻辑演绎的理性主义裁判思路,并且由于有发达的成文法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实践中基本上不援引类似案件作为裁判理据,也较少重视个案裁判可能产生的扩张性影响力。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当个案的条文性依据不足时通常会求助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我国的司法解释与普通法上的创设先例有共同之处,即二者都是能动司法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在司法实践中代行立法者的职权。司法的能动性是不可或缺的,在合理限度内也是非常必要的。受思维模式的影响,我国遵从司法解释而非先例,司法解释相当于制定主体把典型案例中的某些要点抽象成条文,后再在相同情况下对后案发挥普遍化的指引作用。这造就了一种从条文到事实直接进行裁判的模式,与从事实到原则再回到事实的类比性裁判模式相比更加方便,对于个案裁判者适用法律水平的要求也相对较低。当然,也带来了个案中只套用法条而不注重说明论证这一弱点,更有甚者会通过调解来“和稀泥”而置法条于不用,个案纠纷的解决效果即使会比较理想,但是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可能会有较大出入,难以满足宏观上的公平公正。
我国未来的体育仲裁机制很可能遭遇像司法裁判模式所面临的同样问题。更棘手的是,在体育仲裁中常涉及体育组织的规则的适用,而体育组织的规则存在大量漏洞和问题将是难免的。解决此难题,寄希望于某个体育仲裁机构来制定“司法解释”是不现实的,因为,它毕竟不是国家机关,难以得到不特定的一切当事人的共同授权来进行这种“立法”性质的正式活动。若转而向国家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寻求“司法解释”则更不可取,那会带来体育的“行政化”,从而丧失体育在本质上作为一种民间活动而应具有的生命力。再者,当具体争议发生时,相关体育组织已作为一方当事人牵涉其中,若再让它自行解释自己制定的规则中的存疑问题,又难以避免给相对人带来仲裁裁决不公正的印象。综上,重视发挥先例的指引作用,通过仲裁庭对先例的尊重而在裁决实践中自发地形成判例体系,作为仲裁庭未来进行选择性适用的依据,是解决体育仲裁中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一致性的最佳途径。
无论是在司法中还是在仲裁中,发挥先例的指引作用,构建某种形式的判例制度都是重要的,这与法律传统中是否存在“遵循先例原则”无关。司法先例或判例法不仅仍然是普通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渊源,也大量存在于被许多中国学者认为是制定法(成文法)传统的民法法系的国家中,比如,随着欧共体和欧盟的建立,设在卢森堡的欧洲法院判例已经成为欧盟国家的一种重要法律渊源。纯粹的制定法裁判模式只不过是一种理论假设,制定法具有与生俱来的抽象性和一般性,在抽象的法律规范与具体的生活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刚性切割出来的空间,构成裁判者理解正义、当事人感受正义的障碍。只有把先例的指引作用在实践中制度化,通过连贯地在同类具体案件中具体地适用抽象的规范,才能使正义得以在实际生活中具体实现,这才符合“相似案件应当相似判决”这一实现正义的基本原则。
把先例的指引作用制度化,既能发挥裁判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又能约束裁判者依法办事。一方面,先例制度是社会赋予裁判者的一个工具,它把蕴涵在裁判活动中的改进和发展法律的宝贵能量发挥出来,使裁判者能够把自己在填补法律漏洞、纠正制定法失误、丰富制定法、以及使制定法更为确定等方面的经验和决定固定下来,并使之不断发展、完善。另一方面,先例指引作用的主要功能是限制,而不是扩大裁判者的权力。由于相似案件相似处理的制度性要求,裁判者要受先例所包含的规则和所体现的推理的限制,而不能随意偏离先例的规则和推理裁判案件,任何无故的偏离都会受到来自律师、当事人和司法监督部门的质疑和约束。此外,先例的指引作用,会使裁判者在特定案件中提供的理由可能被作为在某种程度上拘束后来案件的一项“承诺”。于是,裁判者将不得不在处理当前案件时更为仔细地考虑,对未来同类案件的当事人应有的潜在的“信赖利益”,应进行何种“承诺”才是恰当的,从而使裁判者在处理每一起案件并形成裁判理由时都非常谨慎[4]。在我国司法界,也有很多学者不断呼吁要完善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构建我国自己的司法判例体系[3]。
为了建设我国体育仲裁机制判例体系,至少应做好以下3点:一是,个案裁决的着眼点不应只限于定纷止争的某个具体目标,而应注意考量个案背后存在着的行业秩序这一整体利益,在进行规则解释时多运用系统论的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某些个案成为先例后能发挥积极正面的指引作用;二是,个案裁决应重视对裁判理据的说明和论证,适当和有必要时要充分地援引先例来强化裁判理据的说服力,这样才能提高判例体系的自洽性和权威性;三是,最基本的,是要着力于建设向社会公开大部分仲裁裁决的有效渠道,这是判例体系得以生成和在实践中发展的基本前提。
[1]黄世席.国际足球争议仲裁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问题[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1(4):506-512.
[2]彭勃.英美法概论:法律文化与法律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
[3]袁轶通.遵循先例与案例指导制度的比较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9.
[4]张骐.建立中国先例制度的意义与路径:兼答《“判例法”质疑》——一个比较法的视角[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60(6):98-113.
[5]A.v.FILA [Z].CAS Arbitration N*CAS 2000/A/317.
[6]Anderson v.IOC[Z].CAS Arbitration N*CAS 2008/A/1545.
[7]ANDREA M S.Sports arbitration:Determination of the applicable regulations and rules of law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J].Int Sports Law J,2010,(3-4):54-68.
[8]ANNIE B.Is there a stare decisis doctrine in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an analysis of published awards for anti-doping disputes in track and field[J].Pepperdine Dispute Res Law J,2012,12(2):189-214.
[9]Baumann v.IOC [Z].CAS Arbitration N*CAS OG 00/006;Melinte v.IAAF [Z].CAS Arbitration N*CAS OG 00/015;IAAF v.MAR.& B.[Z].CAS Arbitration N*CAS 2003/A/452.
[10]CAS ARBITRATION RULES FOR THE OLYMPIC GAMES[EB/OL].http://www.tas-cas.org/d2wfiles/document/422/5048/0/RULES20OG20FOR20LONDON20201220 _ENG _.pdf,2013-4-26.
[11]CAS Statutes of the Bodies Working for the Settlement of Sports-Related Disputes[EB/OL].http://www.tas-cas.org/d2wfiles/document/4962/5048/0/Code20201320corrections20finales20(en).pdf,2013-4-26.
[12]CBDG v.FIBT[Z].CAS Arbitration N*CAS OG 10/002.
[13]FIFA Regulations on the Status and Transfer of Players[EB/OL].http://www.fifa.com/mm/document/affederation/ad-ministration/50/02/49/status_transfer_en_25.pdf,2013-4-26.
[14]GARY B.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Cases and Materials[M].Colorado:Aspen Publishers,2010:1059.
[15]History of the CAS:Origins,Ct.Arb.for Sport[EB/OL].http://www.tas-cas.org/history,2013-04-26.
[16]IAAF v.MAR [Z].CAS Arbitration N*CAS 2003/A/452;Melinte v.IAAF [Z].CAS Arbitration N*CAS 00/015;Baumann v.IOC[Z].CAS Arbitration N*CAS 00/006.
[17]IAN S B.Sport,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M].Hague:T.M.C.Asser Press,2009:155.
[18]Joseph Ward v.IOC,AIBA & ANOC [Z].CAS Arbitration N*CAS OG 12/02.
[19]Kaufmann-Kohler.Artbitra1Precedent:Dream,Necessity or Excuse?[J].Arbitr Int,2007,23(3):365.
[20]KEN F.Lex sportiva and lex ludica: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 jurisprudence[J].Ent Sports L J,2005,3(2):1-14.
[21]KEN F.Is there a global sports law[J].Ent Sports L J,2003,2(1):1-18.
[22]MATTHEW J M,HAYDEN O.“Sports Law”: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comparative,and national law and global dispute resolution[J].Tulane Law Rev,2010,85(2):269,291.
[23]MATTHIEU R.Digest of CAS Awards 1986—1998 [M].Switzerland:Mpfli SA,1998,edt.1st.
[24]Ms.Andrea Schuler v.Swiss Olympic Association[Z].CAS Arbitration N*CAS OG 06/002.
[25]RICHARD H M.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an independent arena for the world’s sports disputes[J].Valparaiso Uni Law Rev,2001,35(2):379-405.
[26]ROBERT C R,JANWILLERN S,et al.Lex Sportiva:What is Sports Law?[C].Hague:T M C,Asser Press,2012:359-391.
[27]SUZANNA S.The eleventh amendment and stare decisis:overruling hans v louisiana[J].Uni Chicago Law Rev,1990(57):1262.
[28]USA Shooting & Q.v.UIT[Z].CAS Arbitration N*CAS 94/129.
[29]USOC v.IOC[Z].CAS Arbitration N*CAS 2004/A/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