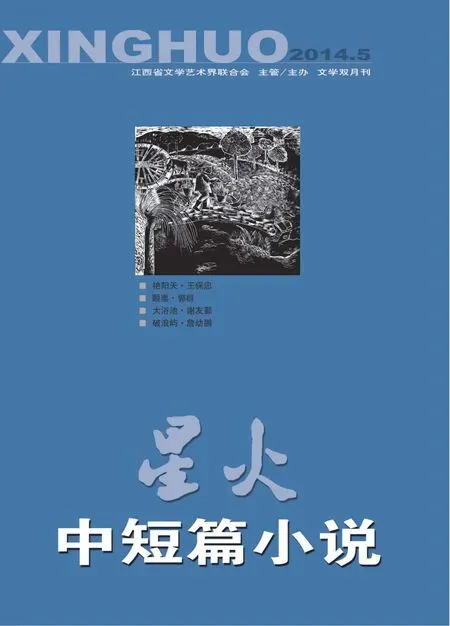担当, 还是担当(创作谈)
□ 郭 群
《颤栗》这篇小说涉及的中心案件,几乎是一个真实案件。
所谓“几乎”是从文本意义上说又不全是,特别是由此一案衍生出的另一起案件——破案领导“我们的头儿”,因为主动担当受牵连而下了大狱,这既是虚构,又是文学意义上的另一种真实。我们面对的生活,几乎每天都在“创作”着这种超具反讽性质和黑色幽默意味的悖论。
这是小说构思最初的酵母和起因。
我当过十八年兵,又当了二十多年警察,这两种职业似乎与生俱来赏赐我一种提神醒脑的本能警示,过去年代流行语叫“提高警惕”,变成如今一己的独特体悟,就是睁大了眼睛看世界。尽管,我自己经常也在沉睡,甚至装睡自我欺骗。但至少我也可能是一个梦,像上帝对莎士比亚所说,“我不是我,我可能是一个梦,但我也做梦,梦我的世界,一如你梦你的作品”。不同的是我的作品即便算是做梦,也是睁大了双眼“逼视”现实的结果。
把这句话说得更清楚明白点,那就是我不想装聋卖傻,尤其不想因为昧了良心去做“粉刷工人”、“糖果贩子”和“麻醉剂师”,从而无视生活的真实、苦难、残忍与心悸。我经历过文革,在那个一味说教和政治高于一切并决定一切的荒唐年代,毫无疑问曾厌恶过为我所用、僵死、教条的所谓“文学艺术”;但改革开放以来类似流行病泛滥成灾的浅薄媚俗、“去崇高化”、以至于“娱乐至死”现象,也让我不以为然和忧虑揪心。
看看现代版的“鸳鸯蝴蝶”,充满色情暴力的武打侦探,弥漫血腥气味和狡狯鬼气的网络通俗小说……你很难想象,这会给我们民族以精神净化与素质提升,并帮助人完成从自然人到理性人的过渡。更不敢期望,对我们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有多少助益!
我不是非要道貌岸然装出一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正人君子假象,从文学发生学来说,这也绝非文学应有的立足点。文学艺术最起码的初衷是不能变,也不该变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鲁迅,仍然需要学习和继承鲁迅,不仅要继续呐喊“救救孩子”,而且要坚持“为人生而艺术”、为人生和改良人生而写作。
我想,现实中既然不乏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尤其是被有形和无形杀戮戕害的孩子,“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这句警策箴言自然也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