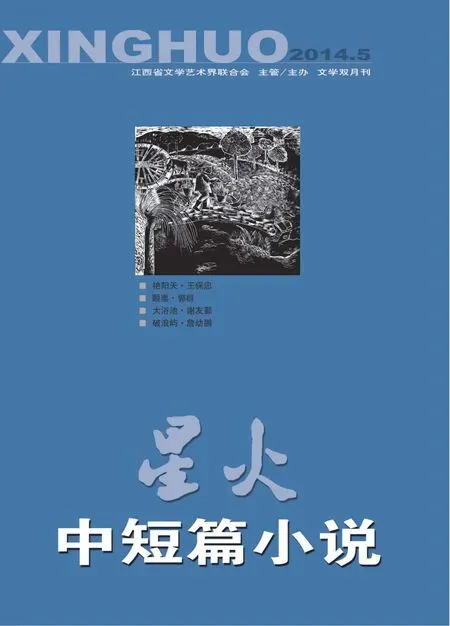小徒弟
□ 范雪明
准备下班,一位穿军大衣的中年人推开了门。
剃头吗?
你明天来吧。罗宝忠说。他在打扫卫生,一绺绺一截截的头发,被扫帚撵着跑,逼到门边,像几团黑色毛线球。
中年人堵在门口,没打算离开,说,明天早上我要出差,麻烦你剃下哩。
街面上的风很大,呼啸着扑进来,扫拢的头发弹跳几下又撒开,逐得满地窜。
罗宝忠拄着扫帚柄说,师傅们都下班回家,我是学徒工,担心剃不好。
中年人问,你拿过剪刀吗?
拿过。罗宝忠说。
那就行。中年人说罢随着风进了店子,身后两扇推拉门咣当来回摇晃几下又合拢,把风挡在门外。他脱下军大衣,打算在门边一把转椅上坐下,被罗宝忠制止,叔叔,请坐这里。罗宝忠指着靠近供暖管旁一把漆皮快脱光的椅子说。这是师傅刘大鼻的工作椅,平时罗宝忠跟着师傅打下手,整天绕着这把椅子转。
中年人屁股刚落在椅上,罗宝忠有点犹豫。他不是怀疑自己的技术,师傅偶尔不在的时候,自己也跟性子急的客人理过发。他是觉得下班后一个人给顾客理发不符合店里规章。
叔叔,你还是等下次剃吧。罗宝忠说。他把刚从墙壁挂衣钩摘下的白围裙又放回原处。
中年人没打算离开座椅,笑着脸说,小兄弟,帮个忙。
罗宝忠说,你改天来,我叫师傅跟你剃。
中年人皱起眉头说,我出差十天半月才回来,不能等,还是请你今天剃。
罗宝忠咂巴着嘴,显得十分为难。
我出双倍的钱,你看行不?中年人开始恳求。
不,真不是加钱的事。罗宝忠嗫嚅着。
小兄弟,来,别耽搁时间。中年人用手扯住罗宝忠的衣服。
罗宝忠被缠得没办法,只好重新取下白围裙,在空中扑扑抖搂几下,系在中年人胸前。他一手按住中年人的头顶,一手拿起电推剪,嗞嗞嗞沿着中年人后脑勺慢慢往耳鬓推。
罗宝忠虽然学徒不足半年,理发手艺还不错,二十分钟就完成了剪发、洗发、刮胡须到最后吹风的程序。中年人很满意,从上衣口袋里搜出一元钱交给罗宝忠说,谢谢你。立马起身离开座椅。
罗宝忠说,还要找你五角钱。
中年人说,不用找。披上军大衣,推门走出了店子。
罗宝忠捏着钱想追上去,但已经晚了,推开的门又咣当几下关上,不见中年人的踪影。罗宝忠忐忑不安地愣在哪儿,第一次私下收了顾客的钱,又没有人知道,瞬间有了做贼似的心悸。他后悔不该给人理发,万一被别人撞见,红口白牙说不清。转念他又想,只要自己堂堂正正做人,莫把钱贪污了,如实交公,也理亏不到哪里去。出纳员荣姐不在,不能把钱丢在桌上,只好先揣进裤荷包里,暂时保管,等明天上班时荣姐来了,再上交给她。
一九八三年的小城,只有一家国营理发店,位于老城的青龙街。店里只有十几名员工,平时来理发的人一般都要排队等候,赶上人多的时候要等大半天才能腾出空座位。一些工作忙的人,没有闲功夫待在理发店里耗着,习惯赶个早,趁师傅们没上班,提前来到店门前徘徊守候。师傅们也善解人意体贴顾客,不到八点上班时间,家里没什么大事,都会早一点进店。
罗宝忠是进店不久的学徒工,来自一个叫罗家岔的小山村。父亲原是县商业联合公司职工,因病去逝,正上初中的罗宝忠顶了父亲的职,安排在县饮食服务公司下属理发店学徒。罗宝忠为人忠厚本分,脏活累活都肯干,每天上班比师傅们来得早,有时还抢在烧锅炉的柯师傅前头。罗宝忠想,顾客来得这么早,不能让他们站在外面干等。他提前把店门打开,让顾客好有地方落脚休息,喝口水,看看报,感受到服务的温暖。进店门正对面的一堵墙上,不是横挂着一块写上“宾至如归”的玻璃匾额么?莫让人有空口说白话之嫌。
罗宝忠手里捏着两个萝卜饼,小跑着往理发店赶。天气很冷,到了店门前,他的鼻尖和两耳廓被霜风刮得紫红。几位郊区菜农稀稀拉拉蹲守在店门两旁,不停地打量过往行人,嘴里偶尔也吆喝几声。三五个准备理发的顾客站在门口,两手拢在袖子里,双脚在地上来回跺着,目光迎着街面左顾右盼。
小徒弟来了。有人一眼认出罗宝忠。
罗宝忠把门打开,几名顾客嘴叫着冷死了冷死了一齐拥进店子。
不一会,锅炉工柯师傅来了,见罗宝忠边啃饼子边拿鸡毛掸子清洁转椅前一排镜子,说,宝忠,店里的煤球烧完了,你今天帮我一起去拉煤球吧。
罗宝忠点头说好,随后又补了一句,让柯师傅跟他师傅刘大鼻说一声。
柯师傅笑着说没问题。
罗宝忠咽下最后一口萝卜饼,师傅们才陆续走进店子。刘大鼻来得稍晚点,他年纪大,比不上年轻人,走路迟缓,一步一挪腿,担心摔了跤。柯师傅告诉刘大鼻,要带罗宝忠去拉煤球。刘大鼻把手轻轻往前晃了两下说,去吧去吧。
柯师傅从后面仓库里扛起板车轮子,走到店门外,把倚在墙壁上一副板车架慢慢放平,使车架中间两个平行相对的半月型卡口,对准轮轴,严严实实合上。
柯师傅拉着板车在街上往前走,罗宝忠跟着后面小步跑。罗宝忠没来学徒前,跟着柯师傅拉煤球的人是周小兵。周小兵也来自农村,与罗宝忠紧邻的一个乡。父亲周升喜原是位理发师傅,比刘大鼻进门还早两年。前年得了风湿病,提前办了病退手续,让正读高二的周小兵中途辍学进城当了名工人。周小兵开始不肯学理发,父亲劝导他说,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不管什么人,都少不了理发。平时在台上拿腔捏调作报告的领导,到理发店转椅上一坐,任凭你摆布,你摸了他的头,他还得找你一句谢谢。店里过去几名员工因为给领导理发理得好,得到领导的赏识,提拔当了经理和局长。上个月,公司经理与食品公司经理进行了对调,新来的经理叫胡瑞生,年轻时在理发店学过徒,师傅就是周升喜。胡瑞生很幸运,出师不足一年,刚赴任的县长来店里理发,一眼看中了他。胡瑞生理发让县长十分满意,每次来理发点名要胡瑞生。一来二往关系密切,有时县长忙没时间来店里理发,胡瑞生就收拾工具背起箱子登门服务。后来县长任了书记,把胡瑞生提拔为公司副经理,副经理位子上没干满两年,又把他调到食品公司转正当了经理。这次胡瑞生回到公司任经理,也算是衣锦还乡。上任不足一个月,他对公司中层干部进行了一次小调整。公司团支部书记调到大众食堂当主任,腾出的位子让周小兵顶了,胡瑞生算是知恩图报。
煤球厂距青龙街约四五公里,位于城郊的黄土岭。路程虽说不远,却要翻越几道陡峭的高坡,走走歇歇,一个来回要一小时,加上开票、排队、上车到回来搬卸煤球,一上午也只能跑两趟。柯师傅在路上对罗宝忠说,快过元旦了,今年的煤球票没用完会过期作废,他打算趁天还没有下雪,路好行走,把煤球全买回店里。罗宝忠说柯师傅你想得真周到,你比莫主任有责任心,有时觉得莫主任不像主任,你才是主任哩。柯师傅赶紧掐断罗宝忠的话,宝忠你别瞎唠叨,这话要让莫主任听见了会给你小鞋穿。罗宝忠笑着说,我只跟你一人说,别人又不知道。柯师傅说,你能保证我不去跟别人说?罗宝忠说,你真要说出去不是个傻瓜。柯师傅笑嘻嘻地说,别看你鬼点大,人倒还蛮精明的。莫主任叫莫三秋,是理发店的负责人,柯师傅和罗宝忠出门时还没见他来上班。莫主任平时喜欢喝酒打麻将,习惯熬夜,早上起不来,职工们都能理解,心里有怨言也只能憋在肚子,他是主任,得罪不起。
柯师傅嘴上强调不去议论领导,可走了一段路,自己也忍不住说起莫主任。宝忠,你晓得吗,莫主任为什么总爱往厕所里跑?
罗宝忠瞅着柯师傅忽然变得神秘的脸,摇摇头说不知道。
柯师傅放缓脚步,叫罗宝忠靠近他。罗宝忠从后面跑了几步跟上来,柯师傅两手握着车把,边走边挨着罗宝忠耳朵低声说,我看你平时不多言多语,这事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可千万不能说出去,莫主任上厕所是借口,他目的是偷看女厕所那边的人拉屎撒尿。
罗宝忠显得十分奇怪,说,隔了一堵墙,什么也看不见呀。
柯师傅说,那墙中间有两块砖是活动的,需要时可以抽出来,一般人发现不了。
你怎么知道?罗宝忠说。
那两块砖是莫主任撬开的。柯师傅说,我也是无意中撞见的,有次我去上厕所,看见有个人两脚踩在墙边蹲位水泥挡板上,手里拿把起子,正埋头抠砖缝,见有人进来,突然慌里慌张地跑下来,我一看,是莫主任,他不敢拿眼正视我,低着头悄悄溜走了。
罗宝忠心里觉得好笑但没有笑出来,怪不得莫主任可以对理发店任何人吹胡子瞪眼,唯独对柯师傅总是很客气。
柯师傅和罗宝忠拉着满满一板车煤球,从郊外的煤球厂吭哧吭哧往青龙街走。柯师傅昂头咬牙躬着腰勒紧绳子往前拉,罗宝忠在后头踮起脚尖脸红脖子粗地用力推,上坡脚挪步,下坡慢步跑,平路快步走,一天来回跑了四趟,中午赶不上公司职工食堂吃饭,只得在路边小店买几个冷馒头凑合一顿。卸完最后一板车煤球,天完全黑了,店里的师傅们都已下班。与柯师傅分手后,罗宝忠独自往宿舍走,街面上的灯都亮了,刺骨的寒风迎面袭来,把粘附在脸膛和头发中的煤碴吹进眼睛里,像石头硌了一样疼,半天撑不开眼。忙碌了一天,刚歇息下来,突然觉得累,仿佛身上骨头快散架,难以支撑起整个躯体,在食堂打饭时,两手拿着碗筷竟然有些颤抖。罗宝忠吃罢晚饭,去宿舍拿几件衣服和一条毛巾,拎只白铁皮水桶,去了洗澡堂。
罗宝忠返回宿舍,拿着衣服正往脸盆里丢,准备端到外面水龙头下洗。他清理裤荷包时,发现顾客给他的一块钱,心蓦地一阵惊悚,砰砰砰狂跳起来。糟糕,忙了一整天,正经事倒忘了,钱没有及时交给荣姐。罗宝忠越想越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贼,偷了店里的钱。做贼是从偷鸡蛋开始,母亲小时候经常这样教育他。一块钱虽然数额不大,却能说明一个人的品德问题,他不希望让一块钱玷污了自己的灵魂。他想明天上班一定要把钱交给荣姐。
洗完衣服,罗宝忠早早地睡了。累了一整天,泡过热水澡后,人更显得困乏,罗宝忠钻进被窝,很快进入梦乡。迷迷糊糊中,他听见房门被推开,周小兵回来了。罗宝忠和周小兵同住一间房。罗宝忠没来的时候,周小兵与大众食堂的一位红案厨师住在一起。厨师有家室,老婆在乡下,每月都要进城与厨师团聚,周小兵只好找公司其他单身职工凑合几晚。次数多了,周小兵也心烦,厨师老婆来了,他偏不走,睡在床上,把头捂在被子里,想睡却睡不着,越睡头脑越清醒,对面床上每一个声音,他都听得一清二楚。有一夜,他听见厨师老婆叫声很凄惨,像一个行将断气的人在作垂死挣扎,周小兵唯恐出人命,猛地掀开被子扯开嗓门喊救命。厨师和他老婆吓得蜷缩一团,大气也不敢喘,一夜相安无事。从此,厨师老婆来的次数减少,偶尔来了,也不在宿舍住,厨师把她领到外面小旅社去。后来,罗宝忠来了,公司给厨师单独分了一间房,安排罗宝忠和周小兵住一起。罗宝忠来后不久,周小兵交了一个女朋友,姓严,在百货公司工作,隔三差五来找周小兵,有时晚上就与周小兵睡在一起。罗宝忠见小严来了,会主动离开,只要看见宿舍的灯是灭的,罗宝忠宁愿在门外长时间蹲守,也不开门进去睡觉。有次周小兵和小严早上起床打开门,发现有个人躺在门边睡着了,走近一看是罗宝忠,心里十分感激,心想这位小兄弟真够义气。
周小兵进门时裹着一身酒气,长一声短一声地打嗝,咯出的气冲出来醺人。去公司任团支书后,周小兵的应酬开始增多。胡瑞生到下属门店检查工作喜欢带着周小兵,公司来客也经常叫周小兵作陪,一星期在食堂吃不了几顿饭,在酒桌上混得多。周小兵打开灯,见罗宝忠睡了,觉得奇怪,蹑手蹑脚往里走,担心惊醒了罗宝忠,但罗宝忠还是睁开了眼。周小兵说睡了。罗宝忠嗯了一声。周小兵说八点钟就睡觉。罗宝忠说有点不舒服。
周小兵忽然发现罗宝忠面色潮红,问他是否喝了酒。罗宝忠摇摇头说没有。周小兵走近床前,伸手在罗宝忠额头上摸了一下,说,怎么这么烫,你发烧了?罗宝忠说他开始觉得累,睡了一觉后头开始痛,估计是感冒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罗宝忠觉得头重脚轻,四肢乏力,去趟厕所,又爬进被窝继续躺下。周小兵吃罢早餐,从食堂端碗稀饭拿两个馒头放在罗宝忠的桌上。罗宝忠两眼无神地看了眼,说声谢谢,没胃口去吃。
小兵哥,我今天不上班,你跟我向莫主任请个假,也对我师傅说一声。罗宝忠说。
周小兵说没问题。他准备出门,忽然又回头说,宝忠你最好去医院请医生看一下。罗宝忠说不用,隔天会好的。
过了三天,罗宝忠才去上班。刘大鼻看见罗宝忠面色苍白,眼眶凹了进去,说,病没好,干脆再休息两天哩。罗宝忠说,没有事,好了。刘大鼻说,我看你也好不了哪里去,风都能把你刮倒。罗宝忠说,师傅你放心,我能干活。刘大鼻刚给一位顾客剪好发,罗宝忠忙上前领着顾客去热水龙头下冲洗,正往顾客头上打肥皂,柯师傅先看见了他,说,宝忠你病好了?罗宝忠说好了。怪我那天不该叫你去拉煤球,让你累病了。柯师傅觉得内心愧疚。罗宝忠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脱。两手在顾客头发上揉出一堆白色泡沫。罗宝忠拧开水龙头,飘着热气的水哗哗流出来,很快冲走了顾客头发上的肥皂泡。莫主任走过来,对罗宝忠说,病好了。罗宝忠点点头。柯师傅打算回锅炉房,见莫主任来了,把头凑近了说,莫主任,宝忠是个好青年,你要多栽培。柯师傅好眼力。莫主任笑着说。在理发店,莫主任可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不能不在乎柯师傅。
罗宝忠取来一条干毛巾,摊在顾客湿透了的头发上,叭拉叭拉用劲擦着。等顾客重新坐回刘大鼻的转椅上,罗宝忠手脚闲下来,觉得该去找荣姐。正打算往荣姐那里走,罗宝忠忽然犹豫了。时间过了几天,再去交钱,让人心存疑虑。今天不交钱可能比交钱好,交了钱心里反而不落拓,不交钱,又没有人知道,不说出去,跟没有事情发生一样。如果真的交上去,是交一块还是交五角?交一块是多交了,交五角留五角,等同钱没交。罗宝忠心里很纠结。他又想,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八块钱,一块钱是三天的伙食费,数目也不算少,不要白不要。罗宝忠横下一条心不打算交出钱。做出这种决定,让罗宝忠一整天闷闷不乐。师傅刘大鼻见罗宝忠一副丢魂落魄的样子,说,宝忠,你这次病得还真是不轻,到现在还没恢复。罗宝忠咧着嘴尴尬地笑着,没吱声。
晚上罗宝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睡睡不着。周小兵问他是否又病了。罗宝忠说没病。周小兵说你好像有心事。罗宝忠呐个呐个没说出来。周小兵说,宝忠,有事别总搁在心里,会憋出病的。罗宝忠想想,又想想,最终还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说给周小兵听。周小兵听后,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惊讶,轻描淡写地说,一块钱也够不上犯罪,交不交我看都是那么回事,我陪客吃餐饭,光烟酒都要花十几块哩,宝忠,别为一点针鼻大的事想不开。罗宝忠还是放不下,郑重其事地说,小兵哥,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也一直把你当哥看,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现在晓得了,只能烂在肚子里。周小兵说你小兵哥不是那种缺德卖良心的人。罗宝忠心里也就踏实了。
过了元旦,离过年的日子一天近一天。小城人按习俗,开始剃年头。每天来理发店的人络绎不绝,想理发的人要排很长的队。理发店几条长板凳不够用,莫主任想得周到,通过胡瑞生打招呼,把赤乌饭店会议室三人座的靠椅临时借来,摆放在店子中间,一条挨一条拢成个口子型,供等候理发的人坐。顾客坐着没事,嘴却没空闲,相互传递小城最近发生的大事。目前,全国上下正在积极开展一场“严打”运动,小城的“严打”工作不甘落伍,正轰轰烈烈地进行。一个穿中山装的人说,这次“严打”不留死角,犯了罪,抓住都会判刑。旁边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接过话说,听说要重判,而且抹面无情。穿中山装的人说,是呵,平时犯罪判十年二十年的,“严打”期间会判死刑或死缓。另外一位穿旧军装的人跟着插嘴说,你们晓得不,明理巷有个十七八岁的伢儿,夜里在电影院门口,抢了一块钱,被抓了起来,听说要判十年。络腮胡子说,是呵是呵,边街上前几天抓了一名小偷,只偷了几包香烟,据说要判两到三年。穿中山装的人说,这次“严打”县里还下指标任务,没按时完成任务的单位要受处罚。已到年关,一些单位眼看完不成任务,只好抓住芝麻当西瓜。有个单位通过检举揭发排查摸底始终没捞到线索,领导坐在办公室苦思冥想,忽然一拍大脑,想起前不久单位一名职工与老婆在大街上吵架,男人一拳挥过去,把女人眉骨处蹭开寸把长的口子,去医院缝了几针。因此把男职工当行凶犯,送进了公安局。
罗宝忠听见这些话,心里怯怯的,像有几把锋利的刀,直逼鼻尖,闪射凛凛寒光。他已坐失良机,澄清事实的渠道被自己关闭。现在他只能听天由命,心存侥幸,寄希望没人知道。但他还是惶惶不安。
罗宝忠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胡瑞生因为没有完成“严打”任务如坐针毡。“严打”工作是硬性指标,不能如期完成,说轻点是工作能力差,说重点属徇私枉法,能力差徇私枉法的领导,其所在单位一概不能评优,没有评优的单位领导不能提拔重用,有通天的本事也无济于事。年底商业局班子准备调整,胡瑞生是副局长的热门人选,这个节骨眼上,他不希望工作上出现任何纰漏,可偏偏摊上这件大事。这一些,周小兵都看在眼里默在心里。胡瑞生曾私下对他承诺过,小兵,你好好干,我升了副局长,提你当副经理,等我升了局长,再提你当经理。美好的前程在向周小兵招手,在权欲和个人利益面前,朋友之情十分脆弱,周小兵检举了罗宝忠贪污的真相。胡瑞生听后兴奋得从座位上站起来,对周小兵说,你怎么不早说。马上拿起桌上的电话,要总机接通设在公安局的严打办。
两名警察接到通知后,迅速朝青龙街方向正步走来。
街上的群众纷纷停下脚步,用奇怪的目光瞅着全副武装的警察,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人感到遗憾,不知是谁家的伢儿要倒霉,撞到枪口上。有人拍手称快,抓得好,让犯罪分子无处藏身,天下才太平。
警察在饮食服务公司门前停下,与经理胡瑞生简单交谈了几句,随后,又昂首挺胸向理发店方向走去。
警察刚推开店门,那些坐在椅子上闲聊的顾客立马抿住嘴,把目光投向大门。裹着凛冽寒气的北风呼地扑进来,让室内温度骤然下降,许多被暖气烘热的顾客不由打个寒噤,连忙披上刚脱下的棉衣。
谁是罗宝忠?一位长着马脸的警察厉声问,冷冷的目光同时在室内漫无目地扫几下。
师傅们都停下手中的活,瞅着罗宝忠,顾客也跟着把目光转向罗宝忠。室内开始有点骚乱,夹着嘈杂声,坐着等候理发的顾客,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
罗宝忠手里拿着一只电吹风,正打算跟顾客吹头发,听见警察喊他的名字,一时手足无措,脸红一阵白一阵。
两名警察顺着大家的视钱,径直走向罗宝忠。
你是罗宝忠?一位矮个子警察问。
罗宝忠目光躲闪,慌乱地点下头。
带走。马脸警察说。
矮个子警察马上从腰带上摘下一副明晃晃的手铐,命令罗宝忠伸出双手。咔的一声,罗宝忠两只鸡爪样的手被拧在一起。
面对不期而遇的各种眼神,罗宝忠羞愧难当,万念俱灰,心想不如一死了之。几把指向鼻尖的刀刃似乎正刺进眼眶,他恍惚嗅到一股血腥味。
店子里一下又静了。嗞嗞嗞响的电推剪、呼呼叫的电吹风和嘀咕的人语声,顷刻消逝,只听见一座连接管道供暖用的煤球炉上,煮沸了的一铝壶水,正噗噗噗有节奏地掀动盖子。
在场的人都以不同的心情目送罗宝忠被警察带走。当理发店两扇活动大门在警察身后来回开关几下复又合拢,店子里像一锅沸腾的开水,又热闹起来。
这回唱主角的是店里的职工。
嗓门最大的是锅炉工柯师傅,他说,是不是搞错了,宝忠这么老实的伢,怎么去干犯法的事?
刘大鼻一脸惆怅,声音低沉,唉,宝忠这伢算是完了。
莫主任说,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表面忠厚本分的人,不一定全是好人。
罗宝忠被送进拘留所,负责审讯他的警官姓钟。钟警官翻阅了罗宝忠的材料,通知看守警察把罗宝忠带到审讯室。钟警官堆着一脸横肉,说话却柔声细气像女人,罗宝忠,你本该有机会把钱交出来,完全可以避免一场犯罪。
罗宝忠说,我是打算第二天交钱,可是一上班,柯师傅突然叫我一起去拖煤球,一拖就是一整天,把这事耽误了。
那你还有第二天第三天呢。
后来几天我生病了,没有上班。
病好后,你不是又照常上了班。
我,我。罗宝忠嗫嚅着,有口难言。
事实证明你还是有贪污动机的。钟警官说完后叹了口气。
罗宝忠的母亲丁桂香知道儿子被抓后,搭上一辆运煤的货车,连夜赶到县城。她找到莫主任家。莫主任打开门,看见蓬头垢面一身煤灰的丁桂香,吓了一跳。仔细看,认出是罗宝忠的母亲,连忙客气地让进屋里,搬只方凳让她坐下。
莫主任,帮帮我伢吧。丁桂香说。
这件事我还真插不上手。莫主任说。眼睛盯着丁桂香棉衣下依然高耸的胸脯。当初丁桂香送罗宝忠来上班,莫主任见过她,是位很有丰韵的女人。你不是有亲戚在公安局吗?丁桂香说。“严打”期间,估计也帮不上。莫主任说。丁桂香从挎在肩上的一只绿色帆布书包里,拿出一只塑料袋,里面装了三十几个鸡蛋,对莫主任说,我们乡下人实在拿不出好东西孝敬你,莫嫌弃。不客气,不客气。莫主任用手推,动作也夸张,有意碰撞丁桂香的胸口,柔软的,有弹性。丁桂香说,是少了点,十天才积攒这么多。不少,不少。莫主任意犹未尽,脑子仍放不下丁桂香的胸脯。他突然说,你把衣服脱下呗。丁桂香知道莫主任想耍流氓,但有求于他,又不便断然拒绝,故意岔开话,嫂子呢?她说话时眼睛有意瞥着房门,希望救星出现。莫主任涎着脸哂笑说,嫂子上夜班,天亮才回家。莫主任一直夫妻俩过日子,不知是谁的身体出了问题,结婚多年未生小孩。丁桂香显得既害羞又无奈。莫主任忽然把门关上,一双手准备往丁桂香胸前钻,丁桂香赶忙起身往后躲闪,说,莫主任,不,不能这样。莫主任说,你别怕,我又不吃了你,把上衣脱下让我看一眼,别的事我不能做。丁桂香考虑到儿子的命运一半是捏在他手中,开始妥协了,她相信莫主任讲了真话,慢慢解开了棉袄,又脱下毛衣和贴身内褂,胸前两堆丰盈的白肉哆嗦着袒露出来。莫主任睁大眼睛,心花怒放,一双冰凉的手不由自主地扑上去,在丁桂香那对温暖撩人的乳房上慌乱而幸福地抚摸起来。他索性抱住丁桂香,用嘴去嘬她胸前两颗鲜活的紫葡萄。突然,他停止了动作,开始气喘起来,双手软绵绵地拥着丁桂香。丁桂香表情羞涩,莫名其妙地问莫主任,好了?莫主任忙缩回手说,好了。又坐回凳子上。丁桂香立马穿上衣服,对莫主任说,我走了,伢儿的事要你费心。莫主任心不在焉有气无力地说,好,好。
丁桂香走出门,天上开始飘起了雪花。白得像棉绒似的雪花,漫天飞舞,大街上很快积攒了一层薄雪,脚踩下去,留下一个浅浅的鞋印,迅速又让雪花覆盖,露出一个模糊的轮廓。丁桂香缩起脖子在雪地里行走,打算先找家小旅馆住一晚,明天再去看守所与儿子见面。她想儿子一定能够平安出来,儿子是冤枉的,这漫天的大雪正是来给儿子洗刷清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