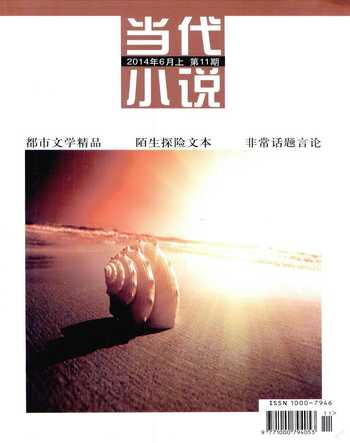现实压迫下的人性坚守
伍润泽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很喜欢的一句话。人生与旅行何其相似,旅行的精彩在于可以经历许多意想不到的美丽,而人生的绚烂也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这一时的平稳安逸,下一时的惊涛骇浪:这一时的孤掌难鸣,下一时的春风得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应该是人生旅途中最让人兴奋的时刻了。人们总在不断前行,却往往遗忘了出发时的初衷。偶然想起,也会被残酷的现实又摁回心底。说破了,人不过是在找一个让自己的肉体和心灵都可以安放的地方,但我们又不愿得过且过,所以谁也不愿停下前行的脚步,总以为前面还有更美好的风景,更安逸的归宿。人们就在这样的期盼中不断前行,在前行中渴望停留。
刘庆邦《合作》,《北京文学》2014年第4期。
刘庆邦作品的写实效果着实让人惊叹,这大概来源于他的生活经历,刘庆邦当过农民。也干过矿工。所以他对普通人,或者说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处境和心理状况都描写得入木三分。《合作》把视角对准了一对生活在北京的底层男女。贺品刚是一家私营企业的员工,属于比较典型的“北漂”一族,为了省下外出租房的钱,他以每个月三千块钱的价格寄居在金子华家里。二人的合住生活就此开始。贺品刚和金子华的合住正应了四个字——各取所需,贺品刚住在这里,可以不用再到处找房子住,不用再为一日三餐操心,还可以在每个星期三星期六和金子华“做好事”,发泄自己的欲望。而金子华离婚后带着四岁的女儿小雨,她什么都没有,只有这套房子,前夫给的一个月一千块的抚养费显然是杯水车薪,所以她需要贺品刚这三千块钱,另外,她还需要贺品刚这个人,这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用她自己话就是“取他的阳,补一补自己的阴”。二人毫无感情基础,这种逢场作戏的关系随着贺品刚的父亲的到来受到了最大的考验和挑战,在“见面礼”的诱惑下,金子华答应贺品刚把戏演好,骗过贺品刚的父亲。也正是因为这份“见面礼”。贺品刚还要求金子华在“做好事”上加了个班。二人的合作,有时让贺品刚也会产生错觉,感觉他、金子华、小雨真的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但假戏并没有真做,二人的合作关系在那一年下第二场雪的时候结束了,贺品刚不得不又踏上寻找新的租住地的征途。小说结构简单,却在平淡的叙述中直击人性的虚伪与贪婪,写出了现实压迫下人们的无奈,贺父的那句话“看来不管哪一辈的人都有难处,走到哪一步都是难”,应该是作者发自内心的感慨吧。
王凯《流氓犯》,《长江文艺》2014年第3期。
与其说有时我们不愿去找寻真相。不如说是我们不敢接受残酷的现实,甚至在我们已经预知了真相之后。都没有勇气去捅破那层窗户纸,宁愿继续装作被骗的样子。《流氓犯》正是在这种纠结中摸索着前行。“我”因酒后打人,被发配到了“相当于唐之岭南清之宁古塔”的四营。但酒后打人是“我”故意为之,因为被打的人欺负的是“我”最爱的女人。高梅。在四营的澡堂,“我”见到了那个因为猥亵女兵被发配到四营的流氓犯,而他猥亵的对象恰恰也是“我”最爱的女人,高梅。因为这个原因,我对他恨之入骨,在出黑板报的时候,“我”借机狠狠地报复了他,但这并没有让“我”的内心里得到宣泄或者些许安宁。反而让我心生不安。后来在“我”犯阑尾炎求医治病的过程中,流氓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也在指导员的鼓动下,买了两瓶好酒去向流氓犯表示谢意,这应该是“我”和流氓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接触,但这接触并不愉快,在不愉快的背后。“我”又仿佛知道了某些真相,某些让“我”不愿意接受的真相。后来高梅走了,带着被“我”打的那个人走了。也或许不是,可能只是他们碰巧坐同一辆车。但这些都不重要了。流氓犯也走了,是“我”送他去办的复员手续,当火车开动的瞬间,他的面目变得扭曲,这是他留给“我”最后的印象,虽然“我”还有太多问题。想知道太多真相。但一切都在那一刻结束了。真相往往更加残酷,或许我们不是没有勇气去揭穿。而是不愿让彼此难堪。因为至少在这个过程里。我们都得到了成长和历练。小说行走在点破与不点破的边缘线上。撩拨着读者的思绪,作者对火候的把握异常精准,点到为止的写法让人感觉作者欲说还休,却又觉得对作者的心思了然于胸。这种感觉,可谓妙极。
俣晗《颤动的日光》,《长江文艺》2014年第3期,《小说选刊》2014年第4期转载。
正如侯晗自己说的。“我是个坚定的存在主义者。我所有的小说都是为了挖掘人存在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所以,她的小说,真实是最高要求,也是最大特点。侯晗努力去挖掘人们心中最深层的感受,最原始的冲动,最纯粹的想法,最本真的诉求。这篇小说追问的是如何平衡物质与情感、奋斗与享受之间的关系。平心而论,这个主题已经被写厌了,不仅作家在写,社会学家、伦理学家、甚至种种所谓的批评家也在写,因这的确是当今这个“一切向钱看”的世界急需解答的问题。但这又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小说中的一对夫妻就存在这样的分歧。鲍玲是从底层慢慢拼出来的挣钱能手,对于生意和投资有天生的兴趣与敏感度。陈曙晖是广州一所大学哲学系的教师,虽然没有被哲学完全弄糊涂,但多年受书生气的熏染。对物质和金钱都不热衷,他反而更喜欢孩子,喜欢下厨做菜,喜欢享受生活。价值取向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巧妙地生活在一起,陈曙晖不反感鲍玲只顾赚钱。至少不会把反感表现出来。鲍玲也不会计较陈曙晖教冷门专业。挣得还不如她的一个零头。本以为生活在这种巧妙的配合中会一直进行下去,但一起车祸让这个三口之家瞬间支离破碎,这起事故夺走了陈曙晖和儿子的生命,对于鲍玲来说,她的生命仿佛在那一刻也一起结束了。鲍玲重新来到他们一家曾经度假的地方,她不再去看楼盘。不再关心什么海景房,她只想去看看当时没有陪丈夫和儿子去看的日出,去回忆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曾经。初读作品时,感觉作者前期做的铺垫有些过于冗长。但熟读几遍后,却发现这样的安排可以让前后的反差更大。让鲍玲的反思更深入,才发现作者的匠心独运。作者安排的这个结局不免让人感觉有些残忍,但如果不用残忍的故事去敲击每个人的心灵,不用痛苦的感受去刺激每个人的神经。那么,像文中这样残忍的故事将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发生。
金少凡《情归何处》,《北京文学》2014年第4期。
所有的故事起源于一次小学同学聚会,彭海在不知怎么三弄两弄就去了的情况下,和自己三十年前最爱的那个女生李彬彬又产生了交集。李彬彬的倩影始终保留在彭海的脑海里,在他曾经的日记里,李彬彬出现了三次,都是和当年插队有关的记忆,惟一留下的物证,就是两块李彬彬给彭海的红虾酥糖,彭海一直舍不得吃,直到糖融化,变形。重逢后两个人又纠缠在了一起。虽然要经受彭海妻子的不断滋扰和李彬彬丈夫每隔一段时间的定时侵入,两个人还是坚持着这份或许本就是个错误的爱。但错了终究还是错了,两个人嘴上所说的渴望在一起,被他们各自的所作所为击得粉碎——彭海放不下孩子,与妻子始终藕断丝连。甚至在李彬彬去陪归国的儿子的时候。又和带刺玫瑰干柴烈火起来。而李彬彬因为孩子。也不得不与丈夫继续硬拼成一个完整的家庭。爱与现实始终不能协调一致。彭海是爱李彬彬的,不然也不会舍不得吃她送的糖,舍不得拆开她叠的衬衫,舍不得穿她洗的白袜子。李彬彬也是爱彭海的,不然也不会哭得那么惨,那么声嘶力竭。小说情节并不曲折,叙事平易质朴,作者在一些细节处理上下了功夫,李彬彬的黄色皮鞋。彭海和老婆办完离婚手续她的那句“谢谢”,带刺的玫瑰来电话时彭海的随机应变。都让人感觉恰到好处,又满含心酸,通过这些描写,作者把彭海和李彬彬这两个感情中的流浪者写活了。
毛胜英《钥匙》,《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2014年第3期。
自我根本上是一个他人。作者探讨的不仅是现实问题,还包括现代人的自我寻找、自我分裂、自我认同等等有关存在的哲学问题。这是一篇让人匪夷所思又充满深意的小说,小说中的角色转换,亦真亦幻的写法让读者有些应接不暇。故事发生在一所学校的两名老师身上。作者毛胜英有从教经历,对于这类题材可谓驾轻就熟。但并没有因为熟悉而使这篇小说落于俗套。林小雪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名师商笑古。她有了商笑古的身躯。商笑古的面容,还拥有了商笑古的地位和威严——校长见了面开始和她打招呼,在办公室她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对学生她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同事也开始讨好她、巴结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林小雪这个才“来学校四年的老处女”从未享受过也无法企及的。她不再是林小雪,而变成了名师商笑古,哪怕她是顶着商笑古的一副皮囊而已。林小雪,或者叫商笑古,一直在追问别人“我是谁?”她抓破了学生叶小亮的脸,抓破了老师沈书韵的脸,但始终无法找到答案,也无法如愿去揭穿别人虚伪的嘴脸。文章用一种亦真亦幻的效果,讽刺的却是最为真实的社会。林小雪的疑问我们无从回答。我们谁也没有能力去抵抗整个社会,当社会变了样,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量保持本心,尽量不随波逐流。作者精心挑选了两个在各个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的人。形成强烈的反差效果,就像一面镜子,轻松照出生活本相。身份转换,则意味着自我迷失,每个人走在现实的丛林之中,渴望自我实现梦想,却又不得不面对各种假面、各种压抑,小说以很独特的视角,拉开了社会现实的帷幕。
孙频《假面》。《上海文学》2014年第2期,《小说选刊》2014年第4期转载。
与之相似的小说,还有孙频的《假面》,作者也是通过近乎于折磨读者的故事情节和叙述方法,抽丝剥茧般探究人性,拷问人性。李正仪是一个失败者,至少在爱情方面是。他一次又一次被当众拒绝。当他已经对这受辱产生免疫的时候,王姝的出现。满足了他在女人身上的一切愿望。王姝在李正仪学校后门卖包子,人长得漂亮高挑,皮肤白皙,在李正仪几次试探性的追求后,他们走到了一起。而王姝惟一的缺点就是曾经被人包养,这也是李正仪心中始终无法逾越的一道心理障碍。正因如此,李正仪不愿让王姝和他在校园里同时出现,不愿陪王姝去那他感觉格格不入的商店买衣服,他更愿意在折磨王姝的过程中得到快感和满足,他在心理上折磨她,在生活中压制她,在做爱时凌辱她。只有这样李正仪才感觉惬意一些。后来。这个心理障碍让李正仪近乎疯癫,他不再满足于凌辱王姝,反而醉心于让‘自己受辱,甚至接受了室友们观摩他和王姝做爱的要求。种种荒唐举动,全被李正仪当做对王姝被包养的惩罚,但他在惩罚王姝的同时,却毫无顾忌的“吃她的,喝她的,住她的,睡她的”,甚至连他的工作都是王姝出钱找的。在这种惩罚王姝与享用王姝的矛盾中。李正仪渐渐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他和王姝在天津的封闭生活被室友王建的到来打破了,李正仪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王建却把他最后抓的那根稻草也割断了,故事只能以彻底的悲剧收场。上天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李正仪的疯狂,与其说是王姝带来的,不如说是自找的,心里的坎过不去,必定会摔得很惨。文章的开头像青涩的校园爱情故事,中间急转直下变成了声色俱厉的人性拷问。结尾的犯罪现场又犹如给读者的当头一棒,不免让人心中一颤,思绪万千。
周瑄璞《雇佣》,《作家》2014年第2期,《小说月报》2014年第4期转载。
《雇佣》很少见地选取了姐妹两个人之间的故事,来展现看似牢不可破的亲情,有时也变得那么脆弱不堪。妹妹的工作很忙,无暇料理家务,她常对别人说的就是:“请你记住,最大限度的节约我的时间。”这句话她对别人说,倒也无可厚非,但现在她开始对自己的姐姐说,因为姐姐接受了替妹妹收拾房间、做饭、打扫屋子的工作。姐姐不再像以前一样进门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惬意地和妹妹聊闲天,现在的她开始关注“抹布在哪,哪个盆是洗什么的,哪个菜板是切肉的,哪个是切菜的”。事实上,姐姐变成了妹妹家的佣人。妹妹也渐渐接受了这样的身份转换,她开始计较姐姐往盐盒里倒盐倒多了,菜叶撕得过大,姜、蒜、辣椒没有切好,还埋怨姐姐只把饺子馅拌好了而没有包,真气不过了就给姐姐打电话,把那句名言再说一遍——“我请你来,是为了节约时间的。”不过,身份甚至是地位的变化并没有让姐姐减少对妹妹的爱,她对妹妹家各个房间的定期巡视,让她对妹妹家的一橱一柜、一碗一筷都了如指掌,特别是那个妹妹和妹夫记录收入和支出的小本。简直让姐姐变成了妹妹家的财政监督员。但妹妹不知道这些,即使知道了可能也不会去理会这些小事,因为她的时间太宝贵了。是不会浪费在这儿的,姐妹俩的关系就在这种关心和忽视的不对等中渐行渐远。周瑄璞对姐妹俩的心理描写构成了这篇小说的一大亮点,姐姐看到妹妹的收支记录本上有一大笔进项时的兴奋,妹妹在打电话责怪姐姐之前心中的纠结,都让人印象深刻。小说细致地写出了人物性格微妙的渐变过程,在复杂的情绪缠绕中。人物形象逐渐变得生动饱满,呼之欲出。
庞善强《蓼儿坎》,《山西文学》2014年第3期。
蓼儿坎是个地名,一个铺满了红蓼花的地方,但现在那里只有几户人家了,女人家就是其中之一。女人和男人像“两头配合默契累不垮的牛”,家里每年打的粮食不仅够吃,还能换些钱贴补家用,但儿子要谈对象,女人和男人的这点儿积蓄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正因如此,原本平静如水的生活被彻底搅乱了。女人在儿子无意中的一句话的提示下,义无返顾地去大医院卖肾,男人也去煤矿下井挣钱,但女人的肾没卖成。男人也在一次事故中被炸死了。但男人不是“炸死”,而是“诈死”,虽然只差了一个字,但后者可以让男人家拿到二十万的抚恤金。这之后,男人不敢再在蓼儿坎出现,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帮着收自家的庄稼,再后。女人家搬走了,去了哪儿,没人知道。小说的语言朴实无华,却字字含泪,句句带血,让人感动不已。初读这篇小说时,觉得小说写到男人被炸死就可以结束了。因为已经足够给读者以震撼,读到最后,方才领悟小说主旨,并非简单歌颂父母之爱。炸死之后又接诈死。小说从生活事件的记述,转入关注人性深层的裂变,把那个自称“心比蓼儿坎的石头还硬”的男人的变化揭示得淋漓尽致,所以说,诈死比炸死更让人唏嘘。男人变了,为了儿子,为了生活,他不得已地变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人性的坚守又有什么意义呢?小说末尾写“蓼儿坎又少了一户人家”,少的难道只是一户人家吗?作者隐于文字背后的呐喊,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张生《大堂》。《作家》2014年第4期。
不知为何。一直对文中使用真实的地名、街名的小说有特殊的好感,可能是因小说本身是一种虚构的文学形式。用真实的东西稍加点缀,多少可以增加它的在场感。当然,喜欢这篇小说不仅是因为它迎合我这种偏好,更因为它在写作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用“我”去修手机引出了女主角甘静。再用回忆的的方式慢慢交代了“我”和甘静交往中的一些记忆碎片。说白了,小说就写了一个农村小姑娘被上海吞噬,逐渐丧失自我的故事。小说中有两处描写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咖啡屋的尴尬约会。一个是酒店大堂的小三被捉现场。这也正是我所说的“独到之处”。作者没有作过多的铺垫,也没有摆弄许多曲折的情节,而是一把将读者拉入到一个真实的场景中。然后用全部的精力去描写场景中每个人的语言、动作、表情、心理。让每个人物竞相为读者表演,甘静不合时宜的装扮。颐指气使的神态;小李略显怯弱的语气,拘谨笨拙的动作:“我”不知所措的局促,英雄救美的勇气,都深深刻进了读者的脑海。有人会认为描写整个场景要比专注于写人物的某个或某些细节更凸显作者设计这个场景的真正用意,这就像普通灯笼和走马灯之间的区别。一个是只给人看一个面,一个却是把方方面面都展示给人看,但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场景描写的作用往往就被低估了。抛开小说内容,作者为女主角起的名字也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甘静——干净。叫做“甘静”的女人变得不再“干净”,不知是不是作者有意为之,这就任由读者自己去想了。
孙学军《老赵的头发》,《青年文学》2014年第4期。
头发,每个人头上都有,作者却用这司空见惯的东西贯穿起了整篇小说。老赵的头发又黑又亮,是天生的好发质,不留长了还真有点糟践了,并且飘逸的长发又恰好对应了他文艺青年的身份。朱有礼没有老赵的好发质,头发“就像盐碱地上生长的一簇簇乱草”。不光头发,朱有礼的工作也不如老赵。正因如此,老赵总感觉朱有礼在和自己比,而在对待柳燕妮这件事上,朱有礼更是半辈子都在和老赵拧着来。柳燕妮是幼儿师范的学生,朱有礼硬拉着刚失恋的老赵去认识一下,嘴上说的借口是喜欢柳燕妮的画。后来的发展作者没有直接点破,但我们大体可以推测,在柳燕妮这件事上,老赵应该又捷足先登了,也可以说在和朱有礼的又一次较量中,老赵又成为了胜利者。但是后来老赵和柳燕妮并没能在一起,柳燕妮去了南方。老赵娶了德贵叔家的淑梅。朱有礼的事业也命运多舛,本想借岳父之力调到镇政府工作,但没能如愿,接着又在企业改制的浪潮中下岗了。不得已去南方转了一圈。回来竟然咸鱼翻身般的有钱了,还做起了生意,不时约老赵一起吃饭,老赵早已没有了年轻时居高临下的气势,每次都随叫随到。柳燕妮的再次出现,或者也不能算出现。因为只是来了一通电话,但正是这次多年后的交集。让老赵彻底放下了过去,他不再千方百计地挽救自己的那寥寥可数的头发,干脆剃了个光头,也一并把原来的那些心结。年轻时的那些回忆都剃光了。老赵无疑是小说的主角。但朱有礼和柳燕妮的笔墨也并不少,特别是柳燕妮,她在文中的每次出现,都会对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产生巨大影响,这样的叙述甚至会让读者感觉真正推动故事发展的原动力不是老赵,而是柳燕妮。柳燕妮其实是胜利者的战利品,战利品的动向当然会牵动每个竞争者的神经,每个人都在为它奋力拼争,带着这样的幻化效果再去读小说,不禁感到妙趣横生。
娜或《将军的美人》,《作品》2014年第4期。
爱一个女人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她不在了。这份爱可能会无限放大为对每个女人的爱,但这时,我们就无法再分清这种放大化的爱是因为对原来爱人的怀念,还是出于单纯的色心。《将军的美人》就在这种纠结的心理状态下作了大胆的摸索和探究。将军把夫人唤作美人。一直叫到美人去世。美人得的病是胰腺癌,将军吼叫着质问医生,但一切喊叫都没用,美人在中秋之后走了。将军在美人最后的时光里。“对待美人像新婚一样耐心”,但这和以前将军常年不在家形成的巨大反差,更加让美人感觉到了自己这一辈子有多寂寞,美人一生都守望着将军,现在要走了,她想让儿子把自己的骨灰撤到长江里。随着江水到处去转转,弥补此生的遗憾,但这最后的愿望也没能实现。将军在美人死后第二年的春天和万物一起复活了,他又出现在广场上,周旋在中老年妇女当中,直到有一天一个不算老的男人找上门来。因为这件事。将军在广场上不再受欢迎,甚至是受人厌弃了。这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在这之后将军开始有了流口水的毛病,流得严重了只能给他围个围兜。更严重的还在后头,将军开始变得“不正经”,保姆和养老院的秀兰,要么被吓跑了,要么被吓得躺在房间不敢出来。最后“迫不得已”的儿子和女儿决定给将军服用雌激素,弄得将军“兜着围兜又兜起了尿不湿”,两年之后,将军睡着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他去找美人去了。作者设计的将军这些怪诞行为着实有点让读者难以理解,或说难以接受,因为作者貌似没有给出将军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样的变化只是因为老了吗?或许读者更愿意接受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将军对美人的爱之深切,生命中不能没有美人,美人走了,将军只能把对美人的爱付之全部女人,他渴望再将找到自己的美人。在这条主线之外。作者潜在的另一条线是将军儿子、儿媳、女儿的各怀鬼胎,尽管作者对他们只是点到为止,但已经足以引起读者的注意。让小说变得更加充实,厚重。
凌寒《自杀的女人》,《北方文学》2014年第3期。
这是一篇别具一格的小说,因为作者选取的视角足够特殊——小说通过一位自杀身亡的母亲死后,魂魄在自己家中的所见所闻,写出了生也咫尺天涯,死也咫尺天涯的情感悲剧。女人的孩子病死之后,女人也从窗口一跃而下,想去另一个世界追上儿子,但因为是自杀身亡,黑白无常不放女人的魂魄过去。女人的魂魄在屋里游荡,她不仅看得到男人,还听得到男人的心声。正因如此。女人知道了男人不让她买化妆品,不是因为男人小气,而是想给她买更好的。知道了男人母亲的势利一点儿也没有影响男人对她的爱。知道了她才是男人惟一的爱。孩子没有了可以再生。丈夫的一夜白头让女人感到了活着时从未有过的爱,也让女人开始悔恨自己这么鲁莽的就放弃了生命。放弃了男人。但女人毕竟是死了,无法再对活着人产生什么实质的影响,男人的生活也要继续前行。或许是女人的祈祷起了作用。他们的房子没有被男人卖出去,但容不得女人有些许庆幸。因为男人为这栋房子领回来了一个新的女主人。有些事情终究要翻篇。男人重新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女人也只能无奈的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她吊在天花板上就像在看一部波澜起伏的电视剧。不再有喜怒哀乐。作者以一个女作家对女性与爱情特有的细致敏感,藉亡灵叙事,呈现生活表象背后的内在世界。探究爱情及亲情的真谛,字字句句中渗透着丝丝入扣的柔美,不禁让人心动,而女人的叹惋与凄美心境又不禁令人心碎。
“人性不重要,生存才重要。”这是电影《男儿本色》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就像每个水杯能装多少毫升的水一样,是一分一毫都不允许改变的,一旦变了,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如登天,底线是人自己定的,当然也可以自己改变。这就给人留下了余地,而人类又是最会见缝插针的动物。现实从不会完全按照人们的意愿存在和运行,所以现实与底线之间的碰撞就变得在所难免,关键是在这个时刻,你会怎么选择——是坚守还是屈服。很遗憾,大多数人选择了屈服,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改变整个现实,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改变自己来迎合现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发出了心底的疑问: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人性的坚守到底还没有意义?——一个无从回答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我们都走在寻找答案的路上,这条路很长,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但也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早已有了自己的答案。(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