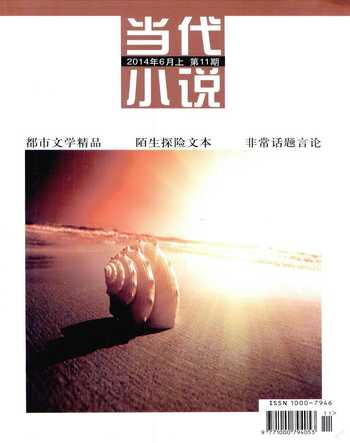暗流
羊亭
在乡村医生柯晟辉那间灰白狭小的屋子里,他看到妻子红霞正仰躺在铁架床上。她脱掉了薄衫。解开胸罩扣,袒露出一对丰硕的好乳。眼前顿时一片雪亮。柯晟辉胡乱披上了平素很少穿的白大褂,到红霞旁边坐下,堆了满脸猥琐的坏笑,之后两手便肆无忌惮地在她周身上下游移开来。
——他疲惫地从梦中醒来,长长嘘了口气。
一支烟吸完。人清醒了许多。回想起刚才的梦境,竟睡意全无。
怎么偏偏会是柯晟辉?如果梦里出现的是别人,兴许他翻一个身就接着睡了。但他一想到穿白大褂的柯晟辉,无论如何也难以成眠。以前,还没有出来打工的·时候,他就常常听到村子里传言关于柯晟辉的种种。人们讲他虽然只是个小小村医,三十五六了也没找个女人成家。却是何等的艳福不浅。譬如张家的疯女子总跑去他那间小房子里。絮叨心里发慌,疑心有人要害自己,柯晟辉便解开她上衣的扣子,一边给她揉胸口一边说:放松,放松,放轻松就不慌了嘛。或者李家的女娃得了痛经病。一来二去地请柯晟辉医治,结果却把人家好端端的处女膜给治没了。还有那个风骚多情的寡妇,男人死掉一年有余了。她居然产下一个七斤重的男婴,有人亲眼见过她一大早蓬松着头发从柯晟辉的诊所里出来……他们讲得绘声绘色,头头是道,然而那毕竟都只是传言,真真假假,不好确定。
他的身体历来强健,一两年都难得看一回医生,因此和柯晟辉少有交集。他拿不准柯晟辉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不过,前年春节回家过年,他曾听村里的朋友和红霞都讲起过一件柯晟辉的趣事:
那年的盛夏时节,村里会计为他家的傻瓜儿子娶老婆。全村几乎所有人都被请去喝喜酒了,柯晟辉当然也在其中。和他同桌的是几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酒喝到一半,大家都有了微醺之感。不晓得是谁起的头,一桌人谈论起正挨桌给大家敬酒的新媳妇来。
一个年轻人打着酒嗝说:会计的儿子便宜捡大了,看那婆娘的腰身,那眉眼,活像电视里跑出来的。
另一个说:求,你看新郎官是个能干活的料吗?我们的会计算盘打得响,搞不好便宜都让谁占呢!
这个说:可惜了可惜了,香喷喷的新鲜菜,还没动筷子就惹来苍蝇叮。
那个说:香不香鲜不鲜,光闻光看不上算,得吃到嘴里头嚼两口才晓得。
柯晟辉突然噗哧一声,笑得有点勉强也有点夸张,脸上却是鄙夷与不屑,等一桌子人都静下来了,满脸期待地望向他,他才不紧不慢地张口道:表象,表象,都不要被表象迷惑了。看着新鲜,闻着香,吃着爽口都是个屁,吃下肚皮身子舒不舒服、消不消受得了才是硬道理嘛。
大家听了觉得这话在理,但心中却更加迷惑了,于是都一副肫肫受教的姿态。吃菜喝汤也不弄出大的响动,连临桌的人也侧过身来。
这对柯晟辉很受用,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竭力压低了嗓门:这女人啊,任她红唇白齿丰乳肥臀,别的再好都顶不了一样好。就好比我们男人,不用我多言,真正的男人是个什么样你们还不清楚?
在座的都纷纷点头,有人说:反正不是会计儿子那个样。
柯晟辉笑了笑。接着说:连寡妇都看不上的瓜娃子,哪有仙女肯百依百顺嫁过来的道理?我们的新媳妇明摆着有问题嘛!
看来你了解内情?对座的一个问。
莫不会早被破了吧?旁边的一个狐疑道。那也不打紧,这年头嘛,熊猫都比处女多。
柯晟辉撇了撇嘴:要真不是处女问题还就简单了。告诉你们吧,那女的其实是个石女!
石女?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
石女都不晓得!就是石芯子,下面没有那个东西!
哦——
柯晟辉的话音一落,每张嘴都张得更大、更圆了。大家明白,女人们在柯晟辉那里是没有一点隐晦的,村里好多婆娘女子不为人知的事他都清清楚楚。
酒精和新媳妇的秘密让他们亢奋不已。
有人说:难怪狗日柯晟辉一直不愿讨老婆,原来是我们这里根本没合他意的,谁让他晓得的太多了!
那我们岂不亏大了,以后娶个老婆啥都让柯晟辉看了。
有人端起酒和柯晟辉碰杯:到时候还请你手下留情啊!
柯晟辉说:那你得把女人当菩萨供起来才保险。
一阵哄笑之后,场面热烈起来。推杯换盏间,也全是些男人才说得出口的下流荤话。
大家只顾着说笑,两个新人不知什么时候已来到桌前。等有人注意到时,才发现新娘子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旁边的新郎官一手拿杯子,一手握酒瓶,看着一桌人乐呵呵傻笑。
柯晟辉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杯中已空空如也,他冲新郎官嚷道:嘿,我说老弟,你不准备好好敬我们几杯吗?
喝不好可不让进洞房啊!旁边的跟着附和。
洞也是白洞……
新郎官正要往杯里倒酒。新娘子却突然扔掉杯子,哭着转身跑开了。一个人敬不成酒,新郎僵在那里,过了好半天才收住笑。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但一时又不能确定。只意味深长地看了柯晟辉一眼,便跌跌撞撞循着新娘子离开的方向而去。
大家都觉得玩笑有点过分了,于是知趣地把筷子伸向盘中已显得狼藉的食物。一顿饭吃完,直到人们各自散去。主人家都没再露面。酒没有喝尽兴,敬烟和回礼的环节也都省略过去了。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发现会计的脸色都特别难看。以前他不抽烟,但从那以后,他却成了个烟不离手的大烟囱。家里出了那样的丑事,听说他打算盘的声音也不再响亮了。
柯晟辉也似乎收敛了不少,不再如从前那样张口闭口都是女人婆娘的一副浪荡样了。过年过节朋友几个聚在一起打牌搓麻将,少了柯晟辉的身影,也少了许多让人开怀大笑的龙门阵。
这事他最初便是从牌桌上听来的。晚上突然想起便问红霞,红霞又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当时他只当笑话一样来听,并没多想,最多也就纠结会计的儿媳那么个水灵清秀的大美人,方圆几十里都难得找到第二个,怎么会是一把打不开的锁。
现在,当他被那个奇怪的梦弄得辗转难眠,再度回想起红霞谈论柯晟辉时,那对一切细节都历历在目的熟知与清晰,让他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这个想法一旦产生,接下来所有未知与梦的虚幻都成了怀疑的证据。
他的怀疑不是无中生有。下午刚下班的时候,红霞曾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记得刚出来打工的头两年,他们对彼此的思念好像一下回到了热恋时节。天天想夜夜念的。他只要一抽得开身。便坐下来给红霞写信。他们几乎保持着一个月四五封信的频率,各种肉麻甚至笨拙下流的词句使用得那么频繁,后来再看都不敢相信是自己写的。之后他买了手机。家里也装上了电话,于是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说几句柔软暖心的悄悄话,也就成了习惯。两个人虽然隔了千山万水,倒像是背靠着背躺一个被窝里一样亲近。再后来他们的女儿灵灵上学了,红霞每天得早早地起来给灵灵做早饭,就改成一个星期打一回了。这样的习惯又持续了一段,现在他们基本是十天半个月互通一次电话,而且还客客气气的,客气中有那么一点陌生与疏离,问候的话也全像是寡淡无味的外交辞令。他们只好不约而同地把话题转向灵灵:灵灵身体怎么样。灵灵的学习好不好,诸如之类。
红霞打来电话时,他还有一丝诧异,没记错的话上周才刚刚打过。莫不会灵灵有什么事?
怎么了?他按下接听键。一天的疲惫,让他多说几个字好像都嫌累。
你吃饭了没有?红霞的声音有点小,听上去非常遥远。
我这才刚下班呢。你们呢?
还没,灵灵去她外婆家了。
哦,灵灵这几天好吗?
还好。
喔。
他把电话换到另一边耳朵。用手挠了挠头,一时不知道再说点什么。
你最近也好吧?
嗯,挺好。就是忙。
红霞沉默片刻,说:忙点总比闲着好。
是啊。
工作忙要多注意身体。
我知道。
别舍不得吃。
好的。你也是啊。
嗯。
每到这时,电话就该挂了。但红霞并没有要挂的意思,她好像还有什么话想说。他等待了一会儿,可一直没有听到红霞的声音。
他掏出一支烟衔在嘴上,找了半天口袋里却没有火机。他有时挺讨厌这样的沉默,就像小孩之间玩谁先开口谁就输的游戏一样幼稚而无聊。他怀疑电话是不是不小心挂断了。仔细看了看却仍在通话中。他不想把工作之外本该轻松的时光让沉默的压抑充满,他说:还有啥子事没有?
其实也没啥,红霞的语气中略有些迟疑,就是这两天身上不太舒服。
他寻思无非是女人惯常的那点毛病罂了,本想说不舒服就多注意着点。少沾凉水别吃得太辣,但话快到嘴边又收了回去。有些话久了没说,再说出口就不免有点假惺惺的。而且也需要勇气。
他轻轻地哦了一声,把烟放回口袋里,问红霞怎么了?
红霞说:前段时间总感觉背上痒,一直也没太在意,最近才发现起了好多疹子,腰上也是,又红又肿的,听老年人说可能是害了蛇缠腰。
蛇缠腰?
是啊,就像一条蛇缠在人身上,长满一圈就要出人命了。
那么严重啊!
谁晓得,我也都只是听人说的。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过了一阵,红霞又说:我昨天冲澡的时候,发现胸口上也长了两颗。
要不找医生看看吧。
我打电话就是想问你一下,要不要去柯晟辉那开点药?
那就去开点药。
好吧。
饭菜吃清淡些。
好的。
没别的事就挂了吧?
好。
挂掉电话的时候,他好像得到某种解脱般松了口气。
坐两个小时的公交回到出租屋,煮了碗白水面条,就着前一天晚上剩下的拍黄瓜胡乱吃下肚。也懒得洗脸刷牙,更省掉了洗脚,他重重地把身体扔在单人床上,不多时便沉沉睡去……
现在,接连抽了好几支烟,他感到越来越清醒了。
他想给红霞打个电话。但又有一丝担心。拿手机看了看时间,快午夜十二点了。打过去红霞肯定会骂他神经,也可能根本就不会接听。
他无法轻易将思绪从先前的梦中抽离出来。梦里的一切都太真实了,红霞起伏的胸口,乳晕间的汗毛,以及柯晟辉白大褂上的皱褶等细枝末节都清晰可见。而且他记得不只一次听人提起过,柯晟辉最引以为傲的,便是有机会穿上那件已不再白净的褂子。他平日给人行医治病,是从来不刻意把自己弄成一副医生派头的,而他一旦穿上那身行头,必定是想隐藏些什么。深谙个中因由的人。拿柯晟辉取笑时。总要问他最近又穿过几回白大褂。
他不想自讨没趣,犹豫再三,终究没有把电话打过去。
出了一身热汗,背上和腿根都湿津津的。更要命的是他满脑子都是红霞和柯晟辉偷情的场面,根本停不下来。最后,他决定起身去冲个凉。当冷水哗啦啦冲刷而下,身体和灵魂都得到了片刻松弛。但胳膊上的皮肤很快就收紧,并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虽是夏天,可毕竟此刻的温度降到了一天的最低。继续冲了一会儿,他关掉水龙头,不禁打了个寒颤。还是不能和以前比了。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他曾经大冬天光着腿脚下水田挖莲藕,竟然一点不觉得冷。
这样过了五六分钟,他才回到床上。头脑中不再如先前那样芜杂纷繁,他便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够快些入睡,但是下水道里的流水声却又让耳朵不能清净。这房子哪里都好。每月的租金也很便宜,就是地板下面纵横交错的下水管道太多。每遇上早晚洗漱或做饭的点,本不算宽敞的平房里,听去简直犹如江河滔滔。而且由于那么多的水流从屋子下面经过,房间不免受潮。干燥的秋冬季节还会好点,春夏时节稍不留意。墙脚或衣橱里便会生霉。前些天,他居然发现碗柜底部腐朽的木头上长出了一朵细瘦的高脚菌子。即便如此,他也不打算搬离这里。但听说这一大片的平房都已划入了拆迁范围,到时候要真拆过来,他还不知道上哪里去找这么合适的房子呢。
水声起先只有一小点。到后来变得越来越大了。他甚至怀疑可能是自己看错了时间。拿出手机确认了一下,凌晨一点半不到,没有弄错。透过窗子。外面也是漆黑一片,于是他起身去看是不是刚才没把水龙头关紧。但是水龙头也好好的,没有一滴水珠落下。
这大半夜的,还真是怪了!他自言自语道。
说完他蹲下身去。水声没有停止,仍是那样不急不缓地潺潺而流。
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男人的咳嗽声。声音是从隔壁传来的,他知道那个老实巴交的安徽男人。平日碰个面总是笑眯眯的,本就很胖的人。稍微一笑眼睛就成了一条缝。他把耳朵贴到墙上听了一阵,冲澡时噼里啪啦的落水声于是清晰可辨。他摇了摇头,心想,这么热的天,也真是难为那些胖子了。
他回到床上,只一小会儿水声便渐渐变低,最终随夜色一道归于沉寂。
第二天一大早被闹钟吵醒后,他像往常一样在床上赖了几分钟,然后开始机械地穿衣、洗脸、刷牙。当他把一切收拾妥当,一看时间吓了一跳,快六点半了。平时这个点已坐上公交车。经过巷口的包子铺时,那里有三五个人正站着付钱买包子豆浆。他没有买早餐。径直朝公交站牌小跑过去。厂子里是有明文规定的。迟到五分钟扣二十,每月一百块的全勤奖也没了。要一顿早饭还是要一百二,傻子也知道怎么选。
但是他足足等了五分钟,公交车才姗姗进站。车上已挤满了人,他好不容易才在前面靠窗的地方站定。身边的年轻人旁若无人地吃着热气腾腾的蒸饺,他抽了抽鼻子,是正合自己口味的白菜馅儿。其实买了早餐再慢条斯理地过来,也未见得会错过这趟车。他有点后悔,不停地吞着唾沫,眼睛望向车窗之外清晨的郊野,希望年轻人快些吃完。
他一心只想着赶上班的点。昨夜的梦境与遭遇皆抛诸脑后,竟如同前世一样遥远。
然而他还是晚了一步,迟到将近十分钟。这让他一整天都闷闷不乐,饭也吃得无滋无味。直至晚上回到出租屋里,仍然没有一点胃口。辛辛苦苦一个月,一下少了一百多块,他很心疼,于是赌气似的倒头就睡。好像省下一顿,钱就能失而复得。
他睡得并不踏实,接二连三地做梦。他梦到红霞站在屋外的桑树下面冲澡,水一盆一盆地淋下去,月光落在桑树上。桑叶与地上的积水都亮闪闪的,惟红霞的身影非常模糊。而他自己却坐在屋檐下,一边摇着扇子一边焦急地催促红霞洗快点,自己还饿着肚子呢。他还梦见厂里的主管大声对他喊:快点。快点,就差一分钟了。你还想被扣钱是不是?眼看着就要走进厂子的大门了,同事们经过指纹打卡机。发出均匀的嘟嘟声响。突然一晃神,自己却还在公交车上,满车人都在吃东西。单单他一人空着双手饥肠辘辘……
他辗转过身,半梦半醒中又听到清晰的流水声。他下意识地寻找着,没有桑树,也没有红霞,起初月光还很柔和。但后来一切归于混沌,化为黑暗。睁开眼睛,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虚弱。
跟前夜一样。水声欢快地流淌着。他再次到厕所里,把耳朵贴在墙壁上,果不其然,是隔壁的那个安徽男人。
刚才睡觉又出了一身汗,但他却无心冲凉。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他觉得四肢无力,两眼发花。
本想做点吃的,但屋里除了面条一棵青菜也没有了。还不到十二点,外面的小店兴许还没关门。他于是穿上衣服,经过长长的巷子,来到外面那条破落的街道上。
不仅小店没有关门,旁边的发廊、洗浴中心都还灯火通明。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坐在门口,低头摆弄着手机。她们穿的都是吊带衫。超短裙,饱满的身子很招眼,而且身体微微前倾,胸前露出白花花一大片。他突然一阵眩晕,真的是太饿了,不敢再多看两眼,便匆匆进了小店。挑来挑去好半天,却不知道要买点什么。小店那位四十来岁的女老板紧盯着他,眼神充满疑惑。最后,他像是为了逃避似的,拿了瓶啤酒就又匆忙出来了。经过洗浴中心时,他不自觉地朝两个女孩子扫了一眼。一个仍然还在玩手机,另一个却已抬起头来,正好与他的目光碰在了一起。他清楚这些女孩子都是做什么的,也听人说过这些发廊和洗浴中心的妙处。他赶紧低下头,朝巷子的方向走去。
回到屋里,他脑中还闪烁着那个女孩的样子。她多年轻啊,红霞好像从来没有那么年轻过。而且人家的身材那才叫好,虽然只是仓促的一面,但他确定女孩比会计的儿媳不知道要好看多少倍,何况那女的还是个石女。没有下酒菜,只有干喝酒了。他仰头咕嘟咕嘟猛灌了一气,打了个响亮的饱嗝,以前居然不知道,单喝酒竟也能管饱。
他正准备接着把剩下的都喝掉时,突然又听到了女人的声音,和昨晚入睡时听到的相似。很微弱,断断续续,但也很真切。这点酒不至于醉。他很清醒。这也不会是在梦里。他来到房间一侧的墙边,听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又来到房间的另一侧。也就是与安徽男人紧邻的那边,这回确定了,声音正是从那边传来的。
难道是男人远在老家的女人来了?他见过那个女人,就在去年春节前他正准备回家的时候,女人带着两个孩子从安徽过来过年。她也是个胖子,不过比男人好点,个子挺高,肉皮白净,要是甩掉四十来斤,说不定会是个端庄清秀的女子。不过,去年倒没发现她有这么放得开。
隔壁的呻吟还在继续,而且越渐高亢。他把余下的大半瓶酒都喝光了,仍然愤愤难平。红霞和自己老是那副不死不活的样,和柯晟辉呢?他又想起了前夜的梦,虽不敢打十足的保票,但他觉得梦里情形不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如今村里不少已婚夫妇都远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打工,但总有那么几个不甘寂寞的男女,日子久了,不免惹出些风流韵事。红霞曾不止一次跟他讲过,村里又有某个婆娘忍不住寂寞,和外面的男人成了嬲家。虽然说的都是些外人的事。但她是否意在传递些别样的信息?好比上了年纪的老人,总喜于向人讲述别人过世的消息。言下之意,是说自己也快走到人生的尽头。
他拿出手机,丝毫没有犹豫就打了过去。
第一次无人接听,他发出一声冷笑,但还有些不甘心。
第二次响了半天,仍然一直没有接听,他正准备打第三次、第四次,这时电话却通了。
那头传来红霞慵懒的声音:哪个?
哪个?他没好气地说,你说我是哪个?
一阵粗重的呼吸后,红霞说:啥事啊?这么晚了。
你在干什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你说干什么!
我在问你。
红霞有点不耐烦:睡觉啊,能干什么!
睡着了吗?等这么久。
嗯,睡着了。
睡着了你还能听到电话响?他开始咄咄逼人。
红霞没有理他。
问你话呢。
红霞仍没有说话。
你又睡着了?
没有。红霞打了个长长的哈欠,你有啥事啊,这么晚还打电话?
怎么,你急着要睡?
再不说我挂了。
没事就不能打电话吗?
他还等待着红霞说话,但是没有声音,红霞已经挂掉了。
他皱了皱眉,心里更加气愤,居然敢挂我电话!他又拨了过去。
这回很快就通了。红霞烦躁地问: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你怎么能挂我电话?
他的脾气一上来,声音也跟着加大了。
红霞沉默了一阵,语气平和下来:是不是工作不顺心?
他本想把白天的事告诉妻子,但心里的气还没消,而且隔壁的声音还在耳边起伏,于是说:没事,你想睡就睡吧。
红霞没说什么,他也不希望她再说什么,便挂了电话。
他以为红霞会打过来,但是没有。
他突然感到一阵百无聊赖,想抽烟,但是烟已经抽完了。刚才去小店的时候忘记买了,现在又不想再出去。他漫无目的地走进厕所,什么也没有做又走了出来。后来,他拿起刷牙的杯子,把杯口的一端贴向墙壁,自己的耳朵则凑到杯底上,那边的一切动静便如同在一间屋子里了。但他没有听到自己想听的,而是传来趿拉着拖鞋走路的声音,然后是哗哗的冲水声,下水道里又是好一阵的嘈杂。放下杯子,他自言自语道:嗬,也是个讲究的女人。
为了避免上班迟到再被扣钱,他强迫自己回到床上。无论如何也要睡上一觉。为此他还将闹铃调早了一刻钟。
接下来的几天。虽然作用不太明显,但好歹总能赶在最后关头扫指纹打卡。后来他才无意中发现,原来是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甩了好几站没有停车。庆幸之余,也有一点不满。太可恶了,不早一天调也不晚一天调?那一百多块扣得也实在太冤太不值得了。
天气越来越热了。白天那么累,晚上却还总是失眠。刚一落枕,就不由得信马由缰。好不容易迷糊过去,红霞与柯晟辉偷情的类似梦境又跑来纠缠。他注意到,每逢午夜时分,自己便会从一阵不安中醒来。他想要极力回避,但多疑的情绪又是那么根深蒂固。每次都要说服自己了,怀疑又跑出来作祟。太矛盾了,这让他苦不堪言。
他习惯了在午夜最清醒时往家里打电话。有时满怀愤怒。有时又不无讨好,这完全取决于先前都梦到了什么。
开头几次红霞还接他的电话,后来索性就不接了。
一天晚上厂里加夜班。早上下班后他坐车回出租屋休息。经过巷子时,正好碰到住他隔壁的那个安徽男人。他老远就给自己打招呼,仍然是笑眯眯的,还出其不意地让了一支烟给他。几天没碰面,安徽男人好像比以前更胖了。而且红光满面,有女人在身边照料还就是不一样。
他随口说:老婆啥时候过来的?
安徽男人脸上的笑戛然收住,迟疑半刻,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然后嘿嘿笑道:不好意思啊,吵到你休息了。
这什么话,都是过来人。老婆好不容易来一趟,应该的嘛。
安徽男人不好意思地笑笑:她不是我老婆。
不是?他有些吃惊。
就一个朋友。安徽男人吸了口烟,满不在乎地说,嗨。现在——不都那么一回事儿吗。
然后两个人相视笑了笑。便各自走了。
他本来已经很困很乏了,但是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安徽男人的话刺激了他,这让他深感不齿,但又有点嫉妒人家。同样是在外打工的男人,看人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其实,还真如安徽男人说的那样,眼下,这样的情形在打工的人群里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就自己所在的这个仅有五六十来人的小工厂里,背着家里和别人过上临时夫妻的,少说也有六七个。这还只是大家都知道的,不知道的又有多少呢?这谁说得清。刚出来那两年,厂里一对小年轻谈恋爱,没处到一个月就同居了,还惹得几个观念保守的中年女人说三道四。后来,那几个女人当中的一个也和另外一个厂里的男人住在了一起,也就见怪不怪了。
他的主管在老家有个当小学教师的妻子,前些年却和一个湖南女人在郊区租下一室一厅,过了将近一年舒坦的小日子。后来这女人的老乡回家不小心说漏了嘴。她家里的男人带着两个亲戚跑来找事。听说当时正好捉奸在床,把两个光溜溜的身体拖到小区里,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主管赔了人家两万块钱,好说歹说才把事情了结。这事好像还上了区里头的报纸,不过两人的名字都用了化名。主管险些丢掉工作,也一改往常作威作福的傲慢姿态,这让他暗自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不到半年,听同事讲他又和一个四川女人做了临时夫妻。有一年厂里过中秋节,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喝酒。主管喝多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妻子在他出来打工不久就给他戴绿帽子。这让在场的人无不唏嘘。
给家里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这让他心乱如麻。他急切地想知道红霞在做什么,自己的担忧会不会成为现实。后来他实在太困,握着手机睡着了。
醒来时正是中午,这个时候红霞应该在给女儿灵灵做午饭。
他又把电话打了过去,没响几声就接通了,但说话的却是灵灵。
爸爸。我好想你哦。女儿稚嫩的声音让他有些感动,心头却掠过一丝阴影。
灵灵乖,爸爸也想你。他说,怎么你来接电话,妈妈呢?
妈妈去柯叔叔那里换药去了。
他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却端端砸中了脚。
你怎么没一起去?
妈妈让我在家吃饭,说柯叔叔的房子里有细菌,小孩子不要去。灵灵天真地说。
胡说!他大吼一声,突然意识到会吓着灵灵,便放低了声音,妈妈什么时候去的?
给我盛好饭就去了。
哦,那灵灵饭吃完了没有?
这就快吃完了。
灵灵吃的大碗还是小碗?
大碗,我早就吃大碗了。爸爸,我现在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妈妈说,大孩子就得吃大碗。
哦,灵灵真乖!
他简直恨得咬牙切齿。家里离柯晟辉那不过两三分钟,换药居然能换这么半天,但他不便当着灵灵发脾气。
他故作镇定地说:灵灵,爸爸给你说,下次妈妈去换药,你远远地跟在后面,但一定不要让她发现了,你就看柯叔叔家的门有没有关。
为什么不能让妈妈发现?
他一时语塞,不知道怎么告诉女儿。
哦,我明白了。灵灵咯咯地笑出了声,这是一个游戏吗?
对,一个游戏。
要是门关着呢?
要是关着,他挠了挠头,就说明屋里没有细菌。你想啊,有细菌就得开门通风嘛。
哈哈,爸爸你真聪明。
他苦笑了一下,嘱咐道:灵灵,这是你和爸爸之间的秘密,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连妈妈也不行吗?
不行,尤其不能告诉妈妈。
我晓得了。
灵灵乖,好好吃饭。爸爸过年回家的时候给你买最漂亮的洋娃娃。
挂掉电话,他整个人突然无力地瘫软了下去。自己最担忧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都说梦是反的,怎么在他身上却应验了?整个下午他都坐在床上,没有一点食欲,也不愿睡觉,头脑昏昏沉沉,想什么事情都变得吃力。
太阳向西移去,屋子里的光线在渐渐变暗。
晚上还要去厂子里加班,他想请个假,就说自己生病了。主管不至于逼着他抱病上夜班,但一天的工资可就没有了。那也无所谓,天天这么没日没夜地劳累,他又不是为了自己。他那么在乎红霞,那么在乎这个家,但最后换来的却还是妻子的不贞。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他以为是红霞或者灵灵,但接了才知道是主管。
主管说:今天晚上工厂片区检修线路。不用去加班了,晚上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再去上班。
电话那头有些嘈杂,传来阵阵水声和女人说话的声音。他料定是那个四川女人,虽然未曾谋过面,然而单听那声音轻细绵软,想必人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
抽了两支烟,他感觉精神好了些。于是起床打开门,一时又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便拉过凳子坐在门边一支接着一支继续吸烟。
这样干坐着真是无聊到了极致。先前还一直想借口请假,现在却开始抱怨怎么偏偏在今天晚上检修线路。就算没有工资,只要能去加班,也比这样无所事事地坐着好。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准备再点一支。这时一个穿花格子连衣裙的高挑女人提着一大袋蔬菜走过来,经过他门前时脸上挂着淡淡的笑,但并没有跟他打招呼。附近的房客他虽然不都熟识,但是人家的容貌他都清楚,他肯定此前从未见过这个女人。女人走过去,留下一股很浓的香水气味。她在旁边的门前停了下来,放下了袋子,在手提包里摸索一阵,然后拿出钥匙打开门便进了屋里。那动作非常自然娴熟,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架势。
他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不禁在心里由衷地赞叹安徽男人虽然其貌不扬却极具眼光。
看到人家提了那么大一口袋的蔬菜,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觉得自己也不能太寒碜了,何况身体是个人的,眼下还不好好对待自己,难道要等别人来可怜和施舍?于是他决定也去买几个菜,做一顿像样的晚饭。
饭菜都弄得像模像样,算得上可口了,可是毕竟心里有事,他没有一个好的胃口去享受。菜没吃多少,酒却已经喝掉了两瓶。只是他胸中愁闷并未消解多少,反而倒更加浓稠了。
上了一个通宵的班,白天又根本没怎么休息,现在早到了睡觉的时间,他还依旧清醒得很。他侧耳倾听了一阵,四下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响。他有点失望,把最后一瓶酒也打开了。小口啜饮起来。他喝得很慢,后来开始觉得头晕,这正是他想要的。以致酒渐渐失去了应有的滋味,脑中也变得一片空白。
他回到床上,一时无法入睡,便抱着试探的心理往家里拨了个电话。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白天已经确定无疑事,现在还要在上面花多余的心思。
出乎他的意料,电话很快就通了,但是那头却没人说话。
他也不急于先开口,看谁耗得过谁。
于是就一直那么沉默着,沉默着。
最终,红霞没能坚持下去,她几乎是极力压低了嗓门。却又异常暴躁地怒吼道:你简直就是个疯子,有病!然后便挂了电话。
再打过去时,一直无人接听。他想,或许红霞把电话线拔掉了,但仍心存一丝侥幸,还准备再打一次,手指却久久地在拨号键上方犹豫着,最后他放弃了。
他又听到了隔壁制造出来的声音,比往日低了许多,但足以让他心中欲念燃烧得更旺。
他不知道每个夜晚会有多少这样的暗流。滔滔不绝,悄然汇聚,慢慢地积少成多,是否已经形成了一条蔚为壮观的大河?
他睡不着觉,想到长夜漫漫,人人都有一个伴陪着,惟独自己是孤零零一人,不免有种莫大的落差与虚无。他一边吸烟,一边出了门,行走在外面无限清凉的夜色中。
穿过巷子,他远远地看到街边亮着灯光的发廊和洗浴中心,门口坐着好几个女孩子。她们有的在玩手机,有的正聊着天,还不时传来几声放浪的大笑。
他心想,自己在外面吃苦受累。而且历来规规矩矩,可红霞还不是说变就变了。这对他太不公平。别人都在做的事,自己又何尝不可以去做?更何况是红霞的不贞与背叛在先。无论是为了寻求平衡,还是找回男人应有的尊严。他都没有理由再这么窝囊下去了。
理是这么个理。但他还是有点心虚。不敢堂而皇之地走上前去,而是拐进旁边的小店买了包烟。从小店里出来时,他点燃一支,然后猛吸了两口,故意放慢脚步,朝女孩们那边望了望。几个聊天的女孩子都停了下来,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他的心跳得很快,胸口有些发闷。一个女孩赶紧起身,向他招呼道:大哥,是要洗头吗?里边请吧!
他站着没动,也没有说话。这些天烟抽得太多,嗓子总是发干发紧。
见他一脸的犹豫和羞涩,老练的女孩很快便明白这是他的初次经历,于是热情地上前挽着他的胳膊。嘴巴凑到他耳朵旁:外面好热,我带你进去吧。
他看了女孩一眼。好像是那天夜里见过的那个,于是心跳渐渐平静下来。他闻到了女孩身上的香气,胳膊触碰到了她饱满结实的乳房,心中升起一丝甜蜜。
但他仍还有一些迟疑,万一红霞和柯晟辉没有那回事呢?
理智告诉他应该拒绝,但他却怎么也经不住女孩那年轻、美妙的诱惑,于是在半推半就中,他迈过那道看似无形的玻璃门,走了进去。
责任编辑:李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