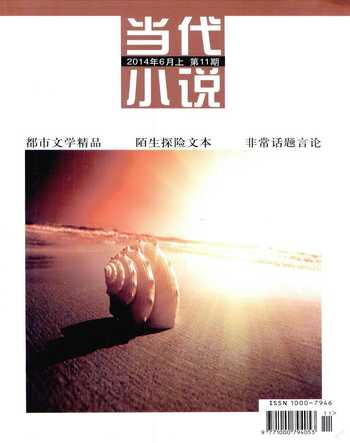刺猬,或者蝴蝶
徐先进
关上房门的一刹那他突然产生一丝疑惑,范丽真的已经离开了家,跟着她的老板到南方去了吗?她说8点钟从家里动身,然后打的直接去机场,和老板在机场会合,乘坐10点钟的班机飞往南方。现在还不到9点,她会不会因为什么意外还滞留在家里?比如。从手机上查到航班误点。她要推迟去机场的时间。亦或许。老板临时改变主意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取消了这次可有可无的飞行?因为范丽说过。这次去南方,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任务,作为新提升的销售业务主管,老板想带她到南方那个城市熟悉一下圈子,打通一下人脉。老板是在那个城市起家的,对那个城市有着特殊的感情,至今那个城市还有他不少的老主顾,保持着生意上的来往。
他还是不自觉地掏出了钥匙,在钥匙插入锁孔之后他又犹豫了片刻,然后像是被谁推了一把似的果断旋转,迅速打开了家门。不知为什么,他想都没想就直接去了卫生间。卫生间的毛玻璃门是关着的。里面隐约有一个灰蒙蒙的人影。他的心随之快速跳动了两下。但等他定睛再看时,灰蒙蒙的人影却雾一样的消失了,他才确信刚才的一瞬间不过是产生了一丝幻觉。他随即推开毛玻璃门,往洗脸池的右侧扫了一眼,那里有一个摆放洗漱用品及化妆品的无门柜子,摆放在玻璃搁板上的化妆品数不胜数,高高低低占满了两层搁板。但他一眼就发现,那两瓶最高档的化妆品不见了。不用说,是范丽带着它们远走高飞了。
接下来他去了卧室,先是在床沿上正襟危坐。目光扫视着一排排紧闭着的柜子门。不用打开它们他也能猜得到。那件范丽非常喜欢,但平时很少穿的驼色风衣应该是不见了。同时不见了的还应该有其它几件物品。范丽虽然表面上喜欢追逐潮流,实际上她是一个有些保守的人,骨子里始终隐藏着一股小家子气,一股在小县城度过青春期后烙在骨子里的猥琐,以及为了掩饰这猥琐而刻意表现出来的开放。他懒得再去猜测她还带走了些什么,顺势从床沿上滑下来,一屁股坐到地板上,双手斜斜地撑在身后,头大幅度后仰着,目光倒视着一切。这无赖相让他想起小时候每每遭人误解时,他就不由自主地摆出这种不愿与人合作的姿态。
其实他很明白,为了这次出行,范丽做了不少铺垫。范丽确定无误地告诉他要实施这次出行是在三天前,但半个月之前她就开始打伏笔。那天下午范丽特意提前一个小时下班,回家烧了一桌好菜,并摆上一瓶红酒和两只高脚酒杯。他一跨进家门就被这突如其来的氛围弄晕了,他有些懵懂地在饭桌边坐下来。范丽端起高脚杯晃了晃里面的酒说。我知道你要问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我还是免得你瞎猜吧,今天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说完她示意他端起酒杯。他很别扭地捉住酒杯的细腿举了起来,也像范丽那样将酒晃了晃,可他并没有像范丽那样抿上一小口,而是等着范丽说下去。范丽接着说,以前只顾在工作上打拼,忽视了家庭生活,今后要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其实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吗,我们不能本末倒置。他听后感觉有些欣慰,又有些不置可否。按说生活和工作的关系应当是两条简单的平行线,像两条钢轨一样,除了在一些重要的节点上换轨。它们很少纠结在一起。可现如今的情形谁能说得清呢,工作的边界在无止境地拓宽,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这一代人已经永远不能像他父母那样,将工作和生活区分得泾渭分明,上班就是上班,下班就完全投入到家庭生活,其间看不到任何工作的影子。就像工作这档子事不存在一样,完全自足地享受家庭生活。没过几天,范丽又如法炮制。在绕了一圈家庭情趣之类的话题之后。她像是不经意地抱怨起来,说销售主管这个职务是很烦人的,免不了经常出差。他没觉得什么不对劲,反倒宽慰她说,作为销售主管,出差联系业务是天经地义的,没必要为此纠结。直到三天前,范丽告诉他要和老板飞一次南方那座城市时,他才感到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他问范丽,和老板一起去?就你们两个人?范丽晃了晃高脚杯里的酒说,是的,这次去没什么实质性的事务。就是熟悉一下那个城市他的朋友圈子。他沉默下来。咂摸了一下范丽所说的话,过了一会儿他猛地喝了一口酒说,你老板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范丽没有解释老板为何要这样做,而是说,你要相信我,不然我可以随便撒个谎把这件事情瞒过去。他很想大度地谢谢她的坦诚,可是一股说不清的沮丧让他失去了冷静,他冲口而出,你不许去,一对孤男寡女没什么特殊的事务飞到另一座城市,想想就叫人受不了,你的同事会怎么说,我的朋友知道了会怎么说?我的父母知道了我还有何颜面?范丽也沉默了,她不停地晃动酒杯里的酒,有一下没有把握好晃动的幅度,酒被洒了两小片出来。但他十分清楚,范丽是不会轻易屈服他的,她那由骨子里的猥琐而反生出来的傲慢会让她一条道走到黑。果然她放下酒杯说,信不信由你,反正事情无法改变。末了她还感叹了一句,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小县城里养成的小家子气!
再次关上房门他显得有些决绝,门锁的咔嚓声还没有消失,他就像一只被人追赶的小兔子噔噔噔地下了楼。出了楼道,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还好,时间还算充裕,于是他放缓脚步,缓慢步行到小区门口。出了小区就是一条主干道,虽然上班的早高峰已经过去,但大街上仍然车流如织。城市就这样连轴转地忙碌着,没有一刻的消停。他看见一辆打着“空车”牌子的出租车,伸手去招,可人家理都没理就直接从他身边开走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又有一辆空车驶来,他招了招手,出租司机问他去哪儿,他说去火车站,司机说火车站不去就把车开走了。连着拦了几辆空车,司机都说不去火车站,说那里堵车堵得厉害。看看时间耗得差不多了,最后他强行上了一辆出租车,答应多付二十块钱的车费,司机才没有再啰嗦。
临近火车站,车子果然堵得厉害。看着车子拱猪一样一拱一停,他不免着急起来,这样下去,肯定会错过接站的时间。于是他干脆下了车。从车缝里穿行而过,花了一刻钟左右终于来到了出站口。他来不及擦一下额头上的汗,赶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后双手高高举了起来。这是一张八开素描纸。上面印着一只彩色蝴蝶。昨天晚上,在和临风确认了接头方式后,他在网上搜了一个多钟头,才决定将这只他自认最漂亮的蝴蝶打印下来,粘贴到素描纸上。
出站口人流涌动,他不清楚临风所乘的那班车是否晚点。如果不晚点的话,正是这班乘客出站的时候。他很想打个电话问问临风。可是临风昨晚有言在先。今天在见到她人之前,不要再打电话联系。他当时想,她要的可能就是这种神秘感吧。于是他赶紧把目光投向一张张涌动的脸,努力把手中的纸举得更高。
人们对他有些滑稽的举动无动于衷。一个个奔命似的急于逃离出站口。眼见着人群越来越稀疏。他的心情渐渐低落。难道临风所乘的这班车真的晚点了?或者是她后悔了,单方面取消了这次约会?最糟糕的是,她一开始就没打算赴这次约会,只是想戏弄他一下?对于初次见面的人,不让打电话联系,怎么说都像是一个拙劣的借口。想起关于网友约会的种种传闻,加上自己如此滑稽落寞的样子。他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一想到此刻范丽正和她的老板肩并肩地在天上飞,他还是咬牙坚持下来。再等等吧。
身后传来一声细细的咳嗽。他转过身来,一下子显得手足无措,站在他面前的正是临风。临风笑盈盈地看着他,落落大方地向他伸出一只手来说,你就是玉树先生吧,看上去比视频上的帅气。他脸唰地一下红了,迟疑着将手伸了过去,轻轻碰一下临风的手指就又收了回来。他急于想说一句轻松俏皮的话来掩饰目前的窘态,可说出口的却是一句非常平庸的大白话,你好,很高兴见到你。临风果然耻笑他说,搞得这么正经,跟国家大使见面似的。他再一次脸红,内心懊恼地想,别看在网络上还算放得开。一旦跌入现实生活中,自己还真像范丽所说的那样,改不了在小县城培养出来的小家子气。和范丽相比,自己实在是差了一截,范丽虽然骨子里也同样有这股小家子气,但早已被她外在的形象遮蔽得严严实实。
接着他又为自己接下来的一句话感到懊恼,在没找到贴切的话题之前,为了避免尴尬的冷场。他问她,要不,我们先住进旅馆再说?好在临风一点也不做作,她讥笑说,你也太急了点吧,我才不想这么快进旅馆呢,说不定进了旅馆之后我们很快就会分手,男人不都这样吗。得手之后赶紧找个理由溜掉。他有点傻地笑了一下,说出的话仍然显得笨拙,像表决心似的。我不是你说的那种男人。临风咯咯笑了起来,反问他,那你是哪种男人?至少不是好男人,好男人不会背着妻子出来跟别的女人幽会。这就合上他们以往在网络上说话的语调了。他有些轻佻地说,那你也承认自己不是好女人了,好女人更不应该背着丈夫出来和别的男人幽会。让他没想到的是,听他这么一说,临风的脸迅速黯淡了下来,嘴里冒出一句冷冰冰的话,你歧视女人。
,就这样边说边走,他们穿过站前广场来到湖边。这个湖面积很大,是这个城市的名片之一。这处的湖边其实就是站前广场的边沿,一条百米来长的木板台子悬空架在湖边,台面高出湖面六、七十公分,台沿上坐满了人,有单独一人的。有五、六个一伙的,当然也有很多成双成对的。他们大多把腿从台子上放下来,不少人用脚试着去戏水。他想,这些成双成对的人当中,会有多少对像他和临风一样,不是夫妻呢?但鉴于临风刚才的突然变脸,他不敢再贸然乱说。好在临风又恢复到轻松大方的姿态,看着满湖怡人的风光,她兴奋地说。我们先在这里坐会儿吧。于是他们找到一处空台沿坐下去,临风一坐下来就急于用脚去戏水。
不知临风说他看上去比视频上帅气是不是真心话,他倒是真切地觉得,临风看上去比视频上更漂亮。她皮肤白皙,身材高挑,穿着入时,气质高雅。如果不是近在眼前,他打死也不相信,这样的女人会从网络上走下来,偷偷地和他幽会。他觉得,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女人越来越难以捉摸了。
一年前他和临风相遇于一个网络论坛。那时他工作不顺,也许真是小县城里养成的小家子气在时不时地作怪吧,新来的老板老是说他保守僵化甚至迂腐。工作上业绩平平倒也罢了,让人忍受不了的是。同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为了得到新老板的赏识,大家暗自较劲,甚至不惜编造谎言排挤他人。他没有把烦恼告诉范丽,而是一头扎进网络。他对网络不是很熟悉,经常像逛大街一样东溜一下西溜一下,后来他溜到一个带点文艺性质的论坛里,看了几篇文章后,勾起了他对高中生活的回忆。他读高中时喜欢在学校附近的一个租书店里租小说看,他租的小说很杂,武打的言情的科幻的甚至名著他都租来看。说起来他能够和范丽走到一起。恐怕还要归功于这租来的小说呢。有一天中午他忘了把租来的小说放进课桌抽屉里就去食堂吃饭,吃完饭回到教室发现范丽正捧着那本小说看得入迷,他没好意思要回来,范丽也没有立即把书还给他,而是过了两天把书看完了才还给他。当然他们没有就此亲近起来,但几年后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谁能肯定不是那时埋下的种子呢。世间的事情别看它千变万化。其实十有八九是由种子的性质决定的。他就在这个论坛驻足下来,注册时发现他喜欢的“玉树临风”早已被人抢注,他干脆取其一半注册了“玉树”这个用户名。没过几天,坛子里有一个叫“临风”的找到他。说他霸道。把她喜欢的“玉树”给抢注了。当然她最喜欢的也是“玉树临风”,“玉树临风”被人抢注了她就想注册“玉树”,结果只能是一退再退注册了“临风”。也许是他看了不少小说的缘故吧,他在这样的论坛里混得很是惬意,跟的帖子轻松活泼,不乏幽默。他回答她说,那我们结合成一体,就“玉树临风”了。从此两人渐渐热络起来,彼此交换了QQ号码,先文字交流,进而视频聊天,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他家的电脑突然坏了。两人的交流也就戛然而止。一个月后他换了一台新电脑,不知是不是那小家子气又跳出来作怪,还是在单位里多多少少顺气了一些,他不想再面对临风了,他几乎不上QQ,即使上也是隐身。大多时间是看看新闻,潜水逛一逛文艺论坛。直到三天前,范丽明确无误地告诉他要和老板飞一次南方时,他才带着极大的委屈打开了QQ,临风就像是一直等着他似的,她没有责备他这么长时间的不告而别,而是一上来就和他热乎地聊了起来。越聊他心里越委屈,说话的方式由自嘲向自虐的方向演进。临风呢。也像是受到了极大的委屈。她火上浇油。最后两人都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委屈的人。那么好吧,前天晚上他向她说。我们两个最委屈的人能否见上一面?临风立马答应了下来。
湖边的人有增无减,走了一拨又来了更多的一拨,他们一个个显得悠闲至极快乐至极。虽然火车站就在身后不远处,但听不到一丁点嘈杂的声响。微风吹拂着湖面,水面漾起丝绸抖动一样的微澜。女人们的长发也被吹得飘逸起来。湖对面这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巍然屹立,像一个不动声色的倾听者。似乎时时刻刻在提醒人们,这是一座优雅的城市,一座有耐心的城市。他不知道临风是不是被这样的情致感染了,她显得特别安静,一改刚见面时的热络大方,大多时间就这样坐着一动不动,可是时间已经不早了,他提出去找个地方吃中饭。
虽然在这个城市生活不少年了,但他对这个城市的许多领域还很陌生。他带着临风穿过了好几条街道。吃不准什么样的餐馆才是合适的,还是临风比较有经验,她从外面透过玻璃墙看到一家餐馆用屏风分隔出一个个简易的包间,她说就这家吧。两人进去找了个靠窗的包间坐下来,将窗帘拉上。阳光透过淡橙色的窗帘渗进来,小小的空间立即充满了暧昧的情调。在点好菜后他问临风要不要来点酒,临风说,当然要酒,葡萄酒。
不知你是否有过与网友见面的经验,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在网络上混得如何熟络,一旦在现实中见面,还是显得很生疏,这算不算是对人的多面性的一种注解呢?拿他自己来说,网上网下就判若两人。临风也只是刚见面的时候表现出轻松大方,似乎是网上风格的一种延续,但之后更多表现出沉思不语,心情不是他想像的那么好。为了避免冷场,他竭力寻找话题,很快那只粘在素描纸上的蝴蝶跳进他的脑海。他说,你喜欢蝴蝶?
临风喝了一口酒说,我讨厌蝴蝶。
他愕然,那你干吗还让我用一只蝴蝶迎接你?
临风回答得极快,我想受刺激。
接着她反问他。你呢,最讨厌什么动物?
他脑中开始搜索。他在小县城出生小县城长大。除了偶尔见到猫和狗,他对动物实在没什么印象,小县城里除了人似乎再没有其它活物。不过他很快想起来,他高中毕业那年,考完高考之后,十多个同学相约去乡下一个同学家里玩,那同学的父亲在山上逮了一只刺猬用鸡笼罩在家里的一个墙角处,十多个同学立即围着鸡笼看新鲜。鸡笼是用竹篾编的,网眼鸡蛋那么大,上方有脸盆那么大的一个洞口。刺猬蜷缩着,花白的硬刺像铠甲一样紧贴在身上,有人想伸手去抚摸,但由于害怕,手刚伸进洞口就又缩了回来,他也有样学样地把手伸进去,可他刚想把手缩回来时,范丽恶作剧地把他胳膊向前推了一把,刺猬瞬间变成一个刺球,一根硬刺扎在了他的中指肚上,他把手收回来时看见豆大的血珠不停地从刺口处冒出来。当时可能他在揣摩范丽恶作剧的意图吧。没来得及对刺猬产生好恶之情。现在被临风这么一问,想想那一刻所受的惊吓以及那种棰心的刺痛,他说,我讨厌刺猬。
临风不无讥诮,一个大男人害怕小刺猬?有什么故事吧?
他不想把这个故事告诉她,掩饰说,其实也算不上讨厌,只是不喜欢而已,你呢,作为一个女人,不应该讨厌一只蝴蝶呀?
临风又喝了一口酒,她的脸越发显得娇艳。她不停地晃动酒杯,葡萄酒像舞女的红裙子在杯壁上不停地飞旋。她的眼眶湿润了,目光渐渐迷离。声音低沉得像是从冰窖里发出来的,她说,蝴蝶是我丈夫的小三名字谐音。
临风和她的丈夫大学同学。临风的父母是国家干部,在那个城市有头有脸。不时在市电视台新闻节目里露个脸面。她丈夫出生偏远的农村,家里穷得丁当响,姐弟三人,为了供他读书,两个姐姐早早外出打工。临风的父母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算满意,因为他长得比较帅,可是当了解到他家的情况后,帅不帅就一文不值了。临风痴心不改,顽抗到底,最后她的父母不得不接受现实,并走关系把他们的工作在市里安排好。都说穷人的脑瓜要么像一潭死水一动不动,要么像火车的轮子一样飞速地旋转,她丈夫的脑子就没有一刻停止过转动。他公务员没干几年就辞掉了,开起了一家装潢公司。利用她父母的人脉关系迅速把公司做大做强。她不无炫耀地对她父母说,我的眼光不错吧,她父母点头称是并做出深刻反思。感叹说。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呀。更让她得意的是。发达后的丈夫对她更呵护体贴,老是对她说,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你不仅是我的妻子,还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可是谁能想到呢,半年前她的父母相继退休。他不久就对她冷淡下来,很快她发现他在外面有了小三,通过私家侦探的调查。她知道那个小三叫胡蝶,是一个学画画的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如果这是从电视或者报刊上看来的故事,他会觉得俗不可耐,但这故事发生在身边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他还是感到很震撼。他有些不知所措,很笨拙地说,那你,这次来是想报复他?
临风回答得很干脆,对,就想报复他。
他感到有些悲哀。自己被当成工具了。但反过来想,自己何尝不是利用她来报复范丽呢。临风又喝下去一大口酒,有几分醉意地说,不过我确实讨厌蝴蝶,初中的时候和一个女同学到公园去玩,看见一只非常好看的蝴蝶趴在一朵花上,我伸手去捉,结果弄得两个手指的指肚上全是蝴蝶翅膀上的粉末,那粉末蓝幽幽滑腻腻冰凉凉的,让人心里直发毛,从此我就开始讨厌蝴蝶了。
走出餐馆已是下午两点多钟,街上人流如织。车水马龙。临风和他并肩走着,神情略显涣散。他知道,接下来他们不得不面对最核心的问题,去不去宾馆开房?他内心跳动得很厉害,脚步也就迈得很是犹疑。他很清楚,自己此行的目的并非是贪图意外之欢,可是从临风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还是让他身体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躁动。他不知道临风此时是怎样的心态,身体对于女人来说是最可宝贵的财富,也是她们最后的本钱,如果她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报复一个人,那说明她所受的伤害是无以复加的。现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口,他相信此刻临风的内心不会像她的外表这么平静,任何一个微小的因素都会影响后面事情的走向,以至于一拍两散。于是他委婉地问临风,现在去哪儿?
临风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低声说,去开房。他们选择了一家中档的全国连锁店,在服务台登记后他们乘电梯来到六楼,穿过U字形的走道,他找到号房。在插房卡时他的手不听话地颤抖起来。连插了几次才终于把房门打开。临风一进门就钻进了卫生间,他则在沙发上坐下来,闻到房间里有一股淡淡的霉味,他担心临风会受不了,就把窗帘窗户和房门全打开,让房间透透空气。
半个钟头后临风从卫生间里出来,他窘迫地瞅了她一眼。从时间上判断,她应该进行了沐浴,并且补了一层淡装。先前柬着的头发披散开来,衣服也换成了一件白底碎花连衣裙。她对他笑了一下,然后安静地坐在床沿上。
他还陷在窘迫之中,虽然全身的血液在燃烧。身体在急剧地膨胀,但黑色的沙发就像是一块巨型磁铁,把他牢牢地吸附住。他缺氧般地呼吸着,眼前呈现出一片混沌的黑暗。要不是黑暗中传来一个缥缈的声音,你后悔了?他不知自己能不能最终摆脱沙发巨大的吸附力。
他也去洗了个澡,出来后发现房门已经关上,窗帘也拉起来了,他不再犹豫。直接在床沿上靠着临风坐下来。在他伸出双臂抱住她的一刹那,临风像发疟疾似的颤抖了一下,豆大的泪珠从眼眶里掉了下来。但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加大了双臂的力量,将嘴向临风的脸上贴过去。
世界静得像黑洞一样。可就在他们要倒下去的时候,门外骤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和大呼小叫的人声,这声音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停止了动作。他心里咯噔一下,立刻想到了捉奸。身体也随之僵硬起来。
他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等待着有人破门而入。
门外嘈杂的声音在不断地膨胀,不时夹杂着一两声尖叫,可是房门却迟迟未被打开。这种坐以待毙的滋味很不好受,不知过了多久,他起身悄悄地走到门边,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就在这时他又听到一片尖叫,他要跳了。要跳?跳什么?看来这嘈杂的声音跟他们无关,一定是外面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倒是临风很敏锐,她不假思索地说,肯定是有人要跳楼。
于是他们来不及整理一下被弄皱的衣服就打开了房门。门前挤满了人,一个个踮着脚,脖子伸得老长,向他们隔壁房间里看去。他们在人缝里挤出一个位置,由于他们的身材都比较高,不用踮脚也能把隔壁房间里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
一个男人站在窗外。只看得见他半截身子,也不知道他的脚踩在窗外的什么地方,如果撒开钩着窗户的手指。无疑会掉下楼去。从他的衣着和蓬乱的头发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农民工。他黝黑的脸上满是泪水,嘴里在念叨一个人的名字。地上满是烟头,中间倒伏着一只酒瓶,里面还剩有一些白酒,浓重的酒味和烟味从房间里散发出来,直呛人的大脑。一个应该是宾馆管理人员的女人站在离窗子两米远的地方,她反复劝说男人,让他不要做傻事。从她不停的劝说中,大家渐渐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这男人的妻子跟另一个男人跑掉了,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寻找。才终于得知他们就在这个城市里。现在他只想见上他妻子一面,然后在她面前跳下楼去。女人几次试着靠近他,但都被他激烈的警告一次次逼退,成功逼退女人后他都要大声呼喊他妻子的名字。
楼道里又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几个消防员跑了过来。他们分拨开门口的人群一下子冲进了房间。在和女人进行简单的交流后,一个消防员走到门口。让门口的人全部离开,然后反身关上了房门。人群一窝蜂地散去。争着往楼下跑,想去楼下接着看事情的进展。
他和临风跟在人群后面,在走道里刚拐过一个弯,就听见后面有人呼喊,让他们等一等。他们停下来,刚才那个劝说跳楼男人的女人跑过来对临风说,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帮我们劝说一下?临风经过短暂的沉默后一口答应下来,两个女人又风驰电掣地跑回去。
他继续沿着走道往前走,电梯已经被关停。只好从楼梯上下去。他想,那女人到底想让临风帮什么忙呢?难道他们想用女人来感化那个跳楼的男人?她自己不也是女人吗?不过她也确实没多少女人的味道,年龄大不说,还穿着宾馆里冷冰冰的制服,她恐怕对自己的女性特征毫无信心,才让临风去试一试吧。
楼下站满了人。一个个仰着头。120救护车已经来了,消防员也在窗下放置好了充气垫子。一个应该是指挥官的人拿着对讲机不停地说着什么。他这才看清跳楼男人的脚踩在窗外墙上装饰性的横档上,那横档不过五公分宽,能看见他一半的鞋底,只要稍一闪失,他必定无疑会栽下来。他在呼喊他妻子的名字,说她好狠心,连见他最后一面也不愿意。
他终于看见了临风。临风离窗子有些近了,看得见她胸部以上的部分,从动作看,她在说话,但听不清说什么。跳楼男人也不理睬她,他仍然面朝窗外。隔一会儿就呼喊他妻子的名字,然后要么哀求、要么咒骂他的妻子。
仰着的头有些累了,他把头低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来抽。等他抽完烟再抬起头来。看到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临风已经贴近了窗子,跳楼男人虽然还在不时地喊他妻子的名字,但他却频频回头看着临风,一边回头一边说着什么,似乎和临风对上了话。这样相持了大约十多分钟,他吃惊地看到。临风隔着窗子抱住了跳楼男人的腰,跳楼男人伏在临风的怀里放声大哭,房间里的消防员小心翼翼地来到窗边,把他从窗外拉进了房间。
不一会儿,消防员架着跳楼男人下来了。120的几个医生护士把他扶进了救护车。人群迅速地散去。
回到楼上。他看见临风在房间里收拾东西。虽然他很清楚临风这是要离开的意思,但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这就走吗?临风似是而非地笑了一下,点头说,我想回去了,晚上10点正好有一班火车。他也似是而非地回笑了一下,没做任何挽留,尽量显出真诚的样子说,那好,我送你上车。
把临风送上火车。回到家已经11点多钟了,他感觉这一天下来从未有过的累。简单洗漱了一下他就爬上了床,很快就滑进了梦的深渊。他梦见两个毫不相干的动物在追逐嬉戏。先是蝴蝶追着刺猬飞,然后停在一根树枝上,刺猬撵过去停在树枝下面,蝴蝶俯冲下来想停在刺猬的身上,刺猬瞬间变成一个刺球,刺破了蝴蝶的翅膀,蓝色的汁液不断从蝴蝶翅膀里流出来,世界顿时变得一片瓦蓝。
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