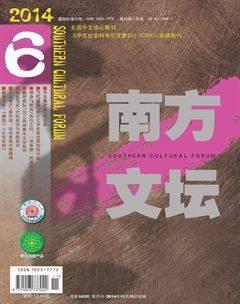中国新诗的旗意象
张立群
像跳动的光焰随风飘动,“旗”作为一种标识常常会在某些场景下唤起人们特定的情感及想象。也许,由于寓意指向过于明确、集中,“旗”没有成为古往今来诗人笔下最常见的书写对象进而发展为诗歌的意象母题,但纵观中国新诗的发展史,“旗”又无处不在并不断呈现新诗与历史之间的“对话”过程。这一过程既是诗意的、情感的与想象的,同时又是诗艺的、文化的与社会的,它通过营造、修饰绘制出各式各样的“旗”,以纷繁的表象反映着诗人“此刻”的内心体验和时代、社会留给诗歌的投影,而“中国新诗的旗意象”也借此获得了研究视野的展开。
一
旗,古语意为一种画有图案的军旗,又作标识、标志之义,后泛指旗帜并有旌、帜、旆、纛等多种表述形式。现代汉语中的“旗”由于词语的组合、比喻义等,又可喻指军队、榜样或模范以及有代表性或号召力的某种思想、学说或政治力量等等。“旗”含义的古今沿用与转义使其拥有了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处于变动的状态。新诗中较早出现“旗”或是其同义语的可列举郭沫若写于1922年的《孤军行》和《哀时古调九首》,其中,前者原文有“张起人道的大纛”,后在1928年编入《前茅》集时改为“撑起我们的红旌”;后者有“神州原来是赤县,/会看赤帜满神州”(1)。从郭沫若在两首诗中以不同的“旗”高歌“前進”、盼望“新世界的诞生”以及赋予的色彩来看,“旗”确然“可以暗示出当时中国的大势”和诗人“自己的心理”(2)。于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中国新诗由于近现代感时忧国的时代背景,注定从一开始就与社会、政治、文化结下不解之缘。随着现代白话在新诗创作中表现力的增强和社会形势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诗逐渐呈现出鲜明的抗争精神及相应的阶级属性,而“旗”也随之在新诗创作中得到了更为繁复的表现。以蒋光慈写于1923年苏联留学期间的《中国劳动歌》《送玄庐归国》为例,“我们高举鲜艳的红旗,/努力向那社会革命走”和“告诉人们,红旗下的生活是怎样呢?”“鲜艳的红旗更把你的血液染红了。”已使“旗”在不断人格化、精神化的过程中,上升至“国家”与“社会”、“革命”与“理想”的层面。然而,这种渴望被带回祖国、唤起劳动者自救、共进的歌声,在现实面前却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在写于归国后的《哀中国》一诗中,“悲哀的中国”与“满国中外邦的旗帜乱飞扬”使当时中国的社会语境得到了直观而形象的表达。“旗帜”持有者身份的变化预示着土地领属关系的变化和现实的残酷:此时的“旗”意象依然可以抵达国家主题的高度,但却有今非昔比、物是人非之感。在此前提下,诗人在诗作中流露出悲哀、叹息及凝重、低回的情绪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然而,在悲哀乍现之余,诗人们与生俱来的“爱国的心”却使其无法消沉下去:“我心头有一幅旌旆/没有风时自然摇摆;/我这幅抖颤的心旌/上面有五样的色彩。//这心腹里海棠叶形/是中华版图底缩本;/谁能偷去伊的版图?/谁能偷得去我的心?”在闻一多发表于1925年的《爱国的心》一诗中,“旗”的“象中之意”显然已被象征化和伦理化了——“旗”归于诗人的心灵,和生命紧密相连,让“旗”意象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而由此考察1925年“五卅运动”对于20年代历史、文学的“分界线”意义,“五卅运动在上海的爆发,把整个中国历史涂上了另一种颜色,文学运动也便转变了另一个方面。”(3)有“狂飙诗人”之称的柯仲平,迅速写出《伟大是“能死”》,要求“男儿呵!可曾磨利着你的兵器?/妇女呀!一夜忙/可曾绣面战旗?”其后,殷夫在《一个红的笑》《Pionier》《写给一个新时代的姑娘》《前进吧,中国!》等诗中,“我们把旗擎高……大风掠着旌旗,/我们上前,上前!”“扯着大旗前进!”等诗句使20年代中期之后诗歌中的“旗”意象已呈现出另一番面貌。
从20世纪20年代新诗对于“旗”意象的关注及凝结的写作经验来看,30年代初期“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继续以“旗”表明鲜明的政治文化立场是不言而喻的。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我们旗帜上的标语是——/保全领土,收复失地”(任钧:《十二月的行列》);“在抗敌的旗帜下面”,“让四万万五千万对仇恨的眼睛/一齐看准同一的目标吧!”(任钧:《中国已经开始怒吼了》)让情感更为激越、诗质更为透明。但这种昂扬、激奋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或曰社会心理,却因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而逐渐冷却下来。人们开始正视战争的残酷性和取得胜利的艰巨性,以及战争时代现实生活的腐败现象,代之而起的是40年代初期“七月派”诗人孙钿在《旗底歌》中对“旗”沉郁、内敛的表述,“中国新诗派”诗人穆旦在《旗》中含蓄、智慧的表达,和臧克家《国旗飘在鸭雀尖》式的实录与叙事。值得一提的是,40年代中国新诗由于地域性及相应的区域政治等原因,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诗歌创作中的“旗”往往显得具体、生动和明确了许多:高咏曾在《旗帜》中描摹了一面在太行山巅、清漳河水上飘荡的旗帜,散发的芳香、激奏着自由与民主、召唤人民在旗下歌唱;严辰和邵子南分别在《我们的队伍》和《人民之歌》中竖起一面“真理的旗帜”,人们“忠诚而坚定”地站立于旗下、行进于旗下;朱子奇和张沛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而作的《我歌颂伟大的七月》和《排列在红旗下》中绘制了“布尔什维克的旗帜”——排列着镰刀斧头的旗帜,工农兵“站在党的四周”“围绕着英明领袖”,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诗的“旗”意象书写都不约而同地延续了这种经验。
二
谈及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至40年代新诗的“旗”意象,外来诗歌的文化资源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以奥地利诗人莱纳·马利亚·里尔克(Re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的创作为例,他的散文诗《旗手》(4)、短诗《旗》及《预感》曾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中得到回应。当然,为了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里尔克作品的本土翻译史。1929年,署名王显庭的译者翻译了里尔克的小说《屋顶老人》,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这被视为里尔克文字被翻译成汉语的“第一次”(5)。1931年,诗人、翻译家梁宗岱译里尔克的文论《罗丹》(收入《华胥社文艺论集》),后于1943年在正中书局翻译出版《罗丹》单行本(包括《罗丹》和《罗丹(一篇演说词)》);1936年,梁宗岱译《一切的峰顶》(杂译外国诗集),收里尔克的诗《严重的时刻》《这村里》,后于1937年再版时补收里尔克的散文诗《军旗手底爱与死之歌》;1942年,梁宗岱在广西华胥社出版《交错集》中还翻译了里尔克的四篇小说。与梁宗岱相比,诗人、翻译家冯至在翻译里尔克的作品时更具主观上的自觉性。1934年,冯至在《沉钟》32期译里尔克的《马尔特·劳利得·布里格随笔》;1936年12月,冯至于《新诗》第1卷第3期“里尔克逝世十周年特辑”中翻译里尔克六首诗,并撰写纪念文章《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在纪念文章中人们可以看到冯至于1926年秋天,“第一次知道里尔克的名字,读到他早期的作品《旗手》(Cornett)。这篇现在已有两种中文译本的散文诗,在我那时是一种意外的、奇异的得获。”(6)1938年,冯至在商务印书馆翻译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后附里尔克的《论“山水”》一文)。此外,在现代翻译史上,里尔克作品翻译较有代表性的还包括1936年卞之琳《西窗集》中据法译本转译里尔克的《旗手》以及诗人吴兴华40年代的译本、“九叶诗人”陈敬容、唐湜在40年代末期《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上刊载的里尔克的译诗等等。
正如冯至所言,“里尔克的诗,由于深邃的意念与独特的风格就是他在本国也不是人人所能理解的,在中国,对于里尔克的接受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竟有人把中国和里尔克这两个生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也许最生疏的事物在生命的深处会有时感到非常的亲切吧。”(7)尽管,没有更多的证据表明现代中国诗人直接化用里尔克的创作经验,但翻译、传播以及将里尔克视为人生道路和诗歌精神的先导和同道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却使里尔克的创作与3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40年代国统区的部分诗人诗作产生“共鸣”。穆旦的《我们肃立,向国旗致敬》(1936)(8)、《旗》(1945);冯至《十四行集》中最后一首;唐祈的《时间与旗》等等,或者以客观之物象征化的手法,赋予了“旗”的国家主题之义;或者以多重的视野,将“旗”置于沉重的历史帷幕之上;或是将其抽象化、成为思想的载体,“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9)这些在特定时代产生的诗中之“旗”,最终见证了时代提供给诗歌的意象与主题。
通过里尔克与抗战至新中国成立前新诗中的“旗”意象比较,人们可以从更为广阔的视域中考察“旗”的主题及艺术呈现过程中的繁复变化。无论是里尔克还是这一阶段的现代新诗,“旗”都经历了现实的、情感的向现代派象征的转变。作为一种共通性,里尔克笔下和现代新诗中的“旗”都不约而同地借助了“风”的力量,进而使“旗”有了形而上的哲思和形而下的具象,“而它的褶纹里默示着多少普遍性!”(里尔克:《旗》)也正在于此!
三
如果将新诗中的“旗”意象做主题史的考察,那么,“旗”在三四十年代大量的浮现,至五六十年代走向极致,一直与民族独立、社会民主等关乎国家主题的内容息息相关。“旗”意象反复在新诗创作中出现,会逐渐形成一种模式乃至体系。它一方面可以以隐喻的形式传达出诗作者复杂的思想感情,给作品定下某种基调,从而深刻地表现新诗的主题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必然秉持一种艺术的立场及相应的审美追求,进而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代表一个时期内诗歌的艺术走向。
对比现代、当代新诗中的“旗”意象,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不同時代“旗”的不同呈现方式,而在这堪称不同“话语讲述”的背后,却隐含着新诗“话语场”的变迁,政治文化对于新诗艺术、创作观念及诗人心态的深刻影响。如果说穆旦写于1945年的《旗》——
我们都在下面,你在高空飘扬,
风是你的身体,你和太阳同行,
常想飞出物外,却为地面拉紧。
是写在天上的话,大家都认识,
又简单明确,又博大无形,
是英雄们的游魂活在今日。
你渺小的身体是战争的动力,
战争过后,而你是唯一的完整,
我们化成灰,光荣由你保存。
太肯负责任,我们有时茫然,
资本家和地主拉你来解释,
用你来取得众人的和平。
是大家的心,可是比大家聪明,
带着清晨来,随黑夜而受苦,
你最会说出自由的欢欣。
四方的风暴,由你最先感受,
是大家的方向,因你而胜利固定,
我们爱慕你,如今属于人民。
是以第二人称的拟人手法,形象地说出“旗”的象征义和主题史——比如:第一节写出了“旗”的位置、高度、指向和“扎根”的特点,它使“我们都在下面”变得自然而然;第二节的“简单明确”“博大无形”,“英雄们的游魂活在今日”让“旗”充满了历史感并指向了战争;但“旗”业已形成的本质并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遗失,她只会随时间增加自己的历史厚度;“旗”的品格是“太肯负责任”,以至于“我们”在艰苦的斗争中有时感到“茫然”,不同立场的人都想利用、占有,但第四节中的“解释”“和平”显然充满了反讽意味并直指诗人正在经历的某些当代现实……从穆旦以现实和现代融合的手法,婉转曲折地揭示“旗”的内涵,人们可以感知一段特定的历史:处于风暴的中心、感知时代的脉搏,“旗”是大家的方向、预言着胜利,如今归于人民,使“旗”最终升华为一个立体的、完整的、有血有肉的意象。穆旦之所以会赋予“旗”意象以丰富的表现力,与其“也许是中国能给万物以生命的同化作用(Identification)的抒情诗人之一,而且似乎也是中国有肉感与思想的感性(Sensibility)的抒情诗人之一”(10)有关。而从观念与艺术的角度上看,穆旦的“旗”又是新诗创作经验总结的结果,见证着中西方诗艺交融、深化的过程。
那么,频繁出现于五六十年代新诗中的“旗”意象,则生动再现了“讲述话语的年代”的隐秘成规:透过那些反复涌现的红色旗帜,人们不仅可以发现此时的“旗”已成为一种符号、一种公共的象征,而且,还可以得出这本就是“话语场”内诗歌生产机制的必然结果:“旗”营造了同时也点缀了当时的诗歌氛围,符合这一氛围下诗歌的写作、发表和阅读标准;“旗”在更多时候不再关乎诗艺的本身,而是引起下文、渲染气氛、抒发情感的契机。透过诸如——
红旗红旗
真真美丽
插遍全球
插在心里——方纪:《红旗歌》(《诗刊》,1958年6月号)
啊!红旗在前,红旗招引……
红旗啊,火样的红,燃烧着战士的心!
我们看见红旗,血液就像钢水沸滚——闻捷:《我们遍插红旗》(1958)
红旗啊,红旗,
红旗在大路上——乘风前进!
红旗在蓝天里——如锦、似云——张志民:《红旗颂》(原文1964,后修改于1977)
以及大量关于红旗的诗句,穆旦时代现代诗的叙述方式已遭遇“自然”地过滤;在主题先行、主题大于形象的习惯思维影响下,诗歌的思想变得异常裸露、透明,不再潜藏艺术个性;那些围绕“旗”而常用的比兴手法,也不过是为了托物起兴、浓重诗歌的格调。历史地看,五六十年代新诗的“旗”意象,由于意识形态机制的制约,在更多的情况下已被抽空了意象所指,唯余符号能指。当然,在具体绘制“旗”意象的过程中,诗人真实的情感、真诚的态度、鲜明的立场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属于创作主体心态层面的内容,显然同样是意识形态规约的结果。
至此,通过40年代与五六十年代的对比,新诗“旗”意象的“变/不变”已较为清晰地显露出来:由于不同的语境,“旗”的表现形式会发生改变,但其已然形成的稳定的价值内核不会发生过多的变化;“旗”的表现方式可以发生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象本身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艺术内涵,中国新诗的旗意象还需在不断历史化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意贯象中、象与意合;“旗”意象在表达上的变化同样反映着诗歌创作手法上的变化,是“现代”的含蓄,是现实的直录,还是浪漫的激情及至主题先行、理念大于写作?上述活生生事实潜含的运行机制早已超过诗歌创作、艺术观念的界限。
四
新时期较早关于“旗”意象的诗应当从艾青复出后第一首诗《红旗》谈起。“红旗是火,/是被压迫者反抗的火,/是被剥削者忿怒的火,/是普天下受苦人的火,/是争自由、求解放的火,……它是理想的象征,/它是信仰的标志,/它是战斗的号召,/它是不屈的鼓舞,/和它在一起就永远胜利”,通过艾青这位跨越现当代诗人的书写,“旗”俨然已获得了较为久远的时间积淀:“旗”于饥寒交迫中像火焰般被点燃,经历硝烟弥漫的战场,如今她继续并将永远引导我们,她在构建未来的同时也在构建自身在当代语境下新的展开。
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的“旗”意象,鉴于此前特定的历史背景、生活经历,诗人的成长史、个体记忆及艺术经验(的转化)首先可以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诗人艾青、公刘、陈敬容等,由于自身的经历,往往在对“旗”意象的使用过程中,强调其公共的象征意义,这一点,可以在艾青的《红旗》、公刘的《但愿我不会那么愚蠢》、陈敬容的《北京城》中“旗”意象上得到具体的证明。而在一批年轻诗人的笔下,比如成名于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人”江河,他的《纪念碑》《没有写完的诗》《葬礼》等作品虽同样出现了“旗”并坚守了理想主义的立场和英雄主义的情怀,但在诸如“我被钉死在墙上/衣襟缓缓飘动/像一面正在升起的旗帜”式的诗句中,第一人称“我”的出现表明个体意识已成为传达诗歌意象的主要表述方式。其次,随着生活的日新月异,“旗”意象也逐渐显露其不断變化的特点,她可以是建设者拓进的象征,是边地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符号,而行至90年代,在更为年轻的诗人如李亚伟的笔下,“旗”又成为怀旧的意象(11)……这不由得需要我们对新诗的“旗”意象及其相关问题进行重新的思考。
能否通过“旗”意象主体意识的嬗变得出不同代际诗人创作观念的变迁?这一点在全面考察之后不仅仅是一个相对于时代、现实而呈现的“集体/个人”的问题,还是一个如何“怀旧”与“记忆”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认为:“怀旧情绪的爆发经常是在革命之后”且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修复型的和反思型的(12)。“修复型的怀旧唤起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因而“倾向于集体的图景象征和口头文化”,“对待自身极为严肃”;“反思型的怀旧更关注个人的和文化的记忆”,“更倾向于个人的叙事,这样的叙事品味细节和纪念性的标记”,且在具体表现时“可能是讽喻的和幽默的”(13)。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中“旗”在相对于战争、革命年代同类意象表达时,确实呈现出浓重的“怀旧情绪”及不同的表现类型。有感于“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人们价值观的迷失、怅惘”(14),昌耀曾于《一天》(1993)中写下“耶稣和十二门徒随着诗人勃洛克的红旗行进。/一天长及一生,千年不过一瞬”。又于《堂吉诃德军团还在前进》中写下“从不相信骑士的旗帜就此倒下”,结合昌耀的创作历程及其自认为始终是一位“怀有左派情感的理想主义者”(15)的心理特征,上述诗中的“旗”潜含着历史、理想与现实“对话”过程中复杂的内容:浪漫骑士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理想主义的刀锋只能作用于自身,忧虑、警示的主题不能掩饰时间之痛与精神之伤。而在写于1994年的《升旗》一诗中,诗人雷抒雁依然以“我们升旗/在东方/以旗帜的语言/为太阳导航/”的诗行讲述着“旗”的故事:“红色/这曾经让人颤栗过的色彩/又让我们如此激动/那些不曾死去的血液/从硝烟的年代/涌流进我们的血管/那些生命最后的语言/终以震惊的色彩/成为永恒的呼唤”,在这种记忆的修复下——“我们无言/面对旗帜/仰望旗帜/我们只是用心在体验、在领会/在感受/一种启示/一种精神的凝聚/或者,在接纳/一种启动灵魂的能源/如同布匹,精神/也需要洗涤/蘸着昂扬的色彩/让清凉的风荡洗/懈怠、萎靡、迷惘和疲惫”的书写,既源于真实、历史和传统、经验,又指向共同的情感、体验和现实与未来,有明显的记忆“复活”和政治抒怀的倾向。应当说,由于生活、创作经历的差异性,不同诗人对于“怀旧”“记忆”和其意象表达方式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一在具体展开过程中会涉及生平代际、成长记忆、创作个性等诸多因素的问题,不仅会影响到诗歌的主题,还会影响诗歌的具体表达方式。“抒情的语言却弯曲成一块漫坡,使妇女们坐下来/忘记害羞,看到了天边的彩虹和婚外的恋爱//但险恶的情形在后边/诗人的才气终遭猖狂的收编和诱杀/然后一切归于大师。”(《怀旧的红旗·第十四首》)在这幅怀旧的图景中,抒情的语言在质地和形态上变得平滑,诗人不再直抒胸臆,生活平常而庸俗,直至价值变得模糊。它是如此怅惘、不失嘲讽,以至于解构了历史和记忆的真实性,而“怀旧”之后的明天,必将仍然是无聊而又世俗的生活情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旗”意象在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中的变化体现了“后革命”的视域下文学创作的整体逻辑:革命记忆的延续与反思革命,而从文化价值的角度上加以考辨,那么,“旗”意象的价值与具体使用过程中的意义模糊又使其明显带有过渡年代的辞藻特征:迂回、善变、不再具有稳定的语义。这当然也是80年代以来生活状况和社会价值观不断变化的结果,但在不同观念立场下,已成为时间、空间和记忆的“双重历史”。它可能是牛庆国重寻长征路所得的长诗《红旗 红旗 红旗》,在具有现代史诗风格的同时不断嵌入今天的眼光;它也可能是翟永明《五十年代的语言》中被重新解读过的“语言”:“那些红旗、传单/暴戾的形象那些/双手紧扣的皮带/和嗜血的口号已僵硬倒下……所有那些失落的字词/只在个别时候活过来”。而现实生活中的旗帜依然矗立高端、迎风飘扬,它们天天如此,只有在偶然的瞬间,才会牵动观望者驻足的目光……
正如安德森所言:“有一种同时代的,完全凭借语言——特别是以诗和歌的形式——来暗示其存在的特殊类型的共同体。”“旗”特别是五星红旗,确然可以像唱国歌一样,会蕴含“一种同时性的经验。恰好就在此时,彼此素不相识的人们伴随相同的旋律唱出了相同的诗篇”(16)。新诗中的“旗”是想象的、带有集体经验意识并具有政治之爱的意象。她在战争年代拔地而起,引领人们为民族、国家、自由抗争直至从容赴死,又在革命年代过后,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而中国新诗的旗意象就这样描绘出其独特的历史风景!
五
按照《比较文学术语汇释》中的说法,意象“是具有某种特殊文化意蕴、文学意味的物象。它存在多种层次,可以是一种自然现象和客观存在,也可以是一种动植物,还可以是一种想象中的事物,等等”(17)。提及意象,熟悉中国古代诗学体系的人自然并不陌生。通过诗人内心体验与客观物象的融合,主、客观意、象内外相合,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历来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突出特点。进入现代之后,意象研究由于受到西方文艺理论各学科交叉、互见和意象派诗歌的影响,得到了深入的发展。“提到意象,吾人立刻会想到庞德(Ezra Pound)的定义‘意象就是在一刹那间同时呈现的一个知性及感性的复合体;这复合体能使人在欣赏艺术品获得一种从时空的限制中挣开来到自在感、一种‘突然成长的意识。意象能在外面面对艺术品的刹那间给我们的感觉是自足的,然后我们才会想到它们所可能给出的意义。”(18)(笔者注:后一句在陈鹏翔的文章中被注明语出弗莱)从多年来致力于主题学研究、成绩卓著的台湾学者陈鹏翔在谈论“意象”一词时,熟悉援引庞德、弗莱的理论,我们不难看出现代视野中意象的认知逻辑及其理论渊源。意象,既是诗歌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同时,也是主题学研究中经常涉及的概念(如意象、意象母题、意象研究等)。只不过,若从主题学研究的角度上加以考量,意象研究还需做如下的注意,“并不是所有的意象都具有主题性的意义。只有当意象作为一种中心象征,与作品的主题发生紧密关系时,才可以成为主题学研究的对象。”(19)
由意象的所指及主题学的理论视野,我们不难看出意象研究不仅需要对文本意象进行内涵、意义的探寻,还期待最终能够提升至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层面。由此考察中国新诗的旗意象,在视觉之象、观念之象和审美之象三种基本表现模式下,“旗”大致可以从如下几个主要方面加以解读。第一,是光明和胜利的象征,正义和理想的化身。牛汉在《有旗帜就扬起来》(1946)中“呼唤旗帜”:“有旗帜/就扬起来!”因为“看见远方有旗帜”,我们就会“突围和行进”“向旗帜/会师!”李瑛在《永不降落的旗》(1984)中称之为“世界的一部分”,“属于人类理想的胜利,/它的价值是无限的”。就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其共同特征是通过抓取“旗”的标识之义,引申出“旗”意象的价值与意义。第二,代指领土与国家。以臧克家《要国旗插上东北的土地》(1936)和彭燕郊的《最初的新中国的旗》(50年代)为例,在“三面旗……一面是吉林,/一面是黑龙江,/一面是辽宁”和“代表我们美丽的国家的这面美丽的旗/是我们自己的”诗句中,“旗”寓意国家与领土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由于此时的“旗”常常和“人民”“战取”“恢复”等词联系在一起,所以,其集体意识、抗争精神和建构意图也往往是十分明显的。第三,指模范形象、权威思想或进步力量及方向。诗人葛力群、刘桂森曾在1948年写过叙事诗《解放战士的旗帜——姚海斌》,它以战士姚海斌的成长为线索,叙述其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英勇事迹,并最终获得“解放战士的旗帜”的称号;曾卓在写于1983年的《理想的象征 战斗的旗帜》来“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这两首诗中的“旗帜”即为模范的“典型形象”;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写过《毛泽东旗帜迎风飘扬》(1952)、《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前进》(1960),这两首诗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新诗创作中具有相当程度的典型性,仅就题目而言,诗中的“旗”的内容所指也是一目了然的。第四,对历史及记忆的言说。这是新诗“旗”意象内涵最为丰富的一个方面。40年代孙钿的《旗底歌》、穆旦的《旗》、唐祈的《时间与旗》、羊翚的《旗帜——写在九一八,为了不要忘却那八年的日子》等都具有回顾历史、言说记忆的特征。“斗争将高于一切意义,/未来发展于这个巨大过程里,残酷的/却又是仁慈的时间,完成于一面/人民底旗——……过去的时间留在这里,这里/不完全是过去,现在也在内膨胀/又常是将来;包容了一致的/方向,一个巨大的历史形象完成于这面光辉的/人民底旗,炫耀的太阳光那样闪熠/映照在外面空间前前后后/从这里到那里。”(唐祈:《时间与旗》)由于“旗”在延展的过程中具有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它不但会增加历史的厚重感,还会在书写“旗”意象时融入更多的艺术元素及创作技法,所以,其复杂程度往往会高于新诗“旗”意象的其他方面,并和那些简单的“旗”意象形成艺术的对比。第五,是和平的代称。张光年的《在绿星旗下》(1936)、杭约赫(曹辛之)长诗《复活的土地》的“第一章舵手”(1949)、郭沫若的《和平的旗帜》(1952)、张学梦的《联合国旗》(1985)等诗作中的“旗”,皆属于“和平的主题”,这种“旗”意象具有很明显的想象性和理想情怀,而其关乎“旗”的领属关系或修饰语也同样值得关注。
总之,中国新诗的旗意象内涵丰富、数量可观,且在具体书写的过程中常常表现为立体的、非孤立、单一的状态。李瑛《我们的旗》既将“旗”作为“钉在空中的我们的行为、思想”,又将“旗”描述为“没有国界会阻拦住你的飘拂”;“你投影在我们心上,我们燃烧着,/把千万只健壮的手臂举起来”,就是一个明证。“旗”意象在具体呈现过程中包括多重含义,进而成为一种集合式的意象,显然与新诗存在的历史语境有关。除此之外,新诗的“旗”意象还会由于修饰语等原因,而使意象本身产生十分显著的意义变化:闻一多在《雪》《天安门》中提到“白旗”;郭沫若在《怀亡友》中以“但不幸我们的革命在中途生了危险,/我们血染了的大旗忽然间白了半边”揭示当时的革命环境;穆木天为《新诗歌》旬刊所写的《发刊诗》中的“吴淞口外花旗太阳旗在飘翻”,等等,都使“旗”在“象”之外另含他意。至于由此可以得出的则是红色“旗帜”是新诗中最常见的“旗”意象,她跨越现当代新诗史、拥有十分广阔的表意空间;她曾在五六十年代政治一体化的年代会聚成“旗”的海洋,极大地强化了诗歌的主题,然而,在那些數量繁多、面目雷同的“旗”意象背后,究竟还存有多少艺术蕴含,也同样成为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
【注释】
(1)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关于两首诗的注释,335、3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郭沫若:《创造十年》,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1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3)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卷〉导言》(影印本),1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4)即《旗手克里斯托弗·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写于1899年。在现代诗歌史上,较为著名的译本主要有:1936年,卞之琳在《西窗集》根据舒姗·克拉(Sussane Kra)法译本转译(陈宁编《里尔克汉语译本系年1929—2008》,认为应为Suzanne Kra,见林笳主编的《里尔克集》“附录”,404页,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名为《旗手》;后梁宗岱在1937年再版译诗集《一切的峰顶》时补进了这首诗,名为《军旗手底爱与死之歌》。
(5)陈宁编:《里尔克汉语译本系年1929—2008》,收入林笳主编的《里尔克集》“附录”,403—419页,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本文记录的里尔克汉语翻译也主要参考了这一“译本系年”。
(6)冯至:《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原载1936年12月10日《新诗》第1卷第3期,本文主要依据《冯至全集》第四卷,8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此外,同期翻译的六首诗包括《豹》《Pietà》《一个妇女的命运》《啊,朋友们,这并不是新鲜》《奥尔弗斯》《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见《冯至全集》第九卷,433—44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7)冯至:《工作而等待》,原载1943年11月《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本文依据《冯至全集》第四卷,9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此诗没有收入李方编选的《穆旦诗文集》(共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笔者最初在易彬的《穆旦评传》中看到此诗部分内容,60—6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后以邮件问询易彬本人,他传给我全文,此处限于篇幅,只注明易彬发掘、整理的原诗出处及其相关内容:“初刊于《清华副刊》第45卷第3期,1936年11月16日,署名慕旦。按:此诗未收入《穆旦诗文集》,属穆旦佚作,重刊于《励耘学刊(文学卷)》,第7辑,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同时刊出的有陈越、解志熙的专题论文《人与诗的成长——穆旦集外诗文校读札记》。”见2013年12月1日易彬邮件附件。
(9)冯至:《十四行集》第27首,后加标题“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见《冯至全集》第一卷,24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0)唐湜:《穆旦论》,《中国新诗》“第三集·收获期”,1948年8月
(11)指李亚伟的组诗《怀旧的红旗》,收入唐晓渡主编《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先锋诗歌》,74—7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此选本为“组诗选四”;后收入李亚伟:《豪猪的诗篇》,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题为《革命的诗》,共计18首。
(12)[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导言”,7页,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13)[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55—56页,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14)(15)均见昌耀:《一份“业务自传”》,载 《诗探索》1997年第1辑。
(16)[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7)尹建民主编:《比较文学术语汇释》,42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8)陈鹏翔:《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见陈鹏翔主编:《主题学研究论文集》,32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4年版。
(19)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第2版),18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3批面上资助课题“现代新诗的國家主题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2013M53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