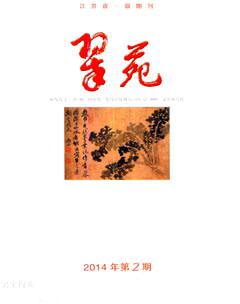茶农
陈维芳
台湾著名的文学大师林清玄先生说“茶”字拆开了就是人在草木之间,人处在天地自然之间,那么我可以把茶农理解为是行走在草木之间,并以此为生存的人。我的父亲母亲便是这样的人。
在我幼年时候的记忆里,在清明节前后就要采摘茶叶了,我对那繁忙、紧张、辛苦的一幕印象深刻。采茶光靠家里的人手是远远不够的,要到邻近村上去请人,母亲人缘很好,她总是早早地上门打招呼,将要请的人员定下来,请她们不要答应第二家的邀请,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请的,需要那人心细手脚利索,能吃苦。母亲请的那些人到最后茶叶采完后便全成了好朋友,是当亲戚一样走动的。来年再采茶时可以不用再请了,虽然我家的伙食跟不上好的人家,可大伙说我母亲人好,待人真心,就算别家再请也都客气地回绝了,有的还自发的带来很多自做的点心、新鲜的蔬菜送我母亲。现如今母亲每每和我说起总是感叹:“好人啊!都是多好的人!”
茶的鲜叶我们叫活草,生长期非常快,隔天的叶片大小、鲜嫩程度就有所不同,所以每天的茶价也不同,为了做出更好的又有市价的茶叶,茶农在采茶的那几个月里都是白天采茶,晚上做茶,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而孩子们不懂这些,忽然发现家里来了很多人,又比平日多了些可口的饭菜,虽然要等大人们吃完才有孩子们吃的,可不妨碍那发自内心的快乐。
我总是在学校快快地将作业写好,然后抱着小书包冲到家,这时采茶的人们陆续回来,父亲会一一称出每个人的采茶重量并大声报数,我会拿出练习册认真记下,碰到姓名中有生字不会写的就请她在纸上写给我看,也有问到一个不识字的她会笑着说你想咋写就咋写,一天的采茶工作有时就在一片欢笑中结束了。
到了晚上做茶完全要靠父母了,那时家中还没有做茶叶的机器,全靠双手揉、培、烘,直到后来生产队里有了茶厂,才可以将活草直接送过去加工,大家轮流值班做茶。再付一定的加工费用给生产队。做茶就用平日做饭的灶头,母亲一遍一遍清洗大铁锅,不能有油渍、异味。父亲对做茶的要求很严格,揉茶手法、下手的轻重,火候的大小都有说法,假如是我看管灶膛的火候时父亲会对着我很慎重地说:“你现在看好了,就依这个火势,不能让它熄掉,你也不能提早加木柴,否则火大了茶叶会焦。”弄得我非常紧张。母亲和父亲会轮流着做茶、看火、烘茶。到了下半夜,筋疲力尽的父亲就倒在灶膛口木柴上就睡着了,灶膛里的火光映照在父亲黝黑消瘦的脸上,安详、温暖。没有平日里那张严肃寡言让我敬畏的脸,灶膛里的木柴发出轻微的劈啪声响,火舌一闪一闪抚摸着辛苦劳作的父亲。母亲这时会停止炒茶,好让父亲再躺会,她开始去烘茶,可是烘着烘着母亲也会在等着翻茶的间隙里打瞌睡,而我们这些孩子一直在屋子里跑来跑去,不去睡觉,瞧见母亲的头慢慢垂下来,我们轻手轻脚地走过去站在母亲的身边伸出双手,等着母亲靠在我们的手掌心里,等着母亲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们歉意地一笑时,我们带着稍许捉弄又好玩又孝顺的心情咯咯地笑不停。
做好的茶叶父亲会称好重量分装包好,天色微明就赶到集市上,将那些还余留着全家人温热的茶叶交到知味或不知味的人手里。母亲是个美丽、贤惠、勤俭持家的人,记得有一次在做茶时不小心将油罐打翻在茶叶锅里,母亲舍不得扔掉,竟然像吃菜一般将那些油茶吃了,之后满嘴发苦发涩,几天吃饭都无味,我无法理解母亲这个举动,至今我问起母亲她从不说:“是不该吃”,她只是说那时的油多金贵,那茶叶多不容易采啊,扔掉多可惜。忽然我内心有酸酸的潮湿涌入眼眶,在那一刹那我竟然体会了母亲用整个身心去热爱茶叶的心情。望着眼前双鬓斑白的母亲,岁月带走了她风华和容颜,美丽不再,可烙印在骨子里的秉性是改变不了的,仍然一如既往做些她力所能及的事。我捧着母亲有着老年斑的手,这双紧紧护着我们长大成人的手,多想用我这个女儿的青春去滋润她啊!若问她什么叫知味,她是不懂的,但是,母亲却用她一生阐述了什么是知味人生。
父亲对于年幼的我来说是有距离的、敬畏的,我们甚至很少交谈,记得上学时要很早去学校,父亲放心不下时时要陪着我走一段,走着走着他就会落后很远,我回头一瞧,他居然在打着瞌睡走路,小小的我心里有些抱怨,既然这样干嘛要一个老早起床送我啊?反倒是耽误了我的时间。现在的我回头看来对父亲更多是怜悯和不舍的心,即便如此我那那疲惫不堪的父亲仍然放心不下他那独自走山路上学的孩子,即便是打着瞌睡走路也要送一程。可是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在同病魔做最后的斗争,一日夜里,我们坐在父亲的床前看望他,他忽然握住我的手,又使劲地握了一下,轻拍了一下我的手背没有说一句话,那深陷的眼睛久久地望着我。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啊!像灶膛里烧火的木柴,像路边风吹日晒的石块,扎得我很疼,我很不习惯这种方式,心里有些别扭,只是这是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握着我的手,没有等我学会怎样去握住他的手,没有等我学会怎样去表达对他的感情,父亲永远永远地走了。
多少年已过去,清明时节我再去看望父亲,父亲安睡的地方前面是一片笼翠的竹林,后面是一片黑黝的茶树,年复一年,茶树又开始吐新绿,父亲不用在清明节时如此辛苦忙碌了,永远沉睡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我跪在墓前,回想着在灶膛前睡着的父亲,打着瞌睡送我上学的父亲,那双长着像木柴像石头的手的父亲,我轻轻地一遍一遍呼唤的父亲,眼泪,终于崩溃决堤。
我想品茶的人如果是天上的神仙,做茶的人应该就是遗落凡间尝遍人生百味的一粒佛珠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