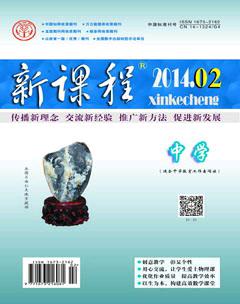语感含义概说
崔秀坤
我国最早提出“语感”问题的是夏丏尊先生,其后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开始倡导语感教学。
夏丏尊和叶圣陶在《文心·语汇与语感》中说:语感是“对辞类的感觉力”。
叶圣陶在《文艺作品的鉴赏》中对语感作了描述:“不了解一个字一个辞的意义和情味,单靠翻查字典是不够的。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随时留意,得到真实的经验,对语言文字才会有正确丰富的了解力,换句话说,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灵敏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叫做‘语感”。这是我国关于语感的最早解释。为了说明这个意思,叶圣陶还在他的《语文教育论集》中引用夏丏尊先生的一段话作为佐证:“在语感锐敏的人的心里,‘赤不但解作红色,‘夜不但解作昼的反面吧。‘田园不但解作种菜的地方,‘春雨不但解作春天的雨吧。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自然的画工,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旨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寞等等说不尽的意味。”这一切的感受和意味,就是语感。
近几年来,关于语感的本质特征,许多专家、学者以及教育教学工作者从语言学、心理学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有见地的阐述。王尚文先生在他的《语感:一个理论和实践的热点》中认为:“语感是人对语言直觉地感知、领悟、把握的能力,即对语言的敏感,是人于感受的刹那毫不遐思索的情况下有关的表象、联想、想象、理解、情感等主动自觉地联翩而至这样一种心理现象”;刘忠华在他的《浅谈发展学生语感的实践策略》中认为“语感是对言语的直觉的、整体的领悟与感受,是在长期的规范语言运用和语言训练中养成的一种对语言文字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比较直接、迅速、灵敏的领会和感悟能力”。他们的定义或解释为我们从不同角度认识语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笔者认为,语感是主体对语言文字的感受,是人们在长期的语言(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实践和训练中培养起来的,与主体即时的思想心境有一定联系的,对语言文字比较迅速、灵敏的领会和感悟能力、语言判断能力。它往往突破语义的束缚,同时受语境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对言语活动起调节和控制作用。
王尚文教授在几年前说他一次遇到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五岁,她俩都穿着新衣服。王问四岁的孩子:“是你的衣服漂亮还是她的衣服漂亮?”这个孩子说:“我们两个的衣服一起漂亮”。那个五岁的孩子忙说:“不要说‘一起漂亮,要说‘都漂亮”。王问她为什么不能那样说,孩子想了好一会儿,摇摇头说“不知道”。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得出:第一,四歲孩子的病句说明母语的语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第二,五岁孩子凭语感判断了“一起漂亮”的说法不对,却说不出其中的道理,可见语感不是基于理论分析的结果。也就是说,知识和理论不是形成语感的必要条件。
语感是一种“顿悟”,是一种不假思索的语言判断能力。它以感性的、直觉的形式表现,依靠直觉,结合主体即时的思想心境,对语言文字加以分析,而不依赖分析思维;其实质是感性中暗含着理性,直觉中积淀着思考。语感也是一种动态的心理过程,即有感知、记忆、联想、思维等心理因素参与的认读、理解、领悟、感受的阅读心理过程。它包括了良好的语言环境中反复运用语言而不自觉地积累形成的良好的语言习惯,这些习惯与素养又有经验的融合,以上是彭天翼在他的《语文美育论》中的论述。
语感往往突破语义的束缚。语言的字面指示义原是与客观事物的本相相对应的,它具有指物、状形、定性的功能,但为了表达情意,往往不满足语言的字面意义的指物、状形、定性,总是调动一切手段拉开语言与客观事物的距离,改变语义与客体的对应性联系。通过对事物创造性的变形抒写,以表明内在的体验。
在语感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言语主体对语境、语义的认知及对言语客体的认知,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的态度体验,是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调节自己的行为,克服困难,从而实现目的的心理过程,互动的言语双方对特定语境中的个体言语所做出的反应行为,或是言语主体对具体语言材料刺激所做出的相应的反应行为伴随其始终。
以上仅是笔者有限阅读后的一点归结,不当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 辽宁省瓦房店市复州城镇第二高级中学)
?誗编辑 马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