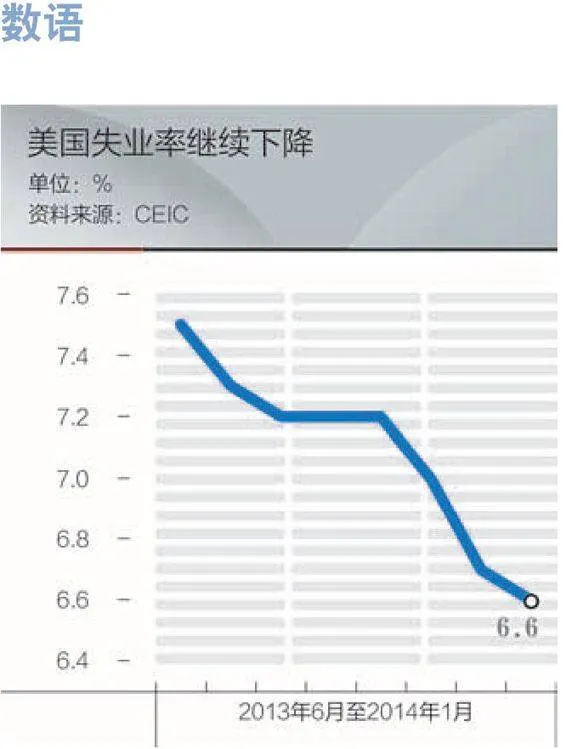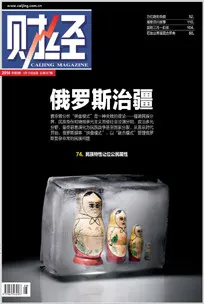学术观点
焦点
重启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失衡
北京大学 柳庆刚、姚洋
“地方政府竞争和结构失衡”
《世界经济》2012年第12期
在政治锦标赛的框架下,地方政府成为生产型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表现为更偏好于投资生产性的公共品,挤压其他非生产性但和民生福利紧密相关的支出项目。生产型政府会加大自身部门的储蓄(投资)倾向,也会通过生产性公共品对企业部门形成补贴,从而进一步加大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及再投资倾向,最终导致低消费和高储蓄的经济结构。当国内储蓄增长过快而国内投资因金融抑制和投资回报率下降等原因无法跟上时,就会形成净储蓄,即经常账户盈余。
鉴于结构失衡源自体制结构问题,要做结构调整必须进行体制改革,而结构的严重失衡就是重启改革议程的契机。首先,要削弱乃至废除GDP挂帅的政绩考核模式;其次,要建立真正的公共财政,强化政府的公共性质,强调民众参与程度。民众参与虽不能解决政府的所有问题,但至少能降低政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的比例。
公共财政型政府和生产型政府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目标单一,即经济增长,而前者目标多样。如何在多样的目标下进行取舍,是公共财政型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更透明的公共财政制度以及更大的民众参与程度,是解决该难题的必由之路,即为了进一步突出财政的公共属性,既要深化公共产权收入制度改革,又要尽快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制度,最重要的是建立编制、执行、监督相制衡的预算管理体制。
中国面临如何从国家规则的从属者到国际规则制定者的转变,也面临着如何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到一个较为富裕国家的转变。这两个转变是由经济增长所促成的,但不可能由经济增长来完成,这需要从理念到实践各层面的跨越式变化。增长模式的转变是这些变化之一,其核心是从“生产型”增长转变为“福利型”增长,而其中的关键是政府转型,即从生产型政府转变为关注提高民众福利的政府。
制度
国有企业改革与福利水平改善
南开大学 盛丹
“国有企业改制、竞争程度与社会福利——基于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考察”
《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4期
运用1999年-2007年我国工业部门34130家持续经营企业的微观数据,对我国国企改制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其对福利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国企改制对企业加成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使企业加成率明显提高,且这种加成率的提高主要集中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
这说明在高竞争度行业,国企改制能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原因在于,在高竞争度行业,企业竞争较为激烈,企业通常是价格的接受者,难以通过变动价格提高加成率。改制后的企业更多通过创新或内部机构重组,降低企业边际成本,从而有利于社会福利提高。但低竞争度和竞争程度降低的行业,这种作用并不明显,甚至不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
此外,国企改制、行业竞争程度和市场化改革之间存在协同效应: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利于国企改制对社会福利发挥积极作用。
观点
积累人力资本
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Stefano Mosso
“人类发展和社会流动的经济学”
NBER工作论文第19925号
已有大量文献讨论了儿童在发展早期的状况对成年后人力资本的影响,尤其是早期状况对获取技能的影响。
当然,这种特定投资既可能来自国家,也可以来自家庭,但都会对儿童早期的人力资本起到巨大作用。但没有针对性地对贫困家庭进行转移支付,可能起不到帮助儿童的效果。也就是说,既然不同的阶段对儿童早期的人力资本和技能获得有重要影响,那么对贫困家庭的转移支付最好也与这些阶段相对应,这样可以把钱真正用在儿童发展身上。尤其是考虑到儿童早期的技能获得将会在未来产生极大的收益,就应该注意转移支付的阶段。
指导、抚养、依偎等都至关重要,不管在儿童发展的哪一个阶段,都是合用的,且有助于开发儿童掌握技能的能力。下一阶段的家庭研究应着重于研究蓬勃兴起的儿童自主性,考察儿童自主性在应对家长、指导者和教师时起到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