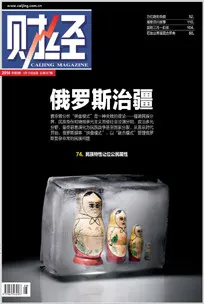帝国农民负担
1910年4月19日下午,浙江慈溪。千余名农民冲入城中,攻击“正始学堂”,“意图将全校教员悉行烧毙。幸各教员及学生越墙而出,得未罹祸,而全校已焚毁无遗”。
随后的几天内,农民们“复焚毁讴浦、进修、龙西三校”,又焚毁鸡山、无择两校,又捣毁龙东、凤山两校,“教员及执事人等,颇被殴伤”,全县各学堂惊恐之下,全面停课。
很难相信,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有着重教传统的江南。更难相信,晚清十年,捣毁学堂的事件,几乎在全国各省都有发生,《东方杂志》甚至质疑:“毁学果竟成风气耶?”
不幸的是,“毁学”的确“成风气”了。而其背后则是清帝国农民负担的不堪承受之重。
永不加赋
中国的农民,曾经以为自己遇上了史上最好的政权——1712年,康熙皇帝宣布史无前例的仁政,“永不加赋”——以当时的人丁数为征收钱粮的上限,此后即便人口增加,国家也不再加收人头税,不只是五十年不动摇、一百年不动摇,而是永远不动摇。
当然,如同任何改革都有自利动机一样,“永不加赋”不仅仅是惠民,也是维稳。
彼时最严重的盛世隐忧是大量人口为逃避繁重赋税,选择成为“黑人”,没有申报户口。而在经济大发展的时期,这些“黑人”却只能打“黑工”,甚至都不敢去开荒——开荒就意味着要承担苛捐杂税。于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出现了:大量的土地乏人耕种,伴随大量“失地”兼“失户”农民成为“黑人”。在土地兼并中形成的一小群既得利益集团,却同时享受着土地兼并和“黑工”廉价劳动力的双重优势,且因为其自身家庭人数普遍稀少,承担着与资产规模并不相称的较低税赋,因此而拉低了整体的财政收入。
这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无论是财政角度还是政治角度,都是巨大风险。在部署“永不加赋”时,康熙明确提出,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搞清人口确切数据——当农民不再担心赋税负担时,就没有必要隐瞒人口。
与大清官方的自我表扬及后世的广泛称颂不同,“永不加赋”这一千古仁政,在推行初期效果并不好,甚至成为苛政。造成异化的原因,是执行层面的“技术”问题。
“永不加赋”的定额税,要层层分摊,最后具体落实到每家每户。作为“分子”的税赋固定,作为“分母”的人丁数却是变动的,地方政府要通过保甲制度调节人丁与税赋之间的关系,每年需修订编制“实征册”及“盛世滋生册”,计算确定每“甲”中的人均税赋。这为地方胥吏们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永不加赋”的政策在执行中被扭曲:其红利被地方官吏和地主们独享,而大多数农民则只能啃到骨头,最后造成了“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者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的局面。
雍正改革
如何让“永不加赋”的红利惠及农民?体制内的改革者将矛头指向“以田为经,以丁为纬”、同时征收田赋和丁税的双轨征收制,提出了“摊丁入亩”的思路。
“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就是把人头税(丁税)合并到土地税(田赋)中,一并征收,以期推进公平税赋、优化税赋结构、提升税赋征收效率。
对于这一改革,无论康熙还是雍正,都有相当顾虑。毕竟,这动的是地主们的奶酪,他们田多丁少,本来承担的丁税就很低,而其中不少人又有“功名”在身,无需服任何徭役。一旦“摊丁入亩”,他们的税赋比重将大大提高,等于他们将用货币化的方式承担国家的徭役。
康熙晚期,在广东和四川进行了谨慎试点,“公私称便”,但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才开始在全国陆续推开。以康熙五十年为基数确定的全国人丁数(2460万)和全国丁银数(335万余两),都固定下来,基本被摊入各地的田赋,“地丁合一”,一体“输纳征解”。
“摊丁入亩”最大的受益者是农村的无田贫农及城市平民,他们因此摆脱了徭役,得以安居乐业,其体现就是人口的井喷式增长。城市平民则因为没有田产负担,开始全力投入商业运营。对政府来说,此前征收难度相当大的丁税,被捆绑进了不可移动和隐匿的土地税,大大提高了征收效率,各地财政收入有不同程度的“溢额”情况。政府不再下民间摊派徭役,转而到市场上购买劳动力,推行“雇役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再就业机会,并推动了劳动力市场兴起。
与此同时,雍正还试图割除另一个农民负担的毒瘤——“耗羡”。
所谓“耗羡”,是“火耗羡余”的简称。“火耗”,指的是将碎银铸成银锭时的损耗;“羡余”,是指粮食在搬运仓储过程中被鸟吃、老鼠偷等造成的损耗。因此,政府在向农民征收皇粮国税时,往往在额定的标准之外,加收一定比例的“火耗”与“羡余”,用以弥补这些损耗。究竟按多大比例抽取,法无定文,完全由具体负责的官员自行决定。这种弹性成为寻租的最好工具。
清初曾严禁征收“耗羡”,但因为延续了明朝的中央财政大一统及官员低薪制度,地方政府缺少基本的运转经费,官员靠正常收入无法保障基本生活,“耗羡”这一明朝苛政也被延续下来,成为体制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顺治年间,“天下火耗之重,每银一两有加耗至五钱者,白粮每百担,官耗至五十两”(《顺治朝实录》)。到了康熙、雍正时期,越演越烈,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
体制内一些改革者提出,既然难以禁绝、无法禁绝,那就退而求其次,不如摆到台面上,实行“耗羡归公”,统一收支,统一监管,将其对政权的杀伤性减少到最低。不过,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将桌面下的弊政堂皇地端上桌面,并非体面的事情,康熙曾经相当犹豫,不敢决断。到了雍正接班后,结合整顿吏治,才下决心改革,并且在这盘上不了台面的菜中,加入了绝对堂而皇之的“养廉银”作料。
根据雍正的思路,“耗羡归公”就是将耗羡的征收从暗变明,以省为单位统一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严防坐支,因此可将其纳入官方监管体系,实行阳光收费和阳光开支;“耗羡”的用途,一半左右作为官员的养廉银,堵上“逼官做贼”的体制漏洞,其余的则全部补充为各地的办公经费。同时,向官员发放“养廉银”,十数倍、数十倍于年薪,有的岗位达到了惊人的130多倍。
“耗羡归公”的确在一段时间内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统一了征收比率,造成实际征收比率大幅下降;官员个人横征暴敛的积极性消褪;丰厚的“养廉银”,再加上雍正对贪腐行为的严厉打击,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官员们敛财的欲望。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场改革是一次对官员的“赎买”,通过对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体制性“漂白”,换取官员们对规则和体制的尊重,及对农民的“放一马”。
惯性强大
帝国的农民没能高兴多久。
雍正批准“耗羡归公”前,最担心的就是“耗羡归公”之后,官员们仍会想出别的办法和名目,征收更多民脂民膏。他的担心不久变成现实。反腐风头过去后,“耗羡渐同正项”,“州县贪员,重新征收,于耗羡之外又增耗羡,养廉之中又私取养廉”。乾隆年间,各地征收苛捐杂税,或直接以“耗羡”名义征收等情况,日益严峻。高额的养廉银已经难以打动领导干部们的心,他们需要更多银子。京官吃外官,大官吃小官,小官吃小吏,小吏吃百姓,胃口越吃越大。已被“整合”到“耗羡”中的各种苛捐杂税,纷纷重出江湖,“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两项改革,自此实际化为乌有。
到晚清改革、尤其是最后十年的新政改革时,百废齐举,财政却难以提供支持。中央能做的,便只有给政策、开口子、依赖各地自筹自支,允许地方“因地制宜”地将改革成本转换为各种捐税。地方政府和贪官污吏趁机搭车收费,“朝廷责之酷吏,酷吏责之有司,有司不取之百姓,将于何取之”,“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形成了改革越深入,苛捐杂税越多的恶性循环。
粱启超曾感慨:“教育之费取诸民也,警察之费取之民也,练兵之费取之民也,地方自治之费取之民也。甚至振兴实业,所以为民阔维持生计者,而亦徒取之民也。民之所输者十,而因之所得者二三,此十之七八者,其大半皆经由官吏疆臣之手,辗转衔接,捆戴而致诸辇下矣。”
1909年,御史赵炳麟列举了各省开办新政所需费用:“司法一项约费百万,教育一项约费百万, 巡警一项大省约费三百万、小省尚需二百万。单此三项计之,各省每年平添四五百万的开支。”
改革的成本,最终落到了农民的头上。美国学者周锡瑞指出,晚清的新政改革只是有利于上层社会,而担负新政捐税的是中国比较贫困的阶级,“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简单的乡下人在其委屈不满中,认定新政就是邪恶的”。“结果,人民站起来了,针对上流阶层的西方化改良主义而进行暴力反抗。”(《改良与革命》)
在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江浙地区,“毁学果竟成风气”。1910年被中央文件提及或者重要媒体报道的20起捣毁学堂事件,浙江9起,江苏6起。
是什么令注重教育的江南农民,将怒火喷向了新学堂,甚至还追打学生?发布于1904年的一道圣旨中尖锐地指出:“从来立国之道,惟在保民。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深宫 怀,常切疚心。
“兹特明白宣示,所有各省派捐等款,除有大宗收数者,姑准照办外,其余巧立名目及苛细私捐,即概行禁止。凡地方应办要政,仍当次第推行,一切学堂工艺,有关教养之事,但当官为剀切劝导,应由绅民自行筹办,不准藉端抽派,致滋苛扰。
“各该督抚务当督令属员,深维邦本,共体时艰,毋负朝廷,不忍重累吾民之至意。”
只是,对于食髓知味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言,农民负担及政权安危早已算不得什么。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