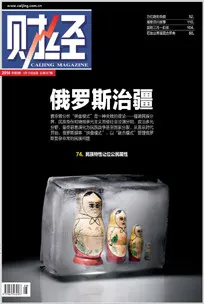精英利维斯
1895年,利维斯(F.R.Leavis)出生在剑桥一个书香门第;除参加“一战”和为数不多的几次学术访问以外,他几乎在剑桥度过了一生。
利维斯毕生笔耕不辍,自由驰骋在文化批评、诗歌批评、小说批评等领域,其《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英诗新方向》《教育与大学》《伟大的传统》等多部力作,成功改写了英国诗歌史和小说史,形塑了20世纪中期英国的批评图景,提升了“英文”及文学批评自身的地位。
更加重要的是,利维斯创办了旨在以严格独立的批评,体现一种标准,从而培养读者的识别能力的文学评论季刊《细察》(Scrutiny),培养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与一批忠实读者,建构了英国文学史、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利维斯主义,有效地改造了自己所在时代的精神。利维斯因此通常显影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批评家之一,但显见于其作品中的精英主义思想,也令他成为最具争议的20世纪英国批评家,遭遇边缘化。
关于这一点,利维斯的成名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可谓最佳证明。一方面,《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作为利维斯对英国文化及文化变迁的严肃思考,能让人从中看到他为提高社会的精神格调、培养公众智慧、纯洁国民趣味的努力,尤其是他对整体生活方式的强调、对广告和电影等大众文化的关注、对理想读者的呼唤。但另一方面,利维斯显然继承了19世纪英国文化精英主义者马修·阿诺德的文明与文化二分思想。
由于二者所处环境不同,他们心中的文化不尽相同:阿诺德所谓的文化意指“甜美”与“光明”,而利维斯的文化问题则主要是语言问题。另外,作为阿诺德文化政治学的忠实信徒,利维斯坚持文学“有一个有机的形式,或者根据作者心目中的重要性建构一个有机秩序”,坚信在任何时期,有洞见地理解艺术与文学都是依赖于极少数人。
具体讲,利维斯认为,虽然仅有少数人能欣赏但丁、莎士比亚、哈代等作家,但他们却有建构出某一时期的人类意识的能力,不但通过保存传统中最精致、最容易毁灭的部分使我们获得人类经验的精华,而且通过确定美好生活的标准使我们具有价值判断能力。少数人于其间所倚重的,是语言及随时代而变化的习语,如果没有这些语言及习语,精神的特性就会因受到阻碍而变得不连贯。基于他对语言的这般认识,利维斯俨如阿诺德那样,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文明”与“文化”相对立的时代,深陷在以处心积虑地利用廉价反映为文化特质的“文化困境”之中。
比如,就报刊而言,“它们始终被伴以一个降低的过程”;电影现在“屈从于最廉价的情感诉求”。所以,英国正遭遇一种“总体文化困境”,表现为界标的滑动、增加及过剩。换言之,总体文化困境的出现,暗示着文化已被文明——标准化与平庸化所代表的功利主义——破坏,虽然大众对危机所警示内容的认识并不普遍。
破坏文化的文明首先来自最能代表工业革命的机器;它们在史无前例地变革生产方式的同时,给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英国有机社会的消失及少数人文化陷入危机。
利维斯指出,以机器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及随之出现的批量生产技术,使得英国不仅不再有见多识广的大众,而且目睹了英国诗歌惨淡收场,出色的价值观不再为少数人以外的任何人所关切,最终灾难性地毁掉了高雅与大众趣味完美结合于其中的有机社会及少数人文化。
此间的利维斯看到了英国有机社会的消失与美国化的关联,认为英国文化问题的症结之一在于发生在英国及世界各地的、以“更高效益、更多销售、更多批量生产与标准化”为特征的美国化。但令利维斯遗憾的是,英国大众对美国化的后果不甚了了,也不打算逆转美国化过程,尽管这正极大地危害着英国的报刊、广告、电影等大众文化。
不难发现,支撑利维斯批评的是一套褒扬精英文化、鄙夷大众文化的批评框架,是他对传统纯文学的怀旧。殊不知,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还是文学批评,都已然与意识形态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独立于一切之外、游离于意识形态之外的纯文学已死亡。正因如此,名扬天下的利维斯并未获得剑桥大学校方的青睐,一直处于学院体制的边缘,直到退休都没能获得教授席位。
作者为社科院外文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