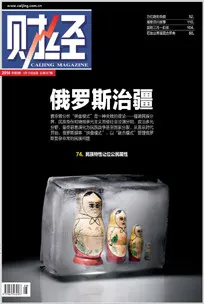全球经济协调断层
乌克兰动荡的阴霾,把已是阴云密布的新兴市场搅得更为躁动不安。
此前,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均未被归类于新兴市场板块的最脆弱国家之列,但政局不稳及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使两国股市在3月3日开盘即大幅下挫,最终均跌收10%以上。针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债务违约的保险成本跃升了15%,小麦、石油和欧洲天然气等严重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宗商品则价格飙升。
市场形势随后陡然急转,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撤军,市场迅即做出正面反应:3月4日,俄罗斯股市展开强劲反弹,股市升逾5%,卢布反弹,欧股也相应大幅回升;美股全线大幅反弹,不但一举收复了此前因乌克兰上空战云密布而录得的跌幅,并走出了多头吞噬的强势形态。财务顾问公司deVere Group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奈杰尔·格伦认为,政治和军事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资本市场的动荡,但这只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颠簸,市场会迅速复原,尽管更多的担忧会指向新兴市场,但相信在尘埃落定后,这更多的是一个区域问题。
即便如此,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政治风险给新兴市场的周期性下滑带来更多挑战。与此同时,美国2月制造业活动自八个月的低点反弹,1月消费者支出增速超过预期,汽车销售增加、建筑支出也意外扩大,种种经济回暖迹象表明,继近几个月经济突然放缓后,美国经济正重获上升的动能。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预计,与其他工业国相比,美国经济前景乐观,有理由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将达到3%左右。
美国国内经济基本面的好转与新兴经济体持续下行的风险相对应,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之间的龃龉也在加深。一方面,金融一体化正使得危机的发展更具有破坏性;另一方面,全球宏观层面的协调合作却不尽如人意。
芝加哥国际事务委员会前执行主任、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托马斯·莱特对《财经》记者说,金融危机塑造的新现实是,尽管仍有支持全球经济的意愿,但让美国来支持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几乎不可能,而涉及到应对危机的具体国际合作行动,包括二十国集团(G20)在内的全球治理工具都缺乏前瞻性和有效性,尤其是在应对全球及区域的经济、金融安全的问题方面。
IMF总裁拉加德表示,未来几十年起支配作用的“两大涌流”,一是全球相互关联性增加带来的紧张关系,二是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紧张关系,而解决这些新出现的全球紧张关系的解决方案是加强国际合作框架,简言之就是为21世纪创建新的多边主义。
歧路扬镳
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在贸易、银行业与FDI几方面联系紧密,而全球相互关联性增加带来紧张关系的一个表现。莱特说,就是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同最初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是两重天地。而美联储在缩减量化宽松时是否考虑到溢出效应,则是一个至今都打不清的官司。
新兴国家和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官员在该问题上的分歧,在2月23日闭幕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得以释放。2013年因卢比不断贬值的经济危机而走马上任的印度央行行长拉詹就指出,美联储在缩减QE时应当考虑到溢出效应。拉詹表示,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均普遍认为,所作的决定需要经过周密的思考而得出,应该担心溢出效应。受美国货币政策退出影响而遭受投资者撤出的南非官员也有同样的呼吁;而发达经济体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官员则支持美联储根据美国情况作决定。
G20上演的这一幕只是显象,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近来的一次调查显示,对美联储缩减QE的政策决定存在观点的截然对立。对OMFIF的问题:美联储此决定应当完全按美国经济的需要还是更多地考虑其他国家的需求和希望,53%的人认为应以国内经济为指引,47%认为应当考虑溢出效应。
美联储主席耶伦强调,只有美国经济展望严重恶化的情况下,美联储才可能考虑暂停缩减购债。格伦对《财经》记者说,全球市场各自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运转,尽管各差万别,但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市场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互关联。而美联储缩减债券购买的举动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美联储政策影响下,新兴市场的脆弱性暴露无疑,彰显了和发达经济体相较偏高的政治风险和偏低的政策可靠性。认同美联储如此决策的经济学家强调,美联储紧盯美国经济并依职责行事无可厚非,除非G20及其央行行长们形成一致观点,加强全球制度化的货币合作,否则大家除了抱怨之外无计可施。
此时G20更多沦为一个聚会场所。悲观者如英格兰银行金融稳定执行主管安迪·霍尔丹指出,新兴市场的不安因素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没能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不能更有效地合作,国家都为了自身的利益各自为战,而不顾及更广泛的金融系统的利益。
对于G20的功能,莱特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一种把它当作危机解决机构;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G20是全球经济现实的体现——新兴势力已经超过了G7或G8所能涵盖的范畴;还有一种观点极力推动G20在全球经济之外,承载更多的议题,如外交政策。
不管以何种诉求为主,以G20为平台的合作都进展缓慢,不仅金融危机之际的众志成城烟消云散,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能力也未能充分展现出来。莱特将此归因于国与国之间巨大的差异。
以刚刚结束的悉尼G20会议为例,新兴市场指责美国的货币政策导致资本外逃,美国指责新兴市场自身基础不牢;同时,美国与德国关系也紧张,美国强调德国应采取更多行动扩大投资并提振国内需求,以贸易为经济支柱的德国也反击美国货币政策不当。
G20及非政府组织网络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WTO和IMF都属于全球治理工具,这些都是解决全球问题的载体,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杨盼盼看来,全球宏观政策协同中,发达国家之间的政策协同相对较好,而在经济向好之后,这一协同将会更为乐观;与之相对,新兴市场之间的政策协同仍然较弱,多边合作领域的实质性进展较小。
杨盼盼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政策协调存在三个主要矛盾: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负面外溢效应,新兴市场国家多有怨言;发达国家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批评主要体现为国内经济结构改革的速度过慢,拖累经济增长;全球及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建立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呈现各自为阵的局面。
谁主世界经济格局
俄罗斯军队一进一退似乎局势峰回路转,但事件对两国的经济、对欧洲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并未由此柳暗花明。而普遍的猜测是,制裁俄罗斯会使俄罗斯在贸易和银行业方面受到较大损失。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截至俄罗斯卷入乌克兰危机之际,今年从俄罗斯股市出逃的资本已经高达20亿美元。而去年全年的总流出不过42亿美元。
相对而言,欧洲主要国家在贸易和金融系统上受到的冲击较小,较小的国家可能损失出口和旅游业方面的部分收入,但其能源安全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比尔·威尔森对《财经》记者说,俄罗斯在冬奥会举办前经济就近于停止增长,现在俄罗斯经济正在陷入衰退,而全球的经济并不强劲。也因为同样的担忧,G20的重点首次从倡导紧缩变成了促进经济增长。G20联合公报中指出,将制定雄心勃勃但切合实际的政策,目的是在今后五年使GDP总额比现有政策形成的轨迹高2%以上。
杨盼盼赞同其背后的政策主张,但对这个促进经济增长的行政指标性要求,则不敢苟同。她说,产出的增加,如果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恶化,则对长期增长有害,危机之前的发达国家和危机之后过度刺激经济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教训并没有消失,因此,以刺激带动增长的方式不可取,而如果希望进行结构改革,就不应当制定增长目标。
拉詹在出任印度央行行长前,引用地壳构造板块挤压冲撞形成的断层线为喻,试图解释六年前的金融危机,书名亦叫《断层线》。而莱特发现,在全球经济秩序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断层。
尽管包括IMF在内的全球治理层面的机构都在运转,但它们不能解决全球经济秩序的基本面存在的断层。从长期角度看,世界经济格局挺过了1994年的墨西哥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但引发危机的高油价因素、金融失衡、天量的资本流动、金融创新与去监管化等制造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却未能解决。
有趣的是,世界经济秩序存在缺陷被世界广泛接受,却基本上被美国忽略。威尔森说,美国过去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发挥引领作用,现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角力及美国的经济挣扎伤害了美国的能力。在美国模式或华盛顿共识受质疑之际,中国能起到什么作用仍不明确。
杨盼盼认为,危机后的欧洲和日本的复苏疲弱、美国的再工业化、TPP/TTIP为代表的世界贸易规则重塑,都使得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增长趋势的脱钩难以为继。中国的国内经济改革、对外走出去的战略,将在需求端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新的大市场机会,在供给端通过直接投资改善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潜在增速水平。中国将有望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良性趋势脱钩中扮演关键的历史性角色。
悲观的是,发达国家重新成为主要增长引擎,可能会削弱新兴市场的经济地位,新兴市场国家将更多地丧失话语权。格莱认为,此后的世界经济秩序可能不是各经济体的趋同,而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和其他经济体上下波动。
乐观的则是,如果发达国家经济继续恢复,全球经济的增长模式将从危机后逐步趋同于危机前模式。杨盼盼说,尽管这一模式也有诸多弊病,但是所需要的政策协同是相对较少的,政策冲突自然就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