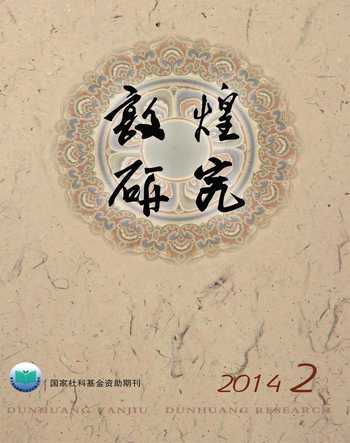从章句问题看敦煌本《诗经》的性质及其学术史意义
吴洋
内容摘要:流传至今的《毛诗》中,每一首诗的章句均标注在诗篇之后,而且有三首诗的章句载有毛公“故言”,说明毛公和郑玄划分章句的差异。然而敦煌本《毛诗》中,却出现章句标注在诗篇之前的现象,且完全不载毛公“故言”。本文针对这一现象,通过比较敦煌本《毛诗》以及宋刻《毛诗正义》和《经典释文》等,认为敦煌本《毛诗》展现了唐以前及唐初南北经学的区别以及融合过程,对于考察《毛诗》传本原貌及其流变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章句;故言;诗经
中图分类号:G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2-0105-04
Characters a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of the Book of Poetry among Dunhuang Documents Based on Its Chapters and Sentences
WU Yang
(S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In the extant versions of Maos Poetry, the commentaries are marked after the verses, and there are three poems with the“original words”of Duke Mao in their sentences, which illustr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ersions commented on by Duke Mao and by Zheng Xuan. However, in the version of“Maos Poetry” found among the Dunhuang documens, commentaries are marked in front of the verses or sentences without“original word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unhuang version of“Maos Poetry,” the Song dynasty engraved version of the“Proper Meaning of Maos Poetry,” and the Explanation on Classics suggests that the Dunhuang version exhibits the difference and process of unification of classical studies in pre-Tang and early Tang periods, and so it is of significant meaning for studying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extant version of Maos Poetry.
Keywords: Chapters and sentences; Duke Maos original words; Book of Poetry
《诗经》中对每一首诗的章句划分,是肇始于先秦的古老传统,《左传》中引《诗》、赋《诗》已有“首章”、“卒章”、“三章”的说法。这一传统为汉代经师所继承,汉代熹平石经所刻《鲁诗》以及近来出土的《阜阳汉简诗经》当中,亦均有章句划分①。流传至今的《毛诗》同样也是如此。
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正义》是最通行的《毛诗》注疏本[1],在这个本子中,每一首诗的后面都附有该诗的章句划分。值得注意的是,在《周南·关雎》一诗的后面,章句划分题作“《关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下面所附陆德明《经典释文》云:“五章是郑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后放此”[2]。这是表明毛公与郑玄的章句划分有区别。在阮校《毛诗正义》中,共保留了三首诗的章句差异,除了《周南·关雎》以外,还有《大雅·思齐》和《大雅·行苇》[2] 1114,1153。
敦煌发现的《诗经》文献中,抄有《周南·关雎》(含章句)的有“斯1722”(白文)、“伯4634B”(白文),抄有《大雅·思齐》(含章句)的有“斯6346”(白文)、“北敦14636”(传笺)、“伯2669A”(传笺),抄有《大雅·行苇》(含章句)的有“斯6346”(白文)②,据《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2册《诗经》类文献的整理者许建平先生的意见,所有这些抄本均为唐代抄本,而所有这些抄本无一例外均只载郑玄的章句划分,完全不载毛公的“故言”。
许建平先生以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敦煌本《诗经》“删毛存郑”[3]。笔者以为,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藏南宋绍兴九年刊刻的单疏本《毛诗正义》中,《大雅·思齐》和《大雅·行苇》二诗同样也仅保留有郑玄的章句[4],尽管该书《郑风》之前的内容残缺,然而我们有理由推测《周南·关雎》一诗也当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在阮元校刻的《毛诗正义》中,每一首诗的章句均列在该诗之后,然而在每一首诗之前的《诗序》下面,孔颖达的《疏》列起止时,均谓起于该诗诗题和章句、止于《诗序》的最后二字,孔颖达在《关雎》章句之后还说“《定本》章句在篇后”。显然,孔颖达《毛诗正义》以及所据《毛诗》原本应当是章句在篇前,而颜师古《毛诗定本》则章句在篇后。清人陈奂已经发现了这一现象,他指出:“然则孔本章句在前可知也,杜甫以‘曲江三章章五句为题,书于前,知唐本多如此。”[5]
陈奂的这一看法在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中得到了印证,在该书中,每一首诗的章句确实置于篇前。而这又与敦煌《诗经》抄本“斯6346”(抄有《大雅·思齐》和《大雅·行苇》)、“伯2669A”(抄有《大雅·思齐》)的情况相合。
我们知道,这部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是据北宋淳化三年刊刻的《毛诗正义》覆刻,后者是《毛诗正义》最早的刊本③。上举敦煌《诗经》抄本在章句问题上与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如此相似,这表明二者一定有相同的渊源。
众所周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是据隋代刘焯的《毛诗义疏》和刘炫的《毛诗述义》写成的。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序》中说:“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醜、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
刘焯、刘炫并从刘轨思受《诗》[6],据《北齐书·儒林传》记载:北方“通《毛诗》者多出于魏朝博陵刘献之。献之传李周仁,周仁传董令度、程归则,归则传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二刘之门。”[7]可见,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实际代表了六朝时期北方《诗经》学者的意见,既然如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上举敦煌《诗经》抄本应当也是主要受到六朝时期北方经学传统的影响。
那么,阮元校刻的《毛诗正义》中的“故言”又是从何而来呢?
就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来看,最早载有“故言”的是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此书作于南朝陈后主至德元年,陆德明入隋之前书已写成。吴承仕指出:“德明撰《释文》时,身仕南朝,其所征引,殆无北方学者。”[8]如此看来,则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实际上代表了六朝时南方《诗经》学者的意见。在《经典释文序录》中,陆德明详述了《毛诗》的郑、王之争,他说:“魏太常王肃更述毛非郑。荆州刺史王基驳王肃,申郑义。晋豫州刺史孙毓为《诗评》,评毛、郑、王肃三家异同,朋于王。徐州从事陈统难孙申郑。”在所列举的《毛诗》注家中,陆德明列“王肃注二十卷”,又列“孙毓《诗同异评》十卷”,而作为他们反对者的王基、陈统之书反不见著录,看来陆德明恐怕更倾向于王肃和孙毓的意见。王肃“述毛非郑”,孙毓“评毛、郑、王肃三家异同”,在章句划分上与郑玄立异自是情理中事,《经典释文》中所录毛公“故言”,很有可能即是采自孙毓或者王肃的说法。
除了载有毛公“故言”之外,《经典释文》所据《诗经》章句列于诗末{1},这与残存的汉代熹平石经《鲁诗》的形式是一致的。唐太宗贞观初,颜师古考定《五经》,贞观七年成《五经定本》颁行天下,《旧唐书·颜籀传》记载:“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9]可见,颜师古据以考定《五经》的为唐代秘书省藏书,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唐初秘书省图书主要来自于隋文帝平陈以后从陈朝搜集之书,与陆德明《经典释文》所用资料比较接近,因此颜师古的《五经定本》与当时传习的通行本多有不同,当时即受非议。体现在《毛诗定本》上,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与《经典释文》一样,《定本》将章句列在诗末,然而,《毛诗正义》在《关雎》章句下仅说“《定本》章句在篇后”,显然《毛诗定本》并没有收录毛公的“故言”,否则《正义》不会不对此作出说明。这样看来,《经典释文》所载“故言”恐怕确实如上文所推测的那样是来自于孙毓或王肃,并非当时《毛诗》的各种传本所有。因此,颜师古也没有将其采入《定本》。
尽管《旧唐书·孔颖达传》中提到颜师古也曾参与《五经正义》的编写,但是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序》中列举的参编人员并没有颜师古的名字,看来颜师古实际上没有参与其事,其中缘由不得而知。正因为如此,《毛诗正义》得以采取与《定本》不同的章句标注位置,在经文和传笺的某些内容上也与《定本》取舍不同,这说明颜师古的《定本》在当时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并没有因为唐太宗的推行而达到统一《五经》文本的效果。
敦煌的《诗经》抄本正好反映了这一学术发展阶段的真实面貌。
第一,当时《毛诗》传本南北杂糅,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威文本。一方面,敦煌的《诗经》抄本多数将章句列于诗篇之后,采取了《经典释文》和《毛诗定本》的形式;另一方面,在上所举的“斯6346”、“伯2669A”两个卷子中又保留了今天非常罕见的将章句列于诗前的情况,与《毛诗正义》相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斯6346”中,两种章句标注方式共存,其所保留的《大雅·文王之什》的部分采用章句在后的形式,而《大雅·生民之什》的部分则采用了章句在前的形式。这一现象直观地向我们展现出当时《毛诗》传本的情况,也就是南北方不同传本共存,学者随意采用。
第二,不管是哪种《毛诗》传本,均渊源于郑玄的《毛诗传笺》。敦煌写本《诗经》中,除了直接抄写《毛诗传笺》的卷子之外,即使是仅抄录《诗经》白文的卷子,也往往题有“诂训传,郑氏笺”的篇题,也说明这些白文同样是来自郑玄的《毛诗传笺》。
我们知道,《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然而到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序录》却说是“《毛诗故训传》二十卷”,下注“郑氏笺”。《隋书·经籍志》则著录“《毛诗》二十卷”,下注:“汉河间太傅毛苌传,郑氏笺。”如此看来,六朝时期所传《毛诗》均为郑玄作笺注并合并为二十卷的本子。敦煌的《诗经》抄本亦是如此。如“伯2529”在《郑风》篇首题“郑缁衣故训传第七”,篇尾题“卷弟四”;在《魏风》篇首题“魏葛屦诂训传第九”,篇尾题“卷第五”;在《唐风》篇首题“唐蟋蟀诂训传第十,卷第六”;在《秦风》篇首题“秦车邻诂训传第十一”,篇尾题“卷六”;在《陈风》篇首题“陈菀丘诂训传第十二,卷七”。又如“斯3330”,在《小雅·节南山之什》前题“节南山之什诂训传第十九,毛诗,小雅,郑氏笺,毛诗卷第十二”;“伯2978”在《小雅·谷风之什》前题“谷风之什诂训传廿,卷第十三”。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不再赘述。敦煌的《诗经》抄本虽然如《经典释文》一样列出《毛诗故训传》的原始卷次,然而真正分卷却是二十卷,正是郑玄《毛诗传笺》的规模。
王国维曾经指出:“考六朝以后行世者,只有经注本,无单经本,唐石经虽单刊经文,其所据亦经注本。如《周易》前题王弼注,《尚书》题孔氏传,《毛诗》题郑氏笺……又注家略例序文无不载入,是石经祖本本有注文,但刊时病其文繁,故存其序例,刊落其注耳。”[10]以敦煌《诗经》抄本观之,王氏所论又添一证据。
第三,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推断,当时流传的郑玄《毛诗传笺》原本就没有记载毛公“故言”。由于毛公的“故言”很可能来自王肃或者孙毓的注本,且仅见于《经典释文》的记录,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并不为学者所广泛接受。
敦煌文献中,已有陆德明的《周易释文》、《尚书释文》、《礼记释文》[11],我们当然可以推测当时敦煌的学者是看得到《毛诗释文》的,然而敦煌的《诗经》抄本却没有采纳《释文》所记录的毛诗“故言”,颜师古的《毛诗定本》和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同样如此,可见当时《经典释文》的影响和地位比较有限。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最早将毛公“故言”整合入《毛诗》本文的,应该是唐文宗时所刻开成石经中的《毛诗》,该《毛诗》的章句列于诗后,亦与《经典释文》相同{1}。然而据《旧唐书·文宗纪下》的记载:“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复校字体,又乖师法。故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以为芜累甚矣。”可见,开成石经如颜师古《五经定本》一样,因为与流行的传本有别,不为当时学者所接受,其影响在当时亦相当有限。
然而开成石经在五代时期却成为印本经籍所依据的祖本。《五代会要》记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12]王国维据此指出,五代时所刻监本经籍乃是取开成石经本的经文合以当时经注而成。而北宋监本经籍,又是在五代监本的基础上校勘重刻,且《五经正义》为单独刊刻,并未与经注本合刊。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毛诗正义》与《毛诗》经注本在章句问题上的分歧。
屈万里先生指出,《正义》与经注的合刊“始于南宋初年浙东茶盐司,初刻《周易》、《尚书》、《周礼》三种。绍熙中,三山黄唐来主是司,继刻《毛诗》、《礼记》二种。”[13]自此以后,经文、注文、疏文合为一本,而《毛诗传笺》、《经典释文》与《毛诗正义》三者之间不同的版本源流和学术传承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亦几于泯灭。幸亏有敦煌的《诗经》抄本出现,参以日本所藏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我们才得以梳理出唐代《毛诗》传本的真实情况,这不能不说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件幸事。
参考文献:
[1]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572.
[3]张涌泉主编审订、许建平撰.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8:472.
[4](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311、340.
[5]陈奂.诗毛氏传疏[M].台湾:学生书局,1975:11.
[6]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718.
[7]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583,584.
[8]陆德明撰.吴承仕疏证.张力伟点校.经典释文序录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8:9,10.
[9]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594.
[10]宋版书考录·五代两宋监本考·卷上[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525-526.
[11]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8.
[13]屈万里.书傭论学集·十三经注疏板刻述略[M].台湾:开明书店,198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