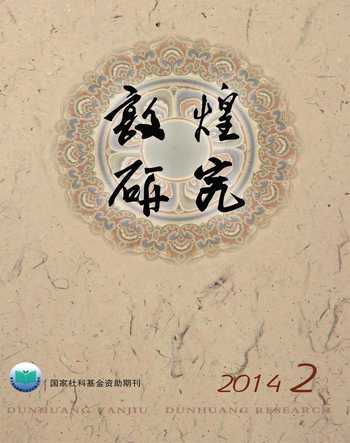肩水金关汉简所见“从者”探析
侯宗辉
内容摘要:“从者”是汉代社会中普遍存在且数量不菲的一种群体身份的称谓。从汉简记载可知,“从者”是吏士等私人所雇佣的随从,故而又常被称为“私从者”或“私从”。“从者”多以青少年为主,具有户籍,可拥有爵位,是国家的编户民。“从者”以协助雇主完成公私事务为职事,并经常随从其一起因公差旅、参与各种具体事务的处理,有效地促进了行政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在边塞屯守系统中,“从者”被视为戍吏的家属成员,由政府统一配给廪食。对“从者”的探析,有助于更全面地分析边郡屯戍人口的构成与了解汉代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
关键词:汉代;从者;身份;汉简
中图分类号:K877.5;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2-0132-09
On the Word “Congzhe” (Retinue) Seen in the Han Dynasty Bamboo Slips from Jianshuijinguan
HOU Zonghui
(Institute of history, Gan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Congzhe” refers to a common group of people because they often acted as attendants employed privately by officials and scholars, also known as “Si congzhe” or “Si cong.” Most of them are youths who had permanent domiciles and could have a title of nobility. They were written into the household register. They not only assisted their employers in finishing their official or private business, but also traveled with their employers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management of different affairs, thus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administrative work. In the frontier garrisons, “congzhe” refers to soldiersfamily members, and they got supplies from the government. This study will help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frontier population and its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Han Dynasty.
Keywords: Han dynasty; Congzhe; Identity; Han dynasty bamboo slips
在秦汉史籍中会偶见“从者”一词,但其记载均极精炼,形象模糊,使人难得其详。最新出版的《肩水金关汉简(壹)》与《肩水金关汉简(贰)》中①,有20余枚与“从者”有关的记载,而且有近三分之一是以“从者”为主体的专门记述,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汉代的“从者”。
本文即以肩水金关汉简为中心,就“从者”相关问题作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从者”的身份称谓
“从者”是汉代社会中一种常见的、普遍的身份称谓。《汉书·两龚传》:“王莽秉政,胜与汉俱乞骸骨。自昭帝时,涿郡韩福以德行征至京师,赐策书束帛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行道舍传舍,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师古注曰:“道次给酒食,并食其从者及马也。”[1]《汉书·韦玄成传》云:“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出遇知识步行,辄下从者,与载送之,以为常。”[1]3108又《后汉书·桓荣列传》载桓晔:“尤修志介,姑为司空杨赐夫人。初鸾卒,姑归宁赴哀,将至,止于传舍,整饰从者而后入,晔心非之。”[2]可见,但凡达官名士均有“从者”侍奉于左右。出土的西北汉简中,也有关于“从者”的记载,如《敦煌汉简》②795简:“元始三年七月,玉门大煎都万世候长马阳所赍操妻子、从者、奴婢出关致籍。”《敦煌悬泉汉简释粹》③Ⅱ0214③:73简:“甘露二年十一月丙戌,富平侯臣延寿,光禄勋臣显,承制诏侍御史曰,穿治渠军□候丞□、万年、□光、王充诣校属作所,为驾二封轺传,载从者各一人,轺传二乘。”《金(壹)》73EJT7:98A简:“永始二年正月以来,居延都尉夫人及吏=从者。”随着汉朝政府在西北开疆拓土的进程中,大量的“从者”跟随屯田戍守的吏士一起远至西北地区,往返于边塞的关隘要道,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高渐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从者”,司马贞《索隐》谓“主人家之左右也”[3]。作为随从人员的“从者”犹如主家之私仆,因而,“从者”有时也常被他人称为私从者或私从。这在出土的汉简资料中有较多的反映,如简文所示:
(1)门下史马刚,米亖斗,从者一人,麦一斛。 《敦》344
(2)从掾位田裒 ,米亖斗,私从二人,麦二斛。 《敦》345
(3)骑吏田阳,米亖斗,从者一人,麦一斛。 《敦》346
(4)高望部元始元年十月,吏妻子、从者、奴、私马廪致。 《敦》545
(5)五凤三年三月丁丑朔癸卯,士吏带敢言之,候官隧和吏妻子、私从者三月廪名籍一编,敢言之。 《敦》998
(6)护从者,敦煌对苑里干宽,年十八,单襦、复襦各二领,单衣、中衣各二领,裘=绔、韦绔、布绔各二两,絮巾、布巾各三□□ 《敦》1144
(7)相私从者,敦煌始昌里阴□,年十五,羊皮裘二领,羊皮绔二两,革履二两 《敦》1146
(8)故居延尉丞王卿,妻宣=君=子小女君至,吏十四人,私从者
《金(壹)》73EJT1:12
(9)居延都尉夫人及吏=从者、库吏、奴婢名 《金(壹)》73EJT7:98B
例(1)、例(2)、例(3)皆出土于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是一组对戍吏及其“从者”发放粮食的记录名册。从木简上文字书写的特征看,属于新莽时期。其中,例(2)中的“私从”当是“私从者”的简称。《敦》1959A号简文也有“私从二人”的记载。再与例(1)、例(3)互相比较,内容与格式一致。以类相从是边塞出土的屯戍账簿、驿传名籍档案分类收藏的基本原则,“有的不仅按文书类别,更进一步按文书内容特点归类立卷”[4]。由此可以看出,例(2)中的“私从”应是“从者”的另一种称谓。例(4)与例(5)均是戍边吏士的家属及“从者”的廪食发放记录。前者是汉平帝元始元年(1)十月份,高望部吏士的妻子、“从者”、奴与私马发放廪食的凭证。后者为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三月士吏带向上级呈报的本辖区内候官、烽燧吏士妻子与私从者的廪食名籍。二者在内容、人物、表述方式上相类,则“从者”和私从者应是同一种身份的不同称呼。例(6)与例(7),在内容上亦属同类。分别是对“护”与“相”这两位官吏之随从的籍贯、年龄及其所携带衣物的详细登记。类比可以看出,“从者”和“私从者”应是对同一种社会群体的不同称呼。例(8),是对故居延尉丞王卿妻子、女儿、属吏以及私从者经过金关时的记录。显然,这只是众多往返于肩水金关戍吏的家属及私从者中的一枚实物遗存。这从例(9)所载内容也可以看出。例(9),从形制而言是一枚楬,楬多作归卷入档案卷的标签牌。此处表明,它是专门记载过往的居延都尉夫人、属吏、吏从者及奴婢名字的一枚标签。例(9)与例(8)在文书性质上有紧密的联系,即类同于例(8)的文书归档捆扎好之后,再以例(9)楬的形式书写档案标题,系于简册之外用于标识案卷内容,以便于寻检。从内涵及用语来看,这里的“从者”和“私从者”没有本质区别。
私从者,《汉书·李广利传》云:“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师古曰:“负私粮食及私从者,不再六万人数中也。”[1]2700《汉书·赵充国传》:“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1]2986私从者一词在《汉书》中仅此两见,而且都与吏士征伐屯守事宜有关系。《李广利传》中汉政府在征讨大宛筹集兵力时,仅“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且“私从者”不在六万人数中。因兵多势强,“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1]2701。汉军征伐进程一路高歌猛进,自然离不开私从者的协助。同样,在《赵充国传》中,赵充国向皇帝奏疏愿罢骑兵,仅留少量步兵及吏士私从者万余人屯田备虏,节省军费,缮治邮亭,“兵决可期月而望”[1]2987。可见,私从者也被赵充国视为兴屯戍、御反羌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据汉简反映,即使边塞戍守系统中一些低级吏员也常有私从者。如《敦》526简:“大煎都候长王习私从者,持牛车一两,十月乙巳出东门。”候长,秩百石[5],有私从者。《敦》280简:“书吏胡丰私从者,零县宜都里胡骏,年三十,长七尺二寸。”有学者指出,“凡两汉简文书签署人书佐的位置上,新莽简皆称作书吏,证书吏为新莽所改书佐称谓”[6]。可见,专门以抄录拟誊公文为职事秩百石以下的书吏亦有私从者[7]。而《敦》295简有“外塞吏子、私从者、奴大男十五人”、《敦》298简“出外塞吏子、私从者大男廿四人”的记录。显而易见,随着屯戍吏士一起远至西北边塞生活的私从者当不在少数。
缘何如此数量颇丰且在汉代社会生活中承担着不可或缺角色的人群,却在史籍中未见更多的描述?笔者认为,这与私从者常被称呼为“从者”或“私从”有莫大的关系。《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中将私从者解释为“吏士出征时私募之随从”[8]。《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一书中认为“私从者是私人的随从”[5]74。二者都强调“从者”的私人属性。亦有学者指出“从者多数是官吏们雇佣”的[9]。这说明,无论是战争时还是和平时期,一旦当“从者”受雇于人后,对雇主而言,他们都是私人雇佣的随从。在“从者”前冠以“私”字,意在表明“从者”与雇主之间是私人而非官方的雇佣依附关系。
二 “从者”的籍贯、年龄与爵位等状况
在传世文献中,“从者”只是偶尔附带出现在传记人物的事件中。如《后汉书·方术列传》:“生到葭萌,与吏争度,津吏破从者头。”[2]2719该“从者”无籍无姓,难以考究。能出现名字则实属不易,《汉书·外戚传》:“贾长皃妻贞及从者师遂辞:‘往二十岁,太子舍人侯明从长安来求歌舞者,请翁须等五人。长皃使遂送至长安,皆入太子家。”[1]3962关于“从者”更多的细节,我们无从知晓。但在西北汉简,尤其是肩水金关汉简中有对“从者”的专门登记,其籍贯、姓名、年龄、身高、肤色等个人状况较为详备,兹举二例:
(10)从者,居延肩水里大夫蓋常,年十三,长六尺三寸,黑色,皆以四月壬戌出。《金(壹)》73EJT10:130
(11)从者,京兆尹长安大原里贾相,年十六岁,长五尺,黑色
《金(壹)》73EJT9:93
毫无疑问,这为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从者”群体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笔者根据已经公布的汉简资料,对“从者”身份信息记录较完整的简文做了归纳统计并列表。下面就表中所及的诸项内容进行简要分析。
1. “从者”的籍贯构成
73EJT1:37简中的“望垣”是县名,《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郡有望垣县;觻得、居延,均为张掖郡属县[1]1612—1613;73EJT2:53只记“阳里”,与之相同的是73EJT9:104简:“五凤四年八月己亥朔己亥,守令史安世敢言之,遣行左尉事亭长安世逐命张掖、酒泉、敦煌、武威、金城郡中,与从者阳里郑常富俱乘占用马轺车一乘,谒移过所县道毋苛留,敢言之。”所记内容表明,这个“从者郑常富”跟随其主人“亭长安世”奉命即将到河西边郡地区逐捕逃犯,他们显然非河西本地人氏。《敦》722简有“河东骐□阳里梁□孙”的记载,据《汉书·地理志》,骐,是河东郡所辖侯国之一[1]1550。参照汉简记录人物籍贯时郡、县、里的顺序习惯,则此“阳里”当属河东郡。73EJT9:88简“魏郡”,依《汉书·地理志》记,属冀州,辖县十八[1]1573;73EJT9:93简有“京兆尹”,汉代三辅之一,辖有长安县;73EJT10:265简之“广郡里”,为里名,所属郡县不详;73EJT24:267A简“河内郡温庠里”,《汉书·地理志》云:“高帝元年为殷国,二年更名。莽曰后队,属司隶。”辖县十八个,“温”为县名之一,[1]1554“庠里”即属“温县”之里名。《敦》280简的“零县”,不见于史书。疑书写简文时有脱字。《汉书·地理志》记零陵郡有零陵县,属于荆州[1]1596;《敦》788简“广陵”,当为县名。《汉书·地理志》载其属广陵国,“高帝六年属荆州,十一年更属吴。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广陵”[1]1638;《敦》1144、1146简之“敦煌”,县名,与郡同名。
尽管参照样本有限,但表中反映出,活动在西北边塞地区的“从者”,除了边郡本地人外,还有来自于中原和南方地区者。这种籍贯地域布局,基本和西北边塞屯戍吏员的来源地相类。非河西本地籍贯的“从者”,可能都是随着他们的雇主,即中原内地屯戍吏士一同来到了西北边郡。罗布淖尔汉简中有这样的记录:
士,南阳郡涅阳里宋钧亲,妻玑,年卅,私从者同县籍同里交上□□□
《疏》34{1}
可见,戍边吏士是可以雇佣同籍“从者”的。而大量河西本地籍贯“从者”的存在,说明吏士除了在征战出发前夕私下招募雇佣“从者”外,更多的可能是在屯守地征募“从者”以为随侍人员。
2. “从者”的年龄状况
表中对“从者”年龄有明确记载的有11例,最小的仅11岁,最大的30岁。其中10~19岁者7人,20~29岁者3人,30岁者1人。这些数据说明,充当“从者”的以青少年为主。此外,表中还有4例只言“大男”,未说具体年龄。“大男”是汉代年龄分层界定的称呼之一。据出土简牍文书记载,“大男和大女,年龄在15岁以上;使男和使女,年龄在7岁至14岁;未使男和未使女,年龄在2岁至6岁”[10]。由此可知,此处4例中“大男从者”的年龄皆在15岁以上。
汉代社会下层中许多青少年很早就参与了艰苦的劳作,承担起了生活的重担。如《汉书·王尊传》记载王尊:“少孤,归诸父,使牧羊泽中。”[1]3226《后汉书·承宫列传》说承宫“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2]944。又如《后汉书·循吏列传》记第五访“少孤贫,常佣耕以养兄嫂”[2]2475,所谓佣耕,即第五访被人雇佣从事耕作。由此或可知,王尊、承宫等人在年少时与第五访经历类似,为人“佣”而放羊牧豕。因此,有11岁、13岁等年龄较小的“从者”,则不足怪矣。
汉代男子的服役年龄,《汉官旧仪》如是记载:“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者,有罪,各尽其刑。”[11]据此,汉代男子有爵位者服役法定年龄是23岁至56岁,无爵位者的是23岁至60岁。参考表中所举“从者”的年龄,大多数都未及法定年龄。之所以年少的“从者”就已经跟随着主人在四处奔波,并不是在履行自己的劳役职责,而是恰恰反映出其与主人之间是一种明确的雇佣关系。
3. “从者”的爵位状况
“从者”有爵位,这在肩水金关汉简之外的其他简文中未曾见到。表中记录“从者”爵位的有四枚简,除了例(10)外,另外三简是:
(12)
对国家的编户民赐予爵位是秦汉时期的一项重要制度。例(10)、(12)中所见“从者”的爵位都是“大夫”,例(13)中“从者”的爵位是“簪褭”,例(14)中“从者”的爵位是“上造”。据《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刘劭《爵制》可知:“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于司徒曰造士,虽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褭,御驷马者。要褭,古之名马也。驾驷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褭也。四爵曰不更……五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车左者也。”[2]3632汉制,赐民爵不得超过公乘八级。《后汉书·明帝纪》云:“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李贤注云:“汉置,赐爵自公士以上不得过公乘,故过得移授。”[2]96-9据此可知,金关汉简中所记“从者”的爵位,都属于民爵范围。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例(10)中,“从者蓋常”年仅“十三”岁,却拥有“大夫”第五等级的爵位,颇显特别。《汉书·文帝纪》有“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的记载,师古注谓“赐爵者,谓一家之长得之也”[1]110。“一家之长”才是赐爵的对象,这与拥有爵位的“从者”的实际年龄似不太相符。类似的情况在居延汉简中亦有反映,如《合校》15·5:“葆,鸾鸟息众里上造颜收,年十二。”针对此情况,日本学者西嶋定生通过对史料全面而细腻的梳理后得出“民爵赐与是对小男亦即14岁以下男子即已实行”的卓见[12]。又有学者依据大量出土文献归纳出小男爵位的获取途径:“实际上除普遍赐爵之外,小男起码还有另外两种途径可以获得爵位,一是因父死而靠世袭继承获爵,二是因爵位的移授而获爵。”[13]至此,我们也就明白了拥有爵位的小男“从者”,在汉代社会中定当不是特例。
三 “从者”的地位与数量
“从者”,身为汉代社会中的一个特定阶层,其社会地位究竟如何呢?从汉简所载内容来看,“从者”常随同雇主一起差旅外,还多与士吏、士吏的妻子及其士吏的私家奴婢等一同出现在简文记录中,如《金(壹)》73EJT7:98A“居延都尉夫人及吏=从者”、《敦》295简“吏子私从者奴”、《敦》298简“吏子私从者”、《敦》795简“妻子从者奴婢”、例(4)“吏妻子从者奴”、例(5)“吏妻子私从者”、例(8)“妻宣=君=子小女君至吏十四人私从者”、例(9)“居延都尉夫人及吏=从者库吏奴婢”,等等。通过对这些与“从者”相关的人或社会阶层分析,有利于我们较全面地了解其社会地位。
“从者”作为吏士的私人助手,他们和主家之间是雇佣关系,这与私家奴婢等贱民阶层显然有别。在上举“从者”的简文中,明确记述有郡、县、里、爵位、名姓、年龄、身高、肤色等,这说明“从者”在法律地位上属于国家的编户齐民。而与其时常一同出现在简文中的奴婢,却是主人的私人财产。尽管汉代奴婢也入籍,但基本是“以人的身份登记在民户的户籍”上[14],虽然有户籍,但不属于编户民。奴婢若要获得像“从者”一样的庶人身份,除了政府统一放良的渠道外,其他方式均有较严苛的条件限制。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亡律》“奴婢为善而主欲免者,许之,奴命曰私属,婢为庶人,皆复使为算,事之如奴婢。主死若有罪,以私属为庶人,刑者以为隐官。所免不善,身免者得复入奴婢之”[15]。又如《汉官六种·汉旧仪卷下》所记“奴婢欲自赎,钱千万,免为庶人”[11]79。如此相比较,“从者”与私家奴婢地位之高下立显。
“从者”可以拥有爵位,这在汉代社会中能够获得更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实惠,张家山汉简所载汉律中多有体现。《二年律令·赐律》言:“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不更比有秩,簪褭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毋爵者,饭一斗、肉五斤、酒大半斗、酱少半升。”[15]49有无爵位,赏赐的标准截然不同。而爵位的高低也对某些特殊权益有直接的影响,《二年律令·具律》:“上造、上造妻以上, 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公士、公士妻及囗囗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15]20有爵位者也可享有徭役免老的优待,《二年律令·傅律》载:“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褭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为免老。不更年五十八,簪褭五十九,上造六十,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五六十二,皆为睆老。”[11]57《汉书·刑法志》云:“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1]1091与奴婢相比,有爵位的“从者”显然有机会享有更多的权益。
秦汉律令中,对“从者”经过驿站时的传食标准也有规定。睡虎地秦简《传食律》:“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采(菜)羹,给之韭葱……使者之从者,食糲米半斗;仆,少半斗。”[16]这里讲的是“御史卒人使者”及其“从者”,相比于雇主粺米、酱、菜羹、韭葱的饭食,“从者”仅可食“糲米半斗”,而使者的仆人比“从者”又“少半斗”。秦制汉承,《二年律令·传食律》:“丞相、御史及诸二千石官使人……车大夫藷粺米半斗,参食,从者糲米,皆给草具。车大夫酱四分升一,盐及从者人各廿二分升一。”“车大夫”,张家山汉简竹简整理小组注释云:“指上述使人等”[15]40。秦汉之《传食律》对“从者”传食标准的规定极为相近,而其与主人和仆人伙食待遇方面的差别,也为我们了解“从者”的地位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者”们所依附的雇主既有佐史、斗食之吏,也有丞相、御史等二千石的高官大员,这些雇主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均身居国家统治机构,身份高贵,权势威重,因此,部分“从者”在其雇主的庇护下,有时狐假虎威,出现肆意横行的不法现象。《史记·滑稽列传》记武帝乳母,“当此之时,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当道掣顿人车马,夺人衣服”[3]3204。《风俗通义》载记太傅陈蕃“到临颍巨陵亭,从者击亭卒数下,亭长闭门收其诸生人客,皆厌毒痛,欲复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当先请,今约敕儿客无素,幸皆坐之,何谓乃欲相及?”[17]当然,也有“从者”经过努力改变自身命运,跨入士阶层的实例,如《汉书·儒林传》所记丁宽:“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才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时至景帝,“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1]3597-3598。丁宽由“从者”而至国之所依的文才武略之士,这也是汉代“从者”身份地位转变的一个鲜活案例。
“从者”虽属国家的编户齐民,但实质上常充当豪族与吏士的私人随从,某种程度上“从者”数量的多寡往往体现着雇主地位的高低。文献记载中,每一名雇主拥有的“从者”数量似乎没有明确的定数。在汉简中常见跟随雇主办理公务的“从者”多为一至二人,如《悬泉》V1311③:226“以食骊靬佐单门安将转,从者一人”;《悬泉》Ⅱ0215③:267“以食伊循侯傀君从者二人”;《金(壹)》73EJT1:25“司马从者二人”;《金(贰)》73EJT21:117“骍北亭长成欧与金关为家室出入符,从者觻得□□里孙偃,从者觻得□□里宣□”;《合校》303·9“以食吏私从者二人”,等等。在这些记载中,雇主拥有“从者”数量的多少,似乎与其官职地位无涉,而是依实际情况所需。《九章算术》卷8:“今有令一人、吏五人、从者一十人,食鸡一十;令一十人、吏一人、从者五人,食鸡八;令五人、吏一十人、从者一人,食鸡六。问令、吏、从者食鸡各几何?”[18]该算题中的“令”、“吏”与“从者”之间并无固定的比例关系,差旅“从者”的数量或由官吏差使任务繁简程度的实际需求来决定。
同时,从上述文献记载中可知,“从者”在随同雇主因公差旅时,所过驿置传舍必须为其提供一定标准的口粮。因而,汉朝政府为了减免食物过度开支,对雇主在公差途中携带的“从者”数额有原则性的要求:“食从者,二千石毋过十人,千石到六百石毋过五人,五百石以下到二百石毋过二人,二百石以下一人。使非吏,食从者,卿以上比千石,五大夫以下到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以下比二百石;吏皆以实从者食之。”[15]40上引各例多是针对吏士差旅中携带“从者”数量的记录和要求。而在日常生活中,吏士雇佣“从者”的多少似乎是其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群书治要》引《崔寔政论》云:“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19]由此可推测,某些地位显赫者定当拥有为数不少的“从者”侍奉于其左右。
四 “从者”的职能及廪食标准
“从者”主要以协助雇主处理完成其公私事务为职事。“从者”以侍奉雇主为己命,当雇主除迁转任一方时,一般都会携带“从者”于左右,类若家属成员。如《悬泉》Ⅰ0112②:18简:“建平四年五月壬子,御史中丞臣宪,承制诏侍御史曰:敦煌玉门都尉忠之官,为驾一乘传,载从者。”即是说,玉门都尉忠即将赴任,一并拉载着他的“从者”远去敦煌。而每当身为吏士的雇主们在奉命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也经常会携“从者”一起差旅,共同完成使命。此类记述如《金(壹)》73EJT2:53简:“□张大守□与从者阳里王得之自令史昌敢言之,遣亭长宋建□□□□□大守府与从者□里王”。有时候,或许根据差事任务繁简程度的不同,官吏携带的从者数额也各异。如《悬泉》I0116: S.14记:“元始二年二月己亥,少傅左将军臣丰、右将军臣建,承制诏御史曰,候旦受送乌孙归义侯侍子,为驾一乘轺传,得别驾载从者二人。”《悬泉》Ⅱ0216③:57云:“五月丙午以食金城允吾尉骆建,从者一人。人再食,西。”此类事例在悬泉汉简中多见,兹不繁举。也有单独派遣“从者”完成公事的情况,如《敦》713A简“唯君月十日莫府用白米一斗、鸡一、从者三人以出报诣文书”。吏士们因公出差途中,有了“从者”的倾心协助,更容易完成使命。《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吴王帐下有一名叫周丘的宾客,拿着吴王赐予的汉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令入户,使从者以罪斩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3]2833。周丘能一夜占据下邳,离不开其“从者”的竭力辅助。
除了跟随雇主处置公务外,为其办理私事也是“从者”日常生活的重要事务。官吏或因坚守岗位不能抽身处理家常事务时,便由“从者”替代完成。如《金(壹)》73EJT6:43简“使从者为自输谷卖肉”;《敦》204简“曹马掾遣从者来伐苇”等记录,就很好地反映了“从者”的个人生活轨迹。另外,在汉简中还有“从者”协助雇主处理私事而发生命案的记录。《敦》221~222记:“大君使从者茂等往綷秉来,秉不肯□□□□□□□□使绳扼秉。秉以刃伤茂三所,大君从欲前助茂,秉刃伤大君头一所。男庶人吉助茂缚秉,元夫与吉共摎杀秉,并使从兄梁杀秉子小男,毋臿斫杀秉妻。”这里名叫茂的“从者”,不仅在搏斗中受伤,还涉及到命案之中。该简文也为我们更深地了解“从者”的职能提供了生动事例。此外,像《合校》67·3“子从者持牛车往来”;《敦》798“玉门千人行君客毕君伯从者范大孙,二月辛亥入东入”等,也应是“从者”单独为雇主办理私事而经关隘时留下的文字记录。
跟随吏士一同来到边塞屯守的“从者”,由政府统一配给廪粮。敦煌汉简中有对“从者”廪食发放的记录明细:
(15)贺,从者,大男宋望,六月食麦二石六斗一升。 《敦》321
(16)从者大男经——元年八月食麦三斛多三升。 《敦》323
(17)从者大男经——元年五月食麦二石七斗。 《敦》324
(18)从者大男经——元年十一月食麦二斛六斗一升。 《敦》325
(19)从者大男经,元年七月食麦二斗六升一升。 《敦》326
(20)况,从者,大男王欽,六月食麦二石六斗一升 《敦》348
所引诸例,皆出土于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第五探方,该探方所掘获枚木简大多反映了新莽时期西域的军事和外交关系,是探讨新朝社会经济及与西域关系极为珍贵的资料[20]。又,简文所见“容量单位‘石、‘斛并用乃新莽初特有”,并据同批简文特征,记“从者大男经”领取口粮的“元年”是“始建国元年”[6]98。这里所记“从者大男经”每月的口粮有两个标准,一是二石七斗,二是二石六斗一升。出现差别当与大小月有关,小月少一天,故扣除一天的口粮。汉代成年男子约“日食食量五升或原粮一斗”[21],简文中“麦”为原粮,该推论与上述口粮标准差异基本相当,可以信从。依此对比,例(15)和例(20)也应属于新莽时期,其简文所记“从者”领取的口粮当是小月标准。这里仅仅是王莽新朝时期“从者”的月廪粮标准记录。
据汉简记载可知,“从者”的月廪食标准与其地位无关,而是和年龄紧密联系。与此同时,该标准应是新莽朝重新划分的等级,相比于西汉中后期,月口粮数额有所减少。
“从者”的地位虽与奴婢不同,但在发放廪食时,被国家视为吏卒家属成员,系于雇主名下,与吏卒的妻子、奴婢等一起登记在册。如前举例(4)、例(5)中“从者”的“廪致”与“廪名籍”可为证。又如《敦》358:“始建国二年桼月尽三年二月,候舍私从者私属廪致。”“私属”,《汉书·王莽传》云始建国元年“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1]4111是“从者”与奴婢一同领取口粮的又一例证。
例(15)—(20)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从者”姓名之前都书写有“大男”二字,“大男”是指年龄在15岁以上的男性。这喻示着“从者”月廪食的发放标准是以年龄大小来划分的。《敦》322:“私属大男吉,元年八月食粟二斛少七斗。”这里“私属吉”也为“大男”,他的月口粮数额与“从者”一致。那么,汉代随军家属中大男的月廪食标准是多少呢?《合校》286·5“父大男贤年六十二,用谷三石。弟大男宜年廿二,用谷三石”;《合校》203·27“父大男相年六十,用谷三石”;《居延新简—甲渠候官》{1}EPT48·30“弟大男田年十六,具署卅日,用谷三石”。“用谷三石”是西汉中后期“大男”每月的核定标准。随军家属的口粮一般都较吏卒为低[22]。通常,边塞吏卒大月廪食三石三斗三升少,逢小月是三石二斗二升少。若以大月计算,家属中的“大男”比吏卒每月少三斗三升余。再和新莽时期的“大男”相比较,则每月多三斗廪粮。检阅汉简,在新莽朝对随军家属口粮的缩减,是王莽政府对戍边吏卒廪食标准整体下调的结果。敦煌汉简中记有新朝时吏卒的廪食数额,如《敦》313:“出穬麦一斛八斗,以给卒麦永三月食。”《敦》314:“出穬麦一斛八斗,以给卒耿咸三月食。”汉简中粮食计量时有大小石之分,此处当为大石计量。按照大石与小石5∶3的比率来计算,王莽时吏卒月廪食大石“一斛八斗”折合成小石为三石。如此可以看出,新莽朝吏卒的月廪食比西汉中后期缩减了三斗左右。依前述,吏卒家属人员较吏卒口粮少三斗左右,则这一时期“从者”及“私属”的口粮应为二石七斗左右,这正好与简文所记相合。戍边吏卒及随军人员的廪食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与粮食丰歉、灾害繁稀、战局和乱等因素有关。王莽新朝普遍缩降屯戍吏士及“从者”等家属成员的廪食数额,或许正是其时社会经济发展困顿的一种体现。
综上所述,“从者”是汉代社会中的一种群体身份称谓,因其常常充当吏士的私人随从,故而也被称作“私从者”或“私从”。“从者”的大量出现是汉代社会雇佣关系发展的需要,吏士私人可以雇佣“从者”的数量似无定数。“从者”最基本的职能是协助雇主完成公职使命与私人事务,并广泛地参与在一些具体行政事务的处理中,因而“从者”的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行政效率与质量的提高。“从者”在因公差旅途中,所过驿站需按国家规定标准为其提供传食。具有户籍、可以拥有爵位的“从者”相比于私家奴婢,社会地位较高。但在边塞屯戍系统中,他们都被视为戍吏的家属成员,依据年龄的大小,由政府统一发放相同数额的廪食。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084.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259.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537.
[4]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204.
[5]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39.
[6]饶宗颐,李均明.敦煌汉简编年考证[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103.
[7]陈梦家.汉简缀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0:146.
[8]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31.
[9]高村武幸著,杨振红译.关于汉代材官、骑士的身份[C]//简帛研究2004.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58.
[10]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354.
[11]孙星衍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0:48-53.
[12]西嶋定生.二十等爵制[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198.
[13]刘敏.秦汉时期的“赐民爵”及“小爵”[J].史学月刊,2009(11):103.
[14]王彦辉.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时期私奴婢的社会地位[J].东北师大学报,2003(2):14.
[15]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30.
[1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101.
[17]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343.
[18]李继闵.九章算术校证 [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434.
[19]魏征,等.群书治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788.
[2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研究: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1:67-92.
[21]徐扬杰.居延汉简廪名籍所记口粮的标准和性质[J].江汉论坛,1993(2):71.
[22]邵正坤.汉代边郡军粮廪给问题探讨[J].南都学坛,2005(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