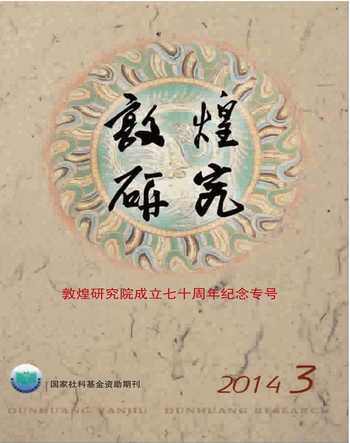遗失的画稿
内容摘要:五十多年前,笔者随北大阎文儒先生进行全国石窟寺调查,收集到数百幅图像资料。然而先生的著作尚未出版使用,却在“文革”中悄然遗失。致使相关单位和个人蒙受了很大损失,也使图像制作者八九个月的心血付诸东流。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遗失的画稿仍杳无音信。阎文儒先生早已作古,画稿作者也成为高龄老人。回首往事,耿耿于怀,特撰此稿。一来在谢世之前,就此事对相关单位作一个交代,二来对尊敬的阎文儒先生略表缅怀之情,三来以此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七十周年华诞。这段难忘的经历是敦煌石窟考古工作早期的一个片断。
关键词:石窟调查;画稿遗失
中图分类号:K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3-0024-11
Lost Drafts of Drawings—Celeb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Dunhuang Academy
LIU Yuquan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More than fifty years ago, I went with Mr. Yan Wenru to investigate all the cave temples in China and collected hundreds of images. However, these images disappeared during the“Cultural Revolution” before Mr. Yan published his work, not only causing great loss to relevant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s, but also wasting several months of the image-makers efforts. Today, a half century later, the images are still nowhere to be found. Mr. Yan Wenru has long-since passed away, and the image-maker is also very old. It still rankles my mind when I look back. So I write this article to explain the whole event to the relevant institutions before I die, to commemorate Mr. Yan Wenru, and to celeb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Dunhuang Academy, because this unforgettable event is also a part of the initial cave archaeological work at Dunhuang.
Keywords: Cave investigation; Loss of drafts of drawing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1961年,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应斯里兰卡邀请,并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承担起《佛教百科全书》之《中国石窟》部分的编撰任务。为完成这项国际学术合作,阎文儒教授组建起一个全国石窟调查组,先后招纳了几个弟子和助手。一位是中国佛教学院刚毕业分配到中国佛教协会的研究生通一法师(俗名刘明渊),一位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年轻摄影师祁铎,还有一位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美术工作者刘玉权。后来当调查工作进行到天水麦积山时,甘肃省博物馆又派遣董玉祥、张宝玺两人加入了调查小组。
其实,阎文儒教授此前早已多次对中国西北地区石窟寺进行过调查,对该地区石窟相当熟悉了解。然而,这次需要对中国各地主要石窟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而且需要综合运用当时可能运用的各种手段,诸如文字、摄影、绘画、测量等记录手段,收集丰富翔实的资料。
此次调查于1961年冬从新疆开始。阎先生由北京出发时,仅仅携通一法师乘飞机直飞乌鲁木齐。祁铎则由敦煌乘火车直奔新疆与其会合。新疆石窟调查结束之后,第二站便是敦煌莫高窟(图1)。此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常书鸿所长又增派了笔者参加调查小组。常所长对我的指示有两条:一是努力帮助阎先生收集所需图像资料,二是虚心向阎先生学习石窟调查和石窟考古研究方法。我记得在莫高窟的调查工作,大约是当年11月底到12月底结束。
当时的调查程序和分工是:每到一处调查的石窟,都以最快速度进入洞窟。由阎先生一边简要地向弟子们解说洞窟,一边随即向各位下达任务。如哪里要拍照,哪里要画图像,哪里需要进行测量等等,都依据分工;各自随手记录工作内容,分别去开展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身为组长的阎先生,除总领组务外,负责文字记录,通一法师负责洞窟测量和事后协助先生对相关佛经内容的查考,祁铎负责拍照,我负责图像绘制。由于阎先生在北大还有授课任务,因此石窟调查主要在寒假期间进行,时间紧迫,调查组全体人员都在阎先生的带领下同时间赛跑。有时在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石窟调查,限定的工作时间短暂到两三个小时或者半天左右,阎先生只得省去了对洞窟的解说,而直接安排任务,各自抓紧完成。之后立即赶路回住地,准备向下一站进发。
本人在调查组中的具体工作内容大体包括:1.主要石窟寺外立面示意图(但要有大体尺寸比例);2.某一区段或某一组洞窟外立面示意图;3.某一洞窟之内整龛造像(含壁画)内容布局图;4.某一铺壁画或某一尊造像的摹写图;5.某尊造像(或壁画)艺术表现技法的局部、细部特写图等。从敦煌莫高窟开始,经天水麦积山,四川广元皇泽寺、千佛崖,重庆大足北山、南山、石门山和宝顶山(图2),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图3),杭州飞来峰、烟霞洞、石屋洞、资延寺。由1961年12月到1962年3月,石窟调查告一段落,回到北京(参见附表1)。
在此期间,由本人绘制的各种铅笔图稿约490余幅,其中有几处石窟寺的总立面示意图是十余张或二三十张16开大小的图稿,回到北京后粘接成完整的全景(长卷)图稿,统计时,将这种图稿算作一幅。由于原始记录资料不全(有丢失),保存下来的图稿目录仅存364幅(参见附表2)。其中,莫高窟计213幅,麦积山计61幅,皇泽寺计11幅,千佛崖计5幅,宝顶山计7幅,北山、石门山合计11幅,南山计3幅,飞来峰及烟霞洞、石屋洞、资延寺合计10幅,龙门石窟计43幅。石窟总立面示意图计6卷,它们是:天水麦积山石窟、广元皇泽寺石窟、大足宝顶山石窟、大足北山石窟、杭州飞来峰石窟、洛阳龙门石窟。至于新疆石窟调查,因单位那时尚未派遣本人参加调查组,据知似未产生图像资料。而对山西云冈石窟的调查,因在此之前单位已将本人召回敦煌,后来是否产生图像资料,具体情况不详。在北京期间(1962年3月末至7月底8月初),我的工作任务是整理全部图像资料。具体是对调查过程中形成的铅笔图稿,一一修整和加工完善,并描绘成墨线定稿。按照事先的约定,所有图像资料,均需复制一份,全部工作结束时,底稿由本人带回单位,而描成墨线的正稿,留在中国佛教协会,提供出书时使用。
在京期间的另一重要任务是,去北大聆听阎先生讲授的石窟寺艺术课程(时间大约在1962年4—6月)。记得每周只有一次,大约两节课时间。当时的全国大专院校,唯独北京大学历史系设有石窟寺艺术和考古专业,能在这里听这门课程,显然是非常幸运的事。边远戈壁沙漠中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年轻工作人员,如果不是工作的特殊关系,获此特殊待遇,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
这次石窟调查是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的首次完全陌生的工作。不消说曾经遇到过较大的困难和挑战,虽已过去了五十多年,但仍记忆犹新,终生难忘。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和挑战是石窟总立面图的绘制。阎先生的要求:虽属示意性的图,但却要有个大体比例。同时还要求是正视图。而当时的工作条件就是我一个人加一盘皮尺。第一幅要绘制的就是难度很大的天水麦积山石窟总立面图。当时,面对满布洞窟和不少摩崖造像与古建筑遗迹的一座大山,真是“老虎吃天,无从下爪”。 我只有全马力开动脑筋,自己逼自己“上梁山”了!在观察好地形、目测好距离后,请附近一位工人帮我拉皮尺,丈量出麦积山石窟东、西崖壁下总尺寸后,再于崖体上找出几个分段控制点,计算出总比例。然而高度无法测量,只能在画面上参考宽度比例,用写生方法来确定。然后按通用程序,由上而下、从左到右,面对石窟各种遗迹,进行多点移动式写生。此外,由于作画者只能在地面左右移动,而无法上下升降移动,许多时候必须发挥想象力。即使如此,人在山脚下要画出山上高处的建筑和造像,透视角度非常大,要做到正视的效果,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总立面图上出现一些透视效果,是无法避免的,特别是高大型石窟。在作画过程中,常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和困难,譬如在移动中,地面坎坷不平,碰到遮挡视线的树木、建筑物等,都需要想办法灵活应对,克服处理,尽可能保证画面的相对准确性与完整性。在本次石窟调查中,第一幅总立面示意图(许多张16开纸拼接而成)——麦积山石窟总立面示意图终于完成。这幅从未绘制过的图,与其说是画出来的,还不如说是“逼”出来的。图稿完成之后,当时还真有一点成就感。从中让我深深体会出一个道理:天底下有些本事与技能,在学校里和书本中是学不到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学到。还有一条就是:有些本事无处可学,而可以被“逼”出来。从此以后,运用同样的办法和经验,顺利完成了五六处石窟寺总立面示意图。
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和挑战仍然与石窟寺总立面图相关。那是在北京整理图稿过程中,当我把杭州飞来峰石窟总立面图稿一张一张拼接起来,准备要描成墨线图时,问题和困难就出现在面前。怪石嶙峋、犬牙交错的山体与苍翠繁茂的树木,交相辉映,算得上是一幅江南幽美的风景画卷。可是,石窟遗迹却被繁茂的树木所掩盖。如果照实描出,那将会喧宾夺主。经小组研究讨论,一时也无好办法。此时有一位名叫耿刘同的年轻人,建议我带上画稿去向他的老师求教。这是一个好点子,他的建议犹如雪中送炭。他的老师似乎叫张光宇(或是叫吴光宇,已记不太准),是北京乃至全国很有名的画家。耿刘同带我到老师家,说明来意后,在画案上立即展开了杭州飞来峰石窟总立面图的长卷,老师看了几眼画卷后,问耿刘同:“这是他画的吗?”耿刘同回答:“是他画的。”老师带着几分疑惑与吃惊的眼神,扫视了我的面孔,然后说:“线条勾得不错,很有力。看得出是在现场画出来的。”我把要请教的问题再次说明后,老师稍加思考,提出怎样进行画面上的技术与艺术处理,怎样既突出石窟遗迹,同时又保留石窟美丽外貌的一些指导意见与建议。老师热心又无保留的指教使我开了眼界,颇有收获。对耿刘同的引见与帮助, 内心由衷地表示感谢。
按原计划,本来要让我跟随阎先生将工作与学习进行到底的。可到头来仍然是突不破“计划跟不上变化”的怪圈,大约从五六月份开始,常书鸿所长要求祁铎和我返回敦煌的信件一封接一封地寄给阎先生。而阎先生以工作上离不开为由,一再回信拖延挽留。同时,阎先生要大家抓紧,加快准备赴云冈石窟调查的步伐,想在祁铎和我两人离京之前, 原班人马顺利完成对云冈石窟寺的调查。然而常书鸿所长一次比一次催得更紧,阎先生只得放人,先搞了个折中,将祁铎放走,想在北京另借一位摄影师,去云冈完成石窟调查。到7月中下旬,云冈调查尚未成行,而在常所长的执意催促下,阎先生不得不放走了我。于是,我将全部图像资料(含已描成墨线的定稿和未描墨线的初稿)留下,告别了阎先生和工作小组同仁们,回到了敦煌。从此,我完全脱离了工作小组,后续工作情况一概不详了。这一中途的人事变动,造成了让我在工作结束后,将全部图像底稿带回敦煌的计划落空。更为严重、更想象不到的是在此后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中 ,这批图稿悄然失踪。而此时阎先生准备撰写的《佛教百科全书》之《中国石窟》一书尚未完成,这批图稿也尚未被其利用,真可谓损失严重矣。
“文革”后 (大约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听说通一法师在“文革”中曾将这批图稿藏在某夹墙里。可惜通一法师又意外早逝,图稿的下落就又成了一个谜 ,至今尚未被解开。笔者一直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解开这一尘封多年的谜。
图稿的遗失,对参与协作的有关单位: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大学、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等以及相关工作人员都是不小的损失。他们为了支持这项有国际意义的工作,同时也为了培养专业人才,在国家三年困难期间,付出了财力和人力等代价,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回报,确实非常遗憾。
在20世纪60年代初,据笔者估计,全国石窟寺除敦煌莫高窟之外,都尚未产生自己的总立面图,即使属于示意性质的。石窟调查组在1962年绘制的这批石窟总立面示意图,可能是我国完成时间最早的这类图。正如前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想要获得这种图像是相当不容易的。因此,这种图像也是至为珍贵的。笔者还是期待将来能够找回这批遗失的图稿。
附表2各石窟寺调查时所绘图稿目录(部分)
收稿日期:2014-03-25
作者简介:刘玉权(1937—),男,四川省简阳市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主要从事敦煌石窟考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