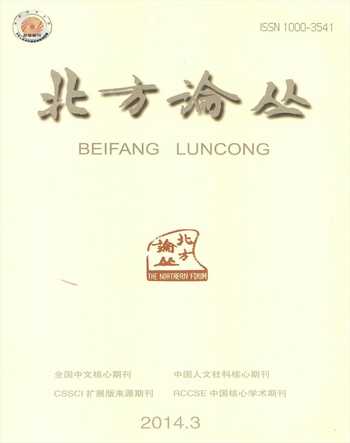当下影视的农民工符码及其叙述伦理
江腊生
[摘要]当下很多农民工影视的出现,与中国当下社会改革进程中一定的意识形态话语力量相关。不同的话语形态,决定了影视创作中不同的文化符码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底层关怀和人性拯救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农民工的苦情符码,他们的身上负载了不平则鸣的批判精神与内在的抗争力量,呼唤主流世界的关注。传统的诗意人文传统决定了其中拒绝与拯救城市欲望化的诗意符码,将现代都市诱惑的复杂,简单拉向乡村的诗意伦理,化作当下民众普遍存在的乡愁情结。市场欲望与消费伦理,则将农民工及其生存场景整合成商业电影中的消费符码,其背后的精神的力量逐渐被消费话语悄悄溶蚀。这三种影像符码,构成了当下农民工影视创作的三种基本倾向,也体现了不同的导演的不同文化追求。
[关键词]农民工;影视文化;文化符码;苦情;诗意;消费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3-0053-04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体越来越受到各种媒体与民众的关注。作为密切关注现实的艺术媒介,在影视作品中也时常出现他们在城市不协调的身影。这些影视创作多以农民工的独特经历和生存环境为描写对象,向人们展示了城市底层的艰辛与无奈、痛苦和梦想。它打破了主流剧作家长期以来面对社会弱势群体失语的尴尬状态,让我们看到了农民工群体的生存世界。
毫无疑问,当下很多农民工影视的出现,与中国当下社会改革进程中一定的意识形态话语力量相关。不同的话语形态,决定了影视创作中不同的文化符码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底层关怀和人性拯救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农民工的苦情符码,他们的身上负载了不平则鸣的批判精神与内在的抗争力量,呼唤主流世界的关注。传统的诗意人文传统决定了其中拒绝与拯救城市欲望化的诗意符码,将现代都市诱惑的复杂,简单拉向乡村的诗意伦理,化作当下民众普遍存在的乡愁情结。市场欲望与消费伦理,则将农民工及其生存场景整合成商业电影中的消费符码,其背后的精神的力量逐渐被消费话语悄悄溶蚀。这三种影像符码,构成了当下农民工影视创作的三种基本倾向,也体现了不同的导演的不同文化追求。
一、苦情符码与批判叙事
众多农民工进城谋生,承担了城市建设的大量体力劳动,却没有被城市社会真正地接纳,始终还在边缘与底层。一些影视作品往往极尽书写他们进城遭遇的苦难,展示在观众面前的总是一个令人同情、无法释怀的画面。导演沉入光鲜亮丽的城市底层,将镜头聚焦于农民工生存的世界。苦难故事的铺陈,既反映了底层民工的生活诉求,又带来了现实批判的强大震撼。本质上,众多影视作品通过一系列农民工的苦难符码化,将批判的视角置于人道主义的关怀之下。这些苦情符码在博取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同情,体现了当下影视对社会底层现实的关注,从而谋求社会和谐地解决。
在《生存之民工》中,身为工长的谢富贵,不但没有要到工钱,还要低三下四地迎合开发商。在牌桌上,他故作输钱给工程负责人张彪,只是希望能够以委曲求全的方式换取血汗钱,因为他比别人更渴望和需要这笔钱:他家中的儿子需要源源不断的钱来治病,他的老婆已弃他而去。为了继续带领大家在城里等工钱,走投无路时他偷偷去卖血,卖完血还去木材厂干苦力。当得知儿子快死了,他再次找到老板要钱时,却被打得头破血流。为了保住劳动合同,他被公司软禁逼供,甚至双脚被戴上锈迹斑斑的铁链。施工队长薛五,从施工楼顶摔下来后,却找不到地方要工伤费。遥遥无期的讨薪之路,陆长友一次次跑到铁架上提起一桶酒往死里喝。最后,他神经质地举着V字形的纸牌,发疯似的咬着易拉罐,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喊:“带我回家!带我回家”,并选择卧轨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组跪求生存、韧劲挣扎、最具震撼感的银屏苦难群像。
剧中这些男性农民工在建筑工地上,往往蓬头垢面,泥水一身,遭遇老板、工头的辱骂和殴打,并经常被恶意欠薪。他们在城市里没有身份、资产,甚至尊严,只有显得生硬而赤裸的身体,但绝不是“咱工人有力量”的激情体现,而是身处城市压抑下的无奈与疲惫。露天吃饭的场景也是众多农民工影视常见的符码。一群满身泥水的农民工,端着一个大饭碗,争抢着没有油水的饭菜,在路边、在工地上狼吞虎咽着。馒头在他们口中坚定地咬着,眼中却透出一种无根的茫然。这些影像符码,本质上呈现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事实,也隐喻了他们在城市中寻求的仅仅是生存的根本。城市的繁华、欲望的享受与他们无关。因此,这些农民工的生活圈子只是局限在工地、厂房、他们的生活与城市的居民基本没有关联。
同样,女性农民工在城市的命运却是与暧昧的发廊、保姆等身份联系在一起。她们往往是时髦的打扮、淳朴的内心,却总是无法融入城市,最终成为城市的阴暗一角。在《工地上的女人》中,玉兰从农村中来,文化不高,又没有什么技术,繁华的都市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她留在城市最大的资本便是自己的青春与容颜。认识有钱的工头杜昆后,玉兰开了个杂货店,有了家。然而,在杜昆看来,玉兰只是自己泄欲的工具、贿赂的筹码。为了能够顺利承揽下“周哥”的工程,他甚至地将玉兰作为礼物“奉献”出去。玉兰在忍受肉体的伤害与精神的摧残后,最终和小军一起返回乡村。
伴随着这些农民工苦难形象的叙述,很多作品总是在空间上做文章。其中主要有垃圾生活、保姆生活、工地生活、小卖部生活等。观众在这些民工剧中看到,“城市外来者”生活的空间相对于城市的高楼大厦来说是边缘地带,那里是尘土弥漫、噪音震天的建筑工地,是小餐馆,是充满暧昧色彩的下等发廊等。城市中的高楼大厦与他们无关,只会给他们仅有的生存空间造成挤压。在很多电影中,总会出现繁华的高楼、购物商场,而农民工却局限于工棚、脚手架这些阴暗的空间,二者的空间转换,正体现了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尖锐对立。在《泥鳅也是鱼》中,一边是正在修建的金碧辉煌的建筑,一边是女“泥鳅”一家窝身的小小木棚。当小木棚被吊车高高吊起,苍穹之下,小木棚在晃晃悠悠,体现了乡下民工在城市中的无根状态。最后,吊车将小木棚重重摔下,激起的阵阵尘土弥散在观众眼前。透过这些二元对立的影像符码,不难感受到其中沉重的哀叹和尖锐的呼喊。“泥鳅也是鱼”,意味着“农民工也是人”。剧中通过这些文化符码的建构,努力传达当下国家改革进程中的沉重质感和寄予的人文批判。
显然,导演在剧中营建一系列受侮辱和受损害的苦情符码,需要一定的精神境界与勇气,他们在追求这种沉重而又尖锐的文化符码中,带给观众的是一种久违的社会批判的力量和人文的关怀。这些影视作品却忽略了当下农民工进城的真实精神面貌,农民工进城谋生,不仅仅是遭遇各种各样的苦难,还有他们走进城市时的喜悦与梦想,还有对幸福的追求与奋进。在电视剧《我的未来不是梦》中,农村青年赵大勇和谢春梅进城打工,自主创业。他们成立装修公司,却被骗得血本无归。最后,从父母带来的竹笋得到启发,贷款开办竹笋加工厂。其中进城打工、创业的痛苦、迷茫与探索,真实地体现了农民工在城市的酸甜苦辣。同样,在《民工》一剧中,鞠广大父子在城市遭遇包工头的殴打,被拖欠克扣工资,穷得扒火车,还要遭受村长的盘剥,但心中抗争命运的火花就像剧中鲜艳的向日葵一样,剧中最后的镜头是父子俩坚定地迈着进城的步伐,寻找人生的理想之路。尽管这些叙述模式都是受挫——成功,却体现了农民进城的艰难与努力。
正是这些复杂的存在,驱使农民工在城市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一些导演沉入城市的底层,以批判的视角,聚焦于一系列农民工生活的尖锐之处。沉重感、苦难化的农民工生存,在体现了当下民众的现实生活诉求中,体现了影视剧富有勇气的批判和关怀。然而,如果导演一味地追求这种生存状态的悲苦,必然丧失他们自身的主体性意识,很容易滑向道德化和情绪化,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农民工形象,也必然脸谱化和机械化。
二、诗意符码与道德焦虑
仔细考察当下的农民工影视作品,不难发现,农民工在城市遭遇生存苦难时,并不像小说界定的那样,一些农民工在城市里报复,以恶抗恶,而是将他们身上的淳朴、善良、美丽无限放大,将他们的乡村场景也重新诗意化。这些导演面对城乡的种种矛盾与冲突,无法找到一种能够舒释苦难的价值体系,也无法落实到具体的解决途径。他们的内心充满焦虑与困惑,只能回到中国传统文学或文化中曾经的诗意空间:“面对突兀而起的现代都市文明及其生存方式,影片创作者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精神流浪者的心态。一方面,他们不能拒绝接受现代都市文明,另一方面,又渴望在精神上保持‘乡土社会的那份情感,那份温馨,那份完整和永恒。这种惶惑、分裂和焦虑症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固有的‘乡土情结与新的都市文明及其生存方式冲撞的结果”[1]。
在一些导演的镜头下,农民工成为一种诗意精神的体现。在拉萨的建筑工地上辛苦打工,傻根脑子里对未来的希望只是农民传统朴素意识里的梦想:带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他原始、单纯,似乎与这个功利化的社会无关。天真简单的个性特征让他觉得在这个社会上人人都是善良的,在和王丽辩论“人性本善”的道理时,傻根说道:“俺家住在大山里,在俺村,有人在山道上看滩牛粪,没带粪筐,就捡了个石头片儿,围着牛粪画了个圈儿,过几天想去捡,那牛粪还在……俺在高原逢年过节都一个人在那看工地。没人跟俺说话,俺跟狼说话,俺不怕狼,狼也没伤害过俺,俺走出高原,这么多人在一起,和俺说话,俺就不信,狼都没伤害过俺。人,他会害俺?人怎么比狼还坏呀?”从电影的开始到结尾,傻根一直作为一个憨厚、单纯、倔强、善良的诗意符号存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品质只是传统社会里的农民具有的精神:文明尚未开化的天真、乡村田园里农民的善良、农民骨子里的执着等,不仅与城市无关,更是王博与王丽二人的道德拯救者。于是,电影本是一个“善”与“恶”相互搏斗的故事,却因为农民工形象的存在而置换成为一个“善”诗意拯救“恶”的故事。傻根的存在,构建了一个后撤式的乡愁世界,将农民工的精神世界完全诗意化,其存在的理由却无法找到现实的文化土壤,只能是导演的一厢情愿罢了。
同样在《叶落归根》中,农民工老赵的形象并不直接与打工生活相关,而是通过背尸返乡这样一个现代传奇来书写农民工身上的淳朴与执着。在深圳工地上打工的老赵因为工友刘全有意外醉死在工地上,出于之前对朋友的许诺,他决定将工友的尸体送回家安葬。在背尸返乡的路途上,老赵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虽一路曲折却义无反顾。整个电影没有死亡始终相随的悲痛,也没有前面论述的愁云惨雾;观众处处能感受到一种人间不乏真情在的暖意和幽默。《落叶归根》导演张杨说:“我不想把电影拍成悲悲切切的样子。我希望通过老赵这个小人物来表现一种积极乐观、苦中作乐的态度,突出农民身上的质朴和执着的劲头。”[2]一路充满艰辛与荒谬的归途,老赵身上的义气感动了劫匪,感动了司机,也拯救了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人。此时,老赵已经成为一路传播“义”的符号,给当下处于市场喧嚣的民众带来内心的宁静和诗意的空间。
在《泥鳅也是鱼》中,重点不是展现物质化的民工生活,而是男女“泥鳅”之间彼此需要的渴望和相濡以沫的情感。男女“泥鳅”在工地、马路、地摊上暗自滋长并渐渐笃定的情感有一番别样的纯净,这份情感在纷乱冷酷的现实背景前显得晶莹透亮。女“泥鳅”对生活的执着,自身的尊严,以及她与民工、老人之间的情感,体现了一种超越农民工生活形态叙述的努力。剧中最后一组镜头:男女主人公悠闲地躺在屋顶,看着飞机划过天空,倾吐着各自的心声:“庙修在天上,我咋还嫌低;你就躺在我身边,我咋还想你。”别有韵致的对白,将农民工对生活和情感的追求诗意化,并为他们惨淡的人生涂上了一抹亮色。
除了这些农民工形象本身的诗意化,影片往往用相关的自然景观来辅助建构现代诗意。《天下无贼》用西藏的雪山、蓝天、纯净的庙宇来强化傻根形象的诗意化。在《落叶归根》中,导演利用“公路”上可能发生的一切,使影片组成了一幅五光十色的现实社会人生的图景。同时,影片中多次出现公路两旁金黄的油菜花、翠绿的山水田园风光,不仅联结着离奇的故事,也使观众对老赵身上的诗意精神有了相应的审美铺垫。也有一些影视利用寓意相反的自然诗意来表现农民工形象在城市的艰难与痛苦,进而传达导演对诗意和谐的一种渴望与呼唤。在《生存之民工》中,当陆长友讨薪未成导致最后疯了,他在一片金黄的向日葵中迎着火车奔跑,喊着“我要回家”而倒在铁轨上。同样,在电视剧《民工》的片头和片尾,金灿灿的向日葵在诗意绽放。当李平离开歇马山庄时,她美丽而决绝的脸与一丛又大又圆的向日葵相互映照,体现了她对城市独立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而鞠广大和双元,最后在金黄的向日葵的辉映下,背着行李,迈步在通往城市的公路上,伴随着画外音:“眼下国家很关心我们,好日子还长着呢”,电视剧在一片追逐阳光的向日葵中走向灿烂。
本质上,为了缓解叙述过程中的道德焦虑,导演将农民工因城乡落差而产生的不适应感,悄然转化为一种诗意的乡愁情绪。也就是说,沉重的农民工生活世界,他们对农村家乡的复杂情感,在导演和城市观众的心目中,变得浪漫和文气。王一川认为:“ 当下乡愁则一般是指身在现代都市的人对于飘逝的往昔乡村生活的伤感或痛苦的回忆, 这种回忆往往伴随或多或少的浪漫愁绪。”[3]显然,无论是正面表达,还是反面映衬,农民工身上的诗意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人间不能缺少诗意,但不能脱离生活,简单的诗意并不能解决复杂的社会冲突与文化冲突。本质上,这些诗意符码能否真正走进人的内心世界是值得思考的。这些弱势符码在强势的话语面前,很难找到自我认同的前提,何况拯救整个社会。其中的诗意最终只能被简单地道德化与浪漫化,从而失去自身存在的根本。
三、消费符码与欲望叙事
农民工题材受到很多导演的关注,还在于人们日常审美的陌生化催生了这类影视消费。这类电影在传达底层关注和人性关怀的同时,将农民工作苦情式与闹剧式的消费。波德里亚指出:“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4](p71)波德里亚强调,消费社会的符码化,并不看重消费对象的物质功用和消费主体的物质需要,看重的是社会层面的符号意义和价值。在影视作品中,农民工的身体、建筑工地、饮食,甚至性,都构成了特定的底层文化元素,在人文关怀的旗号下,实现市场消费的另辟蹊径。这些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场景、遭遇、情感、性都成为消费的符码,电影披着人文关怀的华丽外衣,在书写他们的苦难时,本质上是在消费他们的苦难。所有这些底层形象都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做了悄悄的置换,其中不平而鸣的道德伦理被消费文化的享乐伦理所替代。
很多作品为了凸显其中的底层意识,往往从造型上将农民工形象简单固化。他们往往呈现出傻气老土、滑稽可笑的一面,包括丑陋的长相、可笑的打扮、痴呆的表情、滑稽的姿势等。在这些消费符码身上,更多的是城市民众想象的累积,而不是真正的人性展示。在电影《高兴》中,五富这个人物最具有喜剧性。他顶着西瓜太郎的头型,头发杂乱地张开,如同电击过一般,一条红色的腰带总是露出一大截,拖至膝盖处,还不时地飘扬,圆圆的脸,胖胖的身材,总是傻乎乎地咧嘴大笑,露出一口大白牙,这个形象与他的好吃懒做、贪财好色、胸无大志的品性相映成趣。在《长江七号》中,影片中的周铁头戴白色安全帽,脏乱的头发,脖子上搭着条毛巾,白色的背心衬出黝黑的双肩,一身破衣,捧着铁饭盒坐在高楼顶层的边缘,望着城市漫不经心地大口吃饭。可他却匪夷所思地将自己的儿子送进常人难及的贵族学校。显然,周星驰所扮演的农民工形象作为一个消费符码,呈现的是与贵族学校等,至少是中产阶级的生活迥异的生存状态,在满足了城市观众消费的同时,意在体现一种黏合城乡差别的努力。
王宝强系列形象“又傻又天真”的性格成为日后所扮演农民工的基本特征。《人在囧途》中的牛耿不但耿直憨厚,而且透出一股傻气。他背着一大平底锅上飞机,登机前安检一口气喝完一大罐牛奶,在飞机上让乘务员开窗。显然,王宝强形象在模式化的美女帅哥的审美疲劳中,提供了一个新的消费形象:既是笑料式的审美符号,又是严肃的拯救形象,二者共同构成了城市阶级想象性的消费符号。可以说,王宝强等农民工符号,不仅仅是李成功等城市人的道德拯救符号,也是城市阶级喧嚣异常的语境下道德净化的参照性符号。不难看出,一旦剧中这些农民工形象成为消费性的符码,他们不再处于愁云惨雾的底层状态,而是充满了喜剧色彩,他们的出现正是当下影视拯救与提升商业效益的消费符号。
如果说男性农民工在影视消费中往往是搞笑对象,那么,大多数女性农民工形象则大都作为欲望对象而存在,在强大的城市语境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等待城市男性的救赎或者成为城市男性窥视的符号。女性农民工(大都是年轻、美丽的少女、女青年)在城市寻找梦想,她们往往意味着柔顺、弱势,在陌生、强势、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空间艰难生存。她们身上既承载了农民工遭遇城市话语的符码,也承载了底层女性面对男权话语的欲望消费。《民工》重点刻画了两个农村女人对城市的欲望,从一个侧面呈现了城市民众对农民工女性的想象性消费。一个从未离开过乡村的女人潘桃,不干家务和农活,却将自己对城市的向往化成每天的臆想;另一个是城市打工的女人李平,她渴望成为城市女人,却先后被大学教师和“北漂”所抛弃,最终不得不嫁到“农村”。李平一心将自己的新家布置成城市的样子,以转化自己对城市的想象寄托。无论是潘桃对城市生活的臆想,还是李平对城市女人生活的想象,她们的存在并不是她们二人的主体存在,而是体现了城市话语对农村女性的消费。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一文中指出:“女性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作为性欲对象被展示出来的女人是色情奇观的主导动机,迎合男性欲望,指称他的欲望。”[5](p.644)这些农民工女性形象并不像当下很多艳星那般的充满色欲,无论在穿着,还是在生活场景,都不代表当下的帅哥靓女的欲望符码。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对立,女性农民工作为城市话语的闯入者,具有淳朴、善良、天然等品格,她们容易被置于欲望窥视的角度。她们在剧中的被窥视性,构成了女性农民工在影视消费中的文化符码。
实际上,农民工形象在影视作品中大量出现,都或隐或显地体现了当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诉求。城乡二元对立的现实情境,决定了当下影视弥合与缓解的内在愿望,城乡和谐是这些作品共同的创作指向。无论通过悲剧式的苦情书写,还是闹剧式的消费书写,或是传统回溯式的乡村诗意书写,导演都在不同程度地展现农民工生存状态中,寻求社会和谐的解决。但是,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心理流动,他们复杂的精神状态,却在符码化中被忽略了。当下影视最大的任务在于真正走进个体的内在世界,探求个体精神世界的和谐,
[参考文献]
[1]饶曙光.论新时期后十年电影思潮的演进[J].当代电影,1999,(6).
[2]马或.《落叶归根》笑里含酸——导演张杨在宁说戏里戏外故事[N].扬子晚报,2007-01-09.
[3]王一川.断零体验、乡愁与现代中国身份的认同[J].甘肃社会科学,2002,(1)
[4][法]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英]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C].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周传基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作者系九江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