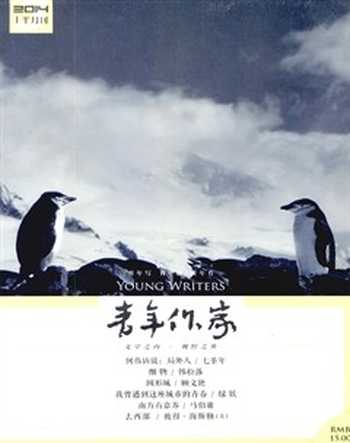细物
韩松落
【红鞋】
杨小萱家里,有两双鞋是动不得的。
一双是她姥姥留下的绣花鞋,粉红色的底子,绣着精致的花样,藤缠蔓,蔓缠藤,藤蔓之间,隐藏着花与鸟,虽然已经有点变色,拿在手里,还是有种“不可能是真的”的那种艳异。那鞋子据说是她姥姥少女时代亲手做的,一辈子也只穿过一次,是出嫁那天。杨小萱的妈妈唯一的偶像,也就是会做绣花鞋的姥姥,她当年如何美貌,如何以小家碧玉的身份和闭门苦练出的女红成为东城壕第一美女,是杨小萱妈妈捏着绣花鞋时永恒的话题:“我,不及她的一百分之一,你,不及你姥姥一万分之一。”杨小萱很不耐烦:“一双绣花鞋。”她妈妈说:“你说什么?”杨小萱的幽默感从来没人理会。
另一双是她哥哥留下的。杨小萱原来是有哥哥的,1978年,她爸爸妈妈带着三岁的哥哥从他们工作的贵州的三线工厂返回西安,哥哥在火车站走丢,到现在也下落不明。她妈妈每每提起小哥哥,就陷入半昏迷状态,捏着小鞋子喃喃地说着:“我要是当时不拿那个搪瓷缸子去接开水……”突然又睁开眼睛,目光炯炯地盯着杨小萱:“怎么丢的不是你!”家里遇到搬家及墙缝漏水,她妈妈绝对少不了要说几句“要是你哥哥在就好了”。杨小萱也不恼:“妈妈,那时候如果已经有我,丢掉也好,不过,女孩子十分不容易丢掉。”“要是我哥哥在,全球气候肯定不会变暖。”她妈妈又说:“你说什么?”杨小萱的幽默感从来没人理会。
又不能跟姥姥比,更不可能跟哥哥比,这个家里两种性别的神,都遥不可及,杨小萱觉得自己不男不女,十分苦恼。她小时候渴望的是一双红鞋,红色的回力鞋,红色的凉鞋,班级里家境好点的女同学就穿着这样的鞋,但她脚上却始终拖着一双不十分合脚的、性别十分模糊的胶鞋,红鞋子的事,提都不敢提。
她是家里的隐形人,约等于空气。有一次和爸妈吵了嘴(印象中非常稀有的几次之一),她也向电视剧主人公学习夺门而出,出门的时候,还赌着点气,怕爸妈会找到自己,于是动了点小心思,没有跑下楼去,而是向上跑,一直跑到楼顶天台去,却到底也没有人来找她,她的一点心思全白费。
报考大学,她的目标是离家越远越好、专业越强悍越好,于是成为交通大学道桥专业的学生,大学毕业,顺理成章地进了施工单位,一年有大半年时间,挤在男人堆里,在荒山秃岭施工作业,心情倒非常好,站在戈壁滩上,看着落日渐渐消失,或者站在半空中看着桥梁吊装成功,根本不必特别觉得自己是男是女,确实心花怒放。好日子终于因为妈妈的电话结束,电话那头,妈妈又气急败坏又不耐烦地说:“你回来吧!回来吧!”潜台词分明是:“回来也没有用,要是你哥哥在就好了。”
她哥哥在也没有用。那一年海南又慢慢热起来,她爸爸当初的战友找上门来,说是三万块就可以在海南买一块地算作入股,由公司种植热带水果,从此以后年年有分红,十分诱人,他爸爸热心地在厂子里召集入股,居然召集到了十个人,筹到了买十六份地的钱,钱一旦交出去,三十五年的老战友立刻人间蒸发。她爸爸豪气干云地承诺由他还钱,一分不少,第二天却在浴室摔了一跤,从此半身不遂,躺在床上。
除掉自己家出的那一份钱,欠的钱是四十五万,那一年,一个效益稍好的单位的员工薪水,大约是一千二百块,黄瓜,即便春节也不过两块钱一斤,市中心最好的房子,大约是不到两干块一平方米。杨小萱按着计算器,眼前浮现出二十二万五千斤春节的黄瓜,以及将近四百个揣着当月薪水的工人。她丢下计算器,跑出门,和多年前一样,没有跑下楼,而是向上跑,一直跑到楼顶去,星星全都在天空,“哗”一下倾泻开来,和以前任何时候看到的都不一样,格外大,格外亮,也格外奇异,像从前那些古书中的乱世里的异象,河水里游着大鱼,天上坠着斗大的流星,挖土挖出刻着字的宝石,巷道里流传着诡异的童谣,也像一切决定命运的时刻所出现的那些异象,哭不出来,没有恐惧,眼前的一切都格外清晰,表情定格了,声音突然蒙上一层布,甚至连空气里的分子都“突突突”地进着金星跳动着,杨小萱坐在水箱边上,被这么多异样的星星激动得头皮发麻。
第二天很快来了,快到不像是隔了十二个小时。她挨个儿去那些股东家拜访,一家家承诺还钱。众生众相,场面和那些煽情的杂志上写的完全不一样,有人面罩寒霜,有人连哭带骂,有人门都不给开,有人还算和气,甚至捧了茶出来,但话语间分明隔着一层,有人已经不抱任何希望,肯听她讲话也更像是自我安慰,也有人赔着小心,生怕不还他家的钱,或者还得太迟,小心翼翼一再表示:“利息我们就不要了,利息不要了。”
坐在那里,杨小萱尽力想着工地账目上的那些钱,动不动八百万、五千万、一个亿,她尽力想着那些钱,有那些钱衬着,眼前的这些钱似乎就变少了一点,她说话似乎就有了点底气,但一出门,大太阳亮晃晃地照,那些钱就连影子都没有了,她自嘲地想,即便不要利息,这个数字也十分庞大,如果靠她的薪水还债,需要四百个月,届时她已经是将近六十岁的老妪,天灾人祸的,只怕债主们没有这个信心。
她去单位请了长假,在街上看了半个月,在街口上盘了一问铺子,简单装修一下,一心一意地开始卖鞋子。那条街不算最繁华,好在,过了那条街的另一区是大学区,学生们要买东西,多半在这附近,鞋子卖得还算快。头几个月是赔了一点,杨小萱从没想到,一间巴掌大的店,一个月的电费都要300块,好在她很快缓过神来,三个月后渐渐开始有了收益。
开始一点点地还债。她把债主分了几拨,有了钱,先还给那些家里有病人的、有孩子上学的,宽裕点,再给别的一家家还。债确实是在减少,但似乎还是太慢了,太慢了,二十二万五千斤春节的黄瓜,消失得十分缓慢。杨小萱每次坐在鞋子中间,半夜三更地贴着标签,会突然被这二十二万五千斤黄瓜压得喘不过气来,房租,300块钱电费,教育附加费,污水处理费,和二十二万五千斤黄瓜比起来,简直不算什么,她胸口发闷,要大口大口地呼吸才能缓解一点,手里的活计,却一点也不敢停,回去太晚,没有公交车,可是要打车的。
有一天,妈妈神经兮兮地跑来,抖着声音说,有债主扬言,不快点还钱,要“先奸后杀”,妈妈六神无主地满屋子乱走着,喃喃地道:“先奸后杀!先奸后杀!要是儿子在就好了。”杨小萱卖了一天的鞋子,十分疲倦,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挥挥手:“哥哥在,一样先奸后杀,你都不知道有种人叫同性恋!”妈妈疯癫癫地,满地兜着圈子,念叨着“先奸后杀”,杨小萱十分崩溃,有点疑心自从哥哥走丢了,妈妈其实就已经疯掉了。
债主里有一家,有个三十五岁还没结婚的儿子,国字脸,睫毛却特别长,眼睛湿漉漉,每次见到她上门,都喜滋滋地迎上来,搓着手:“先不急着还,先不急着还,先还别人的。”杨小萱从没想到,睫毛长的男人会这么龌龊,从前小学中学里,都有那种睫毛黑黑闪闪的男孩子,专注地看着你的时候,睫毛一闪一闪,似乎在人心上一下一下地撩着,十分动人,而眼前的这男人,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青葱水灵过呢?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是不是从前那些撩人的长睫毛的男孩子,最后都变成了一个见到女人就搓着手的猥琐男?真是不敢想。杨小萱每次都逃也似地丢下钱从他家跑出来,也不是要逃他,而是要逃过一些更强大、更可怕的东西。后来她当真不急着还他家的钱了,只是,这么一来,那些由他家匀出来的钱,感觉上更不洁了。
但她渐渐和债主们培养出一种奇异的感情,有时候她上门还钱,赶上他们吃饭,他们也热情地招呼她,她也不客气,偶尔也会坐下来吃一点,店里遇到麻烦,也找有门道的债主帮个忙,有时候去还钱,赶上他们心情好,还要推让一阵子,春节还常常把他们约齐了,一起吃个饭。只有一种时候,感觉非常怪异,就是那些人家来了客人,不明就里,还温和地问着“这是谁”的时候,双方顿时停顿了三秒钟,那三秒钟,杨小萱要在很久之后才能适应。
渐渐又染上个奇怪的嗜好,大约是成天惦记着钱,精神一紧张,就要按一按计算器,算一算手里的钱才能安心,渐渐对计算器上了瘾,见到精致点的计算器,就想要买下来,后来甚至是看到文具店,就要进去找计算器,手里慢慢攒下八九十个计算器,金的银的,铜的铁的,做成书本形状的、地球仪形状的、地雷形状的,卡通造型的、电脑造型的,模仿儿童发音的、成人发音的、带音乐的。如果不是对计算器有了兴趣,杨小萱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计算器可以有这么多的样貌,晚间回到家里,坐在床上,同时打开几个计算器,唱的说的,《铃儿响叮当》和《祝你生日快乐》同时响着,场面十分壮观。杨小萱坐在计算器中间,乐不可支,同时又觉得自己心理完全变态,更加乐不可支。
三年、五年、六年,慢慢能雇得起店员,又开始扩张店面,开了分店,二十二万五千斤黄瓜慢慢减少,她甚至买了一辆二手的客货两用车,又匀出钱来交了首付,买了一处新房子,把朝阳的那间给了躺在床上的爸爸和妈妈。妈妈满地兜圈子的时候少了,那句“要是你哥哥在就好了”渐渐不见了。有天,杨小萱听见她跟楼下的人说“还是女儿好”,口气酷似计划生育宣传员,杨小萱丢下计算器,跑出门,和多年来一样,没有跑下楼,而是向上跑,一直跑到楼顶去,楼比以前的高,从通道里探出头的那一刹那,满城都是灯火。
杨小萱记得非常清楚,全部债务还清楚那天,是2005年8月12日。她曾经无数次设想过这一天,设想过她的表现,大哭、大笑、脱掉衣服当街狂奔,全都想过了,但当真来了,她却十分平静,跟店员打了招呼,去最安静的宾馆开了一个房间,关掉手机,一直睡到第三天的早晨。
她在自己的货品里,挑出一双红鞋子,仔细地穿在脚上,钻进她那小小的客货车里,踩下油门,秋天的早晨,太阳湿漉漉的,打在车窗玻璃上,一点儿也不热。
她开着车向西,一直向西,当年她造的桥,应该还在。她要去看那些桥。
【暗夜】
她刚走出法庭,就闻到了春天那种有点芬芳的空气,而且,是在黄昏那种悠扬的时刻,于是,她临时决定,在那里站一下,站在那里,她觉得自己成了全新的,有足够的勇气走向另外一种生活。就在那个时候,从对面街道上,走过来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人,他甚至没有用什么东西遮住自己的面孔,甚至没有做任何伪装,他直接走到她的面前,拿出一个瓶子,扬起手,向她泼出那些落地后“滋滋”作响、冒着青烟的液体。而她之所以安然无恙,全都因为,她身边的法警提前有所察觉,用力拉着她,躲开了那个人。
无论如何,她必须要离开这个城市。
这个凶险叵测,她只熟悉它的夜晚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她曾经做着一份不大名誉的工作,不止一次,她觉得自己正在变成吸血鬼,已经不适合在白天出现。光线,逐渐在成为一种负累、一种严重的警告,在光线里,她随时可能萎缩、成灰。但是那有什么,这份工作终于让她有了勇气去规划一下自己将来的生活,一部分钱可以用来上学,而且,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她那些单纯的同学应该会觉得她与众不同,她会沉默、微笑,但是显然曾经沧海,在需要的地方,她比他们有更多的智慧应付非常的事务。另外一部分钱可以用来买一个小房子,每间房子涂成一种颜色,连窗台上摆什么花,她也想好了,那应该是一盆海棠,是开着细碎的深红花朵的那种。她对将来如此有把握,连遗忘过去也有把握。但是她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她会成为一件凶案的证人,被杀死的人,是和她在一起工作的姐妹,而凶手是她那死于非命的姐妹写在电话号码本和日记里的一个达官贵人。她们,全都认识他,无数次地看到他出入那个死去的女孩子的屋子。
他们要她出庭作证,她拒绝了,她不断为那个女孩子哭泣,但是依然拒绝。直到有一天,他们给她看她的小姐妹留下的一个清单。在过去的三年里,这个死于非命的女孩子,为自己虚设出了一套房子,每熬过一个晚上或者一周、一个月,她就让这个房子变大一点,并为这个属于她的房子添置一两件东西,连放在床头的毛毛熊也没有拉下。熊是什么颜色的?棕色的。还有,眼珠子要缝得结实一点,以免小孩子把那眼珠子抠下来,吃到肚子里去,那对于孩子来讲,实在太过危险。她看着这个清单,犹如灵魂出壳,看自己犹如看别人,她似乎成了那个死去的女子,站在空中的某个地方,抱着一只棕色的毛毛熊,等待着某种机遇。她为这只买给那还不存在的孩子的不存在的毛毛熊而站在了法庭上。
她必须离开这个城市,到哪里去?那应该是一个已经在变化中但却依然有着某种安稳的城市,还有,那里要有足够多的人口,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足够把她藏起来。那是哪里?兰州。在兰州,她认识了他。
她并不是用通常的手段认识他的。
那也许可以算是一个圈套。
到兰州的前一个月,她小心翼翼地认识这个城市,它的街道、夜晚,和那些在夜晚出没的人。随后,她开始出现在一个网吧,每天,从早晨十点,到凌晨两点,在这个网吧上网,每天如此,大概每三天左右,她就可以看见他出现,有时是早晨,有时是下午,有时是晚上。他专注于某种游戏,一种被称做cs的游戏,网吧里所有的人,都在玩这个游戏,有些人,就此成了朋友。三个月时间,对这个游戏,他从陌生变为熟练,和周围那些同样在打这个游戏的人,也逐渐熟悉起来,但是,他和他们,显然有隔膜,这种隔膜从何而来,她要在很久以后才会知道。
那个网吧,有六十台机子,如果每天最少有五个人使用一台机子,那么,每天就有三百个人来过这里,十天,就是三干人,三个月,就是两万七干人,就算把重复出现的人算到一半那么多,仍然有一万三干五百人。就是说,三个月时间,有一万三千五百个不同的人曾经在她面前出现过,而他,是这一万三千五百个人中间最美的一个。
对她而言,他是一万三干五百个男人合成的。
她从没有见过那样美的一张脸,和那样一个身体,她经常在他身后的一个位置,打量着他胳膊上一条肌肉的紧张和放松,或者无意识的回头,她的鉴赏力绝不应该被怀疑。而且,他不只是美,不只是相貌接近完美,他还美在,他异常纯朴,他从不像别的男人那样,大喝小叫,也从不对服务人员指手画脚,从不,他说话的时候,总在淡淡地笑。三个月时间,她无数次看见他淡淡地笑,她确定了自己的爱。她决定要认识他。
有一天,六月的一天,她走向他,努力地使自己的语气自然,是的,她自然到连自己都吃惊,她走到他身边,说:你好像很久没有来了啊,干什么去了呢?他先是被她的自然所催眠,他摘下耳机,说:是啊,很久没有来了。随后他就意识到,他也许从未和这个女子有过交会,因此一个错愕的表情即将来到。她对此早有准备,她说,你:忘记了?有一次我们等机子,在那里,曾经聊过的。他于是向她道歉,说,她的确非常面熟,但是他真是记性不好。她于是说,那你的电话号码呢?可以说吗?可以啊。他笑了。
她努力克制自己,过了很多天,才打通他的电话,约他出来。去一个生意不大好的酒吧,在那样的地方,他们可以专心地说话。
在约定的地点,她看到了穿着西装的他,站在黄昏的路口。随即他就告诉她,他并不喜欢穿西装,他喜欢穿宽松的衣服。显然,他是为了见她,穿上了这身令他觉得拘束的衣服。
在酒吧里,他告诉她,他多大岁数,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上的中学,他最好的朋友是谁,他的主任是多么刻薄可恨,他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他似乎要把遇见她之前的一切铺陈交代清楚。他说,他的妈妈只拿着很少的退休金,而他的兄长,常年生病,所以,这个家的重担,全在他身上。他非常非常需要帮助,而现在,有人愿意帮助他,帮他做点什么,让这个家能够从此从容一点。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表情非常犹疑,似乎那并不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
他们就这样开始来往。他从来不问她,从哪里来,靠什么生活,为什么不工作,怎么一个人租着这么大的房子,似乎她出现在他面前再自然不过。
有时候去看一场电影。
有时候把甘南路走一遍,数一下这条路上有多少家酒吧。多少家?到2002年7月22日那天,是59家。
夏天的一个中午,他下了班,来到她这里,看着电视,他很累,就在沙发上睡着,整个下午,外面都在下雨,黄昏的时候,天晴了,天空是夏天雨后的那种灿烂。他骑着车,带着她,在南关什字,找一家店,他说那里有很好吃的杂酱面。
她穿着一件白衬衣,在她知道他要骑车带她去的时候,特意换的衬衣,这使她看起来像个中学生。有多少年没被男孩子骑车带过了?也许十年,也许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过。
有的时候,就是坐在她家里,听一首歌,或者看一段电影,她坐在阳台上,偶然偷看他一眼,满心都是欢喜。
终于有一天,他说,要带她去他家里。
他带她到了家里。他有一个过于狭小但却整洁清爽的家,所有的被单和窗帘都是浅淡的颜色,白色,米色,淡淡的苹果绿色,必须是非常非常眷恋生活的人,才会敢于使用这样的颜色的用具,才会不辞劳苦地清洗、整理、更换,让这些容易显得脏污的颜色保持本来面目。而他就有那样一个清爽、整洁的但却狭小的家。窗户统统敞开着,向着天空敞开,可以看见外边淡蓝的天空,窗帘被大风吹得高高扬起,桌子上有一叠白纸,一支笔压在上面,而窗台上,正有那样一盆她喜欢的花,一盆深红色的海棠。眼前的一切是她万分喜爱的,甚至让她开始喜爱自己。
他给她看他家的一切,他的照片,学生时代的纪念册,他母亲的卧室,而他经常穿在身上的那件蓝色的短袖衬衣,现在就挂在阳台上,散发着刚被清洗过的衣服在阳光里的味道,被风吹得歪歪斜斜。她简直心花怒放,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敢相信她就这样容易地走进了一个现成的、充满生活味道的家。直到她看见了那只高压锅。
他似乎把他生活中的一切都介绍完了,似乎为自己的滔滔不绝有点不好意思,他抓抓头发,想要找点别的什么给她看、给她讲。于是,他带她到厨房,指着那只高压锅给她看。他说,那是他妈妈有天上街买菜的时候,用买菜的钱买了彩票,中奖得来的,他妈妈为此高兴了很多天,直到过年的时候,才拿出这只锅,开始使用。
她站在那只锅面前,仿佛被定住了,他和她生活里的一切,此刻就在这只高压锅里,被蒸煮、翻滚,却决不可能相容、渗透,只会急剧膨胀,难以被容纳,最终冲破这只看似坚不可摧的锅。《白蛇传》里的法海,用来镇压妖精的,也许根本不是什么法器,也许就是这样一只高压锅。
她忽然转身向他笑了一下,拉开门就走出去。等到他反应过来,都只听到她下楼的声音。
她没有再去找他,那只他妈妈中奖的高压锅,始终等在某个地方,催促她显出原形。直到秋天过去,冬天过去,春节过去,直到春天再来,她才决定去找到他,决定向他坦白她过去的一切经历,说完就走,绝对不给自己留下一点奢望、一点期待,也许,这种决绝里面,还是含有某种奢望、某种期待,只是她自己不敢承认。她去了。
再过上二十年,她也会记得那天的天气。三月,在兰州这个地方,已经足够温暖,榆树爆出了满树紫红色的芽点,一种水红色的杏花总是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某个街道中心的公园里,稍微空旷一点的地方,就有孩子在放风筝,他们在黄昏的光线里大声叫喊,把自己跑得气喘吁吁,那些叫喊,被春天的空气腐蚀得残缺不全,听也听不清,却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在里面。她走在那样的空气里,慢慢觉得自己有了勇气,仿佛传说里的女鬼被渡了一口生人气。
在他家的路口,她看见了他,他正站在那里,似乎在等人。她也站住了,她在想,他是在等谁呢?要不了多久,她就看到了。
一辆血红的跑车完全不顾任何规则,逆向行驶而来,而且,是在自行车道上,车身在黄昏的光线里,闪着诡异的光,那血红的颜色,和它明目张胆的昂贵,使得它和周围颜色黯淡的街道全不协调,仿佛它是从一个完全不真实的梦境中走出。血红色的车走到他的面前,停下,一个男人摇下窗户,向他说话,他似乎犹豫着,而那个男人已经在催促了,他打开车门,矮下身子,非常熟练地坐在后排的座位上。他消失了,消失在红色的车里。
很快,那辆车也离开了。依然是逆向行驶,根本无所顾忌,并最终消失在黄昏漫湮的光线里。
她站在路边,慢慢地觉得自己浑身冰凉。
她知道那是一辆什么车,也知道那是属于谁的车,而且,也知道那辆车的男主人,有些什么嗜好,而那个男人,有足够的力量满足自己的嗜好。在这个城市不过一年,她已经知道了这些,她从来都有一种和黑暗深处的力量接通的本领。
似乎是突如其来的高烧袭击了她,她开始抱起双臂,没完没了地颤抖。在周围的人开始觉出她的异样之前,在把她当做一个烟鬼、癫痫病患者之前,她开始尝试挪动步子,并终于能够走开。她的悲痛只是她自己的事情,悲痛一旦为别人所知,就会走样,看起来就会像是烟瘾或者癫痫,令人避之不及,痛苦就是这样让人走样、沦落、万劫不复。
所有和她一样的人,不论男女,一生下来,就被摆在了橱窗里,等待出售、被使用,等待毁灭,每长一缕肌肉、一颗牙齿,每度过一个冬天,都只是向着更好地被售出而已,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价格。所有的他或者她,一生下来,就有一个或者很多买主等在某个地方,等在红色的车里,或者汹涌而至的夜色里,面目不清,但却强悍、果断、毋庸置疑。
她抱着双臂走在街上,路灯似乎突然亮了起来,并向着她刷地倾斜过来。黑色的街上,浮动着种种颜色,金黄,鲜红,碧绿,幽蓝,并不断变幻。她每一步都是走在灯光闪烁的梦境里。醒也醒不来,睡也睡不安稳。走着走着,就再也不想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