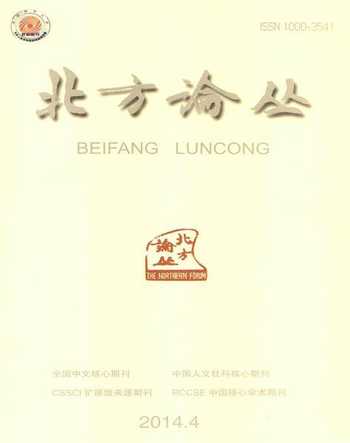秦汉国—家秩序调整中的价值认同
徐栋梁
[摘 要]秦汉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折时期,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均有重大变化。然秦汉想要实现从家—国秩序到国—家秩序的调整,一方面需要完成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的社会表征之改变;另一方面,则要完成意识形态的社会心理认同。具体而言,秦汉政府主要通过从公平性法律到普适性法律的法律认同、从封邦建国到郡县治理的行政认同、从“以吏为师”到“儒术独尊”的学术认同等诸方面的建构最终完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认同,达到了建立统一国家、统一天下思想的目的。
[关键词]秦汉;秩序调整;价值认同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5-0064-05
On Recognition of Values in Adjustment
of Family-country Order of Qin-han Dynasty
XU Dong-lia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Qin-han dynasty has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adjustment of the Order from family-country to country-family, the governors of Qin-han needs to change not only political system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but also ideological identity. Thus by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 entire community, recognition of administrative identity and academic recognition, the country can achieve a unifi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and eventually establish a new Han-value accepted by the whole nation and society.
Key words:VQin-han dynasty; adjustment of the Order; recognition of values
[收稿日期]2014-07-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国家建构与两汉文学格局的形成”(12YJC75100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4批面上资助项目“汉唐礼法调适与公共秩序的建构”(2013M541319)。
① 如吕思勉云:“从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会组织言,实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详见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② 如《左传·昭公六年》引叔向诒子产书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又如,《尚书》中有《吕刑》篇,是夏、商、周三代之法典以“刑”为名之明证。春秋前期之法典亦作“刑”。《左传·昭公六年》曰:“三月,郑人铸刑书。”又《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秦汉时期为中国古代社会之一大转折,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均有极大改变①。经过秦汉两代的努力,旧有的以家族为中心的家—国秩序逐渐为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秩序所取代。然而,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均属社会表征之转变,秦汉实现从家—国秩序到国—家秩序的转变,不仅要在国家制度层面达到整个社会的公共认同,还要自上至下地完成意识形态方面的认同,从而建立起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认同,形成汉人之新价值观。分而言之,秦汉国—家秩序调整过程中所完成的价值认同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从公平性法律到普适性法律的法律认同
秦汉法律变革之前,中国古代法律理念完成的是由制约性法律到公平性法律的转变。自夏、商、周三代以迄春秋前期之法典多曰“刑”②,其本意为诛杀、征伐、惩罚,进而引申为刑罚。这种早期法典产生的目的是对社会产生制约,属于有等级差别的法典,而非公平意义上的法律。即便在春秋时期这种原始的制约性法律已经成为成文法,也依然没有脱离其在人类社会早期由强者制定的痕迹。《左传》:“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体现了这种早期法律的随意性和单方面性。《礼记·曲礼》所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东汉郑玄注曰:“刑不上大夫,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依照郑玄的注解,大夫与贤者是社会上具有特权的阶级,所以,可以不受“刑”的约束,体现了制约性法律下刑罚对象的不平等性[1](p.23)。
春秋中后期,以晋国被庐之法、楚国茅门之法、李悝《法经》等为代表的公平性法律取代了之前的单方面制约性法律,以“成文、公开、平等为特征”[1](p.66)的新式法律被“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韩非子·难三》),开启了公平性法律的时代。
秦汉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亟需在法律方面达到更高程度的认同,而且随着封建法律的不断发展、完善和法制建设经验的进一步积累,社会也已不再满足于法的公平性,而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因此,秦汉国家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也正是秦汉法律认同的过程。然而,秦汉由于治国理念的不同,获得民众法律认同的方式以及在民众中所得到的认同程度也略有区别。
秦国民众对于国家法律的认同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任程度。商鞅变法之初便首重民心,先是通过“徙木立信”的方式,让百姓对于变法的主导者商鞅本人产生认可。然后又通过对于故意犯法的太子进行惩处,“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史记·商君列传》),目的是让百姓意识到秦国所公布的法律是公平的、可信的,于是,“明日,秦人皆趋令”(《史记·商君列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法令出一”、“援法而治”(《秦始皇本纪》),将之前秦国的法律推行全国,并在地方设置啬夫等乡官辅助法律的施行[2]。
第二,民众对于法律的服从程度。普适性法律虽然要尽可能地达到法律的普遍性,但必然也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在社会上形成反对的舆论。如果不能统一对于法律的认识,那么秦国上下就无法对于法律达到整体上地认同。秦国对于这些不服从法律的民众采取的是强行镇压的铁腕手段。如商鞅之法公布后,曾有认为法令不够完善,主动来提出意见的民众,商鞅将其皆视为“乱化之民”,将其“尽迁之于边城”。通过一系列措施,秦国民众对于法律达到了“民莫敢议令”的一致性。《史记·商君列传》中的另外一段记载也充分体现了秦国民众对于法律的服从程度: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远在边陲的客舍之人尚且对法律凛然而尊,可见秦代法律之严苛足以让百姓畏惧和服从。不过,秦国民众的法律认同虽然已经达到了信任法律、遵守法律的程度,但这种认同更接近于一种被迫的接受,或曰被强制地认同,而非百姓发自内心地赞同。
汉代民众对于法律的认同感较秦代更为强烈,第一个原因是汉代法律更加简洁有效。秦律严苛,甚至规定到“步过六尺者,有罚”(《史记·商君列传》)、“弃灰于道者黥”(《汉书·五行志》),仅刑罚的名称就有二十种以上[3],加上连坐之法,以至“褚衣塞路,囹圄成市”(《汉书·刑法志》)。汉代法律不仅在严苛程度上与秦律背道而驰,在法律的繁复程度上也有很大进步。汉初高祖初入关后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约法三章虽然简略,但它既继承了秦法的公平性,同时又具备简单性,因而比详备苛杂的秦法更受欢迎,一时间“蠲削烦苛,兆民大说”(《汉书·刑法志》)。虽然萧何后来又因秦律而增“事律《兴》、《厩》、《户》三篇”(《汉书·刑法志》),叔孙通、张汤、赵禹等人也陆续对汉代法律进行了增补,但汉初之法律除萧何的《九章律》属于以刑罚为主的律法外,叔孙通等人制定的《傍章律》《越宫律》《朝律》皆为礼仪法度、警卫法则等等,实与百姓生活关系较远。
第二个原因是汉代律法更加宽容。汉代多次减轻刑罚,基本上废除了墨刑、劓刑、刖刑,笞刑和肉刑也大量减少,尊重和保障了犯罪者的人身人格。除此之外,汉代对于刑事责任的年龄有了明确规定,如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汉景帝下诏:“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汉书·刑法志》)另外,在甘肃武威出土的《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中也都显示了汉代对老年人权益的重视和法律保护。
普适性法律除了要有公平性,能够达到“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管子·法法》)之外,还要求更大程度地适合整个社会的需求,汉代将儒家传统道德融入法律,不仅达到了普适性法律的设立目的,还大大增强了民众的认同感。汉代律法通过与儒家伦理道德的结合,以一种更加温情的方式实现了法律的认同,其出发点固然是要维护大一统的国家政权,但礼法结合的方式同时也更好地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正如《汉书·贾山传》所云:“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瘙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在阶级社会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对于政治本应是参与度最低的,但汉代百姓却能够在政府发布政令时踊跃前往,足以证明当时民众对于律令的认同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是一种积极地、主动地法律认同,而非消极地、被动地认同。
二、从封邦建国到郡县治理的行政认同
战国之前,由于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削弱,原有“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意图已经为“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现状所取代。彼时虽诸侯各自为政,但齐桓公九合诸侯,晋文公勤王周室,都是以奉周天子为尊才取得霸主地位,说明至少在名义上,春秋尚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之整体认同。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从封邦建国到郡县制的转型时期,其间虽有不同程度之反复与妥协其反复如秦末项羽分封十八王,刘邦分封异姓诸侯王;其妥协如刘邦逐一剪除异姓诸侯王后,实行局部分封,该封宗族子弟为王,至汉武帝“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光武帝刘秀登基前后亦分封宗室和诸子为王,后又加以剪除和制约。,但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趋向是明显的。在大一统政权的政治背景下,延续数百年之分封制度在转变为郡县制的过程中如何取得自上而下的行政认同,从王室家族确切而言,春秋战国时秦国君主之宗族称王族,秦汉君主之宗族当称皇族,此处为方便起见,统一称之为王室宗族。之行政认同便可窥见一斑。在从封邦建国到郡县治理的转变过程中,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便是王室家族,因此,在秦汉从封邦建国到郡县治理的秩序调整中,首先需要予以重视的便是来自于王室宗族内部的行政认同,即帝室新秩序的形成。
此问题的生成取决于是帝王的态度,即帝王是否自愿分封。战国时期,秦国虽然地处西陲,早期“习于戎俗”,但经过与中原文化不断交流和融合,秦国的典章制度实与中原大同小异,宗族分封亦是常例。商鞅变法后推行县制、实行王族以军功封爵,对分封制冲击颇大,导致秦国王族对其十分不满。即便如此,各种分封方式即便在经历商鞅变法之后的战国末期依然留存如秦孝公长子嬴驷为太子,庶子公子疾被封在蜀地严县,封号严君;又如秦昭襄王十六年(公元前291年),封公子市于宛,封公子悝于邓,封其舅魏冉于陶等等。。秦朝建立后,秦始皇虽强力推行郡县制,然秦朝历史尚短,无从考察其后之情况。
秦末汉初,项羽与刘邦均有分封之行为,然彼时之分封一方面来自旧有行政方式在秦灭之后的反弹;另一方面,无论项羽还是刘邦,在天下未定之时大封异姓诸侯,均是当时天下纷争形势使然。及至天下初定,刘邦便逐一剪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很大原因亦是因天下未定,非出于自愿,最典型的是吴王刘濞之立:
……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史记·吴王濞列传》)
刘邦因诸子年少,吴地、会稽无人以镇,于是立其兄子刘濞为吴王,见其面有反相,而未更改决定,除了话已出口,不好更改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其助己度过天下初定时候的难关。其后景帝、武帝便开始或用武力,或用政治手段削减和解除诸侯王的权势和威胁,直至后来“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4](p.135)。光武帝初立之情况与西汉初期颇多相似处,其所封宗室诸王不仅数量少、严格限制在五服之内,而且后来还寻机褫夺血缘关系较疏远的诸王王号,充分显示了汉朝历代帝王分封均属无奈而非自愿,之后对于诸侯王权力的限制也不遗余力。
此外便是诸侯王及王室宗族的态度。新朝建立后分封虽是惯例,但秦国建立后,秦国王室宗族对于由分封到郡县的转变,并没有太多抵触。其原因在于:其一,秦国历代国君大量任用来自六国的才智之士,而不重用宗亲贵族 [5](pp.3-7),致使秦国之宗族势力被限制,宗室权力欲望相对较低;其二,战国时期逐渐推行的郡县制使得秦国上下已经习惯于在新占领的地区置县治理,而非分封诸侯;其三,秦朝建立时,始皇之子较少且幼,尚无争权之野心与能力。
汉兴之初,诸侯王及王室宗族对于分封制度的破坏基本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汉初八个异姓诸侯王中,只有长沙王吴芮因面积最小,实力最弱,地理位置偏远而得以保全。燕王臧荼谋反之原因及过程不详;彭越属于被诬陷;张敖是属下造反,本身被连累;其余韩信、英布、韩王信、卢绾基本都是为刘邦逐一剪除诸侯王的形势所逼而有不臣之心。
在宗族方面,虽然有吴王刘濞“面有反相”在前,但吴楚七国之乱的根本原因却是宗室诸侯不满汉景帝削减诸侯权力而对压制分封的反弹。在汉武帝继续削藩,并将诸侯势力进一步压制之后,宗族诸侯在实力削弱情况下,开始逐渐接受国家郡县治理方式。其具体表现便是武帝一朝,“以有功侯者七十五人,然终帝之世失侯者己六十八人,其能保者七人而已……于是以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然终帝之世失侯者已一百一十三人,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戚恩泽侯者九人,然终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其能保者三人而已。”(《文献通考·封建考》)即便被削夺如此,诸侯仍未有如汉初七国之反抗者,除实力削弱外,宗室诸侯已经逐渐习惯于这种中央集权的行政方式,也是重要的原因。
诸侯王及王室宗族对于封邦建国不再存有过多期望,从另外一个侧面显示了天下乃皇帝一人之天下,而非皇帝家族之天下的帝室新秩序的形成。之前的“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家族天下,逐渐走向以皇帝一人为中心的皇权天下 [6](p.148)。
三、从“以吏为师”到“儒术独尊”的学术认同
法律认同和行政认同体现于社会之表层,易于施行同时也容易收到成效。但社会新价值观形成所需要的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则因关乎意识形态而难于调整和实现。因此,在秦汉国家秩序的建构与调整中,秦、汉两代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学术认同的方式来达到文化认同的目的,两个朝代通过“以吏为师”和“儒术独尊”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策略,其结果却是殊途同归,即都是借政治的力量强行推行学术的一统这种学术认同与统一的结局是一致的,正如雷戈所言:“意识形态是对所有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终极控制。秦皇尊法而法家亡,汉帝崇儒而儒家亡。所以从历史长程走向看,意识形态的建立,所有学术尽被网罗其中……所有学术的结局都是一样。”详见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页。。
《史记·李斯列传》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秦朝“以吏为师”思想的提出:
始皇三十四年,李斯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 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史记·秦本纪》中的记载与之略有差异,意义相去不远,此处不作讨论。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秦朝“以吏为师”的背景有二:第一,禁私学与诸子百家学说;第二,焚烧各国史书和诸家的著作。在这样的基础上,“以吏为师”的目的和意义便变得非常明确:所谓的“以吏为师”,实际是秦朝继“书同文”之后通过禁私学、焚书等手段进一步统一学术的最终走向,其目的就在于是通过将学术与政治合一,达到学术认同,其实质也就是通过思想方面的认同达到统一人心和思想的效果。
汉朝建立之初,一方面要在治国方略方面借鉴秦朝的典章制度,以“汉承秦制”适应草创之初的行政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在治国理念方面摒弃秦朝的苛政,以“汉用周政”汉代治国思想实为“汉承秦制”与“汉用周政”的结合。如汉元帝为太子时,曾表达对其父汉宣帝过于偏向法家不满:“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虽然汉宣帝不同意太子的意见,但其话语中也明显透露出汉代的治国思想不能“纯任德教,用周政”,而是“以霸王道杂之”,也就是说,要以法治为主的“秦制”和以德教为主的“周政”相结合。详见《汉书·元帝纪》。迎合士人、官员乃至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过秦”观念的思想需求,因此,汉代在学术认同方面的调整便包含了两个部分:
第一,“以吏为师”的继承和变通。汉代官方对于“以吏为师”的提出在《汉书·文帝纪》、《汉书·景帝纪》和《汉书·武帝纪》中均可见到:
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汉书·文帝纪》)
五月,诏曰:“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车骑从者不称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闾巷亡吏体者,二千石上其官属,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汉书·景帝纪》)
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汉书·武帝纪》)
从上述资料可以知道,汉代前期,文帝、景帝、武帝都相继在诏令中明确提出,以包括“三老”、“廉吏”在内的“吏”作为民众之师。值得注意的是,除官方的诏令外,在董仲舒的对策中,也可以见到“以吏为师”的类似观点:
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汉书·董仲舒传》)
从汉代上至皇帝、下至士人一致的观点来看,似乎汉代与秦朝“以吏为师”的政治导向是完全相同的,但实际二者之间又有区别:其一,秦朝的“以吏为师”主要针对的是文化和学术,而汉朝的“以吏为师”主要针对的是民风民俗(如《汉书·文帝纪》、《汉书·武帝纪》和《汉书·董仲舒传》所载)以及与之相关的礼仪制度(如《汉书·景帝纪》所载),二者有着施行目的的不同;其二,秦朝的“以吏为师”是伴随着焚书令而强制推行的,而汉朝的“以吏为师”则是劝勉、引导性质的,二者又有着施行方式的不同。换言之,秦朝的“以吏为师”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建制性,而汉朝的“以吏为师”则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象征性[6](p.186)。因此,相对于秦代的“以吏为师”而言,汉代的“以吏为师”既有名义上的继承,又有着实质上的变通。
第二,“独尊儒术”的提出与施行。汉初,刘邦率诸臣进行了初步的行政建设,文帝、汉景帝则通过休养生息完成了基本的经济建设,至武帝时则开始进行思想方面的建设。但单纯从教化的角度提倡“以吏为师”无法完成文化一统、国家一统的目的,汉武帝必须在劝勉性的“以吏为师”之外,强力推行符合汉代大一统建设构想的文化政策,正如之后汉宣帝所总结的那样:“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于是董仲舒适时地提出了“独尊儒术”的文化策略: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这段话是汉代“独尊儒术”思想的核心,具体而言便是要强调儒家纲常中的道德性和伦理性,认为必须改变诸子百家人人异说的现状,排除儒家学说之外的一切“邪辟之说”,进行学术方面的一统,这样才能让臣民无条件服从君主,达到“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的最终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独尊儒术”思想的提出,并非单纯是对于学术领域自上而下的单方面的强力干预,而是通过“天人感应”的方式对君主也提出了要求:
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使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春秋繁露·董仲舒传》)
从这段话中可以发现,董仲舒的儒家仁政思想还要通过“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的理论,以“天”的名义和威严来制约、规范君主行为。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显示出,“独尊儒术”所要达到的是上至君主、下至臣民的整个社会的学术和思想认同。
尽管“以吏为师”是由秦代法家代表人物李斯提出并倡议实施,但其与汉代“儒术独尊”的儒家思想并非背道而驰。儒家“德教”的政治手段,不仅需要君主身体力行,以“孝”德化天下,还需要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官吏,尤其是更接近民众的“三老”之类的下层小吏来完成道德教化的责任。从这个角度和意义上说,汉代的“以吏为师”和“儒术独尊”并行不悖,二者互为表里。汉代将秦代“以吏为师”的学术要求转化为制度和风俗要求,而在学术领域实行“儒术独尊”等措施,让儒家“处于独尊地位,不是在平等的地位上与百家展开争鸣,虽然没有要毁灭百家的意思,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压抑了百家的发展”[7](p.371),以更大程度地实现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的学术认同。
汉武帝这一举措看似单纯是通过政治在学术领域的干涉,但由于在当时政治及社会思想方面产生的强大震荡和后续影响,可以发现其真实的意图是通过学术的认同完成思想方面的认同,进而作用到整个社会的法制和行政认同,通过国家制度建构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调整达到建立新的价值观,完成价值认同的最终目的。
[参 考 文 献]
[1]张晋藩.中国法律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
[2]张金光.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关系[J].历史研究,1997,(6).
[3]林剑鸣.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法律制度[J].西北大学学报,1979,(3).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严耕望.严耕望史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作者系通化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 张晓校]
——秦汉时期“伏日”考论